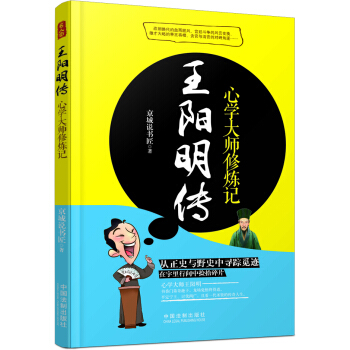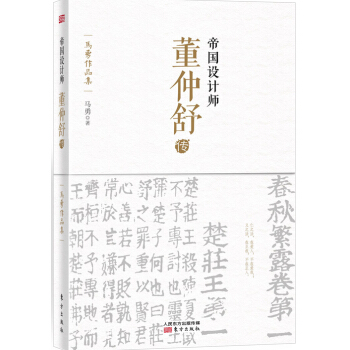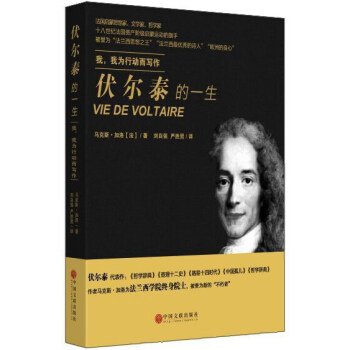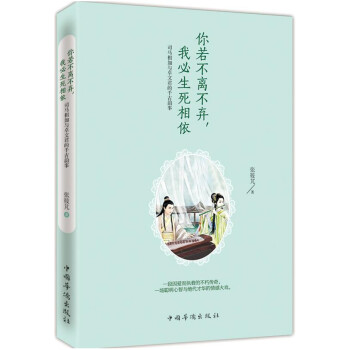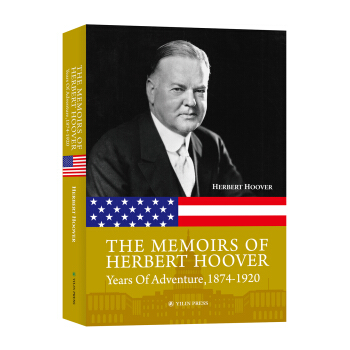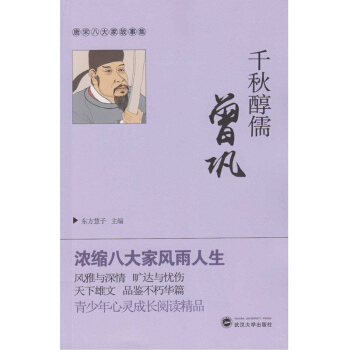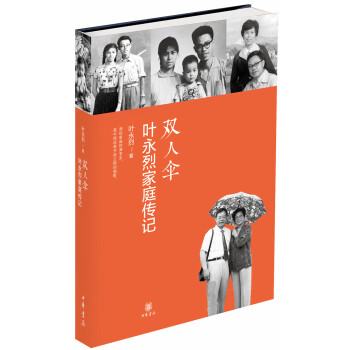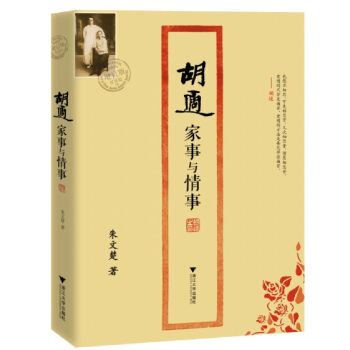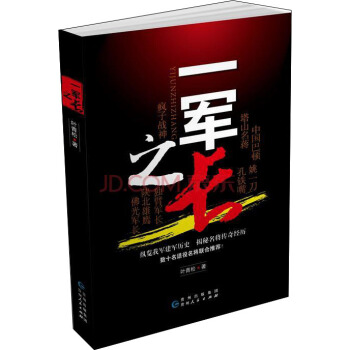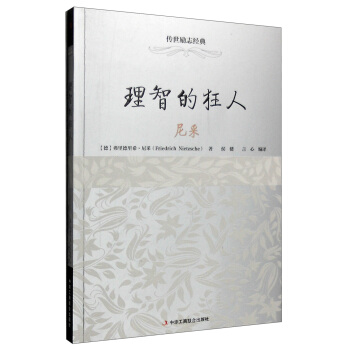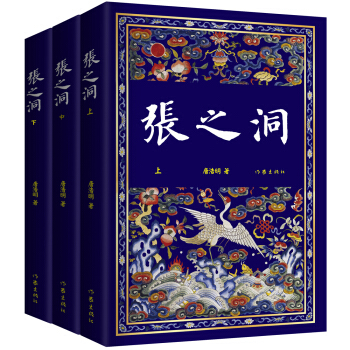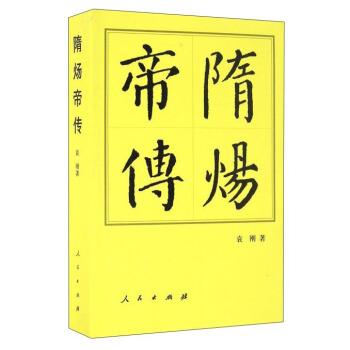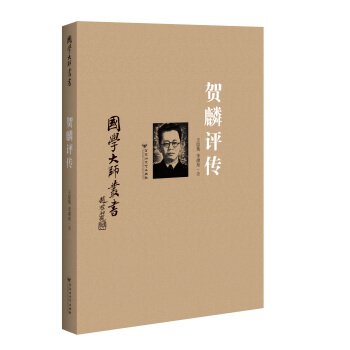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国学大师丛书:贺麟评传》作者用力尤深,几乎搜集和遍阅了一切有关贺麟的资料,对贺麟在解放后学术思想的各个方面作出系统而深入的评介。力求让读者了解一位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崇高而朴实的贺麟。
内容简介
《国学大师丛书:贺麟评传》追踪考察了贺麟一生的学术生涯和心路历程,对其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着力进行深发掘和准确评析,旨在如实展现其纵横现代中国六十余年的重大学术建树,并揭示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蕴。立论新颖,持论公允,材料丰富,理明辞达,为近年来贺麟研究的鲜有佳著。作者简介
王思隽,哲学博士,副教授,已发表专著《科学理论检验论》,合著多部,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李肃东,哲学博士,已发表专著《个体道德论》,担任《走向大市场》主编、《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西方卷》副主编,并发表论文数十篇。
精彩书评
★《国学大师丛书》表现了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了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规模宏大,意义深远。 ——张岱年目录
总 序 张岱年/001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钱宏(执笔)/004序 肖 前/001英文提要/001引 言/001第1章 寻根溯源:东西方正宗文化哺育的学子/0071.1 得天独厚:从小深受儒学熏陶/0071.2 游学欧美:觅取西方哲学的大经大法/0131.3 厚积薄发:书斋里的精神世界/031第2章 高明识度:寻求文化融合的努力/0452.1 “全观”西方:无体即无用 无用即无体/0472.2 貌似神异:全盘西化与真正“化西”/0542.3 归本建新:儒家思想的新开展/0592.4 开出“新外王”:“思想道德的现代化”/075第3章 直捣黄龙:西方正宗哲学的绍述融会/0863.1 借石攻玉:翻译价值在于华化西学/0863.2 曲径通幽:通向黑格尔的两条路线/0973.3 苦心孤诣:深入黑格尔哲学的堂奥/113第4章 独树一帜:初露端倪的新心学/1254.1 纵横捭阖:思潮背景与思想渊源/1254.2 廓开风气:处处有我的哲学特质/1444.3 博大精深:谨严融贯的思想系统/156第5章 众流归海:以真理所在实事求是为归/1725.1 步履维艰:思想的改变与坚执/1725.2 殊途同归:从哲学史途径追求真理/1895.3 古今并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嬗变/210结 语/235附录 贺麟学术行年简表/240后 记/255精彩书摘
贺麟,经常将私人藏书借给他,其中就有焦理堂的《雕菰楼文集》。在梁师的亲自指导下,贺麟写出了国学研究方面的处女作《戴东原研究指南》和《博大精深的焦理堂》,前文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贺麟时年21岁,后文在《清华周刊》上发表。 贺麟在清华读书时,正值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贺麟抓住这一良机,拜访梁几次。梁漱溟与梁启超传授知识的方式不同,不是开出长长的书单,让学生们去阅读,而是只推崇王阳明。他认为:“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不可读。”从时间上看,二梁对贺麟的教育是十分短暂的。然而,如果一个学生能以一种近于崇拜的心理去接受他所敬仰的师长的教育,那么这种教育所产生的效果会是神奇而久远的。几十年后贺麟所创立的“新心学”,显然与二梁的指点不无关系,可以说,是二梁这两位国学大师把贺麟引进了国学研究的大门。 在清华的校园里,对贺麟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吴宓先生。1924年,任《学衡》杂志主编的吴宓,到清华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吴宓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家,在翻译介绍西方古典文学上颇有造诣。他在清华首次开出翻译课,讲授翻译原理与技巧,并辅导翻译练习。贺麟与张荫麟、陈铨是选修此课最认真的学生,人称“吴宓门下三杰”。三位朋友常去吴宓家拜访求学,切磋学问,彼此成了好朋友。在吴宓的指点下,贺麟译了一些英文诗和散文,并对照原文阅读严复的译作。受吴宓的影响,贺麟不仅对翻译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且在翻译问题的研究上产生了自己的见解。1925年,贺麟在《东方杂志》发表了“论严复的翻译”一文,这是自严复去世以后,第一次系统研究严复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的论文。该文从选择翻译对象、翻译标准和译作的文体三个方面,评价了严复的贡献及其可借鉴之处。是吴宓并通过严复,对贺麟的终生事业起了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这绝非夸张。从贺麟后来开拓的学术事业之路,就能证实这一点。不仅如此,在翻译的风格上,贺麟也深受严复的影响。严复习惯在译著前作长序,通过长序来介绍作者的生平、思想,并表达译者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倾向。这一手法影响了贺麟。他在以后的许多译著前也冠以长长的译者“序”,对深奥或晦涩的原著作通俗的简要介绍,同时也借以表述自己在翻译或研究中的看法或体会,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译作。 在清华,还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贺麟对宗教的研究。1925年,基督教大同盟在北平举行会议。对于此举,赞成与反对者皆有之。贺麟关注这一动向,并代表《清华周刊》发表了《论研究宗教是反对外来宗教传播的正当方法》一文,表明他对外来宗教所持有的理性的同情态度。他认为:“反对外来宗教传播最公平、最公正、最有效的根本方法厥为研究基督教。”他强调:“对于外国的学说、主义、宗教,亦须用科学眼光重新估定价值,精研而慎择之”,“重新估定耶教在中国的价值。”十多年后,贺麟在《思想与时代》上发表《基督教与政治》一文,仍是依据上文的基本观点进行的研究与论述。贺麟对宗教的关注,亦是受吴宓的影响。吴宓在清华任教授时,不仅开翻译课程,还开外国文学课程,这就不能不涉及西方宗教。在宗教上,吴宓特别强调宗教与艺术的相通性。他认为,宗教和艺术两者皆能使人离痛苦而得安乐,超出世俗与物质的束缚,进入理想境界。在宗教与艺术关系上,吴宓认为,宗教精神为目的,艺术修养为方法,宗教树立全真至爱,智仁勇兼备,而艺术藉幻以显真,由美以生善。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从贺麟后来的文章《儒学思想新开展》中,言及儒家思想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方向开展,可以看出吴宓的宗教论对贺麟的影响。文中所谓“宗教则为道德之注以热情,鼓以勇气者”,“从艺术的陶养中去求具体美化的道德”,“由道德进而为宗教,由宗教以充实道德”等等,①都是对吴宓思想的发挥。 1926年夏,贺麟结束了清华的校园生活。从学习成绩上看,他并不是最优秀的,但他却获得了两样十分重要而珍贵的东西—良师的指点和益友的帮助。 ……前言/序言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张岱年—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用户评价
“国学大师丛书”这个系列,就像一本本精心挑选的宝藏,每次都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这次的《贺麟评传》,更是让我充满了期待。虽然我还没有来得及阅读它,但我对贺麟先生的学术思想一直心向往之。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位严谨的学者,在书斋中潜心研究,在时代浪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用自己的智慧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我很好奇,他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他又是如何从一位传统学者,成长为一位在新时代背景下,能够融汇中西、引领潮流的哲学大家?我期待这本书能够详细梳理贺麟先生的学术历程,从他早期的求学经历,到他在不同时期所发表的重要论著,再到他对后世学人产生的影响。我尤其想了解,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有着怎样的深刻理解和创新性解读。这本书能否为我揭示,在那个充满挑战的年代,他是如何以坚韧的毅力和卓越的才华,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评分我一直对近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轨迹非常感兴趣,尤其是那些在东西方哲学交融中,努力为中国哲学寻找新出路的大师们。《贺麟评传》的出现,无疑填补了我在这方面认知上的一个重要空白。虽然我还没有翻阅这本书,但光是书名就勾起了我无尽的遐想。我猜测,这本书一定会深入探讨贺麟先生在心学、逻辑学以及比较哲学等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他如何看待西方哲学逻辑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他又是如何巧妙地将二者融合,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我十分好奇他对于“民族化”哲学的思考,这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向是至关重要的议题。他是否力图在吸收西方思想精华的同时,又不失中国哲学的独特精神?这本书能否帮助我理解,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一位学者如何保持独立思考,如何以毕生之力去构建和传播自己的思想体系?我期待这本书能提供丰富的史料和深刻的分析,让我能够清晰地看到贺麟先生的学术脉络,以及他在中国哲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地位。
评分这套《国学大师丛书》的选目一直令我颇为惊喜,每一本都能挖掘出一位在特定领域有着深远影响的国学大家。虽然我尚未读到《贺麟评传》这本书,但仅凭“国学大师丛书”这几个字,我就对它充满了期待。我常常在想,贺麟先生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怎样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一生,是否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描绘着中国传统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转型与碰撞?他所倡导的“新儒家”思潮,究竟是如何在西方哲学思潮的冲击下,重新确立自身价值,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的?我尤其对他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哲学流派所提出的论述和见解感到好奇。例如,他如何看待宋明理学的深厚底蕴,又如何将其精髓融入到现代哲学建构之中?他对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诸多争议人物和事件,又持有怎样的独特视角和评价?我希望这本评传能够带领我走进贺麟先生的内心世界,去理解他思想的形成过程,去感受他治学时的严谨与创新,去探寻他对于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深切忧虑和不懈追求。这是一次未知的阅读旅程,但无疑将是一次充满启迪的学术探索。
评分我一直非常关注“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动态,因为这个系列总能给我带来深刻的阅读体验和知识的拓展。《贺麟评传》这本书,虽然我还没有机会拜读,但仅凭书名,就足以让我对它充满浓厚的兴趣。我对于贺麟先生的学术成就,尤其是他在中国哲学,特别是近现代哲学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抱有极大的好奇心。我猜测,这本书会详细地讲述他的人生经历,他的学术思想的演变过程,以及他在面对西方哲学思潮涌入时,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我特别好奇他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如何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又能保持中国哲学的独立性和原创性。这本书是否会深入探讨他在逻辑学、唯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对“现代新儒家”思想的贡献?我期待能够在这本书中,看到一个鲜活的贺麟,一个在思想王国里不断探索、不懈前行的学者形象,同时也希望这本书能为我提供一个理解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的重要视角。
评分说实话,看到《国学大师丛书》推出了《贺麟评传》,我感到非常振奋。虽然我尚未有幸翻阅此书,但“国学大师”四个字本身就极具分量,而贺麟先生的名字,更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思想高度。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一位在哲学领域深耕不辍、勇于创新的智者形象。我非常想知道,这位大师的人生轨迹是怎样的?他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的时代,又如何在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思潮的碰撞中,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和发展方向?这本书能否深入挖掘贺麟先生的学术思想,例如他对心学、唯识学等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贡献,以及他如何运用现代哲学的方法和语言去重新阐释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更清晰地理解贺麟先生的哲学理念,他的治学方法,以及他对于民族文化传承的深刻思考。这不仅仅是一本传记,更是一次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一次深度回溯。
评分好。
评分一个系列,买了好多本。
评分正版好书。
评分还可以!没看呢!
评分一个系列,买了好多本。
评分纸张不给力
评分好。
评分好。
评分还可以!没看呢!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