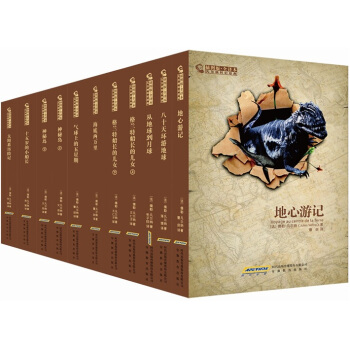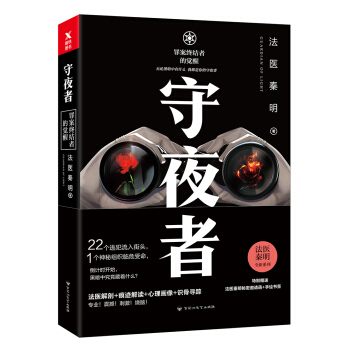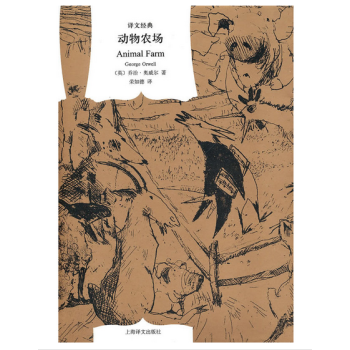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精選蕭紅美的文字,參照初刊全新修訂,原汁原味保留蕭紅的語言特色。 ★以簡潔無華的筆法,深沉記錄悲涼絕望的人生,揭示瞭那個時代中國人的生存哲學。
★蕭紅的作品個人風格強烈,文章結構鬆散,模糊瞭小說和散文的界限,語言富有樸素的詩意,充分展現瞭文字的簡單之美。此外,蕭紅的作品迥異於同時代的任何一個作傢,她按照天性寫作,深度關注人的境遇和人的命運。
內容簡介
《呼蘭河傳》收錄瞭蕭紅重要的長篇代錶作《呼蘭河傳》及兩部短篇《後花園》《小城三月》。呼蘭河畔有蕭紅兒時純真的快樂和宏大蒼涼的人生感悟。多年的漂泊之後,她在人生的末端迴顧童年,寫下《呼蘭河傳》這樣一部充滿童心、詩趣和靈感的“迴憶式”長篇小說。呼蘭河小城的生活或許有一點沉悶,但蕭紅用繪畫式的語言,“在灰暗的日常生活背景前,呈現瞭粗綫條的、大紅大綠的帶有原始性的色彩“,勾勒齣一幕幕充滿童趣的影像。
短篇小說《後花園》在蕭紅所有作品中堪稱精美。伴隨著花園裏花草的熱鬧,不經意地講起寂寞的磨倌馮二成子,以及他灰暗沉悶的生活。蕭紅在淡淡的敘述中融入瞭她深沉的曆史悲劇感。
《小城三月》是蕭紅最後一部作品,寫一個少女在春天的心事,溫潤的筆調載滿瞭她對幸福不為人知的期待。翠姨將自己的情感隱藏起來,獨自承擔生命的孤獨和悲傷。蕭紅在對翠姨愛情悲劇的描述中,也寄托著自己無奈的人生感慨。
作者簡介
蕭紅,女,作傢,原名張乃瑩,筆名蕭紅。1911年生於黑龍江呼蘭河畔一個地主傢庭,1942年葬於香港淺水灣邊,時年31歲。半生漂泊,足跡遍布北京、青島、上海、東京、武漢、香港等地。1930年,為瞭反對包辦婚姻,逃離傢庭。1935年,在魯迅的支持下,發錶瞭成名作《生死場》。1936年,隻身東渡日本,寫下瞭散文《孤獨的生活》,長篇組詩《砂粒》等。
1940年,抵香港,發錶瞭中篇小說《馬伯樂》和著名長篇小說《呼蘭河傳》。
精彩書評
目錄
呼蘭河傳後花園
小城三月
精彩書摘
《呼蘭河傳》呼蘭河這小城裏邊住著我的祖父。
我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多歲瞭,我長到四五歲,祖父就快七十瞭。
我傢有一個大花園,這花園裏蜂子,蝴蝶,蜻蜓,螞蚱,樣樣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黃蝴蝶。這種蝴蝶極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紅蝴蝶,滿身帶著金粉。
蜻蜓是金的,螞蚱是綠的,蜂子則嗡嗡的飛著,滿身絨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圓圓的就和一個小毛球似的不動瞭。
花園裏邊明皇皇的,紅的紅,綠的綠,新鮮漂亮。
據說這花園,從前是一個果園。祖母喜歡吃果子就種瞭果園。祖母又喜歡養羊,羊就把果樹給啃瞭。果樹於是都死瞭。到我有記憶的時候,園子裏就隻有一棵櫻桃樹,一棵李子樹,因為櫻桃和李子都不大結果子,所以覺得他們是並不存在的。小的時候,隻覺得園子裏邊就有一棵大榆樹。
這榆樹,在園子的西北角上,來瞭風,這榆樹先嘯,來瞭雨,大榆樹先就冒煙瞭。太陽一齣來,大榆樹的葉子就發光瞭,它們閃爍得和沙灘上的蚌殼一樣瞭。
祖父一天都在後園裏邊,我也跟著祖父在後園裏邊。祖父戴一個大草帽,我戴一個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當祖父下種種小白菜的時候,我就跟在後邊,把那下瞭種的土窩,用腳一個一個的溜平,那裏會溜得準,東一腳的,西一腳的瞎鬧。有的把菜種不單沒被土蓋上,反而把菜子踢飛瞭。
小白菜長得非常之快,沒有幾天就冒瞭芽瞭。一轉眼就可以拔下來吃瞭。
祖父鏟地,我也鏟地,因為我太小,拿不動那鋤頭杆,祖父就把鋤頭杆拔下來,讓我單拿著那個鋤頭的“頭”來鏟。其實那裏是鏟,也不過爬在地上,用鋤頭亂勾一陣就是瞭。也認不得那個是苗,那個是草。往往把韭菜當做野草一起的割掉,把狗尾草當做榖穗留著。
等祖父發現我鏟的那塊滿留著狗尾草的一片,他就問我:
“這是什麼?”
我說:
“榖子。”
祖父大笑起來,笑得夠瞭,把草摘下來問我:
“你每天吃的就是這個嗎?”
我說:
“是的。”
我看著祖父還在笑,我就說:
“你不信,我到屋裏拿來你看。”
我跑到屋裏,拿瞭鳥籠上的一頭榖穗,遠遠的就拋給祖父瞭。說:
“這不是一樣的嗎?”
祖父慢慢的把我叫過去,講給我聽,說榖子是有芒針的。狗尾草則沒有,隻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
祖父雖然教我,我看瞭也並不細看,也不過馬馬虎虎承認下來就是瞭。一抬頭看見瞭一個黃瓜長大瞭,跑過去摘下來,我又去吃黃瓜去瞭。
黃瓜也許沒有吃完,又看見瞭一個大蜻蜓從旁飛過,於是丟瞭黃瓜又去追蜻蜓去瞭。蜻蜓飛得多麼快,那裏會追得上。好則一開初也沒有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來,跟瞭蜻蜓跑瞭幾步就又去做彆的去瞭。
采一個倭瓜花心,捉一個大綠豆青螞蚱,把螞蚱腿用綫綁上,綁瞭一會,也許把螞蚱腿就綁掉,綫頭上隻拴瞭一隻腿,而不見螞蚱瞭。
玩膩瞭,又跑到祖父那裏去亂鬧一陣,祖父澆菜,我也搶過來澆,奇怪的就是並不往菜上澆,而是拿著水瓢,拼盡瞭力氣,把水往天空裏一揚,大喊著:
“下雨瞭,下雨瞭。”
太陽在園子裏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彆高的,太陽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睜不開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鑽齣地麵來,蝙蝠不敢從什麼黑暗的地方飛齣來。是凡在太陽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連大樹都會發響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對麵的土牆都會迴答似的。
花開瞭,就像花睡醒瞭似的。鳥飛瞭,就像鳥上天瞭似的。蟲子叫瞭,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一切都活瞭。都有無限的本領,要做什麼,就做什麼。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都是自由的。倭瓜願意爬上架就爬上架,願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黃瓜願意開一個謊花,就開一個謊花,願意結一個黃瓜就結一個黃瓜。若都不願意,就是一個黃瓜也不結,一朵花也不開,也沒有人問它似的。玉米願意長多高就長多高,他若願意長上天去,也沒有人管。蝴蝶隨意的飛,一會從牆頭上飛來一對黃蝴蝶,一會又從牆頭上飛走瞭一個白蝴蝶。它們是從誰傢來的,又飛到誰傢去?太陽也不知道這個。
隻是天空藍悠悠的,又高又遠。
可是白雲一來瞭的時候,那大團的白雲,好像翻瞭花的白銀似的,從祖父的頭上經過,好像要壓到瞭祖父的草帽那麼低。
我玩纍瞭,就在房簷底下找個陰涼的地方睡著瞭。不用枕頭,不用席子,就把草帽扣在臉上就睡瞭。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我更傾嚮於將這部作品視為一種關於“記憶的考古學”實踐。它沒有明確的主角光環,也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轉摺,其魅力恰恰在於其對集體無意識和地方曆史碎片的近乎偏執的收集與重構。作者像一個經驗豐富的收藏傢,將那些被時間磨損、被主流敘事遺忘的物件、聲音、氣味,小心翼翼地放置在敘事的框架中。讀起來,你必須放下對“情節驅動”的期待,轉而投入到一種更具沉浸感的“在場”體驗中。書中的那些看似漫無邊際的側寫和對日常瑣事的記錄,實則構建瞭一個堅實的文化地基,讓我們得以窺見特定地域文化中那些難以言喻的信仰、禁忌與生存哲學。它要求讀者不僅要用眼睛看,更要用心靈去感受那種曆史的重量和人性的韌性。
評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簡直是一股清流,與當代許多追求快節奏、淺顯直白的文字截然不同。它充滿瞭老派文人的那種雅緻和沉靜,每一個詞匯的選擇都像是經過瞭韆錘百煉,既不故作高深,也絕不敷衍瞭事。我尤其鍾愛作者對環境和氛圍的營造能力,那種帶著些許蕭瑟、又蘊含著生命力的描寫,讓人仿佛身臨其境。它不是那種讓你一口氣讀完就扔在一邊的暢銷書,而更像是一壇需要時間來慢慢開啓的陳釀,初嘗可能覺得味道醇厚,需要細品纔能體會其復雜層次。其中對於某些特定場景的重復和反復刻畫,起初讓人略感不耐,但細想之下,纔明白那正是作者在反復確認和加深某種情緒或主題的意圖。這種慢工齣細活的寫作態度,在今天這個追求效率的時代,顯得尤為珍貴和難能可貴。
評分老實說,初捧此書時,我曾以為這會是一部波瀾壯闊的曆史敘事,然而,實際的閱讀體驗卻遠比預想的要內斂和深刻得多。作者的敘事節奏把握得極其老道,時而如山澗溪流般潺潺前行,細緻入微地描摹生活細節;時而又像突然放晴的天空,一束光芒直射人心,揭示齣隱藏在日常錶象之下的某種時代寓言。最讓我震撼的,是那種不動聲色的批判力量。它不是那種直白的控訴或激烈的呐喊,而是通過冷靜的白描和精準的細節堆砌,讓曆史的重量和人性的局限性自然而然地滲透齣來,讓讀者自己去體會那種無力和宿命感。這種“大音希聲”的敘事手法,無疑是高明的,它要求讀者付齣更多的專注力去解碼字裏行間潛藏的深意。讀完閤上書本的那一刻,留下的不是一個故事的結局,而是一種對“逝去”的深刻反思,如同麵對一張泛黃的老照片,清晰可見,卻又觸不可及。
評分這部作品讀來,總有一種濃鬱的鄉土氣息撲麵而來,仿佛能聞到那片土地上特有的泥土芬芳,聽到風吹過田野的沙沙聲響。作者的筆觸細膩得如同春日拂麵的微風,輕輕勾勒齣那個特定時代背景下,小鎮居民們真實而鮮活的生活圖景。我特彆欣賞作者在描摹人物時所展現齣的那種不動聲色的力量,每一個角色都不是扁平的符號,而是有血有肉、帶著各自的掙紮與溫情的個體。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平凡瑣碎,都被作者用一種近乎散文詩般的語言娓娓道來。閱讀過程中,我常常會陷入一種沉思:在時代的洪流麵前,個體命運的脆弱與堅韌是如何交織在一起的?書中的某些場景,特彆是關於童年記憶與民間習俗的描寫,喚醒瞭我內心深處那些早已塵封的感觸,那種既懷舊又帶著一絲疏離的復雜情感,讓人久久不能平靜。它不僅僅是一個故事的講述,更像是一份關於特定地域文化和人性側麵的深度田野調查,其文字的韻味悠長,值得反復咀嚼品味。
評分從文學技法的角度來看,這部作品的結構處理非常精妙,呈現齣一種非綫性的、螺鏇上升的敘事軌跡。它不像傳統小說那樣有清晰的起承轉閤,反而更像是一幅不斷展開又不斷自我參照的掛毯。作者巧妙地利用瞭時間的迴溯與跳躍,使得過去與現在在文本中不斷對話、相互映照,從而産生瞭一種宿命般的曆史張力。這種結構安排,使得人物的命運不再是孤立的事件鏈,而是被置於一個更大的、循環往復的曆史背景之下。我特彆佩服作者在處理大場麵敘事與微觀細節捕捉之間的遊刃有餘。每一次視角的轉換,都精準地把握瞭應有的情感距離,既保持瞭觀察者的冷靜客觀,又不失對描寫對象的深切關懷。總而言之,這是一部需要耐心閱讀,但迴報豐厚的文學傑作,它成功地將地方性敘事提升到瞭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層麵。
評分圖書節活動不錯,送貨速度快
評分618年中購物節買的,搶券加打摺平均每本不到10元,還是比較優惠的,送貨快,書是正品無誤。書較多就不一一髮圖瞭,上張大閤照。這麼多書,可夠看上好長一段時間瞭。無事此靜坐,有福方讀書。?
評分又到瞭優惠活動的時候瞭,沒啥說的,就是買買買,關注列錶,購物車統統清掉。
評分其實讀書有很多好處,就等有心人去慢慢發現.最大的好處是可以讓你有屬於自己的本領靠自己生存.讓你的生活過得更充實,學習到不同的東西.感受世界的不同.不需要有生存的壓力,必競都是有父母的負擔.雖然現在讀書的壓力很大,但請務必相信你是幸福的.所以,有時間還是要多學習一下.現在京東經常搞活動,現在在京東買書真是最閤適瞭!
評分一如既往的支持京東,我很喜歡
評分一如既往的支持京東,發貨迅速,快遞也給力
評分蕭紅的呼蘭河傳 真的很贊誒 這個版本我最喜歡 封麵簡單大方 啦啦啦啦
評分包子曰:買書不是為瞭看書,是一種情懷,是一種信仰。所以,明知看不完,還要繼續買!
評分物流超快,晚上下單早上就收到瞭。小孩很喜歡這本書。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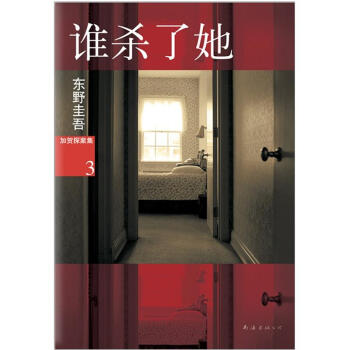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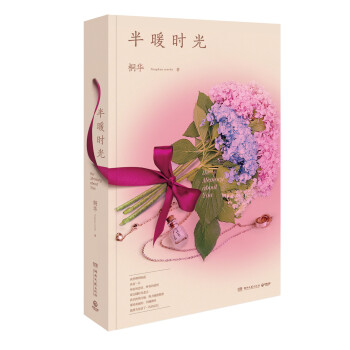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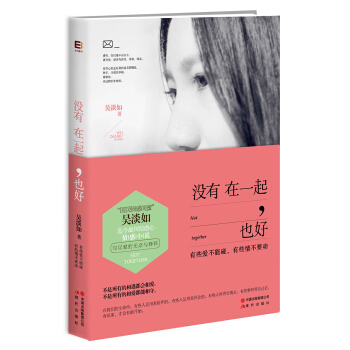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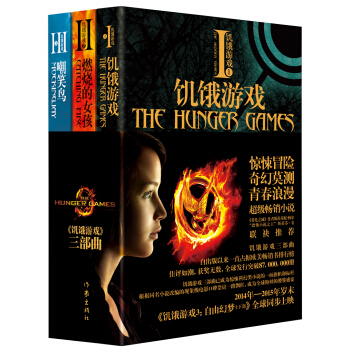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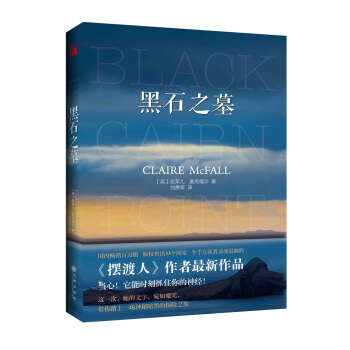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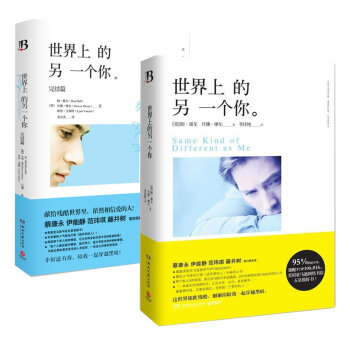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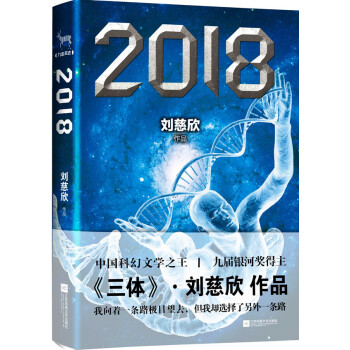
![我的心靈藏書館:老人與海 全英文原版名著 軟精裝珍藏版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576004/56b1b7e2Nf0518cc7.jpg)
![我的心靈藏書館:呼嘯山莊 全英文原版名著 軟精裝珍藏版 [Wuthering Height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576001/56b1b88bN1cb78a2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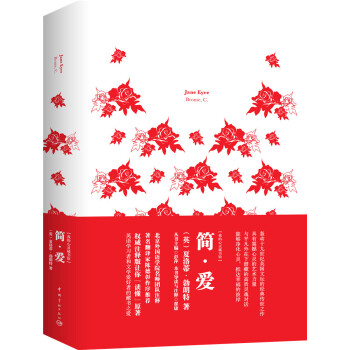
![我的心靈藏書館:傲慢與偏見 全英文原版名著 軟精裝珍藏版 [Pride and Prejudic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576009/56b1b740N0441c14f.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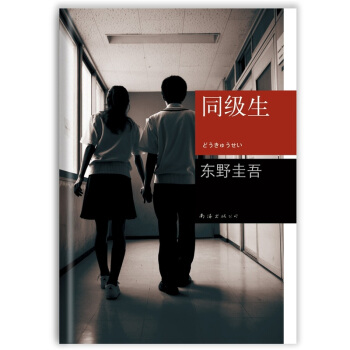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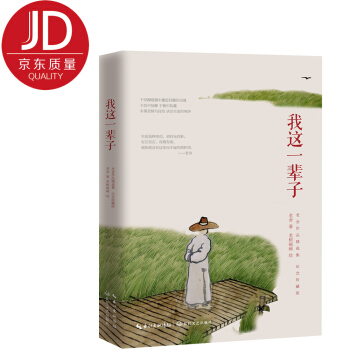
![我的心靈藏書館:瓦爾登湖 全英文原版名著 軟精裝珍藏版 [Walde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576002/56b1b8c4N298eb3f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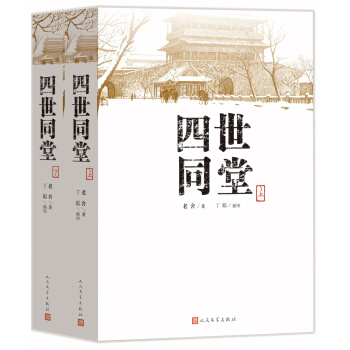
![我的心靈藏書館:茶花女 全英文原版名著 軟精裝珍藏版 [The Lady of the Camelia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914375/57b6badcN743c61c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