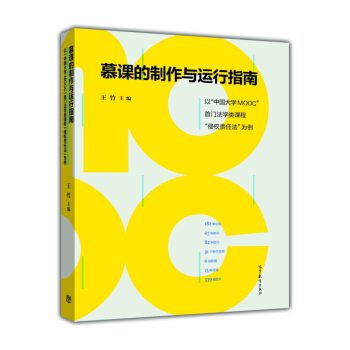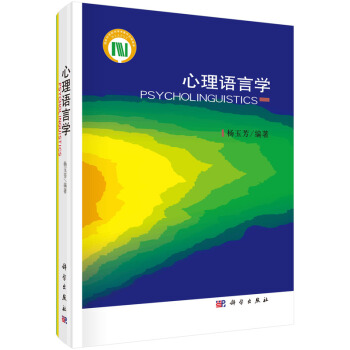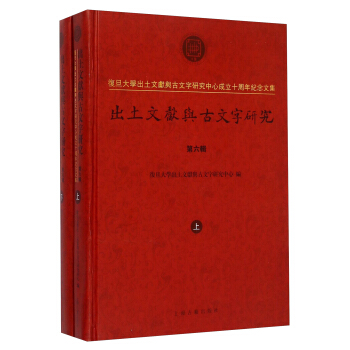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 套装上下册)》是《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集刊的第六辑,收录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方面的相关论文,其中新发现或新出土文献的研究系其特色之一,代表着该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目录
关於地支“巳”的疑问无名组卜辞分类名称纠误
契文琐记 “
读史语所YH工27坑札记——合892正、反释读校正
释甲骨文中的“役”字
甲骨文中的动物之三——“熊”、“兔”
释甲骨文“烈风”——兼说“箩”形来源
花束甲骨字词考释四例
说临
胡应姬鼎试释
读新见“宋公园铺”二器札逐
新见商金文考释(二篇)
新见攻虑王姑登皮鸡剑铭文及其相关问题
“周掌壶”的流传及其着录
它簋盖铭文新释——西周凡国铜器的重新发现
息公子朱相关铜器研究
西周金文与传世文献字词关系之对比研究
《战国文字及其文化意义研究》绪言
一粟居读简记(七)
战国文字中的“宦”字
简介两枚新见楚官玺
《清华四》刍议:闻问,凡是(征),昭穆
楚文献中的教育与清华简《系年》性质初探
谈谈战国文字中值得注意的一些现象——以清华简《厚父》为例
上博六《孔子见季桓子》简序追补
《诗。周颂敬之》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对应颂诗对读
上博九《成王为城濮之行》补释
《容成氏》补释三则
从战国文字所见的类“仓”形“寒”字论古文献中表“寒”义的“沧/沧”
是转写误释的产物
上古汉语中本来是否存在语气词“只”的问题的再检讨——以出土文献所见辞例和字形为中心
石鼓文考释五篇
说俞玉戈铭文中的“才林田俞姐”句
汉代铭文考释三则
渥洼天马西北来,汉简研究新飞跃——读《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
西方汉学界裹的两位中国简牍学大师
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七畜日》的复原问题
银雀山汉简释读小札
秦汉“乞鞫”制度补遗
咸阳出土“徒唯”印考略
江陵凤凰山西汉墓简牍与秦汉印所见人名(双名)互证(之二)
《岳麓书院藏秦简(叁)》校勘记
根据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中的图像资料校读相关传世
古书札记二则
《马王堆汉墓帛书亡肆刁》整理札记(二)
河南平舆出土两汉封泥拼缀十四则——兼论封泥拼缀的标准
马王堆汉墓《丧服图》新探
《东汉元和二年“蜀郡西工造”鎏金银铜舟》补正——兼说“册”字
论《书》与《尚书》的起源——基於新近出土文献的视角
梅本古文《尚书》新考
熹平石经《鲁诗·郑风》复原平议——兼论小序产生之年代
《庄子大宗师》“入水不濡、人火不热”解诂——兼论《庄子》表述“离形去知”相关问题 ”
说《尚书》中的“敉”及相关诸字
汉字形体研究断链管窥
“咸”字音释——侵脂通转例说之二
唐写本《说文》残卷研究
从现代文字学史看容庚先生的《中国文字学形篇》《义篇》
国图藏《梵网经》敦煌残卷缀合研究
敦煌佛经疑难字词考辨三则
精彩书摘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 套装上下册)》:下面我们再顺便讨论一下尊(《集成》06014)铭文中旧所谓“顺”字。“顺”字原作“”(下文用“○”表示),其所在相关文句为:“‘……呜呼!尔有唯小子,亡(无)哉(职)。视于公氏,有庸于天彻命。敬享哉!惠①王弊德,谷(欲)天。我不敏。’王咸诰。珂锡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②陈剑先生曾根据李宗焜先生在《殷墟甲骨文字表》中疑D是临字的意见,怀疑舸尊“○”也可能是临字。但陈剑先生同时也指出此字从“见”,与临字从站立人形有别,因此“。”虽非“顺”字但其可能从“川”声而读为“顺”③。
我们认为珂尊“○”改释作“临”,从字形及文义两方面看,都要优于释“顺”之说。“○”不宜释作“顺”,与甲骨文中“A”、“D”不能释作“顺”理由相同(参见前文)。“○”与甲骨文“临”字相比,有两点区别,一是所从人形有跪与立之别,一是川形与人形的相对位置有别。从与“临”有密切关系的“监”字来看,“监”所从人形一般是站立人形,皿形一般是位于下方。但是“监”字所从人形也偶有作跪坐者,皿形也偶有位于人形正对的那一侧④。因此,“○”完全有可能是甲骨文“厶”的异体,亦可释作“临”。
珂尊“惠王弊德谷天。我不敏”,旧一般认为是器主“珂”的自述之辞。何树环先生指出这一句应视为周王诰教之辞的一部分。句中的“王”、“我”皆为周王之自称,惠有助义。何说可信。
……
用户评价
每一次捧读这套文集,都像是一次对学术前沿的探访。这里汇聚的不仅仅是成熟的定论,更多的是那些正在形成中的、充满活力的研究命题和尚未完全解决的争议焦点。特别是关于一些关键铭文的释读,不同学者的观点碰撞交锋,那种思想的火花四射,比任何情节跌宕的故事都来得引人入胜。它展现了“研究”的动态过程,而非静止的结论,让我深刻体会到,历史和文字的阐释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我尤其欣赏那些在方法论上进行创新尝试的篇章,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去审视那些似乎已被“看透”的材料。这种对研究边界的主动拓展,正是推动整个学科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读后让人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了学术探索的最前沿,心中充满了对知识力量的敬畏。
评分从个人角度来说,这套文集的阅读体验是极其充实的,它带来的不仅是知识的增量,更重要的是思维模式的重塑。过去我对某些特定时期或文字体系的认知,往往受限于既有的教科书框架,而阅读这文集后,我发现许多“定论”都有了更丰富的维度和更具争议性的阐释空间。这种阅读体验,如同对自身知识结构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考古发掘”和“重构”,剔除了不适用的陈旧认知,注入了鲜活的研究血液。它教会了我如何以更审慎、更批判的眼光去对待一切书面记录,无论它们来自何方。对于任何一位对汉字历史、古代思想或者文献学抱有严肃热忱的人士而言,这套书无疑是一份不可或缺的、能够持续提供学术滋养的宝藏。它的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后续研究的深入,愈发显现出来。
评分初次接触这套文集的篇章,那种扑面而来的学术气息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每一个标题都像是一把钥匙,指向了古老文字迷宫深处的一扇门。阅读这些文章的过程,更像是一场与古代先贤的跨时空对话,那些晦涩难懂的符号在研究者的精妙解读下,逐渐还原出它们本来的面貌和承载的历史信息。我必须承认,其中一些论述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了我原有的认知框架,迫使我不断地查阅工具书,甚至回溯到更基础的文献上去印证。这种挑战性恰恰是顶尖学术著作的魅力所在,它不是温和的引导,而是强劲的思维刺激,逼着人不断地思考、质疑和内化。那些对新材料的解读、对旧有观点的修正,都展现出一种严谨到近乎苛刻的治学态度,让人对文集背后汇聚的顶尖智慧肃然起敬。这绝不是可以囫囵吞枣的作品,它要求读者投入百分之百的专注力,才能品尝到那份独属于古文字研究者的学术盛宴。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光是捧在手里就能感受到一种厚重而典雅的气质。封面上的字体选用考究,那种古朴又不失现代感的排版,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与学问的精深。我尤其欣赏它在细节处的用心,比如书脊的处理,既坚固耐用,又方便翻阅,即便是这样一套学术性极强的文集,也兼顾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内页的纸张质感也相当出色,墨色清晰,排版疏朗有致,对于长时间阅读艰深的古文字材料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友好。这套书的实体出版,本身就是对出土文献研究这一小众领域的一种庄严致敬,让人感受到出版方和研究机构对学术成果的珍视。我原本就对相关领域的进展抱有极高的期待,而这精美的外在,无疑进一步烘托了其内容的价值,让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深入探究其中的奥秘。它不仅仅是一套书,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艺术品,彰显了出版界的专业水准和对学术的尊重。
评分这套文集的编排结构处理得非常巧妙,虽然是十年间研究成果的汇集,但整体上却保持了一种令人称奇的内在逻辑性和连贯性。无论是从时间脉络的梳理,还是从专题讨论的深入程度来看,都能感受到编者在组织材料时所花费的心血。我注意到,一些看似孤立的研究个案,在置于整体的框架下审视时,便能发现彼此之间微妙的关联和互相印证之处,这极大地拓宽了我对这些出土文献所处时代背景的理解。它不是简单地罗列成果,而是在构建一个宏大的知识图景,让不同方向的研究成果相互支撑,形成合力。这种编排上的“大局观”,使得即便是初涉此领域的读者,也能顺着清晰的脉络进行探索,而资深学者则能从中找到不同研究路径的交汇点,从中汲取创新的灵感。这种平衡了学术深度与可读性的组织方式,实在值得称道。
评分研究人员
评分中心下设“先秦秦汉出土文献”、“敦煌文献”两个研究室,分别侧重先秦秦汉时期和敦煌出土文献的研究,且研究内容都包含对当时使用的文字的研究。中心的研究领域隶属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和汉语言文字学两个二级学科,与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历史文献学二级学科亦关系密切。
评分出土文献本身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是否它们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这些地下出土的材料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虽然有二十五史,有这么多的传世文献,但是直接看到古代墨迹的机会太少了,资料也太少了。尽管考古发现一个接一个,走马楼吴简出土后,到现在已全部清理完毕,总数超过13万枚,有字简也有近10万枚,超过以往发现的总和。再加上最近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竹简,大概总数超过20万枚;帛书大约有15万字。尽管如此,考古发现的几率还是非常小的。在湖北荆州地区,秦汉墓葬集中的地方,考古人员统计过,出土竹简的墓葬约占已清理发掘墓葬的几百分之一。
评分出土文献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出土”,从内容上看,它和传世文献的分类是一致的。而“时过境迁”,“出土”的特征一旦消失,它也就成为传世文献的一部分。比如说《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最早都是出土文献,但现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我们很少说他们是在进行出土文献研究。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被视为出土文献的,以后可能也就都成为一般文献了。
评分内容没得说,印刷和装祯水平还需要提高。
评分这次活动买真是划算啊
评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1月20日,是复旦大学直属的实体性的研究机构。中心主任为刘钊教授。中心基地位于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光华楼西主楼27楼。
评分中心学生培养采取导师指导、集体指导、学生自学及群体读书会等多种形式。中心鼓励研究生参加集体项目,培养研究生自学和独立研究的能力,在实践中培养创新型人才。
评分出土文献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出土”,从内容上看,它和传世文献的分类是一致的。而“时过境迁”,“出土”的特征一旦消失,它也就成为传世文献的一部分。比如说《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最早都是出土文献,但现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我们很少说他们是在进行出土文献研究。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被视为出土文献的,以后可能也就都成为一般文献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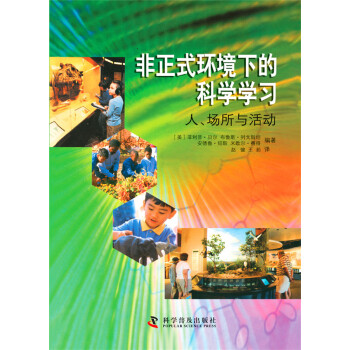
![高校科研质量评价标准研究 [Standard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 in Universiti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01646/556f9fe5Nee1dd1e7.jpg)
![发展的故事:幻象的形成与破灭 [Tales of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Illusion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05047/55780674Ndada9ee2.jpg)
![应用心理统计学 [Applied Statistics for Psycholog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22374/55a316a0N9ca2f00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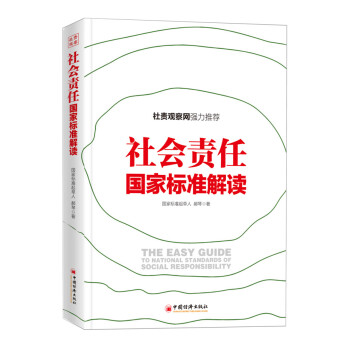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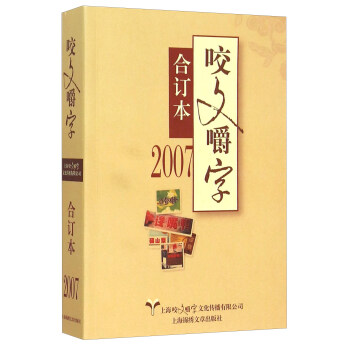
![中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发展研究报告 [Research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ctive School-running In Chin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43942/55c81b43N126cbc8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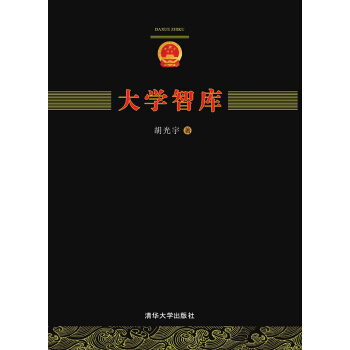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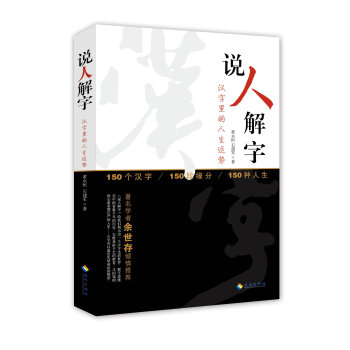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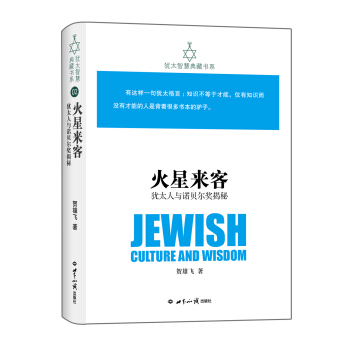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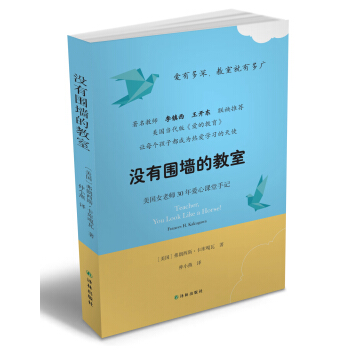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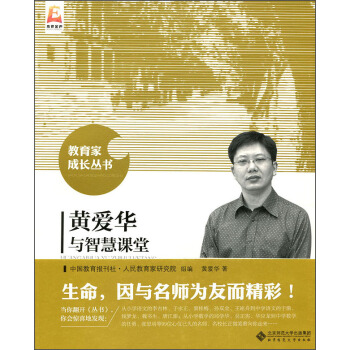
![大学译丛:自己的上帝 宗教的和平能力与潜在暴力 [DER EIGENE GOT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28650/56e8efb6N73a0303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