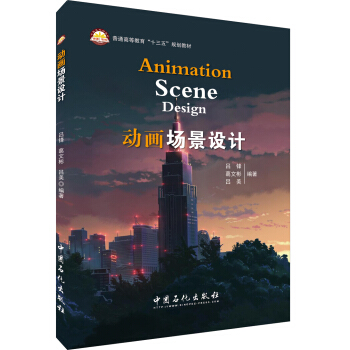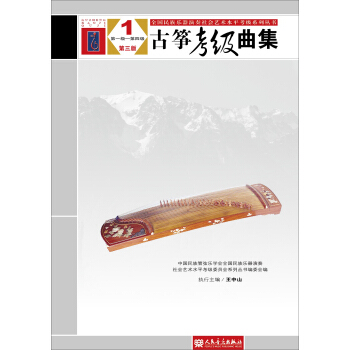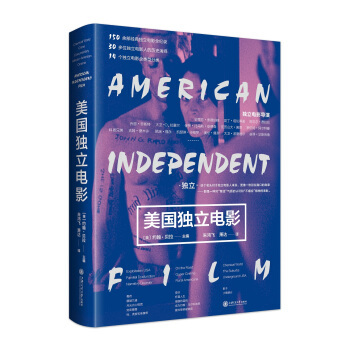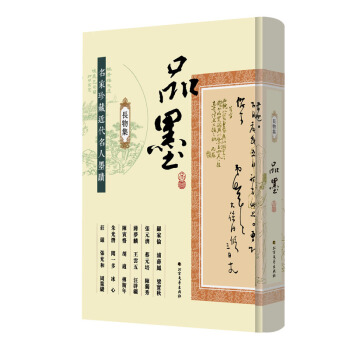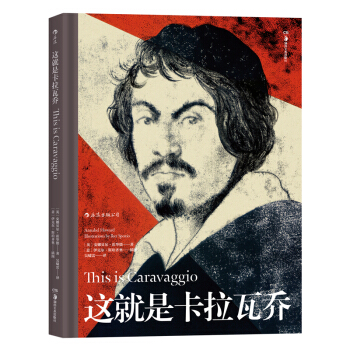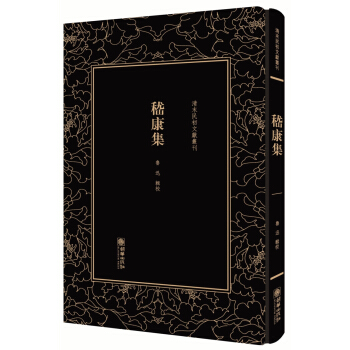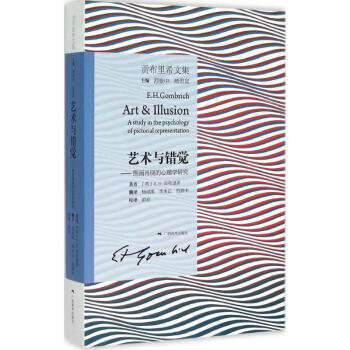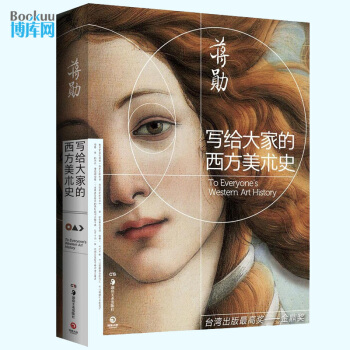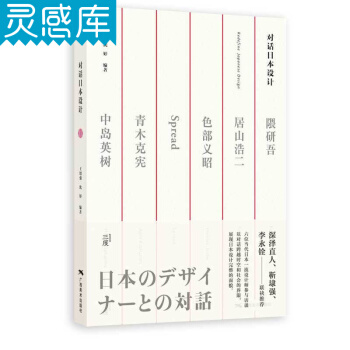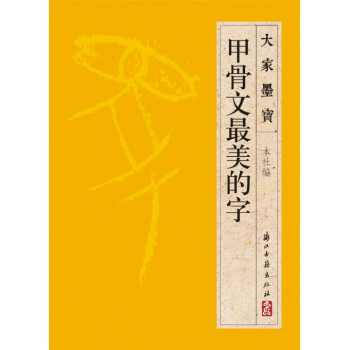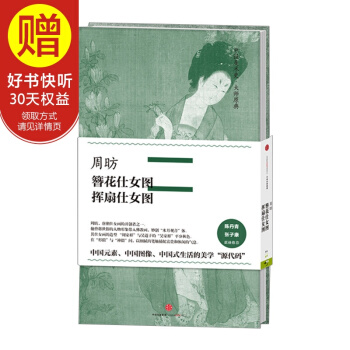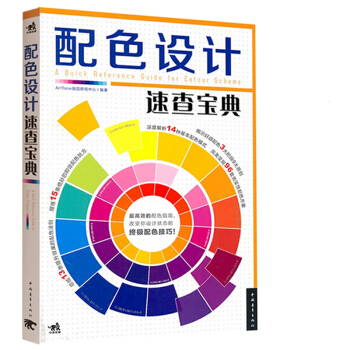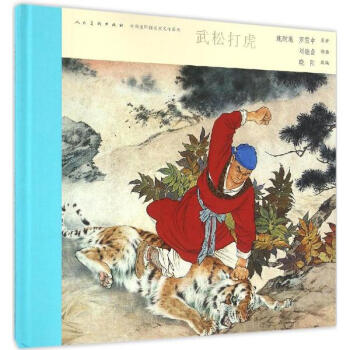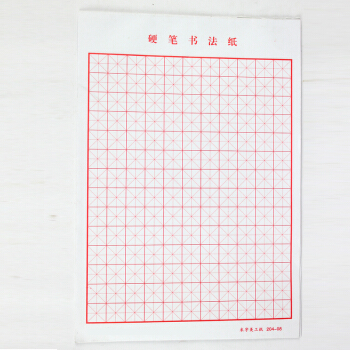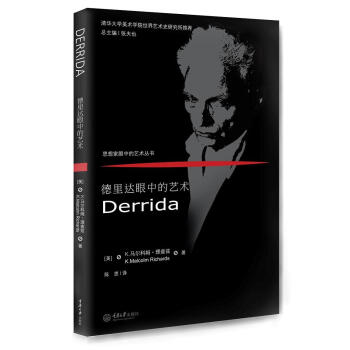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解构”这一由德里达在40 年前首次使用的词语,如今已随处可见,不仅作为学术领域的概念,还成为了艺术工作坊和流行文化领域频频出现的词汇。 “解构”作为当代文化用语如此流行,对于想要了解当代文化潮流、深入理解视觉艺术(visual arts)持久结构的读者来说,熟悉德里达的著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本书中,我们将努力让读者关注到德里达的思想与视觉艺术之间的相互关联。与丛书的其他几本一样,本书旨在呈现德里达的复杂著作,并为那些对视觉艺术感兴趣却不熟悉批判理论的人,提供某种估量他或她思想相关性的方法。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关于德里达的思想与艺术的之间的相互关联的思想理论集,书中从德里达的“解构”概念出发,以马奈的《奥林匹亚》为例,引发出“延异”的意义:一件艺术品的意义,唯有通过时间才能产生出来。通过“解构”来分析:画框、标签、签名等绘画艺术中的种种因素是如何影响观看者的思路的。通过哈迪德、艾森曼、李博斯金的建筑作品来说明:结构主义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建筑学。通过漫画《黑暗骑士归来》《守望者》《睡魔》漫画作品、以及罗伯特?威廉斯的艺术作品和登上油画板的波普艺术来分析“解构”的无处不在。本书通过德里达的思想让人们看见摧垮高等文化和低等文化固定关系的方法。
作者简介
K.马尔科姆·理查兹,美国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高级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艺术思想。陈思,1982年生,福建厦门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学士、文艺学硕士,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导师曹文轩教授。2011-201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交流,导师王德威教授。目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室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电影批评和西方文艺理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评委。在《光明日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文学自由谈》《艺术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部分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专著《现实的多重皱褶》入选“二十一世纪之星”文学丛书2014年卷;另发表小说、散文若干。
精彩书评
在今天,随着“互联网+”,甚至是“万物联网+”热潮的兴起,我们审视艺术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艺术、技术甚至是科技的本质与意义再次被追问和思考的同时,全面地研究和解析西方著名思想家们的艺术观,可以更为深刻地从“高技术”崇拜的表象下,理解艺术本体以及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本套丛书的推出,不是为了回顾过去的艺术或文献的补充,而是提请艺术界同仁共同思考如何理解和看待今天乃至未来的新艺术。——张夫也
目录
『第一章』解构与《论文字学》:名字有什么关系?
022 写作(Ecriture):更广义的书写(writing)
024 伴随延异(différance)的书写
029 补充的危险
035 公开的忏悔
『第二章』
框定画中的真理
045 可渗透的框架
050 把标签放在这里
056 签上大名
『第三章』
这些靴子是用来走路的
073 身份/ 同一性的踪迹
『第四章』
运用解构
084 失落的天真
087 解构与建筑
『第五章』
漫画的反转
100 登上油画板的波普艺术
『第六章』
解构家庭
109 不存在像家的地方
114 家庭的暴力
『第七章』
解构的守灵
121 盲卜者、预言家、诗人和其他的中间人
124 可见之中的盲视
129 当眼睛眨眼的时候
132 回忆当下
136 阳具中心主义
140 反对纪念碑
『第八章』
邮政也疯狂:明信片和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152 粪便也重要(Shit matters)
『第九章』
观看的仪式
159 假的也能一样好
『第十章』
不存在美满的媒介:德里达与影像艺术
172 永动的画面
179/ 结语
183/ 英文精选参考文献
187/ 术语汇编
精彩书摘
解构与建筑1988 年,纽约的当代艺术博物馆(MOMA)为一群笼统归为一类的建筑师举办了一场展览,他们的作品当时已经被归入20 世纪80 年代的解构运动。其中某些建筑师, 比如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和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已经建立起了与德里达之间的密切联系。安德烈斯帕帕达吉斯(Andreas Papadakis)、凯瑟琳·库克(Catherine Cook)和安德鲁·本杰明(Andrew Benjamin)三人合作努力,出版了《解构》(Deconstruction )这本书( New York: Rizzoli,1989)。本章节所包含的建筑师们,不仅表现出与德里达著作的关系,还体现出与俄国构成主义的关系。
构成主义是一个与早期苏联有关的艺术运动。许多被忽视的构成主义观念,都与当今的建筑息息相关。比如, 那种逆城市化(disurbanisation)的概念预言了面对21 世纪初时人们对城市发展和城郊延展的忧虑。接触这些建筑师作品的渠道出现得很晚,这源于冷战时期西方研究文献对构成主义的边缘化。从视觉上看,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与构成主义形式的关系最为紧密。
哈迪德在20 世纪80 年代的绘画跻身于这一时期最有力量的画作之列。它们引领了后来的画家诸如马修·里奇(Matthew Ritchie)和朱莉·马赫瑞图(Julie Mehretu) 等人的视觉实验。正如许多她的同行那样,哈迪德作为建筑师的早期作品主要存在于纸面上。通过这些纸张上的建筑,哈迪德、艾森曼、屈米和丹尼尔·李博斯金(Daniel Libeskind)这些人得以挑战建筑的传统界限和物理界限。比如李博斯金的作品,通常混合了对哲学和建筑史的直接引用,例如《密斯·凡·德罗纪念堂》(Never is the Center , Mies van der Rohe Memorial ,1987)。他的绘画挑战了三维艺术和二维艺术之间的边界。同时,它们朝向第四维度— 时间敞开。对时间的探索是通过音乐这一媒介来进行的, 而这一点①在李博斯金20 世纪80 年代的其他绘画中总是作为一个参照出现,比如《室内乐:对于赫拉克利特主题的建筑学冥想》(Chamberworks: Architectural Meditations on the Themes from Heraclitus ,1983)就是如此。
与建筑结构相关的是,解构式建筑的形式通常给人带来一种悬而未决之感,不断打消着我们的视觉期待。在物理形式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可能来自李博斯金的柏林犹太博物馆(1988—1999)。在这座建筑之前的一些预备工程(作品《城市边缘》,The City Edge ,1987)中,李博斯金把柏林城的标志呈现为一道伤口,而这道伤口作为物理标志则提供了对于解构的易容的另一种再现。跟其他解构的行动因一起,这一伤口通过暴露内部与外部之间不稳定的关系来创造关于整体的纯洁性。
至于那座犹太博物馆,李博斯金重新设计了律师楼(Kollegienhous,一座前普鲁士法院)的外立面,为他的补充物创造了一个入口。首先,一进入犹太博物馆,你会从律师楼(Kollegienhous)的巴洛克风格外立面进入一个地下回廊,它暗指纳粹统治时代犹太人逃出柏林的地下通道, 同时又暗示着犹太人在德国被埋没的历史的整个挖掘过程。但是,这一地下隧道并不单单引向任何一个特定的地点, 这就导致尽头不止一处。其中一条通道终止于一座由49 根水泥柱子构成的花园。其中48 根柱子填满了从柏林城拾来的泥土,而第49 根柱子则用来自1948 年立国的以色列的泥土制成。第二条路线终止于一段死胡同—“大屠杀的空白”,一堵巨大的水泥墙壁,其顶端则是一个通往柏林的开口。这一堵墙在放进来当下外面柏林城的声音的同时又阻断了实际的通路,这就象征着一种断裂性、一种传统或叙事的失落,代表了大屠杀造成的某种断裂。最后的一
条路通往一个展览空间,穿过由60 道拱桥所横断的虚无空白。对于“空白”的强调象征了大屠杀期间生命的逝去, 它把这些死去的人表示成一种缺席,一种以纳粹时期被从家乡清除掉的犹太裔柏林居民的名字来表示的缺席。这种以“空白”(void)的方式得到具象化呈现的“逝去”(loss), 创造出了一个缺席的存在,这一缺席的存在让人想起德里达自己所用的空白、缺席和踪迹这些词汇—那种自发地产生于回应大屠杀和犹太身份议题之中,并试图见证那既不可想象而又过分真实的事实语言。考虑到犹太博物馆在20 世纪晚期的功能,李博斯金创造出了一个结构,去思考那始终无法真正被思考或理解之物:我们损失的惨重,以及这种损失是如何不仅对柏林还对全世界留下创伤的。
现代主义的纯洁性,部分来自于保持媒介和媒介之间的彼此独立。解构则是把那将单一媒介拢在一起的结构进行拆解,就好像对画框所做的拆解一样。同样拒斥泾渭分明的范畴的是,李博斯金的作品告诉我们,视觉艺术的媒介彼此间的藩篱,从来不是永久的,也总是可消弭的。建筑从音乐、哲学、文学和雕塑中获得参考,而绘画则提供了一个空间去探讨第四维度—时间的经验,这就又把寓意多样化了。通过为简单性内部的复杂性高呼,李博斯金的理论书写往往与德里达的作品覆盖了共通的领域。
在艾森曼、李博斯金和哈迪德,也包括其他艺术家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解构主义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建筑学。如果它们之间的交汇本身已经被置放在体制的框架之内—例如放在当代艺术博物馆(MOMA)这样一个框架内, 我们还应该去挑战这些建筑师用以建构解构的方式。那就是说,解构一座房子存在不止一种方法。德里达的思想并不承诺给你任何最后总结性的答案。相反,他的著作给人一种情境化的逻辑,以此去抵抗那种由西方思想构成的对于世界的二元对立式安排。这些建筑师们所给出的建筑与德里达文本之间的关联,仅仅是探讨解构与建筑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而已。同样,对建筑与解构之间关系的考察, 并不必然要从这一个或那一个的领域出发。恰恰是在抵制这种非此即彼(either/or)框架中,德里达的“非此非彼, 亦此亦彼”(neither/nor,both/and)逻辑才能够作为一个寄生虫式的存在,形成于其所要拆解的传统消化道内部。
……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和内容结构之间的呼应,简直是一次精妙的艺术呈现。内页的留白处理得非常大气,仿佛为读者的思考留下了足够的“间隙”,不至于让信息过载。我特别留意了书中引用的那些辅助插图或图表,它们的选择和摆放都极其用心,绝非随意的装饰,而是作为论证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每一次引图,都精准地支撑了作者当下的论点,并且以一种视觉冲击力,强化了理论的重量感。我甚至能感受到排版师对作者思想的深刻理解,他们没有试图去“简化”内容,而是通过设计来“承载”内容。读完这本书后,我发现自己看世界的方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在欣赏任何一件艺术品或阅读任何一段文字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找其背后的“结构”与“断裂点”。这是一本能真正改变你认知工具箱的著作,其影响远远超出了阅读本身。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着实引人注目,那种深邃的、近乎迷幻的色彩搭配,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拿到手上的时候,能感觉到纸张的质感相当不错,厚实而有韧性,给人一种珍藏的冲动。我原本是抱着一种既期待又忐忑的心情翻开的,因为我对理论著作总是有那么一点敬畏。然而,前几章的叙述方式却出乎意料地流畅,作者似乎有一种化繁为简的魔力,能将那些晦涩的概念用生活化的比喻娓娓道来。特别是关于“在场”与“缺席”的探讨,作者没有直接抛出定义,而是通过描绘一个失焦的瞬间,让我们自己去体会那种微妙的张力。我甚至能想象到作者在书桌前沉思的样子,那种对语言边界不倦的探索精神,隔着纸张都能清晰地传达过来。这本书的排版也很考究,字号和行距都恰到好处,长时间阅读也不会感到眼睛疲劳。总而言之,从物理触感到阅读体验,这本书都展现出了极高的制作水准,让人愿意静下心来,慢慢品味文字背后的深意。
评分这本书的行文风格,用“辩证的舞蹈”来形容或许最为贴切。它不像某些理论著作那样,总是保持一种冷峻的、超然的姿态,相反,作者在行文中时常流露出一种对事物本质的深切关怀。他似乎在用一种近乎诗意的语言,去解剖那些冰冷的哲学结构。比如,当他谈及“延异”的概念时,他并没有停留在纯粹的语言游戏层面,而是将其与时间的流逝、记忆的不可靠性联系起来,一下子就把抽象的理论拉回到了人类存在的具体情境中。这使得整本书读起来,既有思想的锐利,又不失人文的温度。我发现自己常常在读完一个段落后,会情不自禁地在脑海中构建出相应的画面,这可能就是作者文字力量的体现。这本书成功地打破了我对纯粹理论读物“枯燥”的刻板印象,它更像是一部充满思辨火花的哲学散文集。
评分说实话,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对我来说,挑战性陡增。或许是因为我自身的知识背景有所局限,某些关于符号学和现象学的交叉论述,我需要反复阅读好几遍才能勉强跟上作者的思绪。我甚至不得不去查阅了几个辅助的词条,才能完全理解他引用的那个哲学家的观点。但这恰恰说明了这本书的深度——它不是一本用来消遣的读物,而更像是一张邀请函,邀请读者进入一个更深层次的学术对话。作者的语气在后半段变得更加凝练和抽象,节奏也随之加快,仿佛进入了高速公路的阶段。虽然有些地方读起来需要更高的专注度,但那种探索知识前沿的兴奋感是无与伦比的。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攀登一座知识的高峰,虽然呼吸有些急促,但顶峰的视野绝对值得这一切努力。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能够提升读者的思维阈值,让人习惯于在更复杂的维度上去思考问题。
评分我花了整整一个周末的时间,几乎是沉浸式地读完了这本书的中间部分,那种感觉就像是跟随一位资深的向导,穿梭在一个逻辑严密但又充满奇遇的迷宫之中。作者对于传统美学范式的解构,简直是刀刀见血,但又不是那种纯粹的破坏欲,而是一种带着温度的重塑。他引入了大量跨学科的案例,从巴洛克时期的雕塑到现代极简主义的建筑,每一个分析都像是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复杂论证时所展现出的耐心,他会先搭建一个基础的框架,然后层层递进,直到最后水到渠成地引出他的核心观点。在某一章节,他讨论到“文本的无限延展性”时,我不得不停下来,合上书,走到窗边,盯着远处的风景发呆了很久。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不是被告知了答案,而是自己找到了通往答案的路径。这本书迫使你重新审视那些你曾经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事实,这种智力上的挑战和收获是巨大的。
评分不错
评分不错,质量还可以,值得阅读!
评分好
评分不错
评分不错,质量还可以,值得阅读!
评分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影响很大。
评分快递小哥很帅,送货很快,昨天下单今天就到了,这也太快了吧,咋不上天呢,哈哈哈哈哈
评分没买拉康那一本,柑橘不太靠谱的样子
评分不错,质量还可以,值得阅读!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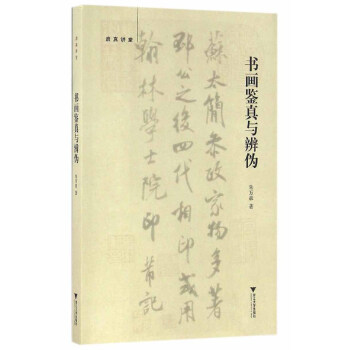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连环画绘本系列:女娲造人 [Nvwa Creates Human Being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68009/59191040Nddefc9b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