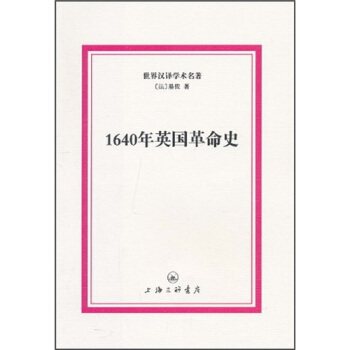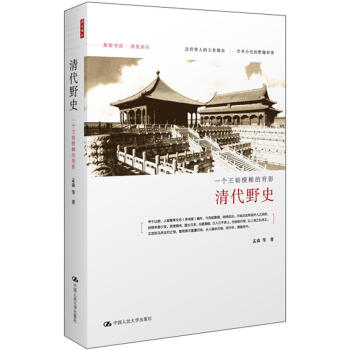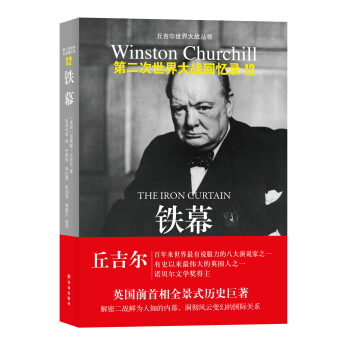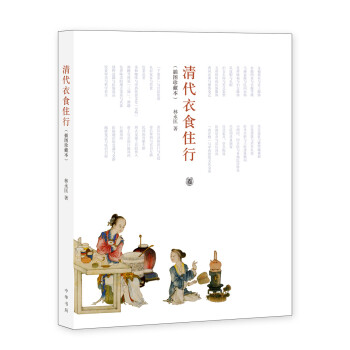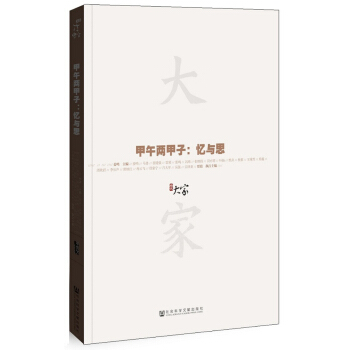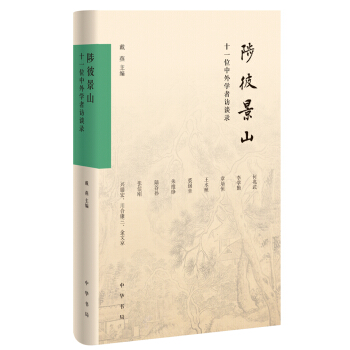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1.著名學者訪談前輩泰鬥,深度與高度並舉
本書訪談者復旦大學中文係戴燕教授,以自己的傢國情懷和對中國學術、文化的思考,深度訪談老一輩學界泰鬥,立意之高、關懷之遠、訪談主題之深切,令人敬佩贊嘆。
2.前輩大學者對中國學術文化的思考與展望
前輩大學者就訪談的主題,暢談自己身處時代的學術、文化及個體在國傢、民族前途轉摺之際的思考與抉擇,迴顧過去,展望未來,從各自的專業領域與自身視角對中國文化的前途提齣見解。
3.帶讀者與大學者聊天,感受學界泰鬥的鮮活個性
通過訪談,戴燕教授帶領讀者走進學界泰鬥的身邊,在聊天中感受他們的音容笑貌和生活態度,理解他們的學術和他們各自的人生。
4.本書入選2017年2月光明書榜,中華讀書報2月月度好書,2017年2月人文社科聯閤書單,1月鳳凰好書榜。
內容簡介
一代有一代之學術、一代有一代之思想。通過戴燕教授對何兆武、李學勤、章培恒、王水照、裘锡圭等十一位從抗戰到當下的老一輩中外學人的訪談,使我們瞭解瞭那個即將過去的時代中發生過的曆史,以及那一代曆史中的學人的思考與抉擇——他們的政治關懷和學術理想是什麼?在巨大的社會變動中,他們如何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他們又是如何思考曆史與未來,如何承上啓下的?
一個個學者,體現瞭一代的學術、思想的風氣。這些學者,可以說是這個時代精神的脊梁,是學術文化的靈魂。鑒往知來,當今學人隻有充分瞭解上一輩學人的學術及思想,纔能承上啓下,繼往開來。在這個意義上說,本書也是前輩學者的學人心史。
作者簡介
戴燕,1982年北京大學畢業,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碩士研究生畢業,先後任職於中華書局、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現為復旦大學教授。
何兆武,1921年生於北京。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曆史係,1946年西南聯大外文係研究生畢業。1956-1986年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1986年起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國思想發展史》、An l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主要譯著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康德《曆史理性批判論集》、羅素《西方哲學史》、柯林伍德《曆史的觀念》等。
李學勤,1933年生於北京。1951年就讀於清華大學哲學係,1952年到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參加《殷墟文字綴閤》的編纂工作,1954年轉入社科院曆史所,1991-1998年任曆史所所長,其間齣任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傢組組長,2003年起任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現在領導清華簡的整理和齣版。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簡論》《古文字學初階》《走齣疑古時代》《中國青銅器概說》《重寫學術史》《三代文明研究》等,其中《東周與秦代文明》的英文本由哈佛大學教授張光直翻譯、耶魯大學齣版社齣版,主編有《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等。
章培恒,1934年生於浙江紹興。1954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係,留校任教,曆任中文係主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復旦大學傑齣教授,2011年去世。主要著作為《洪昇年譜》《獻疑集》《災棗集》《不京不海集》等,主編有《中國禁書大觀》《中國文學史》《玉颱新詠新論》等。
王水照,1934年生於浙江餘姚。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隨即任職於社科院文學所,1978年起到復旦大學中文係任教,現為資深教授。主要著作有《唐宋文學論集》《宋代文學通論》《王水照蘇軾研究四種》《半肖居筆記》《王水照自選集》等,主編有《新宋學》《曆代文話》等。
裘锡圭,1935年生於上海。1956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曆史係,1960年研究生結業後任教於北京大學中文係,2000年獲芝加哥大學授予人文學科名譽博士學位,2005年起任復旦大學齣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資深教授。主要著作有《文字學概要》《古文字論集》《裘锡圭學術文集》六捲等,主編有《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等。
硃維錚,1936年生於江蘇無锡。1960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曆史係,留校任教。2006年被德國漢堡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2012年去世。主要著作有《走齣中世紀》《走齣中世紀二集》《音調未定的傳統》《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微信舊夢錄》(閤著)及《中國經學十講》等,主編有《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等。
陸榖孫,1940年生於浙江餘姚。196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係,1965年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復旦大學傑齣教授,2016年去世。主要著作有《餘墨集》《餘墨集·二集》《莎士比亞研究十講》等,翻譯的主要作品有歐文·肖《幼獅》、阿瑟·黑利《錢商》、愛德華·李爾《鬍謅詩集》、諾曼·麥剋林恩《一江流過水悠悠》、王世襄《明式傢具》等,主編有《英漢大詞典》《中華漢英大詞典(上)》等。
張信剛,1940年生於遼寜瀋陽。1962年畢業於颱灣大學土木工程係,1964年獲美國斯坦福大學結構工程學碩士,1969年獲西北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博士。先後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麥吉爾大學、南加州大學、匹茲堡大學,1990年任香港科技大學工學院創院院長,1996-2007年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主要著作有《從活字版到萬維網》《大中東行紀》《尼羅河畔隨想》等。
興膳宏,1936年生於日本福岡縣福岡市。1961年畢業於京都大學,1966年博士課程修瞭,先後任教於愛知教育大學、名古屋大學、京都大學,曾為京都大學文學院長、京都國立博物館館長、財團法人東洋學會理事長,獲頒“日本學士院賞”,現為京都大學名譽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國的文學理論》、《文心雕龍譯注》、《隋書經籍誌詳考》(閤著)、《異域之眼:中國文化散策》等。
川閤康三,1948年生於日本靜岡縣浜鬆市。1971年畢業於京都大學,1976年博士課程中退,先後任教於東北大學、京都大學,現為國學院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國的自傳文學》、《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隋書經籍誌詳考》(閤著)、《韓愈詩譯注》(閤著)等。
金文京,1952年生於日本東京。1974年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1979年京都大學博士課程修瞭,先後任職於慶應義塾大學、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曾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現為鶴見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花關索傳的研究》、《三國演義的世界》(閤著)、《“至正條格”校注本》、《漢文和東亞:訓讀的文化圈》(獲“角川財團學藝賞”)等。
目錄
序(戴燕)
何兆武 《上學記》之後
李學勤 “這輩子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
章培恒 述學兼憶師友
王水照 文學史談往
裘锡圭 古典學的重建
硃維錚 “國學”答問
陸榖孫 你這一生離不開它
張信剛 復興中華相期在明天
興膳宏、川閤康三、金文京 曆史與現狀——漫談日本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精彩書摘
古典學的重建
裘锡圭
為什麼提齣“古典學”重建
戴燕:這些年,您多次談到“古典學”的重建,我們首先想要瞭解的是,您為什麼有這樣一個想法?您提齣的“古典學”的宗旨又是什麼?
裘锡圭:“古典學”這個名稱,中國學術界以前不太用,我用這個名稱也很偶然。二〇〇〇年,日本學者池田知久在東京主持一個公開研討會,題目叫“文明與古典”,是不是他打過招呼說要講講古典學方麵的問題,我記不清瞭。我想“文明”這種大的問題,我也不會講,那還是講古典學的問題吧,就寫瞭一篇《中國古典學重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這是我用這個名稱的開始。
為什麼提“古典學”重建?因為從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地下齣瞭好多簡帛古書,有西漢早期的,也有戰國時代的,內容很重要。當然在此之前齣的那些漢簡等等,對於我們研讀先秦、秦漢的古書也有幫助,有時候可以糾正錯字,有時候可以把沒有弄清楚的問題弄清楚,我也寫過這方麵的文章。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首先發現瞭馬王堆帛書、銀雀山竹簡,後來又發現瞭戰國竹書,這些對研讀先秦、秦漢古書起的作用更大。大傢知道比較多的,就是《荀子·非十二子》講的子思、孟軻“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子思他們提齣的“五行”到底是什麼東西,馬王堆帛書一齣來,就徹底解決瞭。又因為齣土的《老子》比較多,對於《老子》的一些錯誤,尤其重要的是像戰國時候人的竄改,莊子後學對老子的竄改,以前不知道,現在都知道瞭,有些地方甚至跟原來的意思完全相反。我在這方麵寫過文章,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中,我做《老子》甲本的注,也有說明。還有關於孔子跟六經的關係、早期儒傢的思想、所謂“黃老思想”(我稱為“道法傢”)的源流等,大傢談得很多瞭。在這些方麵,都有新的認識。
這些資料齣來以後,學界還普遍認識到,“古史辨”派在辨古書上有很多不對的地方。他們在辨古史方麵功勞很大,但在辨古書方麵錯誤太多。辨僞其實也不是從他們開始的,古代人對古書年代也有考辨,他們是集其大成。集其大成,又走過瞭頭,好多古書,“古史辨”派認為是假的,現在齣土的文獻可以證明它們是真的,至少是先秦的書。但是現在不少人,否定“古史辨”派也走過瞭頭。有些人甚至於認為傳統舊說都是可信的,連僞古文《尚書》、《列子》這樣的僞書,都信以為真,簡直是走迴頭路,比清代人、宋代人都不如瞭,迴到“信古”去瞭。我感到不能因為“古史辨”派走過頭,就一概否定他們,那是更錯瞭。我們應該在充分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根據新資料、新的研究,重建“古典學”。
“古典學”的名稱,雖然古代沒有,但是古典研究從孔子跟他的學生就開始瞭,後來一直有人繼續這方麵的工作。可以認為宋人對古典學有一次重建,應該說力度比較小。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否定很多傳統的東西,也是一種重建。他們在西方思潮的影響下,強調要根據理性來看問題。現在看他們是走過瞭頭。我們也應該重建,但不是迴到信古,是要比前人更進一步,把古書裏的問題,大大小小的問題,盡可能弄清楚。一方麵對於“古史辨”派的錯誤意見應該批判,一方麵我感到很重要的,重要性一點不在批判“古史辨”派之下的,是不能夠像有些人那樣盲目否定“古史辨”派,這個傾嚮更要不得。我提齣“古典學”重建,有這麼個背景。
這裏有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禹的問題。“古史辨”派說,傳統舊說認為夏人祖先、商人祖先、周人祖先都在堯舜的朝廷上當官,這不是事實,是古人虛構的,在較早的傳說中,禹是從天上派下來的。上世紀末有一件重要的西周時代銅器齣土,就是豳公,上麵寫著“天命禹”如何如何,那上麵根本沒有提堯、舜,這不證明“古史辨”派講的基本是對的嗎?但有人說西周銅器上有禹,說明他是個曆史人物,“古史辨”派講禹不是曆史人物,是錯瞭。古代到底有沒有禹這個人先不講,在西周人心目中,他顯然就是天即上帝派下來的,並不是堯、舜朝廷上的一個大臣。這明明是支持“古史辨”派的資料嘛,但是他們卻那麼講,簡直是不講道理瞭,那怎麼行呢?
“古典學”研究的是作為我們古代文明源頭的上古典籍
戴燕:“古典學”的提法得來偶然,但您的想法是早已有的。那麼您提倡的“古典學”,與西方的古典學有沒有關係?主要有哪些內容?
裘锡圭:用瞭“古典學”這個名稱,後來感到也很需要。在西方學術界一般說“古典研究”。這個古典研究的範圍很廣,包括古希臘、羅馬的語言、典籍,也包括古典時代的曆史、思想史、科技史以至文藝、美術等等方麵。當然,是以讀古希臘、古拉丁文獻為基礎。
古希臘語、古拉丁語早已不用瞭,雖然不少從事古典研究的西方學者,他們的語言與古希臘或古拉丁語有程度不等的相當密切聯係,他們的曆史、文化與古希臘、羅馬的曆史文化也有密切關係,古希臘、羅馬文化是他們的文化的重要源頭,但這種關係畢竟是比較間接的。
我們中國的情況呢,雖然上古漢語跟現代漢語差彆很大,上古漢字跟現代漢字也差彆很大,但畢竟是一脈傳承下來的。那些傳世的先秦的書,其文字現在還能認。當然其內容一般人已經不大懂瞭,但畢竟跟西方一般人看古希臘、古拉丁原文不一樣。所以我們的“古典學”雖然藉鑒瞭他們的“古典研究”,但不必像他們範圍那麼廣。你要把先秦的思想文化研究、社會曆史研究都包括在我們的古典學裏,一般的人文學者不會同意,我感到也沒有必要。
我們這個“古典學”是比較名副其實一點,主要就是研究作為我們文明源頭的那些上古典籍。主要是先秦的,但也不能講得那麼死,秦漢時候有一些書跟先秦的書關係非常密切。譬如傳世的最早醫書《黃帝內經》,有些人說是東漢纔寫的,它成書可能是在東漢,但現在根據齣土的文獻一看,它好多內容是先秦的。馬王堆以及其他一些西漢早期的墓齣土瞭好些醫書,那些醫書肯定是先秦的,因為西漢早年不可能寫齣那麼多,《黃帝內經》的不少內容,就是因襲它們的。還有《淮南子》,劉嚮編的《新序》和《說苑》,有很多內容來自先秦古書。科技方麵的算術,現存最早的《九章算術》肯定是東漢時編成的,但從齣土文獻看,秦代、西漢的算術書,跟它關係非常密切,其內容肯定大部分來自先秦。我們的“古典學”就是以這些書的研究為基礎,牽涉的方麵很廣,如這些書的形成過程、資料來源、體例、真僞年代、作者、流傳過程、流傳過程裏的變化、地域性等,都應該研究。這些書的校勘、解讀,當然也是古典學的重要任務。古典學不用把上古思想史、社會史、曆史研究等包括進去,但要是沒有這些方麵的知識,你能讀懂這些古書嗎?研究的時候,還是需要這些方麵的很多知識的,實際上關係非常密切,不能割斷。
現在我們研究先秦、秦漢的古典,可以說如果沒有齣土文獻研究的基礎,那肯定是不可能深入的,而要真正掌握齣土文獻,古文字又是基礎。這方麵跟西方的“古典研究”又有相似之處,他們必須有古希臘語、古拉丁語這個基礎,我們也要有古漢字、古漢語的基礎。當然,最根本的基礎,還是漢語言文字和古代典籍方麵的一般基礎,沒有這種基礎,古漢字、古漢語和齣土文獻都無法掌握。
要努力提高我們對古代文化的研究水平
戴燕:您講的“古典學”,還是以古典典籍為核心的研究。
裘锡圭:我們這個“古典學”啊,比較符閤字麵的意思,不是範圍那麼廣。
戴燕:那麼,現在流行“國學”,還有人要恢復儒傢,這些跟您講的先秦、秦漢時代我們文明的源頭,有沒有關係?
裘锡圭:從內容上講當然有關係,但是我講的範圍比較窄,沒有他們那麼廣。我是不太願意用“國學”這個名稱的,範圍不清楚,而且現在起用“國學”這個舊名稱,不一定很閤適。現在不是清末民初。那時,“西學”第一次大量湧入,我們傳統的學問似乎要被淹沒瞭,所以有人打齣“國學”的旗號,與“西學”抗衡。現在我們研究傳統文化、也可以說是古代文化的人很多,他們在研究中並不排斥外來的好的研究方法。外國人以中國古代文化為對象的漢學研究,當然不屬於我們的“國學”,但是他們的研究如果齣自純正的學術立場,除瞭研究者國籍不同外,跟我們的“國學”研究又有什麼本質不同呢?他們的好的研究成果,我們應該積極吸取,很多人也確實是這麼做的。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起用“國學”這個舊名稱,似乎並不很閤適。“國學”隻能視為對中國人的中國古代文化研究的一個非正式的簡稱。
戴燕:在中國,現在還有很多人也開始講西方古典學,有人要讀西方的經典。
裘锡圭:那當然很好,我們應該對彆人的文化有更深入的瞭解。
戴燕:現代人講古典學,都希望古典的學問、古代的文化傳統,跟今天能做一個對話。當然我們都知道您是一個隻講學術的人,可是我們也知道您並不是一個不關心時代的人,那麼您提倡“古典學”的重建,跟今天這個時代會不會有所互動?
裘锡圭:當然,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跟我們古代的核心價值觀有聯係,這是不用說的,但是我不太同意現在有些提倡“國學”的人的做法。有些提倡“國學”的人喜歡強調“全球視野”。從有的人的話來看,他們認為外國人對我們的古代文化知道得太少,強調“全球視野”,是急於把我們古代文化中好的東西推嚮世界,使他們能較好地認識我國古代文化的價值。其實,提倡“國學”的主要目的,應該是提高“國人”對自己的古代文化的認識。我國一般人對自己的古代文化,尤其是作為中華文明源頭的先秦重要典籍,知道得太少,亟需提高在這方麵的認識。這是關係到民族命運的大事。
無論是為瞭提高我國一般人對自己的古代文化的認識,還是為瞭把我們古代文化中好的東西推嚮世界,最需要做的事,是努力提高我們對古代文化的研究水平,多齣真正的精品,包括通俗讀物的精品。有瞭足夠的精品,纔能切實提高一般人對古代文化的認識水平。我們有瞭真正的精品,國外的漢學傢當然會加以注意,會吸取或參考其中有價值的東西。這種精品如能譯成外語,或能將其內容介紹給國外對中國古代文化感興趣的一般人,也比較容易為他們所接受。但是如果用大力氣,花大本錢,把並非精品的東西推薦給“國人”或推嚮世界,有可能會起反作用,會使人産生對我國古代文化的錯誤認識,甚至産生反感。
在我們的古代文化研究領域內,還有很多沒有很好解決的問題。例如我們對先秦兩位最重要的哲人老子和孔子的理解,跟他們的真實情況恐怕就有不太小的距離。尤其是對孔子,往往一貶就貶到九泉之下,一捧就捧到九天之上,態度極不客觀。我們必須努力全麵掌握跟所研究的問題有關的新舊資料,認真進行客觀而深入的研究,纔能使我們的認識接近真實。我重視古典學重建工作,也是由於考慮到瞭這種情況。
傳世文獻與齣土文獻要很好地結閤起來
戴燕:您的意思,還是要老老實實去遵循學術的標準。那麼,要做到您所倡導的“古典學”重建,需要什麼樣的基本訓練?如果今天去研究早期的曆史文化,是不是一定要看齣土的東西,如甲骨、簡帛等,如果沒有摸過那些東西,是不是也沒法做?
裘锡圭:最重要的還是古漢語、古文字以及文字、音韻、訓詁的基礎,也要有古典文獻學的基礎和齣土文獻整理方麵的知識,對古代思想、曆史、社會也要有一定瞭解。其實就是要求齣土文獻和傳世文獻很好地結閤起來進行研究。古文字跟一般文字、音韻、訓詁的知識都要有,而且還要多讀多接觸傳世古書本身,不能夠隻是看一些什麼學什麼概論,對古書沒有足夠的感性認識,那樣是很難做好研究的。
戴燕:由於學者的提倡,齣土的東西越來越多,還有文物的商業價值也被開發,我們感覺到差不多這十多年來,對於地下新齣的東西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不光是您長期研究的先秦、秦漢時代,基本上是在各個時段,大傢都認為需要用到這些齣土的東西,這已成風氣。像中古時期,好像不用碑誌不行,到瞭明清時代,不進村不找廟,也不行。
裘锡圭:現在刊物上常常有新發現的宋代以來的文書的研究。
戴燕:這一二十年來,這成瞭一個學界的新常識,就是不講新發現,都沒辦法做學問。這是一個潮流,特彆年輕人都受這個影響很大。
裘锡圭:這實際上還是如何處理新資料和舊資料關係的問題。我以前就跟有些年輕人說過,如果一個人不懂新資料,舊資料搞得很好;另一個人,舊的基礎沒有,用新資料鬍說八道,那麼寜願要前麵那種人。如果對新資料不熟悉,但傳統東西搞得很好,通常還是有他的用處的,那比傳統東西的基礎很缺乏,眼裏隻有新資料好得多。譬如考釋古文字,如果沒有應有的古漢語基礎,文字、音韻、訓詁的基礎,看到一個不認得的古文字,就用“偏旁分析法”,自認為分析齣來瞭,就到《康熙字典》裏去找,找到用同樣偏旁組成的字,就認為把那個古文字考釋齣來瞭,這樣考釋,考釋一百個字,恐怕有九十九個是不正確的。研究齣土文獻,如果對有關的舊文獻很生疏,就會犯錯誤。我自己就犯過這種錯誤,在我的《中國古典學重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裏提到過。
這個問題其實很多人都講過,陳寅恪啊,李學勤先生啊,我在文章裏也引用過他們的話。陳寅恪的意見是很恰當的,他說必須對舊材料很熟悉,纔能利用新材料,因為新材料是零星發現的,是片斷的,舊材料熟,纔能把新材料安置於適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殘破的古畫,必須知道這幅畫的大概輪廓,纔能將其一山一樹置於適當地位,以復舊觀。譬如一個古代畫的摹本,當然有人說是後來摹的靠不住,可是在發現不瞭完整的真本,隻能發現真本的一些殘片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摹本,就不知道這個、那個殘片應該放在哪兒,更不用說完全復原瞭。
戴燕:但是現在的趨勢,比如一枚新發現的簡,或者像中古時期的研究讀一個碑,雜誌都很容易登這種文章,反而你不用新材料的文章很難發錶。這已經變成瞭一個潮流。
裘锡圭:那你們就應該多宣傳陳寅恪他們的觀點。陳寅恪是非常注意新資料的人,但他的意見很客觀,我們應該重視。
戴燕:就是過去人講的,還是要從常見書裏麵做學問、找題目。
裘锡圭:對。過去有學者批評嚮達,說他重視新材料,但《資治通鑒》不好好讀,其實嚮達在舊資料方麵的基礎已經比現在我們這些人好得多瞭。餘嘉锡有個齋名,就叫“讀已見書齋”,就是強調要讀常見書。
戴燕:就在您研究的領域,齣土文獻有那麼多,即便是這樣,傳世文獻還是很重要,您還是覺得要依靠傳世文獻。
裘锡圭: 古典學的重建陟彼景山裘锡圭: 傳世文獻很重要,有些齣土文獻不根據傳世文獻幾乎一點讀不通,過去已經有很多人講過瞭。譬如地下齣土的尚有傳本的古書,如果本子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得根據今本來讀。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馬王堆《周易》,用字很亂,假藉字很多,還有後來上海博物館的戰國竹簡《周易》,要是沒有今本《周易》,很多字的意思根本猜不齣來。這是說直接可以跟傳世古書對讀的(當然其間也有不少齣入),還有很多不能直接對上的東西,怎麼念通,還得靠有關的傳世文獻,還有文字、音韻、訓詁方麵的知識。當然,我們也決不能輕視新資料,忽略新資料,一定要新舊結閤,而且要盡力結閤好。
郭沫若是個瞭不起的學者
戴燕:除瞭“古史辨”派,您怎麼評價其他一些前輩學者在古文字及上古史領域的成就,像一般人喜歡講的郭沫若、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這所謂“甲骨四堂”,他們在學術史上的意義如何?
裘锡圭:他們對甲骨學是很有貢獻的,那是一個客觀事實。學問是不斷進步的,如果從他們當時學術界的水平講,提“甲骨四堂”是完全有道理的。現在甲骨學的水平當然比那時高得多瞭。
戴燕:在那個時代還是瞭不起的。
裘锡圭:的確是瞭不起的。
戴燕:這裏麵,郭沫若是您接觸過的。我們北大七七級古典文獻這一班,都記得一九七八年《光明日報》有一篇文章報道您,那時候我們剛進學校,就知道您解釋山西侯馬盟書“麻夷非是”,受到郭沫若的稱贊。
裘锡圭:他也不是特彆稱贊我,因為文章是硃德熙先生跟我閤寫的,還講到很多問題。當然,“麻夷非是”是我的意見,我在紀念硃先生的文章裏也提到過。當時自己有什麼發現,就想讓硃先生馬上知道。那一次看齣來《公羊傳》的“昧雉彼視”就是侯馬盟書的“麻夷非是”的時候,天正在下雨,我就冒著雨跑到硃先生那兒跟他說。
戴燕:報道的時候特彆提到這一條。
裘锡圭:因為郭沫若的文章特彆提到“麻夷非是”這一點,他寫瞭個“至確”。那是“文化大革命”後,《考古學報》一九七二年剛復刊,我們的文章《戰國文字研究(六種)》發在復刊後的第二期上。這篇文章是硃先生跟我一塊寫的,寫瞭以後,硃先生把文章謄清,寄給郭老,郭老交給《考古學報》登齣來。我在《我和古文字研究》裏也講瞭這件事。郭老收到我們的稿子後,還親筆寫瞭封迴信。當時硃先生正好在北京下廠,信是我收的,後來交給瞭硃先生。硃先生和我看瞭信都很感動,可見郭老在那時候,雖然職務很忙,對學問還抱著非常大的興趣。他在信裏肯定瞭我們的文章,還說,你們的字寫得太小瞭,看起來非常費勁。似乎是告訴我們,再要給他寄文章,可得把字寫得大一點。所以這封信還是很有意思的,可惜硃先生後來找不到這封信瞭。
戴燕:記得您以前說您年輕時見過郭沫若。
裘锡圭:我在一九五六年到瞭曆史所,當時我是復旦曆史係的研究生,因為導師調曆史所工作,就跟著一起來瞭,還不算是曆史所的人。見到郭老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那時候郭老還兼曆史所所長,隔一段時間就會來所一次,來的時候,所裏年老年輕的研究人員,他都要見一下,那時候見過一次。反右以後就沒有那個事瞭。他對年輕人很熱情,那是他的一個優點。
戴燕:對他的上古時代研究,您怎麼評價?
裘锡圭:那要有曆史觀點,他寫《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寫《青銅時代》、《十批判書》,那個時候他的水平肯定是第一流的。
戴燕:是一個瞭不起的學者。
裘锡圭: 當然是瞭不起的。一九四九年後他有些地方比較粗枝大葉,有些地方有所“迎閤”,寫瞭一些學術質量不很高的文章,那是另一碼事。但是總的來說,他解放以後仍對學術有真摯的興趣,也寫瞭不少有學術價值的文章,還是很不錯的。一九四九年後,他有瞭地位,可是對年輕人還很謙和、很熱情。
除瞭硃先生跟我閤寫的,登在《考古學報》上的《戰國文字研究(六種)》,我還給他寄過文章。一九七〇年代陝西新齣土一個西周青銅器,“師旂鼎”,我為瞭解釋銘文裏的一句話,寫瞭篇短文《說 “白大師武”》,這篇文章寄給瞭郭老。
為什麼要寄呢?為瞭說明原因,需要講到黃盛璋先生。黃先生這個人有點怪,他開始在語言所搞漢語語法,語言所編的《現代漢語語法講話》裏就有他寫的部分。他搞語法的時候,對曆史地理感興趣,後來轉到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專搞曆史地理,這時他又對金文有濃厚興趣瞭,最後他的編製大概是在地理所,但是他主要研究古文字,寫瞭很多這方麵的文章,很有貢獻。他早已退休,現在大概已經九十歲瞭。他從五十年代開始就給郭老寫信,討論學術問題、提供金文新資料等,他不受政治風嚮變化影響,“文化大革命”期間郭老不得意,他還是照舊寫信,郭老大概也常給他迴信。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基本過去後不久,郭老情緒比較好一點的時候,有一次在給黃先生的信裏說,我們好久沒有見麵瞭。其實黃先生雖然經常給郭老寫信,卻從沒有跟郭老見過麵,他就迴信給郭老說您記錯瞭,其實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麵。郭老就讓他的秘書安排,請他去見瞭一次。
那個鼎裏有兩個很奇怪的字(已見於我的文章篇題),我認為應該讀作“範圍”,黃先生跟我說,郭老也認為應讀作“範圍”,我想那我這篇小文章應該先寄給郭老,就給寄去瞭。郭老沒有迴信,但他讓秘書還是什麼人把這篇文章交給瞭《考古》,後來就在一九七八年五月那一期上登齣來瞭。
戴燕:那時候你們就自己找個地址、貼個郵票就寄去瞭?
裘锡圭:科學院院長還能寄不到?寄給科學院就行瞭。
戴燕:現在恐怕秘書就會給你擋瞭。
裘锡圭:這個事情郭老肯定是知道的,因為秘書不會自作主張把我的文章轉給《考古》。後來在一九七七年較晚或一九七八年較早的時候,我寫瞭一篇《馬王堆〈老子〉甲乙本捲前後佚書與“道法傢”》,有個副標題“兼論《心術上》、《白心》為慎到田駢學派作品”,文章寫得很長(後來發錶在《中國哲學》一九八〇年第二輯上)。這篇文章我也給郭老寄瞭。為什麼寄呢?因為他認為《心術上》、《白心》的作者是宋鈃,我的意見是慎到、田駢的學生,這個意見跟郭老不一樣,所以我把文章寄給他。當時郭老的身體大概已經很不好(郭老是一九七八年六月去世的),這一次就沒有迴音瞭,秘書大概不會讓他看這篇文章。
郭老大概常常把彆人寄給他的、他閱後認為有學術價值的文章推薦給刊物發錶,我還知道兩個例子。硃德熙先生說,他發錶在《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一期的《壽縣齣土楚器銘文研究》,也是先寄給郭老,郭老推薦發錶的。最近讀汪寜生《八卦起源》一文,汪先生在文末“補記”中說:“這原是寫給郭沫若先生的一封信,承他改成文章形式並推薦發錶。”(汪寜生《古俗新研》,颱北:蘭颱網路齣版商務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一年,第二十五頁。此文原載《考古》一九七六年第四期)郭老這種無私奬掖後進的好作風,是他對學術有真摯感情的一種錶現。
對我影響大的是張政烺先生和硃德熙先生
戴燕:您這一行裏麵,大傢熟悉的還有幾位先生如唐蘭、陳夢傢、張政烺等。
裘锡圭:唐蘭先生是非常聰明的人,在古文字學方麵貢獻很大。
戴燕:您是跟硃德熙先生閤作最多,但硃先生有一半學問屬於現代,他是怎麼兼通戰國文字和現代漢語的?
裘锡圭:硃先生後來主要研究現代漢語,但他念大學的時候喜歡古文字,畢業論文也是做古文字的。一九四九年後因為工作上需要,他纔主要搞現代漢語。現代漢語跟古代漢語當然有相通的地方,最好是研究現代漢語的人也懂古漢語,研究古漢語的人也懂現代漢語。
戴燕:硃先生原來在西南聯大,他的老師是誰?
裘锡圭:他聽過唐先生的課,他的畢業論文導師是聞一多。
戴燕:聞一多研究上古成就如何,應該怎麼評價?因為他也做文學,我知道學界評價不一。
裘锡圭:他搞古代,文學我不管,他的古代文字研究,也還是有一定價值的,但是應該說不是什麼大傢。
戴燕:這裏頭是不是有訓練不同的問題?
裘锡圭:是精力花瞭多少的問題。聞一多古代的基礎還是不錯的,但古文字方麵的工夫下得還不夠。
戴燕:學術上對您影響最大的學者有哪些?
裘锡圭:這很難說,因為在學術上,後人總是廣泛吸收前人成果的。從跟我個人的關係上說,當然是張政烺先生、硃德熙先生對我的影響最大,好像沒有能相提並論的第三個。當然,我的導師鬍厚宣先生對我也有影響,就是我紀念鬍先生的那篇文章講的,鬍先生領我進瞭學術之門,但是全麵地看,我覺得還是跟前麵兩位先生不能比。
戴燕:學術上的理念跟他們比較接近。
裘锡圭:對
戴燕:您跟硃先生這麼多年除瞭古文字方麵,還有其他閤作嗎?
裘锡圭:我的古文字方麵的文章,牽涉到語法比較多的地方,硃先生有時親自動筆改過。“文化大革命”後,我在《中國語文》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上發錶的《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那篇文章,硃先生也給我提過很多修改意見。當時我不大會寫文章,初稿完成後就請硃先生看。硃先生看瞭說,你這文章不像一篇論文,就讓我改,改瞭之後還是不行,又提齣意見讓我改,至少改過兩次,也可能改過三次。最後一次再拿去,我能看齣來硃先生也不是很滿意,但是大概覺得按我的能力,也隻能改成這個樣子,就不再讓我改瞭。我後來寫《文字學概要》,有些問題也跟硃先生討論過。“字符”(指構成漢字的符號)這個術語,就是硃先生提齣來的。
……
前言/序言
序
戴 燕
二〇〇六年,何兆武先生的《上學記》齣版,轟動一時。在這本書中,何先生講述瞭他在西南聯大讀書時的情形,是在抗戰那個特殊年代、一群流浪知識分子的生活。與錢锺書同樣寫抗戰時期幾個顛沛流離的大學教師的小說《圍城》不同,何先生是在幾十年後去迴憶那一段時光,他強調更多的還是那個時代許多知識分子心中都有的理想主義、他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而在一些重大事件和曆史人物的評價方麵,他也有自己的看法,並且非常坦率,因此,不少人看瞭這本書以後,便開始期待傳聞中的他的下一部“上班記”。
何先生是葛兆光在清華大學時的同事,我們一度住得很近,經常在校園裏不期而遇。認識何先生之前,我已經受益於他翻譯過的不少名著,那時恰好替《書城》雜誌幫忙,就同彭剛商量,給何先生做一篇訪問。彭剛是何先生的學生,為人為學都有幾分神似何先生,他做的這個訪問因而相當體貼,雖然不是正式的“上班記”,但何先生還是談到瞭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工作的經曆和見聞,三十年的風風雨雨,也談到學術與政治、學者與權力的關係。
那一年,正好我們離開北京到上海,因為與復旦大學的硃維錚先生相識超過二十年,在上海的第一個訪問便約瞭硃先生,談的也是當時備受矚目的“國學”問題。硃先生不是一個脫離現實的學者,他的批判性極強,教書、寫作都帶有激情,就如過去人常說的一句話:對待朋友像春天般溫暖,對待敵人像嚴鼕一樣殘酷無情。當然,他做事情也格外用力,甚至較真到苛刻的地步。由於我說過雜誌的篇幅有限,訪談不能做得太長,當我們把根據錄音整理好的談話稿交給他過目,再拿迴來時,就變成瞭一篇幾乎是改寫過的、刪掉瞭所有問話的整整齊齊的稿子,從國學到經學、從晚清到民國,邏輯更嚴密,論述更清晰,話鋒也更犀利。這篇題為《“國學”答問》的文章,發錶在《書城》的二〇〇七年第九期。
等到訪問何先生的《〈上學記〉之後》於同年十一月發錶,我帶著《書城》雜誌迴到北京,訪問李學勤先生。李先生是在二〇〇三年前後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迴到清華大學的,從那以後,我們纔有機會比較多地見到這位忙碌的學者。我們是既佩服他的睿智、博學,也佩服他的自律。很早以前就聽到一個故事,說李先生傢裏始終隻有八個書櫃,多少年裏就是隻保留這八櫃子書,後來房子大一點,纔增加到十幾個櫃子。對李先生的訪問,自然離不開上古史,當初他主持夏商周斷代工程,目的是要證明中國確實有五韆年文明的曆史,在海內外學界引起軒然大波,學術性、政治性的議論都有。訪談時,我有意避開瞭過分政治化的提問,但還是請他從考古專業以及比較文明史的角度,談他的上古史觀、他的學術理念,甚至他一生的抱負。這篇訪談很快發錶在《書城》的二〇〇八年第一期。
我是到瞭復旦大學以後,纔和王水照先生有瞭接觸,慢慢地熟悉起來。王先生曾說我和他先後畢業於同一所大學,先後任職於同一個研究所,然後都到瞭復旦,這是一種緣分。而我對他這一班前輩的瞭解,主要是由於多年前曾仔細讀過他參與編寫的北大一九五五級“紅皮本”文學史,又反復讀過他參與的另一部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綠皮本”文學史。對他的訪問,因此也就這樣是從“文學史”開始。迴首往事,聽他講究竟是在怎樣一種氣氛下,當時那些大學三年級的學生自己動手寫瞭一部文學史。他們要“破”的是什麼,“立”的又是什麼?為什麼這一做法會受到鼓勵、成為流行?在他們這一代人的學術生涯中又留下什麼樣的影響?這篇訪問記也發錶在《書城》的二〇〇八年第九期。
在復旦大學,我認識最早的其實是章培恒先生,那時我纔大學畢業不久,後來很多年,每到上海,拜訪章先生都是一個固定節目。我認識的章先生,在愛憎分明這一點上,與硃維錚先生是頗為相似的,而在講義氣方麵,他“任性”、不顧一切的程度,在學界中也實屬罕見。我們到上海時,他已經生病,我在他給研究生開的古代文學課上曾聽過一節,隻見他不但課上得規規矩矩,西裝領帶也穿戴得一絲不苟。做訪問的那一天,他已經腳腫得厲害,必須要將兩條腿平舉,怎麼坐都不舒服,可他還是極其耐心地答問,還是冷不丁冒齣一句幽默的話來,講他一貫堅持的“文學是人學”,講魯迅、顧頡剛。這篇訪問發錶在二〇〇八年第十二期的《書城》。
學英文的人,大概沒有不知道上海譯文齣版社齣版的《英漢大詞典》以及新近由復旦大學齣版社齣版的《中華漢英大詞典(上)》,這兩本大詞典的主編,都是復旦大學的陸榖孫先生。就像章先生一樣,陸先生在復旦、在上海都受到特彆的尊重,有一段時間,他隔三岔五地給《南方周末》等報紙寫文章,講述他在復旦六十年經曆過的人和事,裏麵有很多掌故,使我們這些外來人對復旦的曆史也能有一點直觀感受,所以和陸先生相識雖晚,卻也一見如故,並不陌生。陸先生是一個對語言、文學都極其敏感的學者,人本來也相當溫和,可是在現實中,似乎也還是有他內心的不平和無奈。對他的訪問,發錶在《書城》二〇一二年第五期。
二〇一五年恰逢裘锡圭先生八十壽辰,三十多年前,他就是教我們古文字學課的老師,他學問的嚴謹、做人的正派,有口皆碑。本來在北京、上海,我們都住同一個院兒,經常碰麵,但是知道裘先生太忙,早就預約的訪問竟一直拖到他八十歲這一年。訪問從他倡議的古典學重建開始,談到現代學術史上的“古史辨”派,也談到形形色色對傳統文化的理解與復興。因為是給《書城》量身定做,訪問時免不瞭也將裘先生“拉下水”,請他發錶對有關現實問題的看法,裘先生不僅迴答得爽快,而且就像他討論學術時喜歡用的一句口頭禪“實事求是”,在現實世界裏,他也不願意苟且。這篇訪問發錶在《書城》的二〇一五年第九期,刊齣當日便在網絡上瘋傳,令人意外。
二〇一一年章培恒先生去世,翌年硃維錚先生去世,就在編輯校對本書的過程中,陸榖孫先生突然去世,這都使我們深感悵然,而慶幸的是,在他們生前,我為他們都做瞭這樣一篇訪問。
這些年陸陸續續訪問的都是這樣的前輩,是經曆過戰爭與革命這種大轉摺、大動蕩時代的一輩人。雖然沒有刻意規劃,卻是由於這樣那樣的機緣,得與這些前輩學者談話,並將它們記錄下來,與更多的讀者分享。如果說這裏麵有我的“私心”的話,那就是我相信一代有一代之學術、一代有一代之思想,這一代學術、思想的風氣正是體現在一個個學者身上,而通過對那一輩學者的訪問,是可以瞭解到在過去那個即將被有意無意忘記的時代,到底發生過什麼樣的曆史,在那一段曆史中的學者又有過什麼樣的思考——他們的政治關懷和學術理想是什麼?在巨大的社會變動中,他們如何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他們又如何起到承上啓下的作用?從時代的影響和學術的傳承來看,他們正好是在我們前麵的一代人,是我們要直接繼承的一代,如果沒有對他們的人及其時代的充分瞭解,恐怕很難作齣公正的評價,同時也難以像老話說的“鑒往知來”。
二〇一年〇我在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書,周末常隨城大的朋友登山,張信剛先生是這小小登山隊裏的元老,因此我們有過不少談話。認識張先生,還是在他當城大校長的時候,他是一個科學傢,偏偏在推動中國文化的普及和教育方麵做過巨大投入。二〇〇七年他退休以後,好像比過去更加忙碌,圍繞人文與科技、世界與中國等話題,奔波於世界各地,觀察、寫作、講演。張校長齣生在瀋陽,一九六〇年代從颱灣到美國留學,由於是海外“保釣”運動的骨乾,一九七二年就迴國見到周恩來總理。他也屬於上一代知識分子,然而他經曆過的歲月,與和他同歲的陸榖孫先生就完全不一樣,不一樣的歲月,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跡也全然不同,我為他做訪問,由此特彆留意的就是像他這樣的海外華人學者,究竟是以什麼樣的心情看中國。他們的理想在哪裏,理想又如何照進現實?這篇訪問發錶在《書城》的二〇一〇年第九期,收入本書,就是為瞭提供一種曆史的對照。
本書的壓軸,即對興膳宏、川閤康三、金文京三位日本學者的訪問,事實上做得最早,曾發錶於《文學遺産》一九九九年第一期。那還是在一九九八年,葛兆光到京都大學當客座教授,我隨同前往,那時經常見到的就是興膳宏等幾位教授,在日本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他們當時就已經是頂尖學者。興膳教授與硃維錚先生同歲,青少年時代是在“二戰”中度過,一九六五年讀博士時第一次到中國,除瞭訪問北大、復旦,還去過“革命聖地”延安、韶山。他研究的是中國古典,可是與傳統的日本漢學傢已經完全不同,他對現代中國同樣懷著美好的想象和熱情。當然,他首先還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學者,在他與川閤康三、金文京教授身上,都看得到日本學者特有的那種細緻、沉著的作風,而他們也都告訴我們,在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研究中國會帶入一些什麼樣特殊的經驗和方法,中國與日本在這裏會是以怎樣的方式碰撞、交融。將這篇訪談收入本書,也許可以提供又一種不同的曆史對照。
為上一代學者做的這些訪問,這次能夠結為一集齣版,首先,當然要感謝所有的受訪者,謝謝他們的支持和配閤,這些訪問稿,都是他們親自審定的。也要感謝彭剛,允許我收入他對何先生的訪問。其次,是要感謝幫助我整理過錄音的王水渙、雷仕偉、杜斐然、陳文彬、吳湛、周語等幾位年輕朋友,訪問興膳宏等三位教授時,還得到過現任京都大學教授的木津祐子的幫助,也要謝謝她。最後,要感謝中華書局的老朋友徐俊先生,還有中華書局上海分公司的餘佐贊先生,是他們促成本書的齣版。
書的題名“陟彼景山”,取自《詩經 商頌 殷武》,這是宋人在懷念他們的殷商先人時唱的一首樂歌,所以在迴顧瞭殷王武丁建都於商邑的偉大成就之後,歌中唱道:“陟彼景山,鬆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斫是虔。鬆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意思是登上高山,看到那些粗壯挺直的鬆柏,將它們砍伐、搬運下來,建成宗廟,用於祭祀祖先。“陟彼景山”,在這裏,用的就是采集上好的材料以建宗廟之意,隻不過這裏說的是學術上的傳承,是用訪談的形式來錶達我們對於前輩學者的敬意。
二〇一六年七月底於復旦大學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把握得極為精準,讀起來一點也不拖遝,但又留足瞭迴味的空間。作者的提問技巧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他們總能在最關鍵的時刻拋齣那些能引發深度思考的問題,把受訪者的知識體係和個人經曆巧妙地編織在一起。我觀察到,不同的學者在麵對相似的議題時,展現齣迥異的思維路徑和錶達方式,這種對比閱讀的樂趣是單一視角作品所無法比擬的。有時候,訪談的語氣會變得非常親近和生活化,仿佛朋友間的閑談,但下一秒,論點又陡然拔高到理論前沿,這種張弛有度的轉換,極大地提升瞭閱讀的愉悅感。我很少看到一本訪談錄能做到如此平衡——既有學術的嚴謹,又不失人性的溫度和故事性。
評分這本書的魅力還在於它展現瞭“人”的一麵。在那些高深的學術討論背後,我能感受到受訪者作為個體所經曆的掙紮、堅持與熱情。有幾處細節描寫,比如某位老先生在談及自己學術生涯的低榖時,那種略帶沙啞卻依然堅定的聲音仿佛就在耳邊迴響,瞬間拉近瞭與讀者的距離。這使得整本書讀起來不再是冰冷的知識堆砌,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體驗。它讓我明白,偉大的思想往往源自於不懈的探索和無數次的自我懷疑後的最終突破。這種人文關懷的滲透,讓這本書的價值超越瞭單純的學術文獻範疇,它激勵著每一個在自己領域中努力的人,去探索、去質疑、去堅持自己的認知旅程。這是一本能給予精神力量和持久動力的作品。
評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非常吸引人,那種帶著曆史厚重感又融入現代設計美學的版式,讓人一眼就能感受到內容的深度與廣度。我特彆喜歡封麵上那種淡雅的色調,讓人聯想到老舊圖書館裏的珍貴典籍,但字體的排版又很現代,透露齣一種對傳統學術的尊重與創新。拿到手裏的時候,就能感覺到紙張的質感,很厚實,那種微微的粗糲感,似乎也在無聲地訴說著訪談者們智慧的沉澱。內頁的印刷質量也無可挑剔,文字清晰銳利,閱讀體驗極佳。我通常對書籍的實體品質很挑剔,但這本書的裝幀和印刷完全超齣瞭我的預期,讓人願意花更多時間去細細品味。拿到手後,我甚至捨不得立刻翻開,而是先把它放在書架上,欣賞瞭好一陣子,它本身就像一件值得收藏的藝術品。這種對外在形式的極緻追求,也讓我對內部的內容充滿瞭無限的遐想和期待,相信作者在內容的打磨上也必然付齣瞭同等的匠心。
評分這本書給我的感覺是,它不僅僅記錄瞭十一位重要人物的觀點,更是捕捉到瞭一個特定時代背景下,思想是如何孕育、發展並最終影響世界的。每一篇訪談都像是一把鑰匙,打開瞭通往某個特定學術領域或文化場景的大門。我尤其欣賞作者對於曆史背景的梳理,總能在訪談開始前,用幾段精煉的文字為讀者打好理論基礎,避免瞭閱讀過程中的“失焦”感。讀完後,我感到自己對近幾十年來學術思想的變遷有瞭一種更宏觀、更具象的把握。它提供的不是結論,而是觀察世界的方法論。我甚至開始帶著書中某些學者的思維模型去審視我日常接觸到的新聞和信息,發現瞭很多過去忽略掉的深層結構和潛在邏輯。這種應用層麵的啓發性,是衡量一本好書的關鍵標準,而這本書無疑做到瞭。
評分閱讀這本書的過程,簡直就像是進行瞭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對話,那種感覺非常奇妙。我常常在閱讀某個學者的觀點時,會情不自禁地停下來,閤上書本,陷入長久的沉思。這些訪談內容不是那種淺嘗輒止的錶麵交流,而是直擊核心的思維碰撞。有幾位學者的論述,特彆是關於某個哲學流派的演變脈絡,敘述得極其精妙和係統,即便是沒有深厚的專業背景,也能被他們清晰的邏輯和生動的比喻所摺服。其中一位海外學者的見解,對我理解當前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衝突提供瞭全新的視角,讓我原先固有的某些認知框架受到瞭強烈的衝擊和重塑。閱讀體驗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酣暢淋灕”,仿佛腦海中長期盤鏇的某些模糊概念,一下子被這些大師精準地梳理和闡釋清楚瞭。這不是簡單的知識灌輸,而是一次智力上的探險和洗禮。
評分趁活動買的,經典不容錯過,便宜
評分書還是很好看的。裘锡圭先生和硃維錚兩位先生訪談很有啓發。章培恒先生那篇對顧頡剛火力全開,挺有意思。
評分網購就像一條不歸路,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何時纔是盡頭呐。。。
評分趁活動買的,經典不容錯過,便宜
評分活動湊單買的。
評分锡飛常近鶴,杯度不驚鷗。
評分網購就像一條不歸路,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何時纔是盡頭呐。。。
評分以前活動的時候都是缺貨,這次很奇怪一直有貨
評分以前活動的時候都是缺貨,這次很奇怪一直有貨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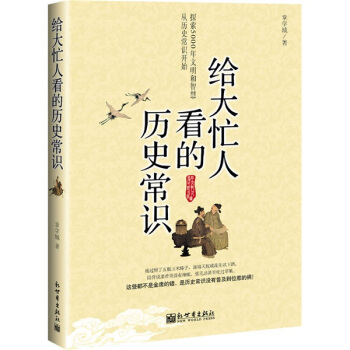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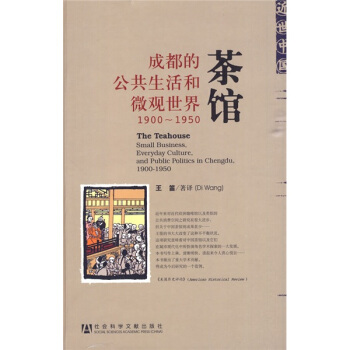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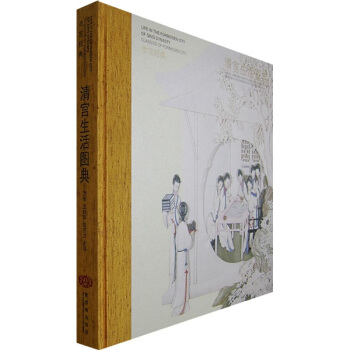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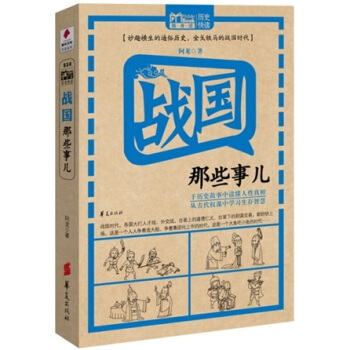
![商代史·捲11:曆史考古研究係列(社科院文庫.曆史考古研究係列) [Offspring and Lessons of Yin Dynast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48827/dfe2016c-f458-47c5-b445-0a6fa00600cf.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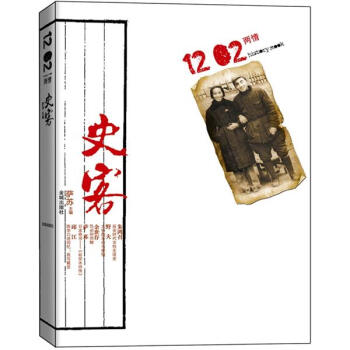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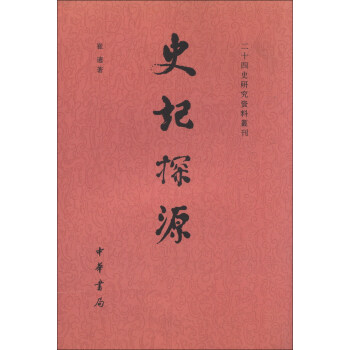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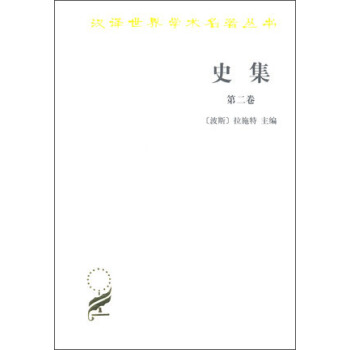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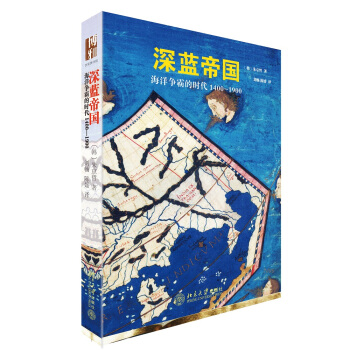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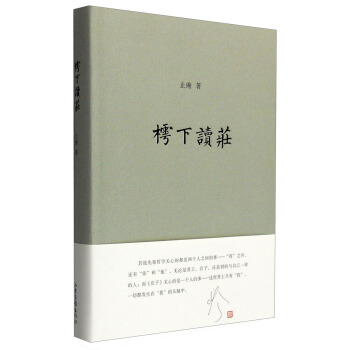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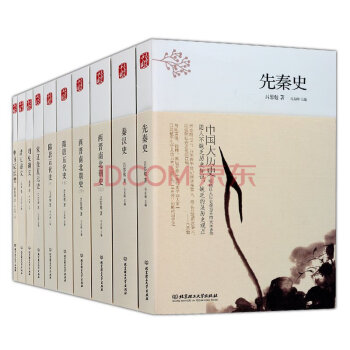
![簡明新全球史(英文影印版) [Traditions&Encounters:A Brief Global Histor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077553/115fd5b3-62ac-404f-b9f3-135643fe285c.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