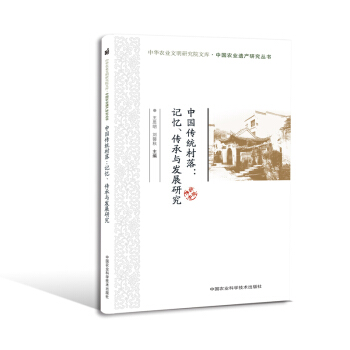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首届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学者们围绕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记忆、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对策研究等不同方面进行了充分讨论与交流,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和对策。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为主题,从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学及建筑与规划学的视角,对传统村落保护的困境、保护什么、如何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跨学科、多角度的剖析和探讨,并借鉴国外传统村落保护的经验,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提供启示。主要内容分为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记忆、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对策研究三个方面。
作者简介
王思明,1961年11月出生,湖南株洲人,农学博士,现任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首席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国家核心期刊《中国农史》杂志主编。
精彩书摘
第一部分 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记忆
庄,贼至则合力迎御,贼去则安生业,既可以捍御乡邑,亦足自护室家,方不负朝廷教养之恩”。a统治者认为,设置团练,其利有三:一是“四乡寨堡一立,则室家皆聚,乡勇无内顾之忧,人心自固,不忧溃散”。二是“寇盗往往因粮于我,故以掠地为能,惟聚乡村之老弱妇女货财米谷,收入寨堡,则敌野掠无所获,其势易饥,不能久淹”。三是“惟随所在都鄙,兴筑寨堡,又不假青吏之手,则事必易集”。b
基于此,皖南圩区组建了不少团练。其中有乡团和民团两种类型。咸丰三年(1853年),翰林院庶吉士陶士霖奉命督办南陵乡勇,取名敬胜勇。招募的乡勇多来自圩区。这些乡勇是在武生陶壁垣劝说下,由各乡绅士捐饷招募而来,自行训练,并由陶壁垣在马家园、马仁渡圩之渡口督带。通过这种方式,南陵招募到乡勇不下6 000余名c,咸丰四年(1854年),南陵县夏永清筹办民团,担任练长,由夏庆余协助办团。d咸丰三年(1853年),当涂官圩太平圩圩民祝嘉量7次投入圩观察营中作战,后来听到官圩告警,即回到当涂组织团练。另外当涂县南子圩陶振鹏组织团练,并于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太平军到来之际,率领练勇迎战。e
可以这么说,这些乡团的存在,主要还是执行清廷坚壁清野的政策,目的在于确保圩区的安宁。
2. 圩区以宗族及乡官等对内部圩民实行控制
上述是对外防御情形,针对日常圩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圩区地主则利用宗族和乡官等施行控制,以维护圩区的安定。
(1)圩区宗族对圩民的控制 关于宗族的控制,因为研究已经较多(亦可参阅王世红的《论家族祭祀对社会的凝聚作用》,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我在此只略作陈述。在笔者家乡安徽南陵,笔者所居住的村庄及周边村庄几乎是按照姓氏命名的,如余村、高村、夏村、胡村等,虽然这种村庄中也存在着其他姓,但是“外姓”至多不出3~5户,而且村庄中同一姓氏的居民存在着或亲或疏的血缘关系,考虑到农村婚嫁习俗,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表明绝大多数的村落存在着聚族而居的现象,这是宗族存在之前提。同时,同处皖南的徽州存有大量的宗族控制实证,不可能相去百里的皖南圩区就没有了。
2009年安徽省第三次文物普查简报第六十三期,南陵县文物普查时在南陵县河湾镇发现一座清代中晚期的张氏宗祠。另据民国《南陵县志》记载,当时全县各地建有规模不等的宗祠近300座,其中位于下乡(今南陵之圩区所属)就有近百所。芜湖市至今也还有以朱家祠命名的胡同。史书上也有关于皖南宗族控制的记载,“乾隆间,南陵县刘姓族长刘魁一将缌麻服弟刘种活埋,致使刘种之母因痛子之死而自杀”。f
宗族之作用,清人冯桂芬曾这样论述宗族:“牧令所不能治者,宗子能治之,牧令远而宗子近也;父兄所不能教者,宗子能教之,父兄可以宽而宗子可以从严也。宗子实能弥乎牧令父兄之际者也”。g农民害怕族长甚于官府。族长权大,而实权多操在绅衿地主之手。
(2)利用乡官体系对圩民控制 关于乡官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圩区的安稳不仅关系圩户生计,同时关系到封建国家税粮的征集。因此,封建政府必然会对圩区加强控制,封建政府对圩区的管理是通过对圩长、塘长、里甲、粮长、老农等乡官采取行政干预手段来实现,有时政府也会直接插手圩区的管理。而乡官体系大致可分为负责生产水利类、主营维稳类和示范仿效类。
第一类是负责生产水利类,主要包括圩长和塘长两种。江南地区早就形成“额设圩长,专为圩岸”
a 《清仁宗实录》卷58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庚辰条,第28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764页
b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81《兵政七·团练上》戟杨士达《上裕抚军论团练事宜书》,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上海:图书集成书局印行本
c 民国《南陵县志》卷1《舆地志》
d 民国《南陵县志》卷33《人物志》
e 民国《当涂县志》卷4《人物志》
f 《清高宗实录》卷1335
g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下卷,《复宗法议》
……
前言/序言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丛书》序
关于《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
中国有上万年农业发展的历史,但对农业历史进行有组织的整理和研究时间却不长,大致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金陵大学建立农业图书研究部,启动中国古代农业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程。同年,中国农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万国鼎(189 7—1963)先生从金陵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发表了第一篇农史学术论文《中国蚕业史》。1924年,万国鼎先生就任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主任,亲自主持《先农集成》等农业历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1932年,金陵大学改农业图书研究部为金陵大学农经系农业历史组,农史工作从单纯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向科学普及和人才培养拓展,万国鼎先生亲自主讲“中国农业史”和“中国田制史”等课程,农业历史的研究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195 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农业部批准建立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南京农学院双重领导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万国鼎先生被任命为主任。在万先生的带领下,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的研究工作发展迅速,硕果累累,成为国内公认、享誉国际的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中心。200 1年,南京农业大学在对相关学科力量进一步整合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承继了自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创建以来的学术资源和学术传统,这就是研究院将1920年作为院庆起点的重要原因。
80余年风雨征程,80春秋耕耘不辍,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在几代学人的辛勤努力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发展成为一个特色鲜明、实力雄厚的以农业历史文化为优势的文科研究机构。研究院目前拥有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专门史、社会学、经济法学、旅游管理等7个硕士学位授权点。除此之外,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还编辑出版国家核心期刊、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会刊《中国农史》;创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先后投入300多万元开展中国农业遗产数字化的研究工作,建成了“中国农业遗产信息平台”和“中华农业文明网”;承担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农学史专业委员会、江苏省农史研究会、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畜牧兽医史专业委员会等学术机构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形成了农业历史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信息收集和传播展示“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万国鼎先生毕生倡导和为之奋斗的事业正在进一步发扬光大。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有着整理和编辑学术著作的优良传统。早在金陵大学时期,农业历史研究组就搜集和整理了《先农集成》4 56册。1 956—1959年,在万国鼎先生的组织领导下,遗产室派专人分赴全国40多个大中城市、100多个文史单位,收集了1 500多万字的资料,整理成《中国农史资料续编》15 7册,共计4 000多万字。20世纪60年代初,又组织人力,从全国各有关单位收藏的8 000多部地方志中摘抄了3 600多万字的农史资料,分辑成《地方志综合资料》《地方志分类资料》及《地方志物产》共689册。在这些宝贵资料的基础上,遗产室陆续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稻、麦、粮食作物、棉、麻、豆类、油料作物、柑橘等八大专辑,《农业遗产研究集刊》《农史研究集刊》等,中国有上万年农业发展的历史,但对农业历史进行有组织的整理和研究时间却不长,大致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金陵大学建立农业图书研究部,启动中国古代农业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程。同年,中国农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万国鼎(189 7—1963)先生从金陵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发表了第一篇农史学术论文《中国蚕业史》。1924年,万国鼎先生就任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主任,亲自主持《先农集成》等农业历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1932年,金陵大学改农业图书研究部为金陵大学农经系农业历史组,农史工作从单纯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向科学普及和人才培养拓展,万国鼎先生亲自主讲“中国农业史”和“中国田制史”等课程,农业历史的研究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195 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农业部批准建立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南京农学院双重领导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万国鼎先生被任命为主任。在万先生的带领下,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的研究工作发展迅速,硕果累累,成为国内公认、享誉国际的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中心。200 1年,南京农业大学在对相关学科力量进一步整合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承继了自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创建以来的学术资源和学术传统,这就是研究院将1920年作为院庆起点的重要原因。
80余年风雨征程,80春秋耕耘不辍,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在几代学人的辛勤努力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发展成为一个特色鲜明、实力雄厚的以农业历史文化为优势的文科研究机构。研究院目前拥有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专门史、社会学、经济法学、旅游管理等7个硕士学位授权点。除此之外,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还编辑出版国家核心期刊、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会刊《中国农史》;创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先后投入300多万元开展中国农业遗产数字化的研究工作,建成了“中国农业遗产信息平台”和“中华农业文明网”;承担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农学史专业委员会、江苏省农史研究会、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畜牧兽医史专业委员会等学术机构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形成了农业历史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信息收集和传播展示“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万国鼎先生毕生倡导和为之奋斗的事业正在进一步发扬光大。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有着整理和编辑学术著作的优良传统。早在金陵大学时期,农业历史研究组就搜集和整理了《先农集成》4 56册。1 956—1959年,在万国鼎先生的组织领导下,遗产室派专人分赴全国40多个大中城市、100多个文史单位,收集了1 500多万字的资料,整理成《中国农史资料续编》15 7册,共计4 000多万字。20世纪60年代初,又组织人力,从全国各有关单位收藏的8 000多部地方志中摘抄了3 600多万字的农史资料,分辑成《地方志综合资料》《地方志分类资料》及《地方志物产》共689册。在这些宝贵资料的基础上,遗产室陆续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稻、麦、粮食作物、棉、麻、豆类、油料作物、柑橘等八大专辑,《农业遗产研究集刊》《农史研究集刊》等,撰写了《中国农学史》等重要学术著作,为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受到国内外农史学人的广泛赞誉。
为了进一步提升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加强农史专门人才的培养,2005年85周年院庆之际,研究院启动了《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文库》推出的第一本书即《万国鼎文集》,以缅怀中国农史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万国鼎先生的丰功伟绩。《文库》主要以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科学研究工作为依托,以学术专著为主,也包括部分经过整理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资料。《文库》启动初期,主要著述将集中在三个方面,形成三个系列,即《中国近现代农业史丛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丛书》和《中国作物史研究丛书》。这也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研究院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方向。我们希望研究院同仁的工作对前辈的工作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希望他们更多地关注经济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就历史而谈历史,就技术而言技术。万国鼎先生就倡导我们,做学术研究时要将“学理之研究、现实之调查、历史之探讨”结合起来。研究农业历史,眼光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内部,要关注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农业发展与经济变迁的关系、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业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关系,为今天中国农业与农村的健康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王思明
2007年11月18日
用户评价
我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村落:记忆、传承与发展研究》这本书爱不释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展现出的那种人文关怀和学术深度。作者在进行研究时,并没有将自己置身于学术的象牙塔中,而是深入到基层,与村民们同吃同住,倾听他们的声音,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这种“蹲点式”的研究方法,使得书中的内容充满了人情味和温度。比如,书中描述的一位老奶奶,她一生都在守护着村落的古井,每天清晨打水,傍晚烧火,她的生活与这口古井紧密相连,而作者则通过对这位老奶奶的细致描摹,展现了传统村落中普通人身上所蕴含的坚韧和奉献精神。同时,作者在理论上也展现了扎实的功底,他借鉴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建筑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框架,对传统村落的演变和发展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我尤其喜欢他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认为这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应该得到保护和传承。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学术研究如何能够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既有严谨的学术论证,又不失鲜活的生活气息。
评分《中国传统村落:记忆、传承与发展研究》这本书对“发展”部分的论述,则展现出一种非常前瞻和务实的态度。作者并没有回避传统村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例如人口外流、经济衰退、环境污染等问题。但他也没有因此陷入悲观,而是积极探索各种可行的发展模式。他提出,不能简单地套用城市化的发展思路,而应该根据每个村落的独特性,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书中举了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某个村落利用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资源,发展起了乡村旅游,不仅增加了村民收入,还带动了当地的特色产业。还有的村落,则通过发展创意农业、手工艺品生产等方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我特别欣赏作者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他强调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保护好村落的生态环境和文化风貌,避免过度开发和商业化对传统村落造成的破坏。书中还提出了一些关于政策支持、人才引进、社区参与等方面的建议,这些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读完这部分,我感觉对传统村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看到了它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能够绽放独特魅力的可能性。
评分在阅读《中国传统村落:记忆、传承与发展研究》的过程中,我最感触的莫过于书中对于“传承”的深入探讨。作者并非将传统村落简单地视为过去的遗迹,而是深刻地分析了那些能够跨越时代、保留下来的文化基因。他关注的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建筑遗存,更深入到村民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书中详细介绍了某个村落如何将传统的农耕技艺与现代农业相结合,既保留了古老的智慧,又提高了生产效率。又比如,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讲述某个地方戏曲的传承故事,从艺人的艰辛学艺,到观众的朴实热情,再到年轻人对传统艺术的重新发现和热爱,每一个环节都写得淋漓尽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某个少数民族村落的服饰传承,那些精美的绣花图案,每一个针脚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和民族的审美,而作者更是挖掘出这些服饰背后蕴含的家族历史和图腾意义,让简单的衣物变得意义非凡。这本书让我明白,传承并非一成不变的守旧,而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注入新的生命力,让古老的文化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光彩。我尤其赞赏作者对于“活态传承”的强调,他认为只有当传统文化真正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才能实现真正的传承。
评分《中国传统村落:记忆、传承与发展研究》这本书,我拿在手里的时候,就有一种沉甸甸的厚重感。书的封面设计很有意境,一幅水墨风格的古村落图,远处青山叠翠,近处白墙黑瓦,仿佛能听到微风吹过老屋的瓦片发出的沙沙声。我迫不及待地翻开第一页,就被作者开篇的引言深深吸引。他并没有一开始就抛出干涩的理论,而是用一种非常贴近生活化的语言,描绘了一个个鲜活的村落故事。我仿佛亲身走进了那些古老的巷道,触摸着斑驳的墙壁,感受着岁月的痕迹。书中对村落的“记忆”部分的描写尤其精彩,作者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访谈,挖掘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例如某个村落流传下来的独特习俗,某个家族世代相传的手艺,甚至是某位老者口中模糊但充满人情味的回忆。这些零散的“记忆碎片”,在作者的笔下被巧妙地串联起来,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我尤其喜欢他描写某个村落的宗祠,那里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地方,更是村落凝聚力的象征,是村民们共同的情感寄托。书中的图片也很精美,每一张都配有详细的说明,让我对书中所描写的村落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读完这部分,我感觉自己不再仅仅是在阅读一本书,而是在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旅行,与那些古老的村落进行一场深刻的心灵对话。
评分《中国传统村落:记忆、传承与发展研究》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示在于,它让我重新审视了“村落”的价值。在当下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我们常常会忽略那些散落在乡村深处的宝藏。作者通过对一个个传统村落的深入剖析,让我看到了它们身上所承载的独特的美学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书中对村落建筑格局、空间布局、生活习俗的描写,都充满了诗意和韵味,让我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例如,某个村落依山傍水而建,房屋错落有致,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浑然天成的画卷。作者还强调了传统村落作为“乡村记忆体”的重要性,它们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是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这本书让我更加珍视这些古老的村落,并认识到保护和传承它们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为了留住历史,更是为了汲取智慧,为我们当下的生活和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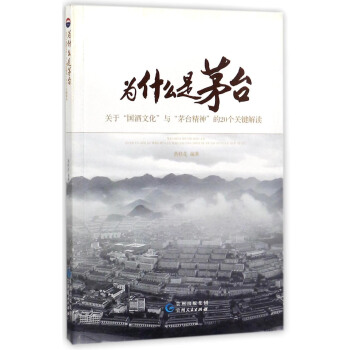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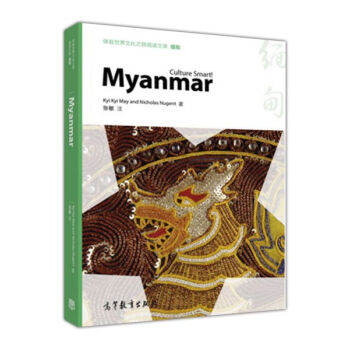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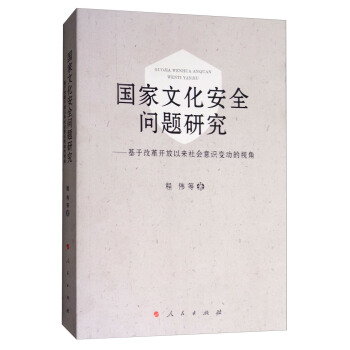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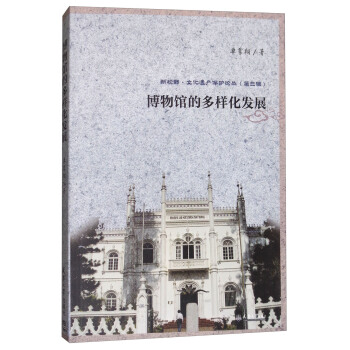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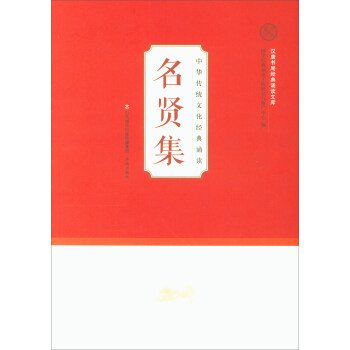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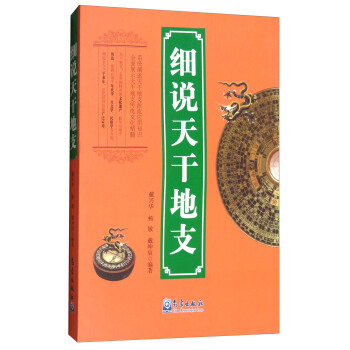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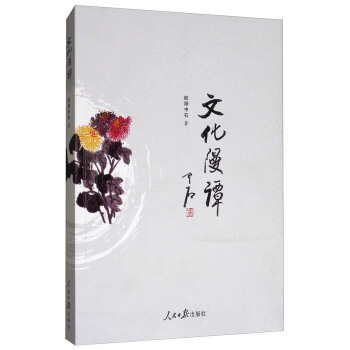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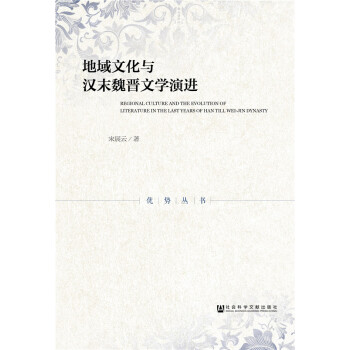
![诚品时光 [CHITEKI SHIHON RON Subete No Kigyo Ga Designer Shu]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84703/5ab35809Nb256402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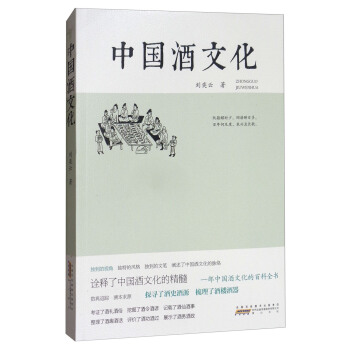
![慈善与文化选择/陕西省慈善文化研究文库 [Charity and cultural selec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04679/5aa5e2c2Naf57e10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