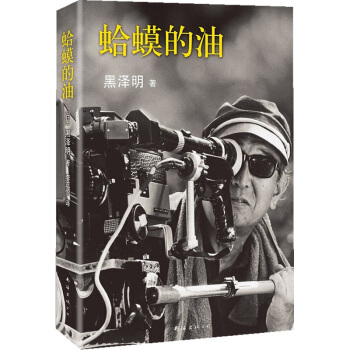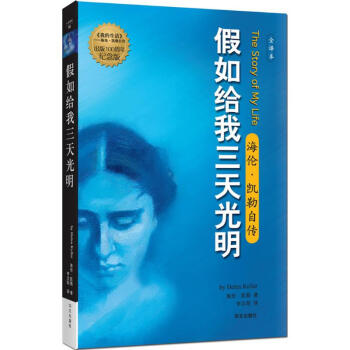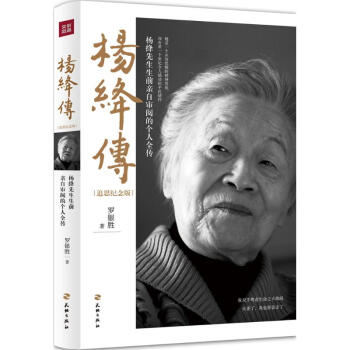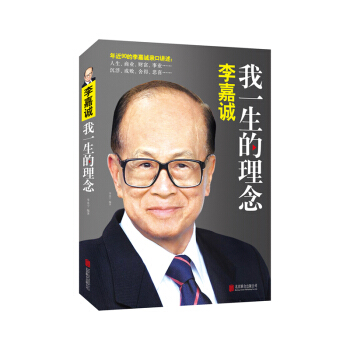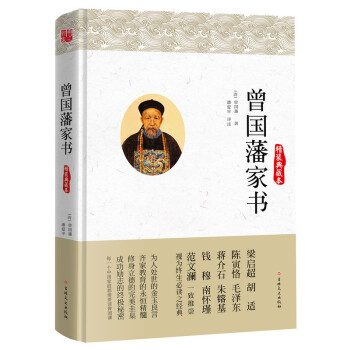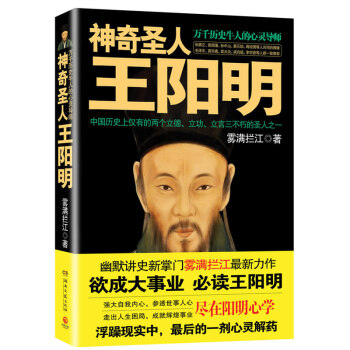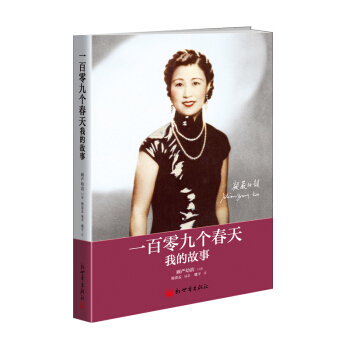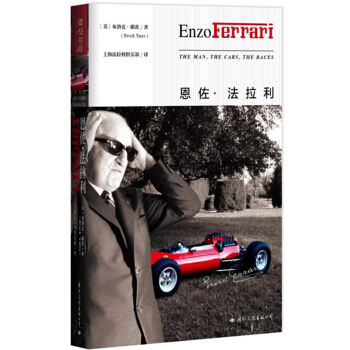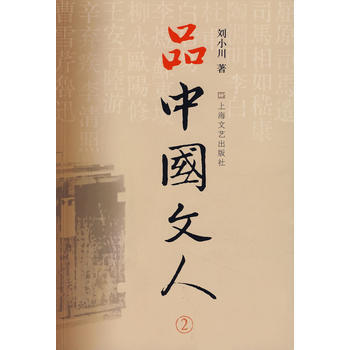具体描述
★过得刚好,这是郭德纲式幽默,也是郭德纲的人生态度。我争者人必争,极力争未必得。我让者人必让,极力让未必失。真放肆不在饮酒放荡,假矜持偏要慷慨激昂。万事留一线,江湖好相见。
★郭德纲亲笔讲述人生四十年的江湖过往,你能看到行文冷静、处变不惊的郭德纲,也能看到当年语言犀利、口无遮拦的郭德纲,同样能看到一个才华横溢的郭德纲。
★一本拒绝传递任何价值观的闲书,充满了郭德纲独有的诙谐和幽默。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不喜欢郭德纲的读者。
郭德纲亲笔作品,讲述人生四十年的江湖过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迄今为止,人生回顾,荣辱浮沉,冷暖自知,自浊自清自安然。书中的文字记录了郭德纲这些年的心路历程以及对人生、相声艺术、生活的感悟和思考,行文冷静,不煽情,不夸张,不做作,不隐瞒,不回避。
《过得刚好》有着极其鲜明的郭式风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妙语连珠,文字独特,语言幽默风趣,读之不禁令人捧腹,为我们营造了一份无与伦比的阅读快感,这份快感和他的相声作品一样过瘾。即使面对着台下无人的惨淡局面,郭德纲依然保持着他的幽默感。
过得刚好,这是郭德纲式幽默,也是郭德纲的人生态度。我争者人必争,极力争未必得。我让者人必让,极力让未必失。真放肆不在饮酒放荡,假矜持偏要慷慨激昂。万事留一线,江湖好相见。
郭德纲,相声演员,德云班主。天津人,生于1973年,自幼酷爱各种民间艺术,八岁投身艺坛。1996年创办北京德云社,说相声、讲评书、唱戏、拍电影、拍电视剧、主持电视节目。
鱼龙夜话
男人四十
我与我师
我与张文顺
我与于谦
德云后台
江湖梦眺
高雅与低俗
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
“反三俗”
我要“反三俗”
停滞的不是相声,是演员
相声圈
天津同行
曲艺笔记
专家
艺人
大鹏
曲艺的衰落
红桥旧事
“骂人”指南
艺术家
相声世界
你是“黑社会”
角色
友人来访
聊天
师徒
旧巷斜阳
读书
江湖
人生
戏语
偶感
北京
共勉
故事
微言
是非
名利
传统
心泪
曲目
前辈
旧事
似水流年
菜园小记
鸡犬不宁
修身养性
岁月
拉黑秘语
“毁”人不倦
“骂人”指南
围了个脖
偷拍
出走
途中
出国
马过梨园
一本正经
段子
相声史话
代后记:感恩
精彩书摘 男人四十不惑但从今日始,韬光氍毹正当年。忍忍忍,难难难。身处池畔,自浊自清自安然。若不登高看,怎知海天蓝。人到用时仁义少,事无经过不知烦。静坐思过观花谢,三省吾身饮清泉。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偷笑钓鱼船。
(三十九岁生日所作,虚岁四十,年届不惑,几句残言,聊以自勉。)我天生对舞台就没有恐惧感我是天津人。天津是相声窝子,我是在天津学艺长大的,后来来到北京发展。我离开天津移居北京大概是在1995年。
我父亲是警察,我母亲是老师。我小时候住在天津的老城区,附近有很多剧场、茶馆什么的。我父亲有时候要执勤,就把我放在剧场里,时间长了就对相声产生了兴趣。一次说相声是九岁左右,就是说着玩。那时候还喜欢挂着胡子扮包公,被小朋友叫作“老头秧子”。
我天生对舞台就没有恐惧感。
我没有别的爱好,一的爱好就是相声,因此,从小就跟同龄人玩不到一块儿去。直到今天,我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不会打扑克、不会跳舞,也没有应酬。台上说相声,台下琢磨相声。对相声的感情是我从小培养起来的,天津的氛围很好。我为了这行抛家舍业,受了这么多年的罪,相声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生命。可能有人拿相声当个手艺,养家糊口,跟剃头、修脚、卖包子一样;有人当是玩具,玩会儿就搁下,可玩可不玩。但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命。
一次进北京是在1988年,当时我是在全国总工会文工团,那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就跟着混。当时脑子里也常想,我什么时候能当上相声大腕儿?这是那时的真实想法。那一年,我十六岁,待了两三年,因为种种原因就回去了。有一年的春节,我碰到了当年全总文工团的老团长。跟老团长吃饭的时候,他一脸愧疚,再三敬酒。我跟老团长说,您不用这样,我当年确实一文不值。这不是谦虚,回想当初,我只是比不会说相声的好那么一点点,离开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是我一次进北京。
1994年,第二次进北京,漫无目的,到处瞎撞,自序:人在江湖要出书了。
有人说要出书先出事儿。我也没出事儿,倒是把书出了。
我在私底下是一个特别无趣、乏味的人,喜欢待在书房里写字、听戏、看书,没有别的爱好,不抽烟,不喝酒,当然,也不喜欢烫头。
如果我不做艺人,大的愿望是做文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和黄金屋我都没遇到,但我依然爱看书,也爱写字。几张纸,一支笔,将心中事写下来,我觉得很快乐。
回头翻看这些文字的时候,也许这些事情都已经显得不再重要了,但是我很感慨,从中能看到我这些年的心路历程。人在天涯,身不由己,风雨踏歌行。江湖子弟,拿得起来放得下。放不下,也得放。活一百岁的没几个人,开心就笑,不开心待会儿再笑。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一辈子,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首先,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系统写作的人生自传,仅仅是把我这些年写的文章整理出版。这些文章记录了我这些年的经历和心路历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心态。
大部分文章存于文档,唯有二十八篇录于博客。输密码登录,打开文件。尘封三载又逢天日,抚案追昔不胜悲凉。这些年经历了太多事儿,远远超出了一个艺人的负荷能力。品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观荣辱纷争、死走逃亡,自浊自清自安然。台上笑传千万,台下苦闷凄惶。
整理、分类、筛选、修改,反复校对,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在满足你们对我合理的好奇心的同时,还能存在一点点其他的价值,也许是阅读的快乐或者其他,但如果您希望能在我的书中获得高深的知识或者思想,我猜您只能失望而归,这是一本拒绝传递任何价值观的闲书,我还是说相声的草根艺人郭德纲。别人都说我们是草根。什么叫草根?其实草根很便宜,人参、灵芝、冬虫夏草,都是这些不上档次的东西,我们比不了人家大棚里的香椿芽、韭黄。
在这本书出版之际,我已经四十岁了。八岁从艺,至今已经三十多年。
初书名叫《人在江湖》,后来我接受本书编辑的建议,换了一个书名,也就是你们看到的《过得刚好》。一路走来,各种坎坷,各种不顺和阻碍,终于我也看到了花团锦簇,也看到了灯彩佳话。那一夜,我也曾梦见百万雄兵。
万幸,我一直在做我喜欢的事情。现在的生活我很满意,就像你们看到的书名一样,过得刚好。如果说我还有什么追求和愿望的话,那就是我希望能说一辈子的相声,等到八十多岁还能跟于谦老师站在小茶馆的舞台给大家说相声。那时候,估计我的头发都掉光了,于老师的头发也白了,一脑袋的白毛,还烫头,跟喜羊羊似的。我不指望天塌地陷,地球都毁灭了,还有我的一段相声在宇宙间飘荡,那是扯臊。
功名富贵,人间惊见白首;诗酒琴书,世外喜逢青眼。巿争利朝争名,伶逐势恶逐威。且看沧海日、赤城霞、峨嵋雪、巫峡云、洞庭月、潇湘雨、彭蠡烟、广陵涛,奇观宇宙但赏何妨?我争者人必争,极力争未必得。我让者人必让,极力让未必失。真放肆不在饮酒放荡,假矜持偏要慷慨激昂。万事留一线,江湖好相见。
如果,这本书您没看懂。
那么,再买一本。
郭德纲癸巳春于墨尔本也没有什么头绪,待了十几天就回去了。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在民族宫大戏院看演出,之后从戏院出来,晚上十一点多顺着长安街由西往东走,一直走到了前门大栅栏。当时我还穿着双很新的鞋,不适合步行,脚后跟都磨破了,一步都走不了,干脆把鞋跟都踩塌了接着走。终于走到一个小旅馆,在那儿住下来,一晚上十八块钱。那旅馆的屋很破,屋里面还有树,就跟贫嘴张大民家的树似的。里面住着的几个人都是小商贩,有很刺鼻的一股脚臭味儿。
我在那儿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就买了张票回天津了。第二次进北京,也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到北京大概是1995年,一直熬到今天。
当时进北京的时候很急功近利,要当大腕儿,想一场挣好多钱,发财。只不过来了之后,现实把我敲醒了。
数载浮游客燕京,遥望桑梓衣未荣。
苦海难寻慈悲岸,穷穴埋没大英雄。
郭德纲,你记住了刚到北京的时候,住在青塔,很偏僻,在河边的一间小平房。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那时候写东西就是拿一马扎坐在床边趴着写。那时候觉得大的幸福就是有一张桌子。后来住过北京的很多地方,海淀、通州、大兴……哪里便宜就去哪里,经常没钱交房租。
有一段时间住在通县北杨洼的一个小区,交不起房租,房东在外边咣咣砸门,连踢门带骂街,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声。
那时候,我自制了一种能顶饿的食谱:到市场买一捆大葱,再买点儿挂面,然后用锅烧点儿水煮面,等面条都煮烂了,成了一锅糊糊了,再往里面放点儿大酱,这就做完了。以后每天把这锅糊糊热一热,拿葱就着吃。我挺乐:不仅吃到了维生素——大葱,也补充了碳水化合物——面条。
那时候,在蒲黄榆有个小评剧团,剧场能坐四五十人,舞台也就两张席梦思床那么大,我去了,答应一个月给我一千块钱。唱了俩月,一分钱没给。这时候你要是不唱了,这钱就拿不回来了。当时,我住在大兴黄村,骑个破自行车,车胎上有个眼儿,舍不得补,这一趟打三回气才能坚持到。后来没法骑了,就坐公共汽车。终于有一天,散了夜戏之后没有公交车了,只能走着回家。路过西红门,当时没有高速路,都是大桥,桥底下漆黑一片,只好走桥上面。桥上面走大车,我只能走旁边的马路牙子,不到一尺宽。我扶着栏杆,借着车的光亮往前走,身边是一辆接着一辆的大车呼啸而过。站在桥上,抬头一看,几点寒星,残月高悬。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坎坷和艰辛,我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哗哗的,一边哭一边给自己打气:“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在北京吃苦多年,我从来没哭过,这是仅有的一次。那时候,看不见光明,也不能回家,前途一片渺茫。
当时我就想,郭德纲,你记住了,今天的一切是你永远的资本,你必须成功。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瓦片尚有翻身日,何况我郭德纲呢。我这个人耳朵根子硬,多少次身临险境,多少次一点儿辙都没有,我都咬牙挺过来了。所以到今天,除了我自己,谁也害不了我。
从小茶馆到德云社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某电视台录制一个节目,摄影师跟我说:“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他说:“相声要死了你承认不?,”我说:“我不承认啊!”他说:“你证明给我看。”我说:“我证明不了给你看。但凡有能力,还来做综艺节目啊?”那时候我也很纳闷,怎么办呢?难道这门艺术真的就没有人愿意听了吗?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路过南城的一个茶馆,看见一帮孩子在茶馆里说相声,说着玩儿。我坐在那要了一壶茶,太感慨了。我是奔着这个来的,从小学的也是相声,现如今我因为相声困在北京了。看见他们说相声,心里不是滋味。总去听很快就熟悉了,聊天的时候他们问我是干吗的,我说我也是说相声的,他们就让我也说一段。说了一段,打那儿起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其实那茶馆也不挣钱,在墙上贴了一张纸,听相声、听评书两块钱一位。那段时间,对我后来把相声带回剧场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刚回到剧场的时候,观众不熟悉,我就立了一个规矩,只来一位观众也得说。有一天,能容两三百人的剧场真的只来了一位观众,开场的老先生叫邢文昭,刘宝瑞先生的亲传弟子,说一个单口相声,台上一个人台下一个人。说到半截,台下的观众手机响了,老先生停下来看着他不说话,他也不好意思,接起来说两句就挂了,继续听老先生说相声。到我上场的时候,我指着他说,你要好好听相声,上厕所必须跟我打招呼,今天动起手来你跑不了,我后台人比你多。他哈哈大笑。今天说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但那时是一件很心酸的事情。
在广德楼演出,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大栅栏里连条狗都没有。下午场散了,卖了十几张票,把票钱拿过来,我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钱放到一块儿,给大伙买盒饭。吃完盒饭,一起拿着竹板站在门口,呱唧,呱唧,呱唧,听相声了。顶着风,顶着雪,站在那儿喊,拉观众。真的有一两个人进来了,赶紧有人往后台跑,穿大褂上台说相声。我愿意干这个,所以,我不觉得苦。我也想找别人跟我一块儿干。但是谁会跟我一块儿干呢,这是一个不赚钱的事情。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来了两天就走了,有人因为不赚钱半途退出了,但是也有人坚持了下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走了穿红的来了挂绿的。
从1995年开始我就在茶馆里说相声,可称任重道远。我们的宗旨就是:相声必须先继承传统,然后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作。其实传统相声没有一天不在创新,可我们的很多演员无知,觉得传统相声很陈旧,不值得一用。事实是,从清末到现在,老先生们已经把中国语言中能够构成包袱、构成笑料的技巧都提炼出来了,现在无论多新的相声,包袱也都是旧相声里有的,只不过他们不承认。所以我们先继承,再发展,两条腿走路。
相声回剧场还是很舒服的,很火,好多节目都伸得开腰。这条路一走就是十几年,当初我不知道今天会这么火爆,当初也没有想过坚持下来会怎么怎么样,就是一条道走到黑,小车不倒只管推。刚回剧场,那时候有人看就好,当然也有火爆的时候,五六十人,那就了不得了。不像现在,场场爆满。剧场里面坐六百人,外面还有二百人在等着。
三五十人坐在下面听你说相声是件很享受的事情,那时候我就没指着说相声挣钱,就是想尽一个相声演员的良心和责任。我能多拉拢一位观众是一位,能多抢救一个活儿就是一个。当时就抱着这目的。能走到今天说明我们的道路是选对了,说明这十多年来我们的功夫没有白下。
从2006年春节开始,不断有专家出来表态,郭德纲即将过气。有人说我2月份就会下去了,后来又改口说4月份,接着又说是劳动节,没几天又表态说儿童节就差不多了。北大的一位教授咬牙切齿地说:“郭德纲就是一个泡沫,没几天就完了。”听说他算出来的日子是当年的8月份。
当年,相声界普遍认为,我应该在国庆节左右就灭亡了。他们没想到的是,我一路走来,越来越好。那年,我们搞了一个北京德云社十周年大型庆典活动,无论在电视台的收视率还是现场的卖票情况,都非常不错,我辜负了他们的期望。2006年春节,无数媒体的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了郭德纲。我必须承认媒体的力量,但是我想说的是,单凭媒体的力量也不能让那么多人那么长时间喜欢我的作品。因为在我的背后,其实是“传统文化”四个字支撑着我一路走来。
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回头看我得感谢那段岁月。想当初是真没辙啊,孤身一人流落京城,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穷过,苦过,受过罪,挨过饿。
穷人站在十字街头耍十把钢钩,钩不着亲人骨肉;有钱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枪棍棒,打不散无义宾朋。英雄至此,未必英雄。大英雄手中枪翻江倒海,抵挡不住饥寒穷三个字。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又何况一帮说相声的呢?一步一步地苦熬苦掖,终于我们也看见了花团锦簇,我们也知道了灯彩佳话。
那一夜,我也曾梦见百万雄兵。我没有破坏江湖规矩
2010年,德云社出了一点儿小小的状况,让同行们乐得都不行了。北京的同行借钱买韭菜包饺子,天津同行包苣荬菜饺子。
其实,从德云社创办至今,大部分同行都希望我们毁掉。北京相声界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段话:“在郭德纲之前,我们可以很安静地安乐死,可以很舒服地混到死,但是他出现之后,打乱了我们的正常生活,我们在台上再说十分钟的相声,观众不认可,他让观众知道了什么是相声,我们怎么办?”我们在2005年刚火起来的时候,相声界甚至有人希望组织一次游行,建议有关方面封杀我们。这一切只是因为我触动了某个利益集团。经过十年浩劫,我们很多老艺人都去世了,相声的传授断档了。我曾经统计过,我们百分之八十五的相声艺人在三十岁之前都是从事其他行业的,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转到这个行业来的。他们表演个节目、录个晚会没有问题,但和卖票演出是两回事,那个需要真东西。“演出不要超过十二分钟”本是相声界的共识,但我们的出现把这一切打破了。
其实,我没有破坏江湖规矩,只是当初人们成批破坏的时候没有人提出来。这好比有一帮人开车在一条大路上走,这时候来了批人把司机打跑了,然后把车开到麦田里了,在里面开了三十年,我只不过又把车开回到大路上而已。
……
前言/序言
自序:人在江湖
要出书了。
有人说要出书先出事儿。我也没出事儿,倒是把书出了。
我在私底下是一个特别无趣、乏味的人,喜欢待在书房里写字、听戏、看书,没有别的爱好,不抽烟,不喝酒,当然,也不喜欢烫头。
如果我不做艺人,大的愿望是做文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和黄金屋我都没遇到,但我依然爱看书,也爱写字。几张纸,一支笔,将心中事写下来,我觉得很快乐。
回头翻看这些文字的时候,也许这些事情都已经显得不再重要了,但是我很感慨,从中能看到我这些年的心路历程。人在天涯,身不由己,风雨踏歌行。江湖子弟,拿得起来放得下。放不下,也得放。活一百岁的没几个人,开心就笑,不开心待会儿再笑。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一辈子,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首先,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系统写作的人生自传,仅仅是把我这些年写的文章整理出版。这些文章记录了我这些年的经历和心路历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心态。
大部分文章存于文档,唯有二十八篇录于博客。输密码登录,打开文件。尘封三载又逢天日,抚案追昔不胜悲凉。这些年经历了太多事儿,远远超出了一个艺人的负荷能力。品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观荣辱纷争、死走逃亡,自浊自清自安然。台上笑传千万,台下苦闷凄惶。
整理、分类、筛选、修改,反复校对,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在满足你们对我合理的好奇心的同时,还能存在一点点其他的价值,也许是阅读的快乐或者其他,但如果您希望能在我的书中获得高深的知识或者思想,我猜您只能失望而归,这是一本拒绝传递任何价值观的闲书,我还是说相声的草根艺人郭德纲。别人都说我们是草根。什么叫草根?其实草根很便宜,人参、灵芝、冬虫夏草,都是这些不上档次的东西,我们比不了人家大棚里的香椿芽、韭黄。
在这本书出版之际,我已经四十岁了。八岁从艺,至今已经三十多年。
最初书名叫《人在江湖》,后来我接受本书编辑的建议,换了一个书名,也就是你们看到的《过得刚好》。一路走来,各种坎坷,各种不顺和阻碍,终于我也看到了花团锦簇,也看到了灯彩佳话。那一夜,我也曾梦见百万雄兵。
万幸,我一直在做我喜欢的事情。现在的生活我很满意,就像你们看到的书名一样,过得刚好。如果说我还有什么追求和愿望的话,那就是我希望能说一辈子的相声,等到八十多岁还能跟于谦老师站在小茶馆的舞台给大家说相声。那时候,估计我的头发都掉光了,于老师的头发也白了,一脑袋的白毛,还烫头,跟喜羊羊似的。我不指望天塌地陷,地球都毁灭了,还有我的一段相声在宇宙间飘荡,那是扯臊。
功名富贵,人间惊见白首;诗酒琴书,世外喜逢青眼。巿争利朝争名,伶逐势恶逐威。且看沧海日、赤城霞、峨嵋雪、巫峡云、洞庭月、潇湘雨、彭蠡烟、广陵涛,奇观宇宙但赏何妨?我争者人必争,极力争未必得。我让者人必让,极力让未必失。真放肆不在饮酒放荡,假矜持偏要慷慨激昂。万事留一线,江湖好相见。
如果,这本书您没看懂。
那么,再买一本。
郭德纲
癸巳春于墨尔本
在线试读《过得刚好》鱼龙夜话
不惑但从今日始,韬光氍毹正当年。忍忍忍,难难难。身处池畔,自浊自清自安然。若不登高看,怎知海天蓝。人到用时仁义少,事无经过不知烦。静坐思过观花谢,三省吾身饮清泉。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偷笑钓鱼船。(三十九岁生日所作,虚岁四十,年届不惑,几句残言,聊以自勉。)
用户评价
《过得刚好》这本书,读来别有一番滋味。它不像那些严肃的传记那样,总是板着面孔讲道理,而是以一种轻松、幽默的语调,将郭德纲四十年的江湖路娓娓道来。书中的每一段文字,都仿佛凝聚了他的人生智慧和生活感悟。“人必争极力争未必得,我让者人必让极力让未必失”,这句话,更是点出了他为人处世的核心哲学。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我们常常被教育要寸土必争,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然而,郭德纲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有时候,“让”是一种更高级的智慧。他不是在宣扬消极避世,而是在提倡一种懂得取舍、审时度势的处世之道。书里没有空洞的说教,只有鲜活的案例,生动的故事。他将那些生活中的鸡毛蒜皮,那些人情世故,都描绘得淋漓尽致,让人读来不禁拍案叫绝。这本书,更像是一位老友在跟你促膝长谈,分享他的人生经验,让你在笑声中,体味人生的酸甜苦辣,感悟生活的真谛。它让我重新审视了“争”与“让”的意义,让我明白,人生最好的状态,或许就是“过得刚好”,不卑不亢,不骄不躁。
评分《过得刚好》这本书,光是书名就充满了郭德纲式的智慧和幽默感,读起来简直是一种享受。这本书与其说是传记,不如说是郭德纲这位说书人的“人生讲堂”。他用一种极其接地气的方式,将自己四十年来的江湖风云娓娓道来。其中最让我触动的,莫过于他对“争”与“让”的深刻体悟。“人必争极力争未必得,我让者人必让极力让未必失”,这句话简直是点醒梦中人。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总是被教导要拼尽全力去争取,去赢过别人。但郭德纲却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有时候,“不争”反而是一种更高的境界。“让”不代表软弱,而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智慧,一种胸怀天地的气度。他讲述的那些恩怨情仇,那些起起伏伏,都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让人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看这本书,就像听一场精心策划的单口相声,笑声背后,是生活的百般滋味,是人生的跌宕起伏,是郭德纲那颗洞察世事的玲珑心。他没有矫揉造作,没有故作高深,只是坦诚地分享,真挚地感悟,让读者在捧腹大笑的同时,也能从中汲取人生的养分,找到属于自己的“刚好”之道。这本书,绝对是那些对人生有思考,对世事有洞察的读者不容错过的佳作。
评分作为一名读者,我一直对那些能够用文字传递生活智慧的书籍情有独钟,《过得刚好》这本书无疑就是其中之一。郭德纲用他特有的幽默和睿智,为我们展现了他四十年跌宕起伏的江湖人生。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关于“争”与“让”的论述。“人必争极力争未必得,我让者人必让极力让未必失”,这句话,仿佛是他从多年的江湖历练中提炼出的金玉良言。它不是教导我们要放弃,而是让我们懂得,在人生的赛道上,有时候适度的“让”,反而能为自己赢得更大的空间和更远的未来。他讲述的那些关于事业、关于人际、关于成长的故事,都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人生的哲理。读这本书,就像在与一位经验丰富的人生导师对话,他的话语朴实无华,却字字珠玑。他没有故作深沉,也没有刻意渲染,只是用最真实的情感,去剖析自己的人生,去感悟世间的百态。这本书,不仅是一部传记,更是一本关于人生选择的智慧指南,它会让你在捧腹大笑之余,对人生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刚好”节奏。
评分《过得刚好》这本书,读起来有一种亲切感,仿佛郭德纲就坐在你身边,用他那标志性的嗓音,给你讲他这些年的故事。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他对人生哲学,尤其是“争”与“让”的独到见解。“人必争极力争未必得,我让者人必让极力让未必失”,这句话,简直是他多年混迹江湖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们这些普通人的一种人生启示。在这个强调竞争的时代,我们似乎都被灌输了“不争就是落后”的观念。但郭德纲却用一种更辩证、更具智慧的方式,告诉我们,“让”并不意味着失败,而是一种更高明的策略,一种成熟的心态。他将自己一路走来的坎坷与辉煌,都以一种接地气的方式呈现出来,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也没有故作高深。读他的文字,就像品一杯陈年的老酒,越品越有味。他讲述的那些关于相声的梦想,关于人生的起伏,关于世事的变迁,都充满了人生的智慧和生活的热情。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郭德纲,一个懂得在纷繁复杂的江湖中,找到自己“刚好”位置的智者。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人生哲学的深刻探讨。
评分拿到《过得刚好》这本书,我第一眼就被它独特的封面设计和书名吸引了。郭德纲,这个名字本身就自带流量和话题,而他笔下的“四十年江湖过往”,更是让人充满了好奇。翻开书页,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浓浓的京味儿,仿佛能听到他在耳边低语,诉说那些关于梦想、关于坚持、关于成长的故事。这本书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生涩的理论,全是用最朴实、最真诚的语言,描绘了他从一个普通人,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的轨迹。尤其在关于“争”与“让”的哲学探讨上,他用自己独特的视角,颠覆了许多人固有的观念。“人必争极力争未必得,我让者人必让极力让未必失”,这句话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许多人在迷茫中前行的道路。他讲述的那些关于同行、关于观众、关于生活中的种种际遇,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读这本书,不仅仅是在了解一个相声演员的生平,更是在学习一种处世哲学,一种面对人生风雨的豁达态度。它让我明白,人生并非只有向前冲刺这一种方式,有时候,放慢脚步,学会“让”,反而能收获意想不到的风景。这本书,绝对是值得反复品读的,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感悟和启发。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