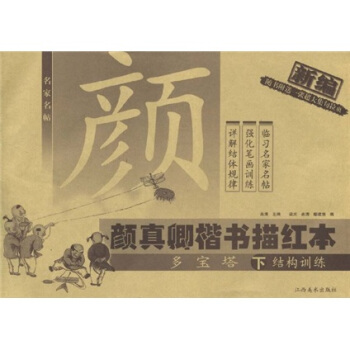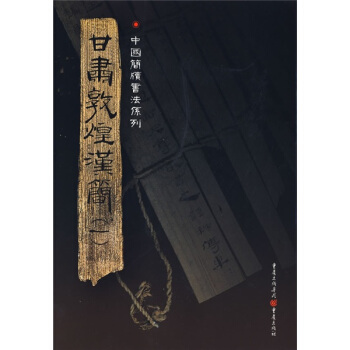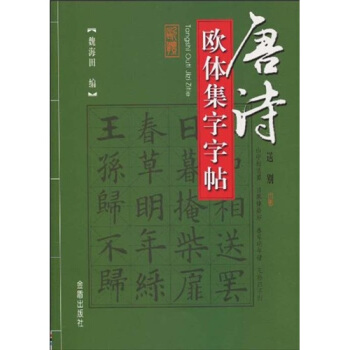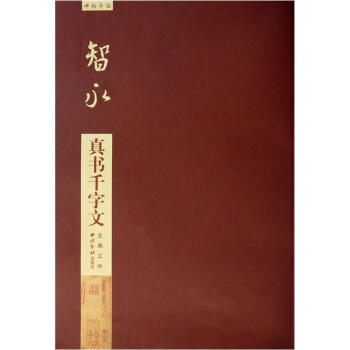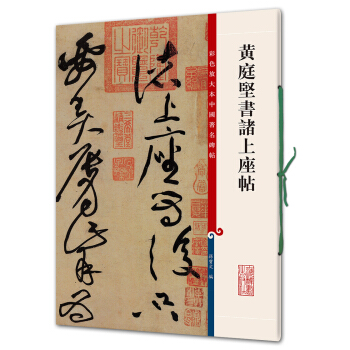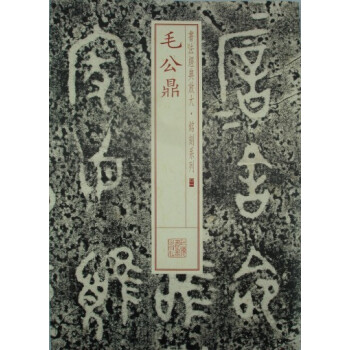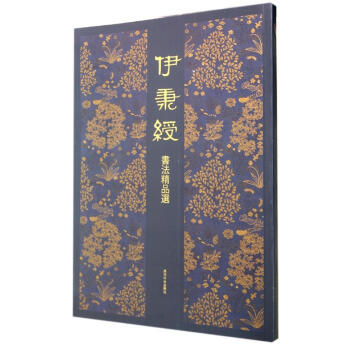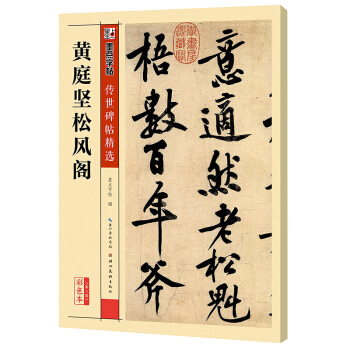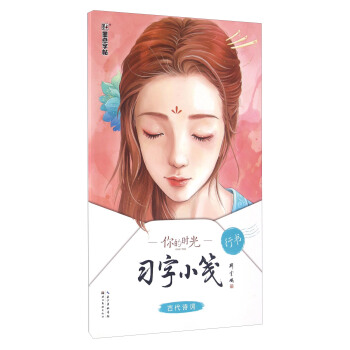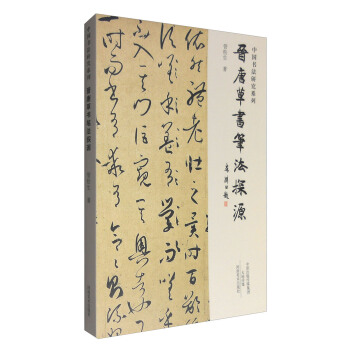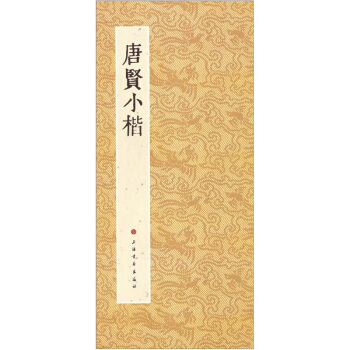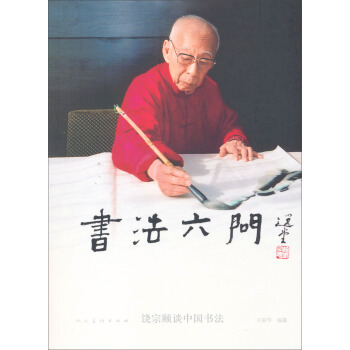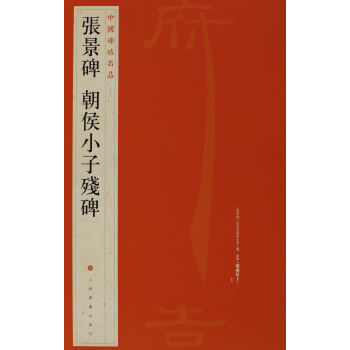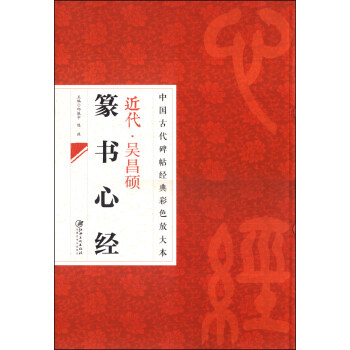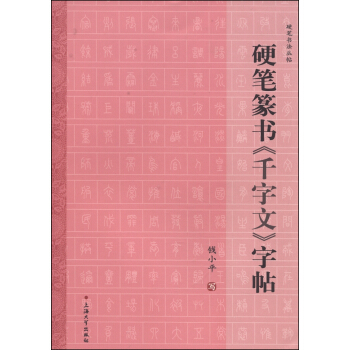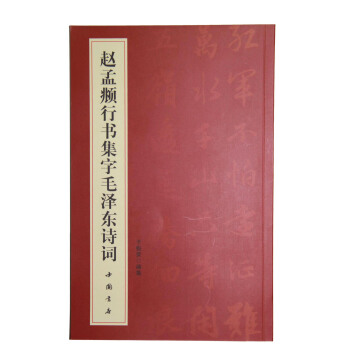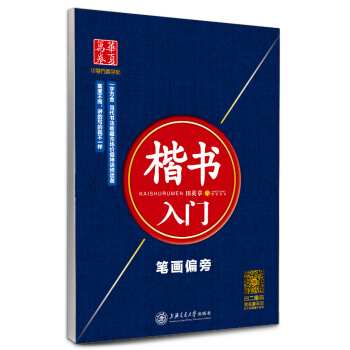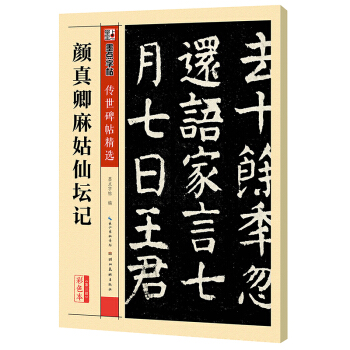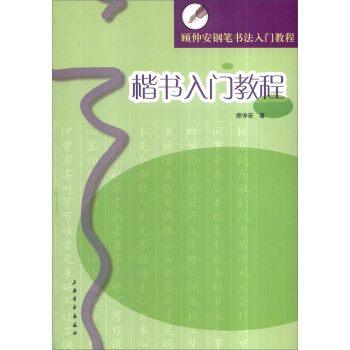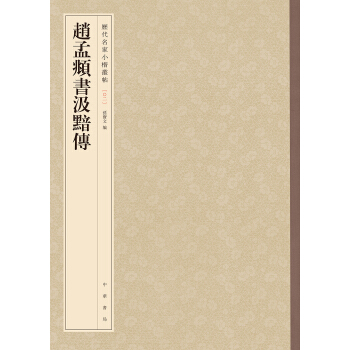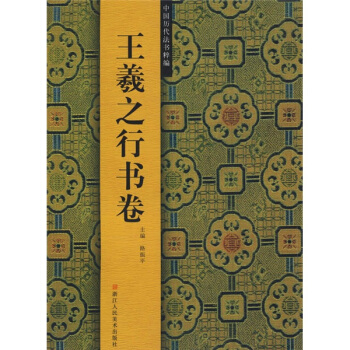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王羲之生于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卒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后迁居会稽(今浙江绍兴)。曾历任秘书郎、临川太守、江州刺史、宁远将军、会稽内史、右军将军,所以后世又称其为“王右军”。少年时的王羲之讷于言而敏于行,非常聪慧,长大以后却能言善辩,对书画悟性甚高,且性格耿直,不流尘俗。
王羲之出身于名门望族,书画世家。其父亲与伯父均为当时赫赫有名的书法家。王羲之从小就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卫夫人。卫夫人名铄,字茂漪,为西晋书法家卫桓的侄女,汝阳太守李矩的妻子。卫氏四世善书,家学渊源,尤善钟繇的隶书。王羲之跟她学习,自然受她的熏陶,一遵钟法,姿媚习尚,自然难免。后来,王羲之出游名山大川,见到了李斯、曹喜、张芝、梁鹄、钟繇、蔡邕的书迹,一改本师,剖析张芝的草书,增损钟繇的隶书,并把平生博览所得的秦砖汉瓦中各种不同的笔法,悉数融入到行草中去,推陈出新,熔古铸今,遂创造出他那个时代的最佳书体,亦即王体行书,当时就受到人们的推崇。后来他被人们尊称为“书圣”。王体书道逸劲健,千变万化,尤其晚年行书炉火纯青,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梁武帝称其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
王羲之一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书法作品。据《二王书录》记载: “二王书大凡一万五千纸。”但自恒玄失败,萧梁亡国,王羲之行书或失于战乱,或毁于水火,到了唐朝已所剩无几。后来,由于朝代更迭,沧桑巨变,王羲之的书法真迹至现在早已灰飞烟灭,只能从摹本、法帖及碑刻中寻求消息了。由于篇幅所限,本书选录其《冯承素摹兰亭集序》《虞世南临兰亭集序》《褚遂良临兰亭集序》《赵孟频临兰亭集序》《丧乱帖》《远宦帖》《初月帖》 《姨母帖》《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快雪时晴帖》《二谢帖》《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忧悬帖》《寒切帖》《游目帖》《上虞帖》及《雨后帖》。
内页插图
前言/序言
王羲之生于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卒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后迁居会稽(今浙江绍兴)。曾历任秘书郎、临川太守、江州刺史、宁远将军、会稽内史、右军将军,所以后世又称其为“王右军”。少年时的王羲之讷于言而敏于行,非常聪慧,长大以后却能言善辩,对书画悟性甚高,且性格耿直,不流尘俗。
《冯承素摹兰亭集序》,唐摹本,纵24.5厘米,横69.9厘米,28行,计324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兰亭集序》是主羲之于晋永和九年(353年)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与友人聚会时所写的文稿。唐太宗千方百计得到了它,让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临摹以赐群臣,真迹则带进昭陵成陪葬品。《冯承素摹兰亭集序》即冯承素的摹本,因钤有“神龙”鉴藏印,故又称《兰亭集序神龙本》,最接近真迹。尤其是帖中20个“之”字别具恣态,无一雷同,其章法笔意顾盼,朝向偃仰,气韵生动,风神潇洒,被尊为“天下第一行书”。
用户评价
翻开这套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那种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和艺术的纯粹性。它摒弃了花里胡哨的装帧,用最朴素却最考究的方式呈现了这些中华瑰宝。那些宋代的楷书大家,他们的笔法结构之严谨,结体之欹侧有度,在这套书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我花了大量时间去对比不同时期大家在行草书中的过渡和融合,这本书恰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比如,对某位大家晚年笔法的“放逸”程度,书中通过并置不同时期的作品,清晰地展示了其心境的变化是如何映射到纸面上的。这种对比研究的方法,远比单纯看一本单人作品集要来得深刻。而且,它的装帧设计也很有讲究,大开本的尺寸保证了细节的清晰度,即便是微小的墨迹飞白,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这对临帖时的观察至关重要。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已经成了我书房里最高频使用的工具书之一,它让我对“法度”和“性情”的辩证统一有了更深的理解。
评分说实话,市场上充斥着大量质量参差不齐的书法字帖,很多都是粗制滥造的电脑描摹版,完全失去了原作的神韵。直到我接触到这套法书粹编,才算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尊重经典”。这套书在选材上的严谨和对原件的忠实度,是其他同类书籍难以企及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残破或难以辨认的古代墨迹,编者团队通过多方比对、甚至引入了拓片作为辅助参照,力求还原其最接近原貌的状态。这对于我们学习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我们不能对着一个被误读的版本去练习。书中对某些特定字体风格的梳理脉络清晰,比如对某一时期“今草”的演变,它通过不同地域、不同书家的作品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分析,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这种体系化的整理,极大地提高了我的学习效率,让我不再盲目地东学西看,而是能找到一条清晰的学习路径。
评分这套书带来的震撼是多层次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更是对中国书写精神的一种再确认。我尤其欣赏其中对“神韵”的捕捉。很多时候,一个字写得好不好,关键在于那一瞬间的“气”是否贯通。这套书中的高清晰度摹本,捕捉到了这种“气”的流动。例如,在欣赏那些狂放不入流的书作时,你甚至能感受到纸张被笔锋“刮擦”的粗粝感和墨汁洇开的层次变化。编者们在附注中对某些技巧的解读也极其到位,他们没有停留在表面,而是探讨了比如“腕法如何配合呼吸节奏”这样深层次的问题。这让我意识到,书法是身体与心灵的统一运动。读这套书的过程,与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一种浸入式的文化体验。它让你谦卑下来,去敬畏古人的智慧,同时也激发了自己对追求极致艺术境界的热情,是近些年来我收藏中分量最重的一部艺术著作。
评分这套《中国历代法书粹编》着实让人惊艳,尤其是收录的那些唐宋大家墨迹,简直是书法学习者案头必备的宝典。光是看到那些摹本和影印件的清晰度,就让人心潮澎湃。不同于市面上那些仅仅罗列字帖的普通书籍,这套书在释文和考证上下了很大功夫,对于每一个碑帖的流传和版本差异都有深入的探讨,这对于我们理解古代书法的流变脉络至关重要。尤其是对那些流传有争议的作品,作者们往往能提出独到的见解,令人信服。我特别喜欢它对章法和用笔的细致分析,不再是简单地描述“起笔顿挫有力”,而是深入到笔毫的提按变化中去,让你仿佛能触摸到古人运笔时的气息。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本书可能略显深奥,但对于有一定基础,想要精进技艺的书家而言,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一座座金矿,值得反复摩挲,细细品味。它不仅仅是一部书法作品的汇编,更是一部中国书法史的活化石,让人深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厚重与魅力。
评分我一直觉得,要真正学好中国传统艺术,就得沉下心来研究“源头活水”。这套法书汇编,完美地满足了我的需求。它不仅仅收录了那些耳熟能详的“榜书”,更挖掘整理了许多散见于各处、但艺术价值极高的碑帖和手札。比如,其中对某些魏晋尺牍的整理和考证,简直是下了苦功的,连纸张的纤维纹理似乎都能通过影印件感受得到。这种对“原貌”的尊重,是很多现代出版物所缺乏的。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能与古人隔空对话,体会他们写信时的心境——那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风骨和雅致,是刻意模仿不出来的。这本书的排版也十分科学,它会根据作品的特点进行巧妙布局,使得读者在欣赏单个作品的同时,也能顾及到整体的篇章气韵。它让我明白,书法的美,绝不仅仅在于一笔一画的技巧,更在于其背后蕴含的文化修养和生命体验,这套书在这方面做得极为出色,让人受益匪浅。
评分字迹模糊,一点都不清晰,简直没法写
评分书不错值得收藏、应该是正版
评分历代法书粹编:王羲之行书卷
评分感觉还行吧………………………
评分快递小哥非常好,书也很好
评分非常好!
评分收录了多个墨迹版的兰亭序,但是彩印的分辨率依然不足
评分好
评分中国古代经典,学习中国文化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