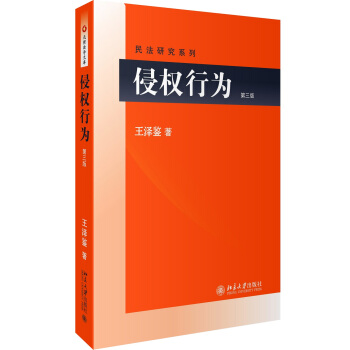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较其他版本的两大特色:一是考虑到刑事诉讼法条文很长,特将篇章等详细目录在总目录中体现出来,方便读者找到相关条文;二是全文收录全国人大关于本法修订的草案说明。内容简介
此次修正涉及内容一百多处,主要表现在:一、完善证据制度。原有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比较原则,修正案对此主要作出以下补充:1.完善证据种类和证明标准。2.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3.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4.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二、完善强制措施。由于犯罪情况日趋复杂,执法环境有所变化,现行关于强制措施的有些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修正案对此主要作出以下补充:1.完善逮捕条件。2.完善审查逮捕程序。3.完善监视居住措施。4.适当延长拘传时间。
三、完善辩护制度。为进一步完善辩护制度,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强化法律援助,修正案对此主要作出以下补充:1.规定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2.完善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3.完善律师阅卷的相关规定。4.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四、完善侦查措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情况的变化,一方面,要完善侦查措施,赋予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防止滥用,修正案对此主要作出以下补充:1.明确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2.完善侦查监督规定。
五、完善审判程序。为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有必要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区别案件的不同情况,进一步完善审判程序,修正案对此主要作出以下补充:1.调整简易程序适用范围。2.完善一审、第二审程序。3.完善死刑复核程序。
六、完善执行规定:1.完善暂予监外执行规定。2.加强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3.增加社区矫正规定。
七、规定特别程序:1.设置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2.规定特定范围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3.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4.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任务和基本原则
第二章 管辖
第三章 回避
第四章 辩护与代理
第五章 证据
第六章 强制措施
第七章 附带民事诉讼
第八章 期间、送达
第九章 其他规定
第二编 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
第一章 立案
第二章 侦查
第三章 提起公诉
第三编 审判
第一章 审判组织
第二章 第一审程序
第三章 第二审程序
第四章 死刑复核程序
第五章 审判监督程序
第四编 执行
第五编 特别程序
第一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章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三章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四章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附则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精彩书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编 总 则
第一章 任务和基本原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三条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四条 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
第五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六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第七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九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第十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第十二条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本法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
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十六条 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
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七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
第二章 管 辖
第十八条 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第十九条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但是依照本法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除外。
第二十条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
(一)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
(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
第二十一条 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第二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第二十三条 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下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
第二十四条 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五条 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
第二十六条 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第二十七条 专门人民法院案件的管辖另行规定。
第三章 回 避
第二十八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第二十九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第三十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院长的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检察长和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
对侦查人员的回避作出决定前,侦查人员不能停止对案件的侦查。
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第三十一条 本章关于回避的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
第四章 辩护与代理
第三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
(一)律师;
(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
第三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
第三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三十五条 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第三十六条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第三十七条 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
第三十八条 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第三十九条 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
第四十条 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第四十一条 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第四十二条 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辩护人是律师的,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第四十三条 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
第四十四条 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代理人。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第四十五条 委托诉讼代理人,参照本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 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
第四十七条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最新修订)》这本书,我必须说,它是一部真正“有用”的法律书籍。我是一名社会学研究者,一直对中国的司法体系及其社会影响非常感兴趣。我一直认为,要真正理解一个国家的法律,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条文层面,更要深入了解其背后的社会逻辑和实践操作。这本书恰恰满足了我的这一需求。它不仅仅罗列了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展现了这些条文是如何在现实社会中被解读、被适用、被执行的。例如,书中关于“刑事和解”的章节,我读到了很多关于犯罪受害者、加害者以及社会各方如何在法律框架内达成和解的生动故事,这让我看到了法律在化解社会矛盾、修复社会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此外,书中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案件的处理方式的差异性描述,也让我得以窥见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让我看到了法律在制度设计上的理性,也看到了在实际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这本书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洞见,让我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社会意义和实践价值。
评分刚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最新修订)》这本书,我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作为一名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基层工作者,我每天都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法律咨询和案件。虽然我并非科班出身,但多年来在实践中的摸爬滚打,让我对法律条文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本书的出现,无疑是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书中对不同程序阶段的规定,如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解释。我尤其关注的是关于辩护权保障的部分,书中列举了大量的实际案例,清晰地说明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不同阶段享有的权利,以及这些权利如何得到有效的行使。这对我日常工作中为受援人提供法律帮助至关重要。而且,书中对一些常见的法律误区和争议点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比如“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适用,以及“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这些都是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的难题。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有理论深度,又不失实践指导意义。这本书让我深刻认识到,刑事诉讼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堆砌,更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它让我更加有底气地去面对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复杂情况,也更加坚定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决心。
评分这本书简直是我近期阅读体验中最令人惊喜的一部作品!我是一名正在准备法考的学生,每天都在和海量的法律条文以及案例打交道,说实话,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迷茫。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最新修订)》这本书,就像一道清泉,让我重新燃起了学习的热情。它的内容编排非常合理,逻辑清晰,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到公诉机关的职责,再到法院的审判程序,每个环节都衔接得天衣无缝。我特别喜欢书中对“疑罪从无”原则的深入解读,它通过对几个经典案例的剖析,清晰地阐释了这一原则在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书中对各个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和相互配合的描述也极为详尽,这对于理解刑事诉讼的整体运作机制非常有帮助。更令我赞赏的是,作者在解释某些复杂的法律概念时,采用了类比和图示等多种方式,使得原本抽象的理论变得具体生动,极大地降低了理解门槛。我感觉这本书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引导,它教会我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整个刑事诉讼流程,以及在微观层面关注每一个细节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对于我这样要面对严峻法考挑战的学生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件利器,让我信心倍增。
评分我刚入手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最新修订)》,翻了几页就觉得如获至宝。作为一名对法律有着浓厚兴趣的普通市民,我一直觉得法律条文晦涩难懂,枯燥乏味。然而,这本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它不仅仅是一部法律文本,更像是一本生动详实的案例分析集。书中对每一个条文的解释都辅以了大量现实案例,这些案例都来自于真实发生过的案件,而且都经过了精心的筛选和提炼,能够非常直观地展现法律条文在实践中的应用。例如,在关于侦查措施的章节,作者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件,生动地展现了搜查、扣押、强制传唤等措施的合法界限和操作要点,让我深刻理解了这些程序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此外,书中的语言也力求通俗易懂,避免了过多专业术语的堆砌,即使是没有法律背景的读者,也能轻松理解。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编写方式,极大地提升了我的阅读体验和学习效果。我尤其欣赏书中对证据规则的详细阐述,它不仅仅列举了哪些证据是合法的,更重要的是解释了为什么这些证据是合法的,以及如何排除非法证据,这对于理解公正司法的核心至关重要。这本书让我感觉,法律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冰冷条文,而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充满人情味和正义感的实践指导。
评分我最近拿到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最新修订)》,说实话,一开始我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我一直觉得法律条文过于专业,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但这本书的出版,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它的内容极其丰富,而且叙述方式非常接地气。书中对刑事诉讼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从案件的立案到最终的判决,环环相扣,逻辑清晰。我尤其喜欢书中关于“侦查羁押”的章节,它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了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制度,以及它对公民自由的限制是如何被法律所规范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通过对比不同的司法实践,阐述了法律的进步性。它不仅介绍了最新的修订内容,还回顾了历史上的发展,让读者能够更清晰地看到法律是如何不断完善的。此外,书中还穿插了一些关于程序正义的讨论,比如如何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如何防止权力滥用等等,这些都让我觉得这部法律不仅是约束犯罪的工具,更是保护公民权利的盾牌。这本书让我感觉,法律离我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并且在努力地维护着我们的生活秩序和个人权益。
评分封面有点脏
评分多学法律知识,帮人家买的,
评分DJ电话费观后感
评分您对本次购物的总体满意度如何?
评分唯一好像纸张一般
评分简洁,方便。
评分东西很好用,质量和好很好
评分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
评分新法刚出,书籍就上市,速度真快。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塑造美国的88本书:联邦党人文集 [The Federalist Paper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352421/rBEhWVKUR1IIAAAAAAMV_rp4pfEAAF9JQO1Le0AAxYW30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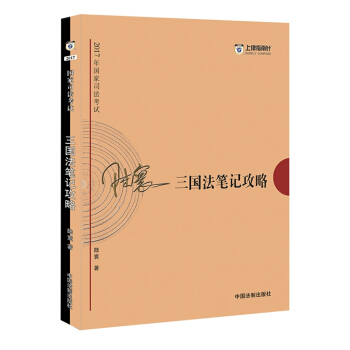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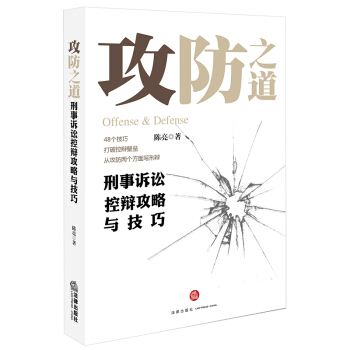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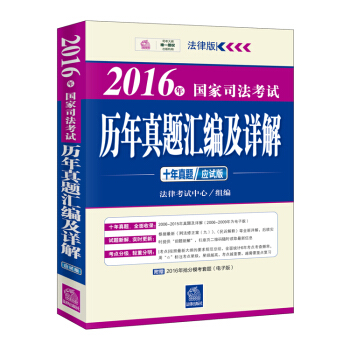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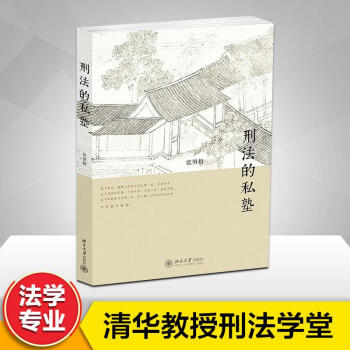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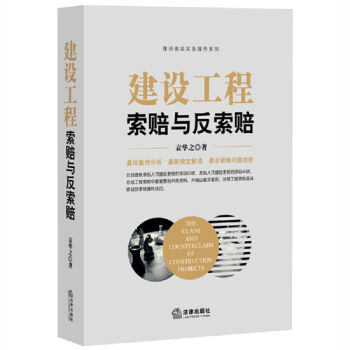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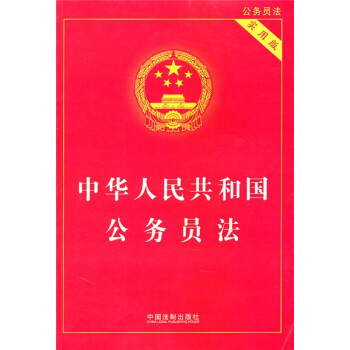
![与绝望抗争:寻求正义的3300个日夜 [なぜ君は絶望と闘えたのか: 本村洋の3300日]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21160/53eace6fN427ca83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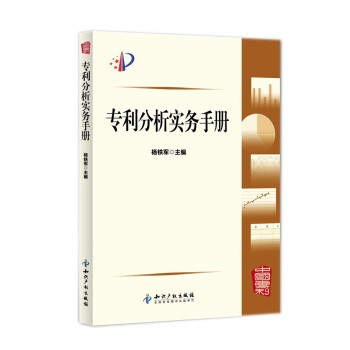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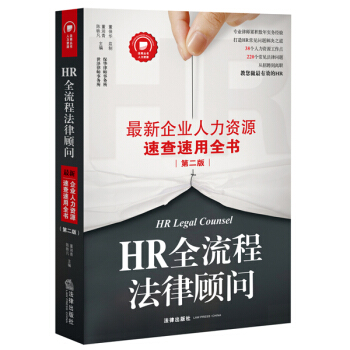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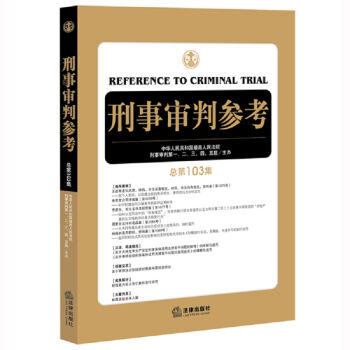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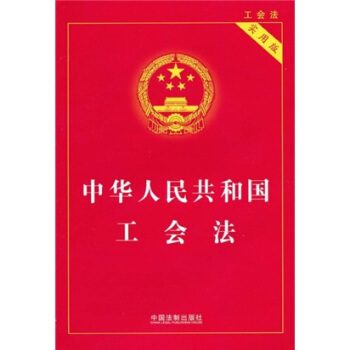
![西方学术经典译丛:法学讲演录(英汉对照)(全译本)(共4册)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161968/48090cf1-7c87-45b7-85e8-10d8ebb7cea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