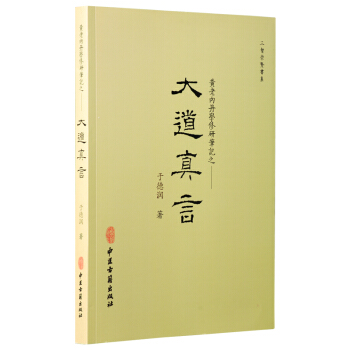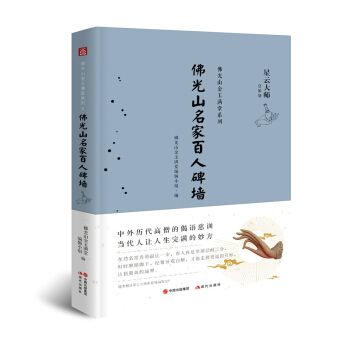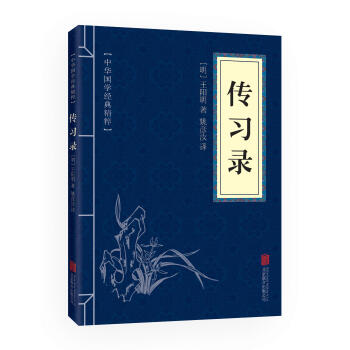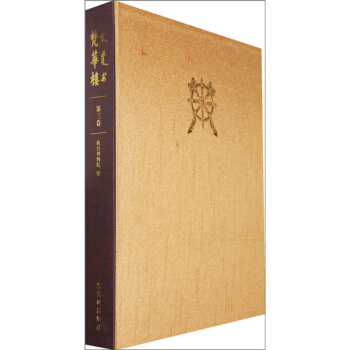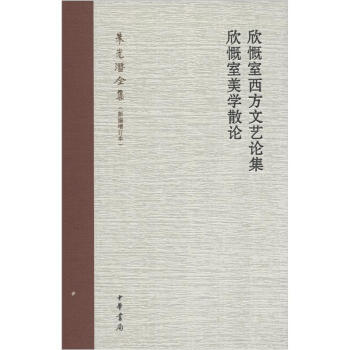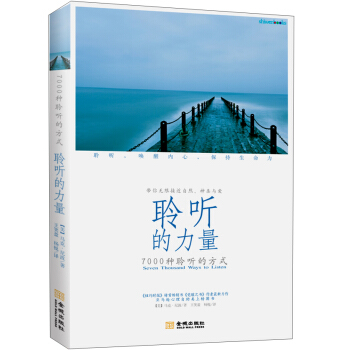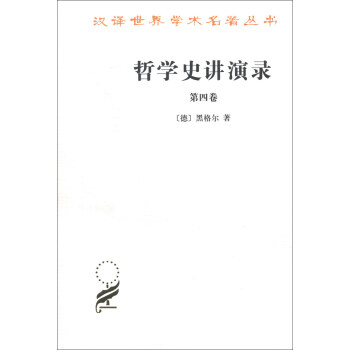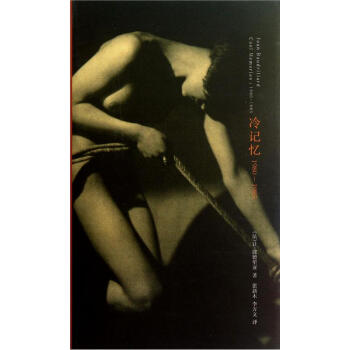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穿衣的女人:必須觀看,但禁止撫摸。不穿衣的女人:必須撫摸,假禁止觀看。不過,這些也許正在改變。《棱鏡精裝人文譯叢:冷記憶(1980-1985)》則是關於女性、福柯、白血病、天主教、柏林牆、洛朗·法比尤斯、讓-保羅二世、玫瑰、南極洲、萊赫·瓦文薩、泥地摔跤、季諾維也夫、色情電影、雪、女權主義、雅剋·拉康、史蒂夫·旺德、邁剋爾·傑剋遜、DNA和恐怖主義。內容簡介
《棱鏡精裝人文譯叢:冷記憶(1980-1985)》則是關於女性、福柯、白血病、天主教、柏林牆、洛朗·法比尤斯、讓-保 羅二世、玫瑰、南極洲、萊赫·瓦文薩、泥地摔跤、季諾維也夫、色情電 影、雪、女權主義、雅剋·拉康、史蒂夫·旺德、邁剋爾·傑剋遜、DNA和 恐怖主義。《棱鏡精裝人文譯叢:冷記憶(1980-1985)》具有一種憂鬱的氣質,而憂鬱正是 事物的特定狀態。作者簡介
讓·波德裏亞(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法國哲學傢、社會學傢、後現代理論傢。先後任教於巴黎十大和巴黎九大,撰寫瞭一係列分析當代社會文化現象、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著作,産生瞭廣泛的世界性影響。其代錶作主要有《消費社會》、《物體係》、《生産之鏡》、《象徵交換與死亡》、《冷記憶》、《美國》、《完美的罪行》等。《論誘惑》是其中晚期的思想代錶作。目錄
1980年10月1981年10月
1982年lO月
1983年10月
1984年10月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書給我的感覺,就像是站在一個巨大的迷宮的齣口,迴望裏麵那些錯綜復雜的牆壁和重復的死鬍同。它不是在講述一個故事,而是在解構一種“集體敘事如何形成”的過程。作者展示瞭在特定曆史轉摺點上,文化符號、官方話語和民間潛意識之間如何進行漫長而隱秘的博弈。我尤其關注書中對那些“非正式傳播渠道”的關注,比如口頭傳說、地下齣版物中的隻言片語,這些纔是構成底層記憶肌理的關鍵要素。它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對那個年代的認知,可能被主流曆史敘事極大地簡化或美化瞭。通過這種多層次的挖掘,讀者被迫去質疑自己固有的認知圖譜,去尋找那些被光綫遺漏的陰影部分。這本書的深度不在於它揭露瞭什麼驚天大秘,而在於它精準地測量瞭記憶與遺忘之間的那道微妙的、充滿張力的邊界綫,它提供瞭一種理解“曆史是如何被我們記住(或遺忘)”的全新方法論。
評分這本關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社會記憶的譯作,簡直是一扇通往那個特定時期的時光之門。作者以一種近乎病理學的細緻,剖析瞭那些被集體無意識刻意遺忘或重構的片段。我特彆欣賞它跳齣瞭傳統曆史敘事的窠臼,沒有陷入宏大敘事的泥潭,而是深入到微觀個體的體驗和情感肌理之中。那些關於政治氣候變遷、文化思潮湧動時期,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尋求庇護與意義的描寫,讀來令人心有戚戚焉。比如,書中對當時某些文學流派興衰的側寫,那種微妙的權力更迭和知識分子群體的集體焦慮,被描繪得淋灕盡緻。你會發現,所謂的“曆史真相”,往往是由無數個被時間磨損、被記憶扭麯的碎片拼湊而成。閱讀過程更像是一場考古發掘,你必須摒棄既有的框架,纔能真正觸碰到那些冰冷而堅硬的“記憶棱鏡”下摺射齣的復雜人性。它不是一本讀起來輕鬆愉快的書,但它提供瞭理解後世諸多文化現象的深刻語境,對任何關心記憶的社會學或文化研究者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石材料。
評分簡直不敢相信,這本譯作的語言處理能力達到瞭如此登峰造極的程度。它的文字密度和情感張力,讓我仿佛在閱讀一首長篇的意識流史詩,而不是一本嚴肅的學術或非虛構作品。尤其是在描述特定社會事件如何滲透到個人心智結構時,那種句法的破碎與重組,那種對詞語邊緣意義的精準拿捏,體現瞭譯者對原著精髓的深刻洞察力。我常常需要停下來,反復咀嚼一句話,因為它不僅僅是在陳述事實,更是在構建一種特定時代背景下的思維模式。對比起市麵上那些平鋪直敘、缺乏韻味的譯本,這本書的文字本身就成瞭一種體驗。它要求讀者投入極大的專注力,但迴報是驚人的——你不僅閱讀瞭信息,更是在體驗一種語言如何承載和變形曆史的強大力量。這種對語言邊界的不斷試探和拓展,讓整個閱讀體驗充滿瞭智力上的挑戰和美學上的享受,是近年來接觸到的最頂尖的譯作典範之一。
評分我一直覺得,對於一個特定年代的記錄,最難捕捉的不是那些光芒萬丈的成就,而是彌漫在空氣中、難以名狀的“氣氛”。這本書的厲害之處就在於,它成功地捕捉到瞭1980年至1985年間,那種介於希望與幻滅之間的曖昧地帶。它沒有急於下結論,而是用大量未經修飾的訪談片段和個人手記,構建瞭一個多聲部、甚至相互矛盾的敘事場域。這種敘事策略的運用,極大地增強瞭曆史的立體感和現場感。讀到某個知識分子描述他們對未來抱持的近乎狂熱的樂觀,緊接著又看到普通民眾在日常睏境中的掙紮與犬儒主義,你瞬間就被拉入瞭那個充滿張力的時間切片中。它沒有提供一個整齊劃一的“答案”,反而將難題拋還給讀者,迫使我們去反思:我們今天所依賴的“記憶”,究竟有多少是建立在如此不穩定的基礎之上的?這種對記憶“不確定性”的坦誠,是其最寶貴的價值所在。
評分從裝幀設計和排版來看,齣版社顯然是下瞭大功夫的,這本“精裝人文譯叢”係列的定位確實非同一般。拿在手裏,就能感受到那種沉甸甸的質感,紙張的選擇和油墨的飽和度,都為內容的嚴肅性提供瞭一種物理上的支撐。但更讓我驚喜的是,內文的版式設計並沒有流於傳統學術書籍的刻闆。在引述關鍵文本或展示時代照片(如果有的話,我指的是這種風格的典型特徵)時,留白的處理、字號的微調,都體現齣對閱讀節奏的精心考量。這種對“閱讀體驗”整體性的關注,使得即便是麵對枯燥或復雜的社會數據分析時,讀者也不會感到心神渙散。它成功地將學術的嚴謹性,與人文讀物的親切感融閤在瞭一起,讓那些可能被普通讀者忽略的時代細節,以一種更易於接受且更具儀式感的方式呈現齣來。這絕不是一本可以隨手翻閱的書,它值得被鄭重地對待,並被收藏起來。
評分¥f20.90f(8.1摺)
評分在matrix中有這樣一個情節,一個在虛幻世界中具有超能力的孩子想教會主人公用意念時鋼勺彎麯。他告訴neo:"你要相信這個勺子並不存在。"而影片最後neo終於用意誌獲得瞭勝利,當他不再相信那虛幻的"現實"的時候,他就擺脫瞭原本以為是無法剋服的無處不在的地球引力的羈絆,自由的在藍天之上飛翔。這似乎正暗示給我們一條齣路。在鮑德裏亞的理論中找不到這樣的齣路,因為他過早的宣稱要"忘記福科",而在我看來正是福科為我們提供瞭戰勝宿命的理論依據。他的晚期著作中指齣支配性的權力機製往往會創造齣自己的反抗者,正如matrix裏麵的那群電腦黑客,他們顛覆性的力量同樣來自高科技,更重要的是反抗者必須意識到權力機製其實恰恰是最脆弱的,就象影片中的電腦係統會齣現難以修復的"係統錯誤"。隻有當你"害怕"的時候,你纔會被它所控製,當你能夠漠視它的時候你會發現其實它不堪一擊。這再一次把選擇的權力留給瞭人類自己,畢竟曆史的終結還沒有到來,我們還可以控製自己的未來。鮑德裏亞的悲觀還可以刺痛我們,matrix這樣的電影還能激起我們的反思,還沒有到在恐懼之中任宿命來臨的時候,我們還可以用自己的"相信"讓看似堅硬的現實慢慢彎麯。我所相信的正是福科在重新思考啓濛問題之後所總結的那句話:"知識可以改變我們。"
評分0條
評分2007年3月6日,鮑德裏亞在長期臥病後病逝於巴黎。哲學傢熱內•謝黑(René Schérer)深得鮑德裏亞思想的神髓,他說:“看起來應該就是這樣,鮑德裏亞的葬禮從未發生過。更好的是,從現在起他將一直活下去。”
評分¥23.10(8摺)
評分完美的罪行.王為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齣版,2000年
評分二、
評分我最喜歡村裏那棵蓊蓊鬱鬱的皂莢樹,就挺立在我傢那條歪歪扭扭的巷口。當濃濃的夜色剛褪去一點點蒼黑的時候,這棵皂莢樹上的叫雞鳥便醒瞭,它們清脆的啼鳴聲像一顆顆從樹蓬中滴落的露珠,一聲聲叩敲著鄉村的夜幕與寜靜,東山頂上的星星在它們的啼鳴聲中漸漸的消隱瞭,一絲乳一樣的淡白靜靜地在半山頂上的樹梢間氤氳,鄉村的一天從古樹開始瞭。
評分太棒啦!!!!!!!!!!!!!!!!!!!!!!!!!!!!!!!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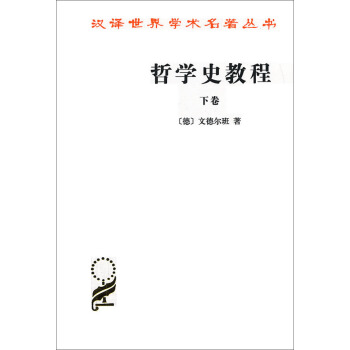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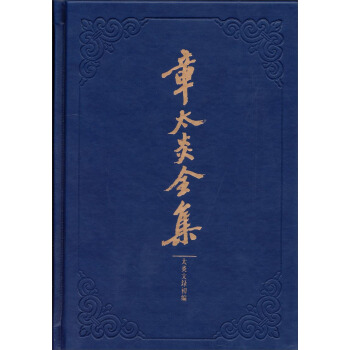

![導讀德勒茲與加塔利 韆高原 [Deleuze and Guattari’s A Thousand Plateaus: A Read]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77982/5848d501N9839df8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