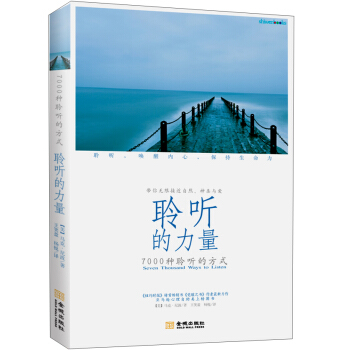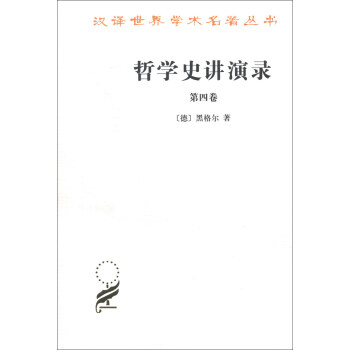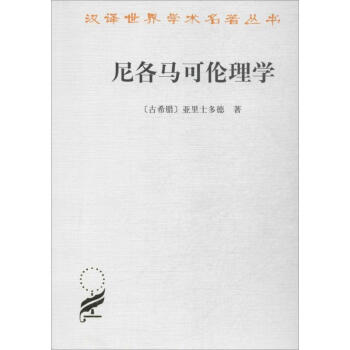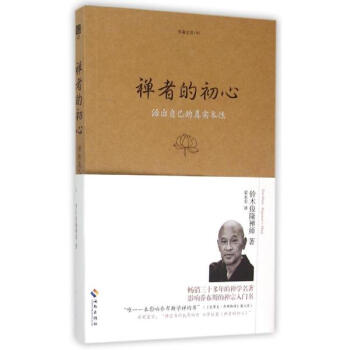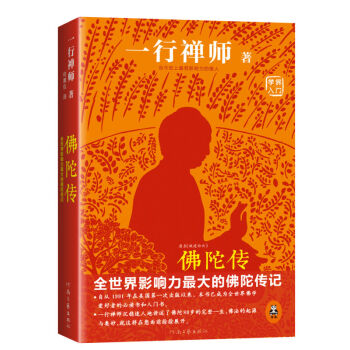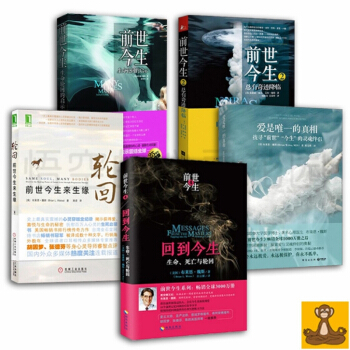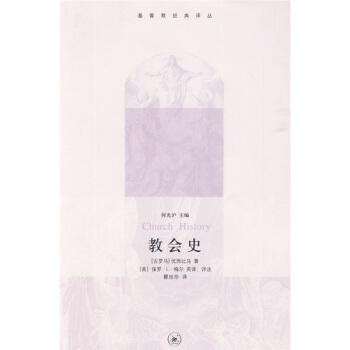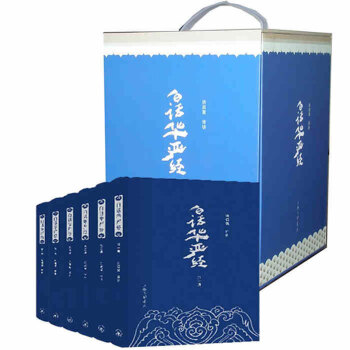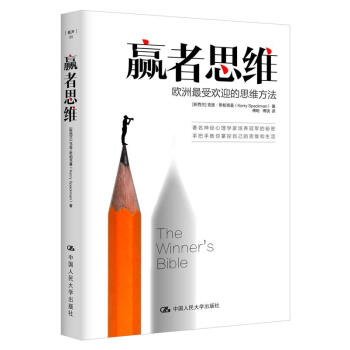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20世纪50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涎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至2011年已先后分十二辑印行名著500种。现继续编印第十三辑。到2012年出版至55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得更好。目录
绪言第一章 思考方案
二
1.在先的状态
2.教师
3.信徒 第二章 作为教师和救世主的上帝一一一个诗人的冒险
第三章 绝对的悖论一一一个形上学的奇想
附录 悖论的冒犯一一一种听觉的幻想 第四章 与主同时的信徒的处境
插曲
一、趋向实存
二、历史的
三、过去的
四、对过去的理解
附录:应用 第五章 再传的信徒
…… 跋
译者后记
用户评价
翻开这本书,我立刻感受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它更像是在与一位博学却不失幽默感的智者进行一场深夜的对谈。作者似乎有一种魔力,能够将最复杂、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形而上学问题,用一种近乎散文诗的轻盈姿态呈现出来。我特别钟爱那些关于“存在的偶然性”的探讨,它们不是枯燥的逻辑推演,而是充满了生命力的比喻。比如,他将宇宙的开端描述为一次“绝对美妙却又极其不负责任的抛硬币”,这个形象一下子就击中了我的心。它剥离了宏大叙事下的宿命感,赋予了个体选择以一种令人振奋的轻盈。整本书的节奏感把握得极好,时而急促,如同一串密集的追问;时而又舒缓下来,留出大片的留白,让读者有时间去消化那些突然出现的洞见。阅读过程中,我常常忍不住停下来,望着窗外沉思许久,回味刚才那句看似平淡却暗藏玄机的陈述。这本书的结构是开放的,它拒绝被简单归类,它既有哲学的严谨骨架,又披着文学的华丽外衣,甚至偶尔还闪烁着科学观察的锐利光芒。它不是让你去“学习”哲学,而是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更具反思精神的人。对于那些厌倦了教科书式哲学阐释的读者,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急需的、呼吸新鲜空气的出口。
评分这本新近出版的文集,实在是一场思想的漫游,让我这个习惯于结构化叙事的读者,体验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思维“野餐”。作者的笔触极为灵动,仿佛不是在构建宏大的哲学体系,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缝隙中,悄悄放置了几块闪光的卵石。我尤其欣赏其中探讨“时间感知的非线性”的那几篇。它们没有晦涩的术语,而是通过对一次等待日落的细致描摹,将我们习以为常的钟表时间观彻底瓦解。那种感觉,就像是突然从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上跳了下来,赤脚踩在了松软的泥土上,感官被瞬间放大了无数倍。书中的论述不是为了给出标准答案,更像是抛出了一系列极富挑衅性的问题,迫使你不得不停下来,审视自己是如何“度过”生命的。例如,有一段关于“遗忘的必要性”的论述,它没有引用任何古典哲学家的定义,而是从一个孩子丢失玩具的瞬间切入,细腻地揭示了记忆如何在过滤和重塑中,才使得我们能够继续前行。这使得那些原本高高在上的哲学命题,瞬间变得可以触摸,可以共情。对于那些渴望在纷繁的现代生活中寻找一点清醒的间隙的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剂良药,它让你慢下来,不是为了停滞,而是为了更清晰地看清自己正走向何方。它的价值,不在于它能提供什么明确的地图,而在于它能帮你校准内在的指南针。
评分坦白说,我通常对这种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思辨性作品持保留态度,因为它们很容易沦为作者的自言自语。然而,这本集子完全打破了我的偏见。它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它极其真诚地处理了“知识的局限性”这一主题。作者并没有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无所不知的导师形象,反而大量笔墨用在了对“我不知道”的边界进行探索和赞美。书中有一段关于“意义的建构”的论述,它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意义是什么”的定义,而是花了大量的篇幅去描述“追寻意义过程中那些令人心碎又令人振奋的失败”。这种对不确定性的坦然拥抱,让我感到无比的踏实。它没有许诺给你一个终极的救赎蓝图,而是告诉你,在迷雾中摸索本身就是人类最崇高的任务之一。这种近乎苦行僧般的求真态度,通过其极富节奏感的句子和大量的反问句得以完美体现。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它在不断地自我修正和推翻中前进,这使得阅读过程本身变成了一种动态的、共同参与的探险。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好像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心灵排毒”,那些平日里积压在心头的宏大困惑,似乎被轻轻地疏导了。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震撼的,是它对“道德模糊地带”的处理方式。很多探讨伦理的作品往往倾向于二元对立,非黑即白,但这本书却深入泥泞,毫不回避那些让人夜不能寐的灰色区域。作者似乎天生就对“一刀切”的解决方案抱有警惕,他总能找到那个最微妙的平衡点,然后轻轻地摇晃它,观察其反应。例如,书中对“英雄主义的代价”的分析,没有简单地歌颂或批判,而是细致入微地剖析了英雄在完成壮举后,如何被社会期望的重担压垮。文字的密度极高,但又处理得非常得体,不会让人感到窒息。我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放慢语速来阅读,不是因为内容晦涩,而是因为我需要给那些被揭示出来的复杂人性留出足够的呼吸空间。这本书的篇章之间看似松散,实则暗流涌动,它们在潜意识中相互呼应,最终汇集成一股强大的、对既有认知提出质疑的洪流。对于那些寻求智力上的挑战,同时又渴望情感共鸣的读者来说,这绝对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精神盛宴。它带来的思考余温,比任何一碗热汤都要持久。
评分这部作品的语言风格独树一帜,它既有古典的韵味,又饱含现代的疏离感,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张力。它的评价点很难聚焦,因为它更像是一系列独立的小型“思想实验”的集合,每个片段都有其独立的生命力。我特别欣赏作者如何运用日常的、近乎琐碎的细节来引爆深层的问题。比如,书中对“排队哲学”的探讨,从银行大厅里人们僵硬的站姿,延展到社会契约的根基,这种由小及大的穿透力,令人拍案叫绝。它不是那种需要你备好笔记本去圈点标注的书,它更像是一首需要反复哼唱的旋律,每一次重听,都能捕捉到新的和弦变化。不同于那些试图用严密逻辑链条将读者锁死的作品,它更像是为你打开了一扇扇不规则的窗户,每一扇窗外的风景都指向一个不同的宇宙。这种散漫却又精准的叙事策略,极大地激发了我的联想能力。它不强迫你接受任何既定的观点,而是鼓励你将书中的某个概念,带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检验、去碰撞。可以说,这本书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将“阅读”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重新校准。
评分我很是高兴的一次购物,我支持!
评分很满意,东西很好
评分作为一个存在主义思想家,他试图将一切与个体自身的情况相联系,而不是从中提取本质,借此来理解生活。他的第一本著作《非此即彼》集中论述了自由与奴役之间的选择,这一论题几乎可以在他的所有著述中找到。他坚持认为责任和宿命论在人类中互相缠绕,由此预示了深蕴于心理学中的去个性化和意志危机等课题。在他看来,当自我包括许多非意志的或自我创造的因素时,自我仍然不是一架机器。他反对怀疑论,反对宿命论的超然旁观,把道德和伦理责任作为普遍目标,把由此促进的世俗判断和绝望戏剧化。他认识到“精神失助”这一奇特的现代病,指出自我疏忽或自我隔离,真正的自我一直未能实现也无法实现。要纠正这种现象必须在信任上获得飞跃,树立“新生活”或真正的自我是个体摆脱与一个人的社会文化环境彻底同化的个体化和分化过程。克尔凯郭尔认为,实现这种自我的标准在基督教的核心人物耶稣身上得到体现和表明。在一个人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另一个人可以是“助产士”,但是“分娩”最终还是个人自己的事。 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有两大要义:其一是存在先于本质的理念,其意义是指人的生存是被动的、命定的(人之出生是男是女都不能由自己决定),可是人可以利用自己命定的这种存在,去创造自己的本质。所以人之所贵,并非由于他有一个命定的存在,并非由于他的历史背景、家世,亦非由于他出身的地位,而是在于人有选择改造自己的本质的自由,他如何选择做自己想要做的人,选择自己想要做的事,这就是人的本质。
评分哲学爱好者喜欢的宝贝啊哦
评分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评分书....好评
评分翻译得很优美
评分京东好书,多快好省上京东!
评分丹麦哲人克尔凯郭尔在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20世纪的哲学、神学、文学均有深远影响,这种影响的持久效力并不仅限于由生存哲学、辩证神学和生存神学来概括或衡量。该书在知识与信仰、苏格拉底遗训与福音书之间的紧张中展开思想论辩,力图确立新的思想认知——信仰、新的思想预设——罪的意识、新的思想决断——瞬间和新的思想之师——在时间中显现的上帝。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