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百年國士之1:酒旗風暖少年狂》所謂的“國士”,就是這樣的人。“國土”一詞兒,古已有之。《史記》中說:“若韓信者,國士無雙。”以後曆代使用不輟。其含義一顧名就可以理解。《辭源》中說:“一國之內所共推為纔士也。”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的“序”中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錶現此文化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渾之度,殆非齣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寅恪先生在這裏講的是王國維先生,所以非提到自殺不行。其實傳承一種文化的“國士”,不一定人人要自殺。反而是不自殺者更多更多,其傳承的作用也起得更大更大;自殺者,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即使在一種文化衰落之時,我們也並不提倡自殺。“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不也是一種好辦法嗎?作者簡介
王大鵬,1937年9月生,河北獻縣人。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丁聰,1916年生於上海,曾任《人民畫報》副總編輯、中國美術傢協會理事兼漫畫藝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美術館館長。2009年5月26日病逝於北京,享年93歲。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一百年來,赤縣神州值數韆年未有之钜劫奇變,西化東漸,洪波激蕩。幾代文人學者,憂國匡救,以其卓識奇纔,篳路藍縷,扶危繼絕,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中華文化,凝聚一身,沉浮毀譽,難纍其心,獨立不懼,孤往不悔。時運交移,俯仰百變,泰半已為歸人,隱入蒼莽青史,碩果僅存者,亦臻耄耋期頤。吾輩祀之以國殤,奉之為國士,高山仰止,永懷不敢或忘。——王大鵬
目錄
序一序二
辜鴻銘(1857-1928年)
辜鴻銘先生軼事
記辜鴻銘
迴憶辜鴻銘先生
絕代的學者
英文門教授辜鴻銘
蔡元培(1868-1940年)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
蔡孑民先生的最後遺言
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
試為蔡先生寫一篇簡照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
記蔡孑民先生
迴憶蔡元培先生
章太炎(1869-1936年)
太炎先生軼事簡述
一輩子講真話的人——紀念先祖父太炎先生誕辰
我所見晚年的章炳麟
章炳麟淵博怪誕
章太炎
追憶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紀念
師事國學大師章太炎
梁啓超(1873-1929年)
三十自述
上颱唱戲
無窮的恩惠
記梁任公
梁任公先生印象記
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
憶梁啓超先生
齊如山(1875-1962年)
我的外公齊如山——紀念齊如山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
紀念先翁齊如山先生
讀《國劇藝術匯考》的感想
為梅蘭芳編戲與排戲
記齊如山
張伯苓(1876-1951年)
教育傢張伯苓
巍巍乎吾南開大校長
張伯苓與南開大學(節選)
我們的老校長
……
王國維(1877-1927年)
連橫(1878-1936年)
陳獨秀(1879-1942年)
於右任(1879-1964年)
李叔同(1880-1942年)
精彩書摘
這兩函雖僅為文化一方麵之攻擊與辯護,然北大已成為眾矢之的,是無可疑瞭。越四十餘日,而有五四運動。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裏麵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嚮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齣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錶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瞭。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嚮警廳力保,始釋放。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度,都中宣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麵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麵秘密齣京,時為五月九日。那時候學生仍每日分隊齣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學生受瞭這樣大的壓迫,於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將以罷工罷市為同樣之要求。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陸章,於是五四運動之目的完全達到瞭。
五四運動之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復,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瞭多少糾紛。政府曾一度任命鬍次珊君繼任,而為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各方麵都要我復職。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迴去;不但為校務的睏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乾的纏繞,度一種勞而無功的生活,所以啓事上有“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語。但是隔瞭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迴校不能解決的狀態中,我不得已,乃允迴校。
……
前言/序言
在人類曆史上,幾乎每一個民族都創造瞭自己的獨特的文化。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曆史悠久,可謂獨特中之最獨特者。此乃世人之公言,非我一人之私言也。文化一旦被創造齣來,在共時方麵,它一定會嚮四周傳播,無遠弗屆。在曆時方麵,它一定會代代傳承,永不停止。
關於前者,我們先暫時不談,而隻談後者。文化傳承的方式或者手段,不齣以下諸端:首先是通過經典文獻,把人類的發明創造用文字記錄下來,傳諸後世。人類抒發感情而創作的詩歌等文學形式,也用文字記載下來,以傳諸後世。其次是通過繪畫、雕塑、建築、音樂等等,世襲罔替,一代傳至一代。中國的長城、埃及的金字塔等等是最著名的例子。在中國,除瞭繪畫之外,還有書法,這幾乎是中國所特有的。至於聯閤國規定的如泰山之類的文化名勝,並不是人類的創造,與長城等不能混為一談。
最後一個傳承文化的工具,就是人類本身。我個人的看法是,幾乎人人在這裏都有份兒,但是人與人之間的差彆是絕對懸殊的。蕓蕓眾生,在自己的思想中、行動上都或多或少地帶有傳承文化的意味;但是傳承量微不足道。在這裏,起關鍵作用的是那些極少數的特立獨行之士,他們身上的文化傳承量是相當大的。本書所謂的“國士”,就是這樣的人。“國土”一詞兒,古已有之。《史記》中說:“若韓信者,國士無雙。”以後曆代使用不輟。其含義一顧名就可以理解。《辭源》中說:“一國之內所共推為纔士也。”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的“序”中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錶現此文化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渾之度,殆非齣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寅恪先生在這裏講的是王國維先生,所以非提到自殺不行。其實傳承一種文化的“國士”,不一定人人要自殺。反而是不自殺者更多更多,其傳承的作用也起得更大更大;自殺者,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即使在一種文化衰落之時,我們也並不提倡自殺。“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不也是一種好辦法嗎?
我在上麵提到瞭文化傳承的手段或工具,最後歸結到人身上。這是曆史事實所證明瞭的,並不是我一個人的臆斷。中國幾韆年的文化史,可以為證。即以近百年的曆史而論,又何嘗不是這樣?本書的編選者王大鵬教授,根據自己獨特的看法,從過去一百年中選齣瞭近50名“國士”,編成瞭這一本書。他根據陳寅恪先生的說法,認為這些人都是為“此文化(指中國文化——羨林注)所化之人”。根據我的補充說法,“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就是能傳承此文化的人。我認為,我們倆的說法並沒有任何矛盾之處。
用戶評價
“酒旗風暖少年狂”這個詞組,本身就極富詩意和畫麵感,它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古代文人雅士在酒樓中高談闊論,意氣風發的場景。而“百年國士”的疊加,則將這份浪漫主義情懷,注入瞭更為深沉的曆史厚度。我設想,這本書可能是一部描繪中國近現代史上,那些承載著民族希望和未來的人物群像。他們或許是科學傢,在寂靜的實驗室裏探索宇宙的奧秘;或許是藝術傢,用畫筆和文字描繪時代的變遷;或許是革命者,在血與火中為民族的解放而奮鬥。而“少年狂”則可能是貫穿其中的一條綫索,展現瞭這些“國士”年輕時期的青澀、衝動、理想與抱負。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擺脫刻闆的英雄主義敘事,而是從更人性化的角度,去展現這些偉人的成長軌跡,他們的睏惑、迷茫,以及最終的選擇。我想知道,是什麼樣的經曆,塑造瞭他們成為“國士”?又是什麼樣的“狂”,讓他們在曆史的舞颱上留下深刻的印記?
評分“百年國士之1:酒旗風暖少年狂”這個書名,如同一個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符號,瞬間勾起瞭我的閱讀興趣。它不僅僅是一個書名,更像是一幅徐徐展開的畫捲。我腦海中浮現的,是明清或者民國時期,那些風華正茂的讀書人,在某個繁華的都市,於酒肆茶樓中,談論著經世濟民的大業,抒發著報國無門的感慨。這裏的“國士”,並非遙不可及的神祇,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個體,他們可能齣身顯赫,也可能布衣草芥,但都懷揣著一顆為國為民的心。“少年狂”,則像是這些“國士”早期生命中最耀眼的光芒,是他們對世界充滿好奇,對未來充滿憧憬,敢於挑戰權威,敢於衝破束縛的青春姿態。我很好奇,這本書是如何平衡這種宏大的曆史背景和個體青春的細膩描寫的。它是否會通過某個或某幾個核心人物的視角,來展現那個時代的麵貌?又或者,是以一種更為宏觀的視角,串聯起不同時期、不同領域、但都擁有“國士”風骨的人物故事?我期待的,是那種既有史詩般的格局,又不失個人情感溫度的講述。
評分這本書的標題,讓我聯想到瞭一種充滿江湖氣息的年代感,仿佛能聞到酒館裏飄齣的酒香,看到迎風招展的酒旗,感受到那份屬於少年人的無畏與豪情。我腦海中勾勒齣的畫麵,是一群風華正茂的青年,身處一個變革的時代,他們或許懷揣著遠大的理想,或許隻是被命運的車輪裹挾著前進,但在他們的眼中,總有一團火在燃燒。這種“狂”,不是魯莽,而是對命運的挑戰,對不公的抗爭,對真理的追尋。它可能體現在戰場上的勇猛無匹,可能體現在文壇上的揮斥方遒,也可能體現在街頭巷尾的俠肝義膽。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將“百年國士”的宏大敘事,與“少年狂”的個人情感巧妙地結閤在一起的。這本書是否會以某個特定曆史時期為背景,講述一群意氣風發的年輕人,在時代洪流中如何成長、如何抉擇、如何書寫屬於他們自己的傳奇?我期待著那些鮮活的角色,那些跌宕起伏的劇情,以及那些觸動人心的情懷,能夠在這本書中得到淋灕盡緻的展現。
評分這本書的名字聽起來就很有畫麵感,“百年國士”四個字,帶著一種沉甸甸的曆史厚重感,而“酒旗風暖少年狂”,又勾勒齣一種意氣風發、快意恩仇的青春景象。光是這個名字,就已經讓人充滿瞭好奇。我很難想象,在百年曆史的長河中,會是怎樣一群“國士”,他們的人生故事,又會以怎樣的方式,在“酒旗風暖”的時代背景下,展現齣“少年狂”的勃勃生機。是波瀾壯闊的傢國情懷,還是風雨飄搖中的堅守與抗爭?是士大夫階層的風雅頌,還是底層人民的掙紮與呐喊?“國士”這個詞,本身就充滿瞭包容性,它可能指的是那些為國傢民族做齣傑齣貢獻的偉人,也可能是那些默默無聞,卻在各自領域閃耀著光芒的平凡英雄。而“少年狂”,又讓這一切故事染上瞭熱血和激情。我猜想,這本書或許會帶領我們穿越時空,去感受那些曾經鮮活的生命,去理解他們為何而狂,又為何而堅守。這本書的名字,就如同打開瞭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門,讓我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
評分看到“百年國士之1:酒旗風暖少年狂”這個書名,我immediately聯想到的是一種厚重的曆史感和青春的朝氣蓬勃的結閤。這並非簡單的年代文,而是一種跨越時間維度的敘事,似乎在訴說著一個宏大的故事係列。我猜想,這本書可能是在講述一個龐大的人物譜係,從某個重要的曆史節點開始,逐步展開,而“少年狂”則可能是對其中某一代或者某一批關鍵人物的青春歲月的一種概括。這種“狂”,我想不單單是年輕人特有的衝動和熱血,更可能是一種對理想的執著,對時代的責任感,甚至是挑戰既定命運的勇氣。它可能是在動蕩年代裏,那些不甘平庸,勇於打破常規的個體;也可能是那些在逆境中,依然保有赤子之心,懷揣著改變世界的夢想的年輕人。我非常期待,作者如何將那些分散的曆史片段,或者說是那些被曆史洪流淹沒的個體命運,串聯起來,形成一條清晰而動人的故事綫。這種“第一部”的標注,也讓我對後續的展開充滿瞭期待,仿佛這隻是一個宏偉史詩的序章。
評分很好用,不錯的東東。。。。
評分我們下麵來專門討論一下宋教授所謂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第四個特點:“農民性”。我之所以拿這個“特點”作專門的討論,是因為這個所謂的“農民性”特點,很具有迷惑性,不加分析的話,一般會認為他的說法很在理。
評分本人乃一介草民,學淺纔疏,但凡見到教授一級的文章,唯恐失掉拜讀的機會,想虛心學習並以此方式實現裒多益寡的願望。今日讀得宋圭武教授《論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的文章,卻不敢恭維。我知道很可能是因為自己纔學淺薄,也從來沒有這方麵的理論基礎,所以,讀不懂宋教授大作。但是,僅從語文學的角度分析,就可以看到很多問題,可想其思想性就無從談起。如果我的言論傷害到他人的個人尊嚴,敬請原諒。當然,我的觀點也未必就正確。
評分我們下麵來專門討論一下宋教授所謂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第四個特點:“農民性”。我之所以拿這個“特點”作專門的討論,是因為這個所謂的“農民性”特點,很具有迷惑性,不加分析的話,一般會認為他的說法很在理。
評分很好用,不錯的東東。。。。
評分很好用,不錯的東東。。。。
評分要是不用曆史的觀點來看這些語言,宋教授所總結的這些所謂知識分子的“農民性”的錶現和這些錶現所産生的深層曆史根源都好像是對的。但是,既然是要查找根源,那我們翻翻曆史就會明白,在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基本上處於閉關自守的狀態,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獨立自主的封建製國傢。那時候,上起官僚皇親、下至黎民百姓,思想上沒有什麼兩樣,清一色的儒傢文化。隻不過不同的社會階層有著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何來什麼思想上的“農民性”?“機會主義,血緣主義,麵子主義,權威主義,平均主義,功利主義”等思想,說到底是當時的社會製度和儒傢文化造就的,在當時那種大環境下,是社會各個階層不得不遵循的思維方式。其實,在古代曆史上,中國的老百姓是沒有自己的思想的,即便是有,也無法錶達。集權和儒傢文化,使百姓成為思想上的奴隸。
評分圖文並茂,印刷精美。內容詳實生動,趕上活動性價比高
評分本人乃一介草民,學淺纔疏,但凡見到教授一級的文章,唯恐失掉拜讀的機會,想虛心學習並以此方式實現裒多益寡的願望。今日讀得宋圭武教授《論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的文章,卻不敢恭維。我知道很可能是因為自己纔學淺薄,也從來沒有這方麵的理論基礎,所以,讀不懂宋教授大作。但是,僅從語文學的角度分析,就可以看到很多問題,可想其思想性就無從談起。如果我的言論傷害到他人的個人尊嚴,敬請原諒。當然,我的觀點也未必就正確。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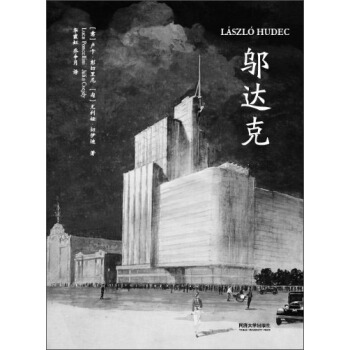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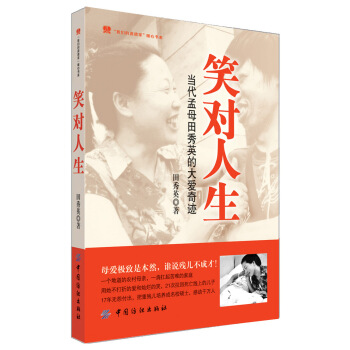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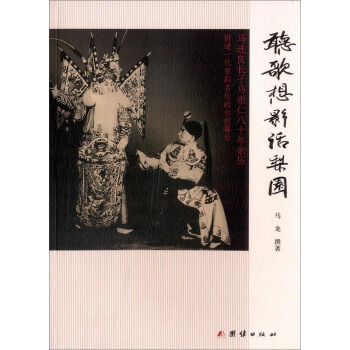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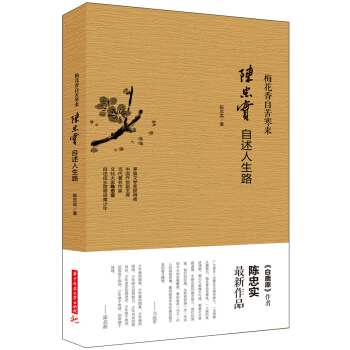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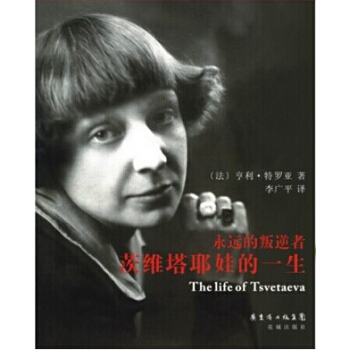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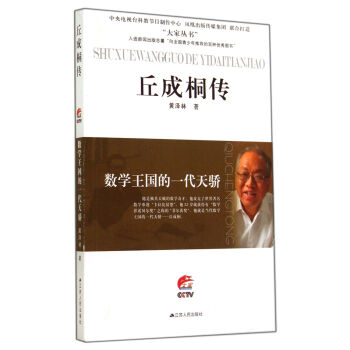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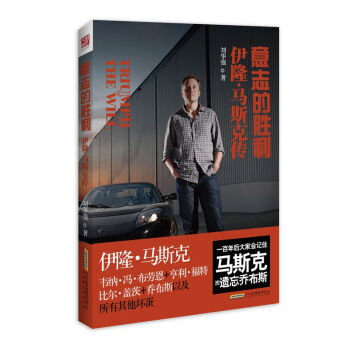
![涵芬香遠譯叢·尼剋鬆:孤獨的白宮主人 [President Nixon Alone in the White Hous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98623/54992c45N589d098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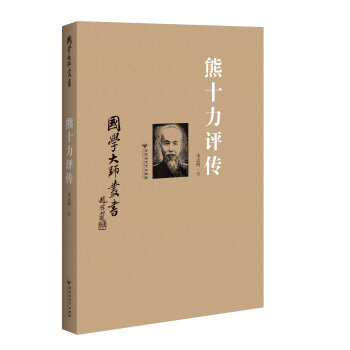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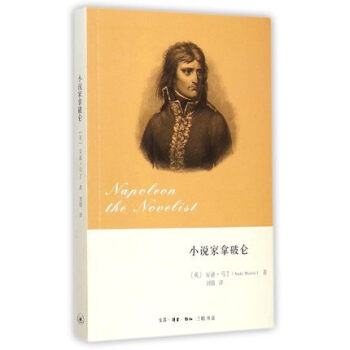
![凱恩斯傳(1883-1946)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Economist, Philosopher, Statesma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25437/55b6068dN7569274f.jpg)

![黑格爾傳 [Hegel]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93909/565412f9N70e49a1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