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文学史(套装上下册)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95114/rBEhVVIUUzsIAAAAAAOn9OPd8fwAACUOwD2s6IAA6gM710.jpg)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以叙事的方式写成的一部整体连贯、可通读的文学史
内容简介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系列国别文学史之一,该系列由著名学者主编,因定位的读者目标为普通大众,故力求以叙事的方式写成一部整体连贯、可通读的文学史,而非仅供专家参考的研究性论著;同时又能把相关领域最前沿的观点和学术成果呈现出来。以1375年为界分为上、下两卷,分别由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作者涵括十几位美国汉学界的重要学者。《剑桥中国文学史》以断代而非文体的结构方式介绍了从殷商晚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中国文学三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和中国文化中关于写作的故事。各章因作者各异其趣的学术与表达风格而呈现出不同的叙述面貌。
作者简介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1375年之前)》
从上古时期汉语书写肇始及早期铭文等问题入手,追溯了这一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学传统的起源。到了本卷结束的十四世纪下叶,商业印刷文化已高度发展,在文言文写作之外,新兴的城市白话写作已逐渐蔚为大观。《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各章描述了一些重要王朝的兴衰起灭、宫廷在文学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孕育著名大作家的社会及物质语境、亚洲其它各国的文化影响,包括佛教的输入等等。而在这一长时段中,写作以及对写作的阐释,已从附着于宫廷贵族的文士们的特殊技能,转变为一个大帝国精英阶层的根本身份象征。
《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1375-1949)》
以1400年前后形成的明代文化开篇,贯穿满族治下的清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的现代文学。这一时期多样的文学形式和风格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范畴,因而《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文学史的写作也相应包括了多样的主题,如政治审查对文学的影响、印刷文化的变迁、朝代更迭与文学发展、青楼文化、女性作家等等。除了诗词、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外,本卷还深入探讨了西方文学的汉译,现代“新小说”的兴起等等。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哈佛大学James Bryant Conant特级讲座教授,任教于比较文学系和东亚语言文明系。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文学、抒情诗和比较诗学。他的研究以中国中古时代( 200-1200)的文学为主,目前正在从事杜甫全集的翻译。主要著作包括《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 827-860)》(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Harvard,2006),《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assica)Poetry,Harvard,2006),《诺顿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Norton, 1996),《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论集》(The End of the Chinese“Middle Ages”,Stanford,1996),《中国文论 英译与评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Harvard,1992),《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Mi-Iou: Poetry and the Labynnth of Desire,Harvard,1989),《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1986),《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Omen of the World: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Wisconsin,1985),《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Yale,1980),《初唐诗》(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Yale,1977)等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自2003年起陆续出版“宇文所安作品系列。
孙康宜(Kang-i Sun Chang),耶鲁大学首任Malcolm G.Chace' 56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古典文学、抒情诗、性别研究以及文化理论和美学。
主要英文著作有:《词与文类研究》(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Princeton,1980),《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Six Dynasties Poetry,Princeton,1986),《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The Late Ming Poet Ch'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Yale,1991)。除了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合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Cambridge,2010)以外,还与魏爱莲(Ellen Widmer)合作主编《明清女作家》(Writ,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1997),与苏源熙(Haun Saussy)合作主编《历代女作家选集:诗歌与评论》(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Stantord,1999)。此外,还用中文出版了多部关于美国文化、女性主义、文学及电影的著作。自传《走出白色恐怖》(增补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
目录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1375年之前)》本卷作者简介
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
致谢
上卷导言
第一章早期中国文学:开端至西汉柯马丁
第二章东汉至西晋(25-317)康达维
第三章从东晋到初唐(317-649)
第四章文化唐朝(650-1020)
第五章北宋(1020-1126)
第六章北与南:十二与十三世纪
第七章金末至明初文学(约1230-约1375)
英文版参考书目
索引
《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1375-1949)》
本卷作者简介
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
致谢
下卷导言
第一章明代前中期文学(1375-1572)
第二章晚明文学文化(1573-1644)
第三章清初文学(1644-1723)
第四章文人的时代及其终结(1723-1840)
第五章说唱文学
第六章1841-1937年的中国文学
第七章1937-1949年的中国文学
精彩书摘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1375年之前)》《庄子》中的故事具有虚构性,乃至是奇思异想。它反复运用的技巧之一便是将事件转化为梦的维度。例如在梦里,会有骷髅代表死者的立场开口说话,并成为交谈的对象。在最有名的故事中,梦境与现实之间的暖昧边界本身成为了话题:庄周在梦里变成了一只蝴蝶,醒来之后,却“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整部《庄子》里,各种正常秩序全都颠倒了过来:跛脚之人、拳曲之树,因其无用而得以免受侵残、尽享天年;社会义务要求人们哀悼死者,这违背了万物存在的自然过程,因为生与死不过是自然变化这一更大架构中的不同阶段;古代的神圣文本不过是久已作古的死人的糟粕;繁琐的讲解妨碍人们的真正理解,并不能使人掌握任何技艺(如轮扁、庖丁),真正的掌握只有通过彻底与技艺合一才能达到。在这无数的寓言里,社会秩序都作为自然秩序的对立面而被摈弃。
《庄子》还进一步利用机智的诡辩术,迫使常规逻辑得出荒谬结论,对理性自身提出了挑战。它既展示了辩才滔滔的操控力,又指出其局限与超越的可能。就这一点而言,中古时期的玄学以及佛教禅宗充满悖论的“话头”,同样都受到了《庄子》的深刻影响。此外,《庄子》排斥公共事务的天道自然哲学思想,还有它的神话幻想、丰沛酣畅的想象力,自汉代以来,激发了诗人、哲学家、小说家(如六朝时期的“志怪”)的无数灵感。
……
《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1375-1949)》
本章的讨论将从明初的几年开始,很多人认为这 一过渡时期对中国文人而言是最黑暗的时代之一。首 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元代(1234—,1271—或 1276—1368),中国文人享有一定的自由(元代的开始 时间仍在讨论中,或始于金灭亡的1234年,或是忽必 烈可汗改国号为“大元”的1271年,或为南宋灭亡的 1276年)。正如奚如谷在本书上卷所指出的,有元一 代并无文字审查,这是因为蒙古皇帝“对汉族文臣的 写作根本就不感兴趣”。1368年驱逐了蒙古人之后, 朱元璋重新开始了对文学的控制,以儒家意识形态作 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如前所述,明初的很多文人成 为“暴君”朱元璋的受害者。刘基(1311—1375)长期 忠诚地担任朱元璋的谋士,他不仅是杰出的思想家和 作家,更以治国能力闻名,但即便是刘基最终也触怒 了朱元璋而遭免职。境遇更危险的是宋濂(1310—— 1381),他同为朱元璋的文臣,一直为朱元璋所敬重 ,受命担任《元史》编纂总裁官。然而,他的孙子牵 连了一桩谋反案,他几乎因此被处决。马皇后亲自介 入营救宋濂,才使他免死流放。而宋濂的家人,包括 父母、孙子和一个叔叔都被处死。在朱元璋清洗想象 的“异己”的过程中,有数字称一万五千人被逮捕并 处决。在所有的受害者之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历元 而人明的高启(1336一1374)。
高启和英国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eel,约 1340—1400)同代而生,乔叟一辈子太平无事,高启 却不幸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年代。元末天下大 乱,兵祸加天灾,干旱后紧跟着瘟疫流行,正如薄伽 丘《十日谈》中描写的瘟疫。高启幸好生长在富庶繁 华的苏州,在十四世纪的大动乱年代,苏州不仅是骚 人墨客避乱的安乐窝,就是对比当时的欧洲,亦很难 找出一个在各方面都优于苏州的城市。也正是在苏州 ,从未应考和出仕的高启成就了他的诗才,结交了, 批文友。早在十六七岁,他便与张羽、杨基和徐贲号 称“吴中四杰”,再往后,他与这三个能诗善画的文 友又被纳入“北郭十友”的团体,且位居十人之首。
这些年轻的诗人和书画家经常在姑苏城中雅集,诗酒 酬唱,咏遍了城内外的风景名胜,其中咏狮子林的组 诗在园林题咏中至今仍属脍炙人口的名作。所谓“国 家不幸诗人幸”,身处动乱的年代,这群文友却在苏 州城求得了庇护。
无奈好景不长,1356年,出身盐贩子的张士诚率 叛军攻占苏州,从此在这里割据长达十二年。张羽、 杨基和徐贲均在胁迫下供职张氏小朝廷。高启则可能 考虑到全身远祸,举家迁至附近一个名叫青邱的小山 下居住。在创作于当时的名作《青邱子歌》中,诗人 以“闲居无事、终日苦吟”的隐者自居。后来他离开 青邱,漫游吴越达两三年之久。这次出游显然是在躲 避来自张氏小朝廷的压力,从写于此间的托喻之作《 南宫生传》即可看出,在这一充满危机的时期,诗人 在漫漫旅途中进退维谷。《南宫生传》描写一个“藩 府”屡次要把南宫生招到自己的幕下,但终于“不 能得”,因为南宫生凭着机智脱逃了。而就在此时, 接二连三的内斗和残杀终于敲响了苏州小朝廷的丧钟 。尽管在张士诚的割据下,该城曾一度出现小小的文 化复兴,但1367年,朱元璋大军兵临城下,很多文人 学士相继逃亡,苏州城随即一片萧条,接着便在强 攻下陷落。城破后,成千上万的当地士绅,包括杨基 、徐贲等诗人均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出于仇视强敌张 士诚的心理,朱元璋对占领后的苏州特别残酷无情。
处此动乱中,高启旦夕自危,后来他赴南京,短期参 加《元史》的编纂工作,但最终还是因文字招惹了杀 身之祸,没能逃脱灭顶之灾。
……
前言/序言
这部两卷本《剑桥中国文学史》横跨三千载,从上古时代的钟鼎铭文到二十世纪的移民创作*,追溯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久远历程。在全书编写过程中,作者们通力合作,对主题相关或时段交叠的章节予以特别的关注,力求提供一个首尾连贯、可读性强的文学史叙述。我们亦认真考虑了每个章节的结构和写作目标,并斟酌在何处分卷以便于读者的理解。当代中国的文学史写作浸润于两种传统之中:其一为中国古典学术范畴,其二为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史书写。出于对学术习惯的尊重,当代西方学者在介绍中国文学时往往袭用中国学界术语,对西方读者而言这些语汇常常难于理解。本书试图解决这些问题,采用更为综合的文化史或文学文化史视角,特别避免囿于文体分类的藩篱。对中国早期和中古文学而言这种方法较为适用,但应用于明清和现代文学则多有困难。虽然如此,通过清晰地架构总体文化史或政治史,我们还是有可能实现最初的目标。例如,上卷的唐代文学一章没有采用“唐诗”、“唐代散文”、“唐代小说”、“唐代词”等标准范畴,而是用“武后时期”、“玄宗时期”等主题,叙述作为整体历史有机组成部分的诗文、笔记小说等作品。与此相似,下卷关于明代前中期文学的一章分为“明初至1450年”、“1450—1520年”及“1520—1572年”,分别关注诸如“政治迫害和文字审查”、“对空间的新视角”、“贬谪文学”等文化主题。文体问题当然值得注意,但是相对于以文体本身作为主题的叙述,文体产生发展的历史语境更能体现其文学及社会角色。这种方法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有些作品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因而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样的作品主要是属于流行文化的通俗文学,就文本流传而言它们出现较晚,但是却拥有更久远的渊源。伊维德在下卷第五章处理了这个问题,将他自己的写作与其它章节的历史叙述融合起来。
由于这项工程的规模和复杂性,我们决定不提供冗长的情节概括,只在必要的时候对作品进行简短介绍。中国学术界的文学史写作通常围绕作家个体展开,其它剑桥文学史作品同样如此。这部文学史不可避免地也会讨论不同时代的伟大作家,但是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关注历史语境和写作方式而非作家个人,除非作家的生平(不管真实与否)已经与其作品的接受融为一体。
随着文学作品本身及其传播途径的多样化,明清和现代文学更难以用统一的方式叙述。篇幅所限,我们决定暂不讨论当前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同时,基于我们的历史维度,我们也不得不排除韩国、越南以及日本境内的汉文作品。但如果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文学交流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则适当予以关注。
除了作品本身,文学史写作无疑还会受到一个民族国家的学术传统和标准范畴的约束。就中国文学而言,年号、人名、文体以及中文语汇的传统汉学翻译方式都可能对欧美读者造成阅读障碍。鉴于此,我们努力保持术语翻译的一致,尽管我们要求作者根据各自时代的需要选择最恰当的英文译文。每部作品首次出现时都给出英文译名,并在括号中注出汉语拼音,汉字原文则收人书后词汇表。除特别说明外,本书所引中文资料的英语译文均为作者自译。同样由于篇幅所限,引文出处一般随文提及,未以脚注形式标出。本书的《书目》所列出的英文参考文献也只选择性地收入了部分著作,尤其鉴于中文出版物数量之庞大,作者们所参考的中文文献一律未予列出。不必说,我们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所给予的启发是永远充满感激的。
用户评价
购买这套《剑桥中国文学史》纯粹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我并非文学专业出身,一开始抱着学习的心态,没想到它带给我的惊喜远超预期。这本书的叙述方式非常引人入胜,它不仅仅是学术性的堆砌,而是充满了故事性和人文关怀。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者们对于中国文学的热爱,以及他们试图将这份热爱传递给读者的真诚。我特别喜欢书中对于文学现象背后社会文化动因的分析,例如,如何解释某些时期文人心态的转变,或者某些文学流派的兴盛与衰落,都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经济发展、社会思潮紧密相连。这种宏观的视角让我对中国文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孤立的作品,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我从中学习到了很多关于文学批评理论的知识,以及如何用不同的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这本书让我对中国文学的看法,从“知道几首诗词”上升到了“理解一个文化脉络”的层次,非常有启发性。
评分这套《剑桥中国文学史》简直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发现,我一直以为自己对中国文学多少有些了解,但翻开它之后,才意识到自己过去的认知是多么浅显。它不只是简单罗列作家作品,而是以一种宏大的视野,将中国文学置于整个历史、社会、文化甚至哲学的大背景下去审视。书中对于每个时期文学的演变、风格的流转,以及各流派之间的碰撞与融合,都分析得鞭辟入里。我尤其喜欢它对文学与政治、经济、宗教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这让我第一次理解到,文学并非孤芳自赏的存在,而是深深植根于现实土壤之中,并反过来影响着现实。比如,书中对唐代诗歌如何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文人阶层的心态,以及如何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就写得非常精彩。又比如,它详细梳理了元杂剧在当时社会结构下的兴衰,以及如何成为一种独特的大众艺术形式。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像是穿越了千年的时光,与无数伟大的灵魂进行了对话,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不再是零散的片段,而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每一页都充满了智慧与感动。
评分我一直认为,要真正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剑桥中国文学史》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绝佳的途径。它以一种非常系统、严谨的方式,将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演变历程呈现在我面前。我曾尝试阅读过一些中国文学史的普及读物,但总是觉得不够深入,不够权威。而这套书,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阔的视野,真正做到了“全景式”的展现。书中对不同时期文学作品的解读,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介绍,而是深入到其艺术特色、思想内涵、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我尤其欣赏书中对文学理论的讨论,以及不同学派的观点碰撞,这让我得以窥见文学研究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它让我明白了,文学的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的创新与反思中向前发展。从先秦的质朴,到唐诗的辉煌,再到宋词的细腻,以及明清小说的繁盛,每一步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这本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本工具书,更是一次思想的旅行,一次对中国文明的深度探索。
评分我一直对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情怀充满好奇,这套《剑桥中国文学史》恰好满足了我这一点。它在介绍文学作品的同时,也深入挖掘了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塑造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和思想观念。我常常在阅读过程中,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生动的人物形象:从饱经沧桑的骚人墨客,到风华绝代的歌姬舞女,再到寄情山水的隐士高人。书中对不同时期文学批评思潮的梳理,也让我大开眼界,理解了不同时代对于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是如何变化的。特别是一些边缘文学、通俗文学的介绍,让我看到了中国文学更为多元和丰富的一面,打破了我之前对“文学”的狭隘定义。我被书中那些充满个性的文学流派所吸引,比如魏晋时期的玄学与文学的交融,宋代词的婉约与豪放的并存,以及明清小说中市井百态的描绘。它不仅仅是一本文学史,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社会文化史,读起来既有知识的收获,又有情感的共鸣。
评分老实说,我之前对中国文学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几位耳熟能详的大文豪身上,比如李白、杜甫、苏轼等等,总觉得中国文学似乎就只有那么几个顶峰。但《剑桥中国文学史》彻底颠覆了我的这种认知。它展现了一个更加立体、更加丰富、更加错综复杂的文学世界。从先秦的诗歌,到后来的小说、戏曲,再到近代的白话文学,每一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我尤其惊讶于书中对许多被我忽视的文学形式和作者的深入介绍,比如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默默无闻但同样重要的民间文学、宗教文学,以及一些地域性非常强的文学传统。它让我明白,中国文学的宝藏远比我想象的要深厚得多。书中关于文学观念的演变,比如从“文以载道”到“为艺术而艺术”,再到现代主义的探索,都让我对文学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它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一点一点地为我揭开中国文学的层层迷雾,让我看到一个更加广阔、更加精彩的世界。
评分此公所编著的张充和先生事迹之书亦好!
评分物流迅速,价格便宜,值得购买!
评分不错 还可以 送货数度快
评分很好,但是折扣不是太多,但是太想买了,最后下单。
评分好书,活动非常优惠,书包装也完整,买书就得买精装的
评分开心的不得了,三百减一百。一百五件五十我都抢到了
评分不错的书,不错的书还是不错的,同事很满意,下次有活动再洗再买吧
评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系列国别文学史之一,该系列由著名学者主编,因定位的读者目标为普通大众,故力求以叙事的方式写成一部整体连贯、可通读的文学史,而非仅供专家参考的研究性论著;同时又能把相关领域最前沿的观点和学术成果呈现出来。
评分集合海外名家,书写中国文学史,不一样的视角来看中国文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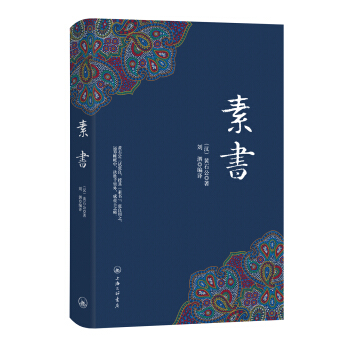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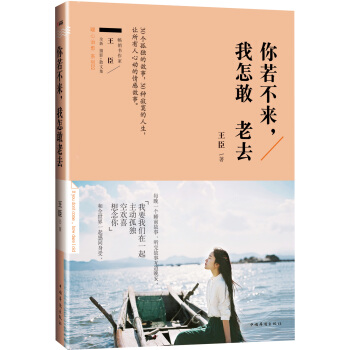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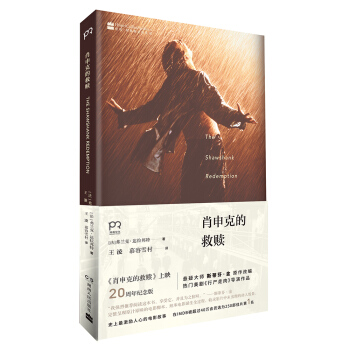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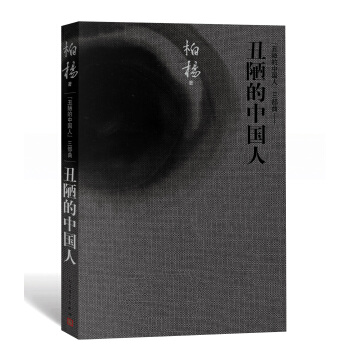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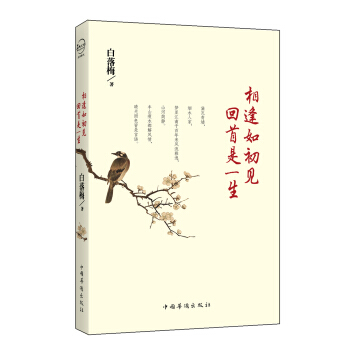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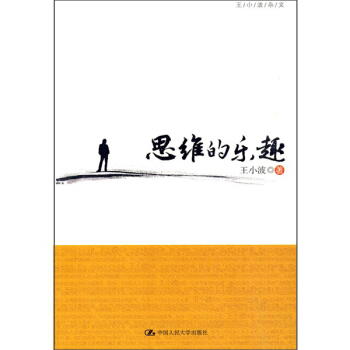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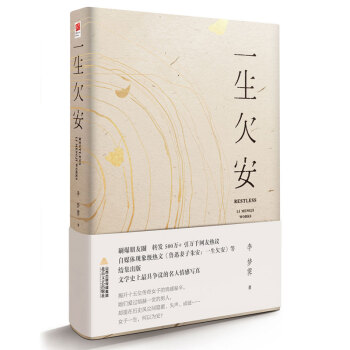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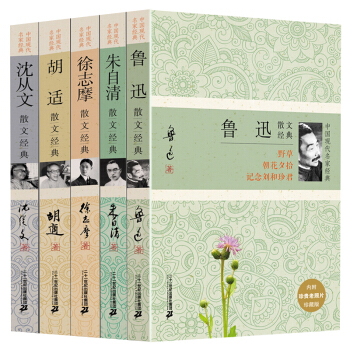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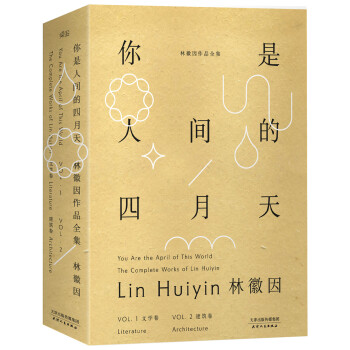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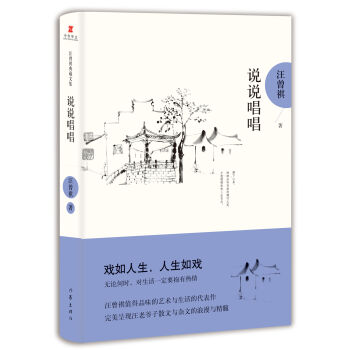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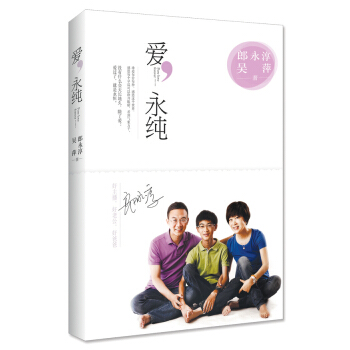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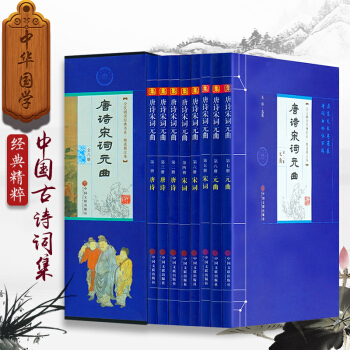
![哈佛蓝星双语名著导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027476/579857caN29fd6cf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