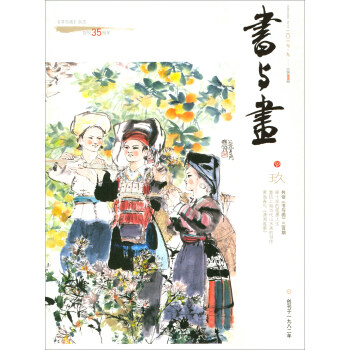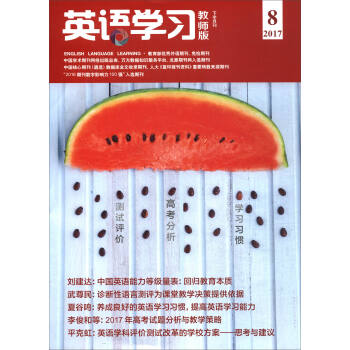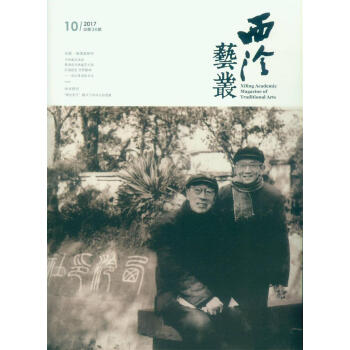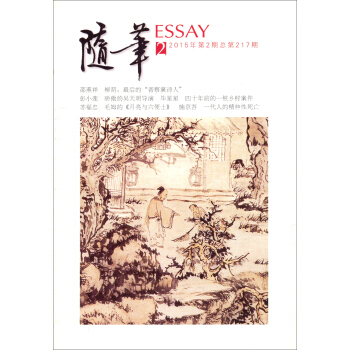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随笔》(双月刊)创刊于1979年,由花城出版社主办。它是中国文艺界、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刊物之一,致力于在思想文化界的突破,更多地关注深层次的历史、思想、文化的挖掘;关注现实,提倡理性的、建设性的批评批判。目录
邵燕祥 柳荫:最后的“晋察冀诗人”张恩和 钟敬文先生的鲁迅研究
杜书瀛 再忆吴晓铃先生
彭小莲 骄傲的吴天明导演
翟志成 胡适的冯友兰情结
朱仲南 改变我们的“好人好事观”(外一篇)
毕星星 四十年前的一桩乡村案件
张 鸣 头发的故事(外一篇)
郑异凡 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争论和斯大林“认错”
苏福忠 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
施京吾 一代人的精神性死亡
李木生 墙是一面镜子
王开林 仁爱无疆
顾 农 玄览堂读书散札四则
精彩书摘
钟敬文先生的鲁迅研究钟敬文先生是著名学者、诗人、教育家、现代民俗学学科奠基人,有一段时间他曾用主要精力从事鲁迅研究,成果丰硕,从而也理应称为鲁迅研究家。
钟敬文先生早在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写关于鲁迅的文章,第一篇《记找鲁迅先生》即作于1927年2月,接着零星也写有一些,但更多的文字是写于半个世纪以后的七八十年代。这中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时间跨度呢?
我自195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即成为钟敬文先生的学生。那时,钟先生是系里赫赫有名的三大一级教授之一(其他二位是黎锦熙先生和黄药眠先生)。钟先生教的是民间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包括鲁迅)没有什么关系。他的夫人陈秋帆先生倒是教我们“现代文选及习作”,不但讲课,还批阅作业。1957年钟先生夫妇均被划为“右派”;钟先生辛苦创建的全国高校唯一的民间文学教研组随即被撤并到现代文学组,“民间文学”课亦被取消。我毕业后留校,分到现代文学组,就和钟先生成为同事。那时,钟先生被剥夺教学的权利,只能在组里做点资料工作(而他的夫人陈秋帆先生干脆被罚到资料室当资料员)。这样,我们的接触就比较多,我会经常就一些专业问题向他请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乱起,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有意思的是他“当仁不让”地承认是“学术权威”但不承认“反动”),从原住的教授楼赶到我们青年教师住的筒子楼,我们又成了邻居,接触就更多了,说话也比较随便。筒子楼原是学生住单问宿舍楼,学校为照顾青年教师结婚应急转用,故曾被戏称为“鸳鸯楼”;“文革”时一批“革命对象”被罚赶出教授楼而住进来(名日“接受群众监督”或“与群众共甘苦”),筒子楼旋即被戏称为“牛鬼蛇神楼”。我曾笑对钟老夫妇说,你们老夫妻住进“鸳鸯楼”倒也。“情可以堪”,而我们成了“牛鬼蛇神楼”住户就有点“情何以堪”了。说完我们白是苦笑。
就我所知,钟先生还是文学青年时,即对鲁迅充满尊敬和仰慕。1927年鲁迅刚从厦门到广州,他就急着寻访鲁迅,写《记找鲁迅先生》的文章,编《鲁迅先生在广州》。但由于和鲁迅先生的一点小小的误会,更由于他的志趣原就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开创性研究,无暇他顾,后来就一直潜心在这块园地里耕耘,并且收获甚丰,名传遐迩。如果不是五十年代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他本应该在他热爱的这一领域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可从划为“右派”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整整二十年问,他基本上“无所事事”(不让他做事,限制他做事),真正是“光阴虚度”,“蹉跎岁月”。这对一位真诚的学者不啻是极大的精神折磨。
历史的转机出乎钟敬文先生的意料——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学点鲁迅”,各高校文科自然闻风而动。为落实“最高指示”推出两大举措:一是在北京成立“鲁迅研究室”。
……
用户评价
这次翻阅《随笔》(2015年第2期),最大的惊喜在于其中一些关于艺术和文化的探讨,其视角之独特,见解之深刻,令我耳目一新。特别是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了当代艺术创作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作者从多个维度进行了阐述,既有理论的高度,又不乏实践的落脚点。他并没有简单地褒扬或批判某种风格,而是引导读者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艺术。我尤其被作者对于“留白”之美的论述所吸引,他认为,艺术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呈现了什么,更在于其省略了什么,那些未被言说的部分,往往留给观者最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观点,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对人生的理解。很多时候,我们过于追求圆满和充实,反而忽略了“留白”所带来的意境和深度。这期《随笔》中的许多文章,都体现了这种“留白”的美学,它们不事事皆要言尽,而是留下一些余味,让读者自行体会,自行品味。这种阅读体验,就像在欣赏一幅中国山水画,画面中的雾气、远山,都需要观者去想象,去感受,才能真正领略其意境。
评分这期《随笔》给我的整体感受,就像品一杯陈年的普洱,初入口略显醇厚,需要细细咀嚼,才能品味出那回甘悠长。我尤其欣赏其中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剖析,作者没有流于表面,而是深入到问题的根源,用犀利的笔触揭示了隐藏在繁华都市背后的种种无奈与辛酸。其中一篇关于城市发展与人情味消逝的文章,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作者用生动的案例和翔实的论据,描绘了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同时,邻里之间曾经的温情与互助是如何逐渐淡漠。这种变化,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难以忽视的失落。阅读这样的文章,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获取,更是一种思维的碰撞,它迫使我停下来,审视自己所处的环境,反思我们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常常被各种事务裹挟着前进,很少有时间去思考这些宏大的命题。而这本《随笔》,恰好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得以慢下来,去倾听内心的声音,去理解更深层次的社会脉络。它不是那种能让人立刻拍案叫绝的评论,而是那种能在读者心中埋下一颗思考的种子,让它慢慢发芽,直至枝繁叶茂。
评分不得不说,这本《随笔》(2015年第2期)呈现出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人文关怀。它不像新闻报道那样关注热点事件,也不像学术论文那样严谨求证,而是以一种更加个人化、更具温度的方式,去触碰那些被时代洪流所忽略的个体命运。我尤其被其中一些关于“小人物”的故事所打动,作者没有去歌颂伟人,也没有去批判反派,而是将目光聚焦在那些在社会角落里默默耕耘、默默承受的人们身上。他们可能是平凡的劳动者,可能是被遗忘的老人,也可能是迷茫的年轻人。作者用充满同情的笔触,记录下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坚持与放弃,他们的梦想与失落。读着这些故事,我感受到了作者对生命最真挚的敬意,他看到了每一个个体存在的价值,即使在宏大的叙事中,他们微不足道,但在作者的笔下,他们却闪耀着独特的光芒。这种人文关怀,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它温暖了读者的心,也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有温度。
评分拿到这本《随笔》(2015年第2期 总第217期)的时候,心里涌起一股久违的阅读冲动,仿佛置身于一个熟悉的书房,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纸墨香。翻开扉页,每一篇文章都像一位老友在低语,讲述着属于他们的故事,分享着他们的感悟。我最喜欢的是那些描绘生活细节的篇章,它们不华丽,不矫揉造作,却像涓涓细流,缓缓地渗入心田,勾勒出寻常日子里的诗意。作者笔下的场景,无论是清晨街角弥漫的豆浆香气,还是午后窗边洒落的斑驳阳光,亦或是夜晚独自漫步时的思绪万千,都充满了细腻的情感和真挚的温度。读着读着,我仿佛也走进了那些场景,感受着作者的情绪,体验着他们的人生。有时候,读一篇文章,就像经历了一段旅程,作者是那位引路的向导,用他的文字带我穿越山川湖海,领略不同的风景,品味别样的人生。而这本《随笔》,则像一个宝藏盒,里面装着无数珍贵的瞬间,等待我去一一发掘,一一珍藏。我迫不及待地想将这份美好分享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也能在这字里行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感动。
评分我必须承认,《随笔》(2015年第2期)中有些篇章的语言风格,对我来说颇具挑战性,它不像一般读物那样平铺直叙,而是充满了文学的张力和哲学的思辨。有一篇文章,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古典诗词和哲学典故,构建了一个宏大的思想图景。起初,我读得有些吃力,但当我耐下心来,逐字逐句地去理解,去揣摩作者的意图时,我逐渐被一种强大的思想洪流所吸引。作者的文字,犹如精雕细琢的玉石,每一笔都蕴含着深意。他并没有刻意卖弄学问,而是将深奥的道理,通过富有韵律和节奏的文字巧妙地呈现出来。这种阅读过程,与其说是在“读”,不如说是在“悟”。我时常需要停下来,反复咀嚼,才能领会其中的精髓。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这样的阅读是值得的,它拓展了我认知的边界,提升了我对语言和思想的敏感度。这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体验,在挑战中收获成长的喜悦,让我更加期待下一次的阅读。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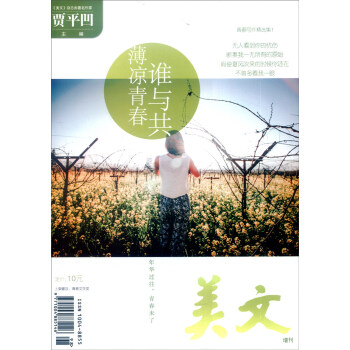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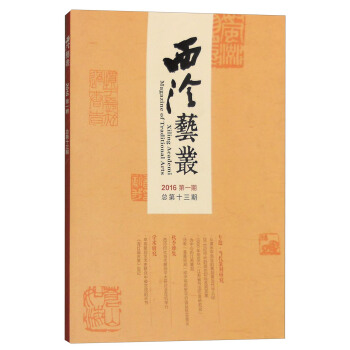

![花城(文学双月刊 2016第3期 总第220期) [Flower Cit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76454/5811db11Nd86bb11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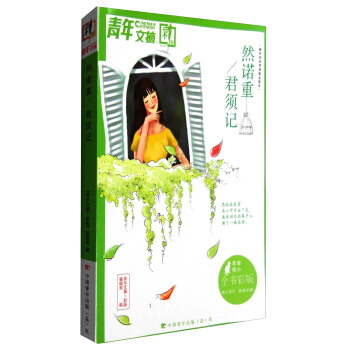
![西泠艺丛(二〇一六年第八期 总第二十期) [Xileng Academic Magazine of Traditional Art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42870/580f2911N3d6d248c.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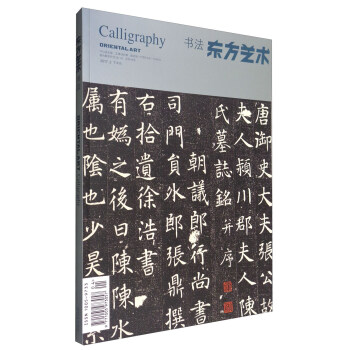
![西泠艺丛(二〇一七年第三期 总第二十七期) [Xiling Academic Magazing of Traditional Art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71131/59293949Ne647dbf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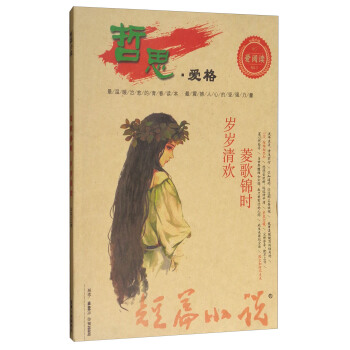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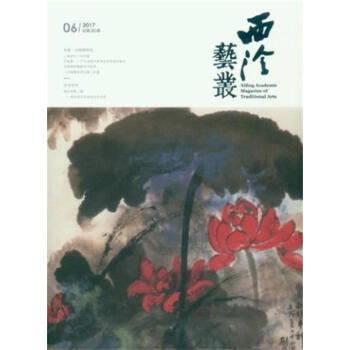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2 外国语文双月刊)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184942/59280d74N7243dea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