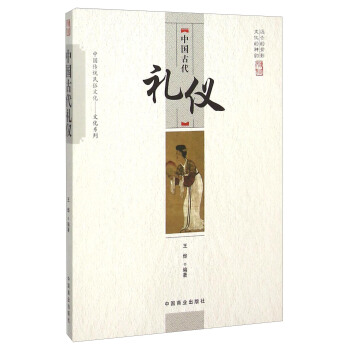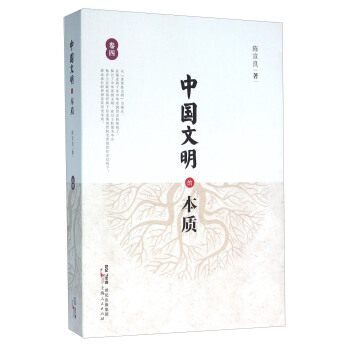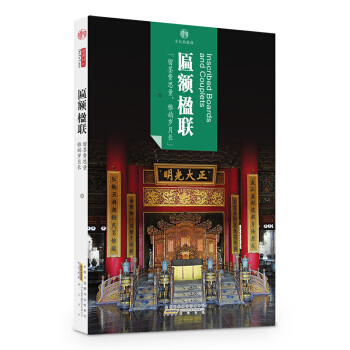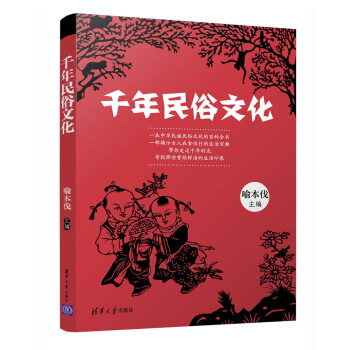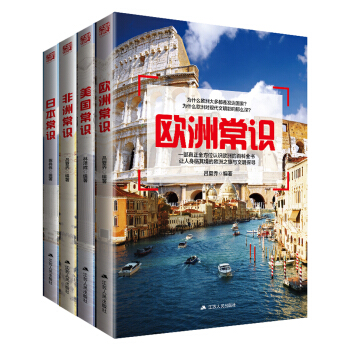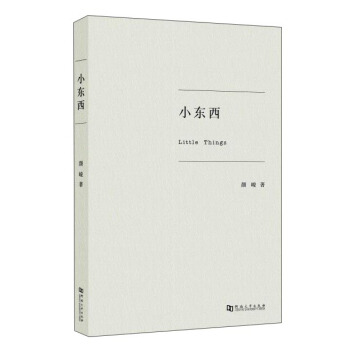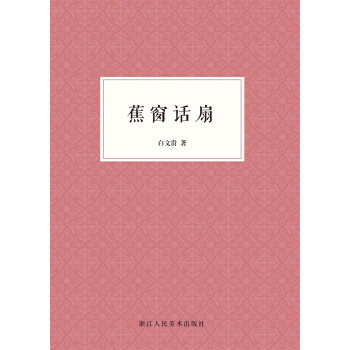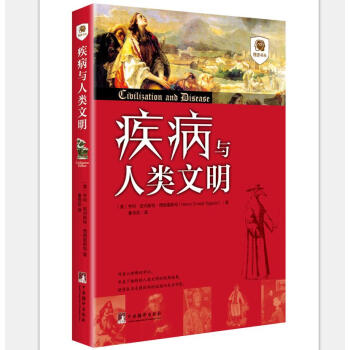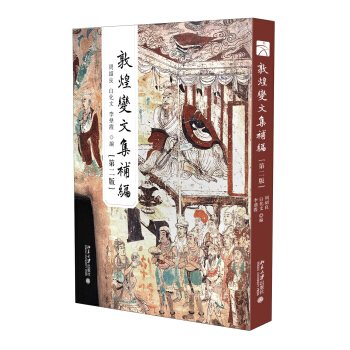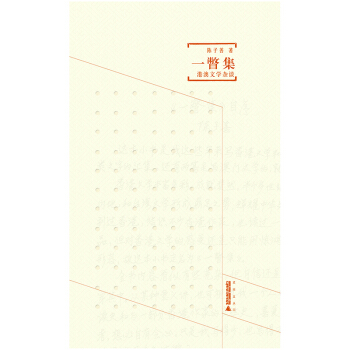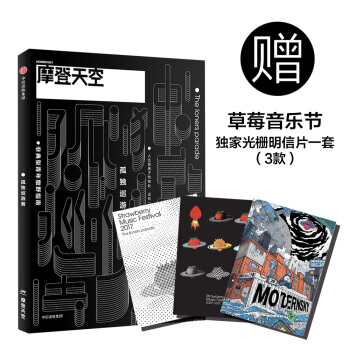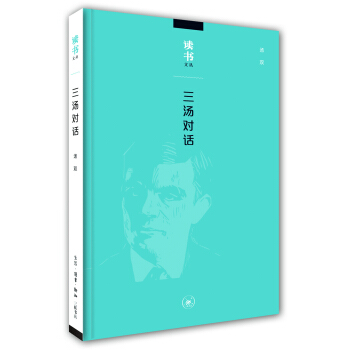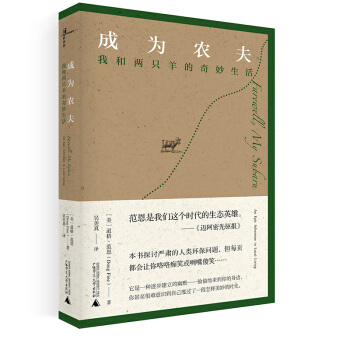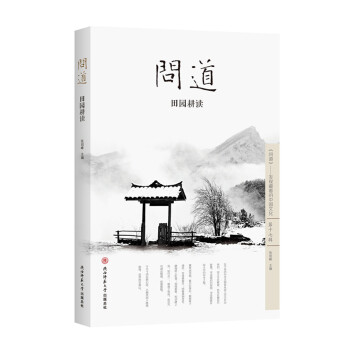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A. 捧上此书,远离城市喧嚣,回归田园宁静,在清泉石流旁,抬头凝视,悠然见南山,似入桃源秘境一般。B. 以“耕读”贯穿中国人的精神符号,在造舍编篱、香道、茶道、行住坐卧、山居饮食、服饰、 田园养生中体会传统耕读文化的内在力量。
C. 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终南文化旅行。
内容简介
以“耕”来体认四季交替,以读书来修养身心。全文从宏观的文化概念和耕读文化的现象上展示“耕读”这一主题,并深入民间寻访耕读传家的印迹,于筑舍编篱、行住坐卧、山居饮食、田园养生中细细品味自在、恬静的耕读生活。本书是继《问道·茶之书》后的另一本新作,全彩印刷,精美田园、山居图片与文字交相呼应,引人入胜。作者简介
张剑峰,终南山文化行者。2008年于终南山下创办《问道》丛书,并建立传统文化传习基地――终南草堂。2011年出版《寻访终南隐士》,“终南山5000隐士”被凤凰、央视多家电视和各种杂志、报纸报道,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话题。2012年“问道”系列先后推出《寻访武林》《茶之书》,致力于弘扬茶、道、武术等中华传统文化。精彩书评
翻开大作,清风徐徐吹来。我从事出版三十余年,阅书无数,阅人无数,这样的奇文,这样一些奇人奇思妙想,很少见到。要感谢终南山瑰丽景色;要感谢华夏人文景观至深无下、至高无上的无尽内蕴;要感谢书中三五同人,同声相求,妙笔生花,胸中山水,腕下笔墨,让人醉梦其中!——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
《问道》系列图书是颇有特色的文化丛书,即将出版的《问道·田园耕读》一书将带领读者重返久违的田园生活,在耕作之余,有书相伴。如此山居生活,田园景致,令人遐想而且心驰神往。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子善
数千年来躬耕陇亩之间,泛舟于江湖之上者多出高士智者。渔、樵、耕、读间隐藏着中国文化恢弘而幽深的智慧。物欲横流,道德日丧是文明的悲哀,回归田园捧读诗书,寄情山水,穷通自然,古今智者莫不如此。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无论世界怎样变化,懂得回
归者必厚德载物执大道而行。
——中国文化书院三智道商国学院常务副院长、三智书院理事长高斌
目录
田园耕读序/问道编辑部 01寻彼南山 悠然采菊/肖伊绯 1
耕读雨读 琴剑与归/琴剑逍人访谈录 25
布衣清庐可听雨/熊厚音访谈录 57
筑舍南山 白云满屋/马守仁 77
君子谦谦 行止有节/盛日 107
文房清供/高铖临 133
被褐怀玉 广袖飘飘/蒹葭从风 153
居山晴雨集/杨子莹 175
精彩书摘
第一章节:寻彼南山悠然采菊
文/肖伊绯
据说唐代草书大家怀素的《自叙帖》,并没有真迹存世。现在所能看到的“国宝”,曾经是苏舜钦的珍藏,然而这件藏品也只是摹本罢了。更为奇特的是,由于当年卷子已经碎裂损坏,苏氏还临摹补上了前六行草书,使得这件摹本之上的摹本在收藏界又有了一个学术符号式的命名:苏补本。
其实,中国人的临摹功夫是天生的。这种优秀如果发挥到极致,可以成为优雅。岂止是唐代的草书可以临摹,即使这种书法变化多端,如云水龙蛇,难度极高,只要苦心钻研,终能入木三分。那临水照花、拈花一笑的心手如一,使苏舜钦自家心田里的那一枝花,花中的那一支笔,可摹可写的上天入地,无所不可。曾经建造过沧浪亭的人,并不介意书法的难度,因为再难,也难不过苏氏心中变幻的云霞。
应时植我东篱菊
东篱,是东边的篱笆,还是东向的篱笆?
怀素的草书,有些字形局部看来,就如同一枝枝篱条。其实,不一定非得是怀素的狂草,只要是一整幅毛笔字合在一起,无论什么书法,真草行楷篆种种,皆可看作一围篱笆。即使那些规规矩矩并不卓然独立的“草民们”,也可以写出一围篱笆来。无论东向与否,自顾自地享受“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自得,这是中国人的自然而然,没什么道理可讲的。
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将东篱、南山定格于经典惯用语中,东与南、篱与山。人与自然的距离由远及近,最终不再有远近之分,融为一体。疏离中是自然,感受到的却是自然而然。
南山是自然造化,东篱则是人为。如何先自然,再以人力去自然而然?这是陶渊明的障眼法,还是篱笆内外看山者的视觉误差?山是自家山、院是谁家院?陶氏拾来枯枝败木,草草营围,一栏篱笆隔开的岂止是人与荒野,隔开的只是喧嚣的欲望而已。
东篱南山逸人
苏东坡读到陶渊明,感受到那份近乎天然的自然而然。苏东坡曰:“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景与意会。”
从诗学的角度来谈当年看山者的心理感受,总是有所欠缺,苏东坡说得够贴切,却还是欠妥当。无论怎么自然而然,撇开了篱笆谈看山,忽视了篱向东、山坐南的地理位置,为诗而诗的话语,虽是老练成熟,却终究不是真自然,缺少了一丝天然境界。
苏舜钦的六行临摹补书,究竟是按照怀素草书的本来形态描摹,还是原来神髓追摹?这不但是个需要考证的史学问题,还是个需要推理的哲学问题。史学家们可能倾向于苏氏手中还有一个完整的摹本,然后按照这个底本一笔一画的进行描摹。可现在存世的最早摹本只有“苏补本”,而且长期以来就被当作怀素的真迹来珍藏,即使在清代宫廷也是如此。
苏氏手中有没有一个底本,或者那个底本究竟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臆想附加的,或许都不重要。其实,形似与神似都只是相似,而非等同,但形似与神似之间的那道篱却相当关键,居——篱——山的空间区隔,也正是园——墙——林的构筑模式。
山居的重要屏障是那道篱,园林的首要屏障是那道墙,很难想象,没有空间区隔的山居与园林是何种模样。如果没有篱与墙的区隔,山居不如洞穴,园林即是真山水。
中国园林就是这么一个法则,与书法相通,在形似与神似之间,“园”并非惯常纯粹的居所空间,“林”也并非荒僻野蛮的深山老林。一道倚湖山或避市井而砌的墙,将神似与形似隔开,也将神似与形式包围,“园林”二字是园与林的叠加,但已然复合为一个单词了。这种美学体系的始作俑者,是否就是陶渊明的“东篱”,没有人予以定论,但其间的默契已逾千年。
其实,东篱和南山之间,只有一个“人”字。可以是陶渊明,也可以是其他人。这个人可以写诗,但最好不要谈论诗学。
……
前言/序言
序:田园耕读序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从泥土中生长,泥土生长粮食,也生长着东方智慧。寻觅将逝的田园,寻觅与节气相应的朴素的传统文明,寻觅隐匿在泥土中的中华之根。
乡村孕育了城邦,上古华夏祖先躬耕在陇亩之间,城市只是发布政令和交易的地方。如果熟谙了变化之道,田园则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宏大背景。桃花源是被中国人触摸得发亮得词语。上至帝王下至庶民,没有人不渴望能够拥有一块生机盎然的田园。不同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中国人只有拥有了田园,才会拥有对于和谐和宁静的追求。田园耕读是中国人修身养性的母体,是抚慰心灵的终极故乡。
通过“耕读”阅读中国人的精神符号,从中可以发现中华道统的衍生和衰落。上古的人,行而论道,既通过师承制传承、明了道之体,又通过回归自然走进田园,躬耕陇亩体认了道之用,使中华文明持续发出光华。战国时期,中国的古人因为对道统的不同理解而产生了百家争鸣。唐代之后,中国人坐而论道知行分离之后才呼吁知行合一,士人们要么远离了田园,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要么只知道其理而不通达其用。道、法、术、器不能贯通,所以田园和土地逐渐贫瘠,最终成了城市的附庸。生机勃勃的中国文化因为体用关系的脱落而出现疾病,田园的失落实际上是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遗忘。寻觅最初的田园,以此归真达道。
中国文化是华夏先祖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象形取意形成的东方智慧。古人俯仰之间体察自然变化,通过躬耕陇亩之间体察自然之动静,生命之变化,进而发散以至观照生命的各个层面。
内圣外王之道,进退之间,中国人正是通过一片田园来承载和展开,体验并书写,进而传承。
数千年来,古人们就是通过躬耕于陇亩进而耕作心田的。由此向内心望去,丘壑俨然,正是如陶令之桃花源。寻觅最初的田园,沿着那条摇曳着童谣的陌上小径就能回到故乡。
光耀兮正兮,晨照于林;德显兮彰兮,在天地之行。
当晨曦的阳光穿透纸窗,鸟儿在林间鸣唱。
窗外的菜地沐浴着阳光。
案上的书卷翻阅着松风。
汗水顺着额头滑下、滴落,它们会成为滋养土地的养分,会让锄头的木柄更加光滑、发亮。放下锄头,看着作物渐渐发芽、长大、成熟,沾满泥土和汗水的手中握着果实,生命会因此而充实。
窗外的雨,打在青石上或打在草叶上,是一卷卷“云集”之书。书中有雨,雨中有书,读这一卷书,同时也在读这一场雨。每一个文字就像是一颗雨滴,敲打着石上苔绿,敲打着闲适心灵。那些美丽的诗文词卷,就像是采集晨曦的露水,汇聚天上的彩云,将它们绘于纸上,融进书卷。
夫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见一雪消,乃知万物春。夫若修身立命,一锄之耕,当知事在躬行。一卷之读,当知物在善察。
晴可耕,雨可读。又可陪伴琴棋书画、诗酒茶,泉石松云、东篱黄花。
回归田园,是回归心灵与精神的美好家园。
从那茅屋后面升起来的缭绕青烟,已缓缓飘散了五千多年……
华夏民族从遥远的上古时期开始,便已耕读于天地之间。从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耕时代,五帝之一的尧帝时期是华夏民族农耕文化繁茂发展阶段。相传尧帝德高望重,严肃恭谨,光照四方,团结族人,使邦族之间聚合如一家,和睦相处,深受人民的爱戴。他生活简朴,吃粗米饭,喝野菜汤。
《史记》记载尧帝“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他命部下的羲氏、和氏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制定推出历法——四时成岁,为百姓颁授农耕时令,测定出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使天下生民农耕生产有所依循,叫作“敬授民时”。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安居。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此乃无为之治也。
相传尧帝来到历山,从民间选用贤良之才。听说舜在田间耕地,便到了田间,看见一个身材魁伟、体阔神敏青年聚精会神地耕地,犁前驾着一头黑牛、一头黄牛。奇怪的是,这个青年从不用鞭打牛,而是在犁辕上挂一个簸箕,隔一会儿,敲一下簸箕,吆喝一声。尧帝等着舜犁到地头,便问:“耕夫都用鞭打牛,你为何只敲簸箕不打牛?”舜见有老人问,拱手作揖答道:“牛为人耕田出力流汗很辛苦,再用鞭打,于心何忍!我打簸箕,黑牛以为我打黄牛,黄牛以为我打黑牛,就都卖力拉犁了。”尧帝一听,觉得这个青年有智慧,又有善心,对牛尚如此,对百姓会更有爱心,便与舜在田间谈论了一些治理天下的道理。舜明事理,晓大义,非一般凡人之见。尧又走访了方圆百里,人们都夸舜是一个贤良之才。于是,尧便决定先让舜先在朝中做虞官,三年后,舜在文庙拜了先祖,尧便让舜代其行天子之政。
一个人的德行智慧完全可以从日常的耕作乃言行举止中体现出来。正如《周礼·地官》一书所言:“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中华民族的这两位伟大的圣王第一次相遇便是在田野耕作间,一切都是那么朴实,自然。治国之道,在田野间的风中幽幽回荡。尧帝看重舜的明事理、晓大义,智慧而有善心。以至于后来有了华夏民族历史上一次伟大而重要的禅让。
耕读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它需要顺天应命,需要守望田园,需要辛勤劳作,需要修身立命,洞彻天地智慧。
距尧舜时代一千八百多年以后,圣人老子隐居于宋国沛地。他自耕而食,自织而衣,清澹退静,洞晓天地智慧。他的名声远播在外,慕名求道者接踵而来。在这里,他授予了南荣趎养生之经、孔夫子大道之妙。老子向孔夫子阐述了大道之元奥,孔夫子闻之,觉已为鹊,飞于枝头;觉己为鱼,游于江湖;觉己为蜂,采蜜花丛;觉已为人,求道于老子。不禁心旷神怡,说:“吾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今五十一方知造化为何物矣!造我为鹊则顺鹊性而化,造我为鱼则顺鱼性而化,造我为蜂则顺蜂性而化,造我为人则顺人性而化。鹊、鱼、蜂、人不同,然而顺自然本性变化却相同。顺本性而变化,即顺道而行也。立身于不同之中,游神于大同之境,则合于大道也。我日日求道,不知道即在吾身!”言罢,起身拜别。
耕读于尧舜是德,于老子是道。先贤圣哲们耕种于这片大地之上,他们读的是刻在石头上、写在树叶上的文字,读的是天地自然日月星辰之书。伏羲推演出河图、大禹治水现洛书;文王演《周易》,老子著《道德经》五千言,孔子编《诗经》……
这些皆是古人从天地自然之间领悟出的智慧和实践成果。黄卷幽深,汗青浩瀚。后世之书虽然庞杂繁复如星辰一般,但无不出其源流。
耕读,修身、立命、养德。耕,外可耕种田地,事稼穑以自给自足;内可耕自身之心田,打磨心性,知行合一。所谓耕种心田是也。读,有形则可读黄绢圣贤之书,无形则可读天地自然、万物之书。云石烟霞、星辰日月、山河草木……无不可为书。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其意原在天地万物、造化自然之中,也需从自然造化之中去寻找与领悟。要读有形之书,更要读无形之书。
在此之后,耕读修身便已成为了历代文人志士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志向高洁的象征。同时也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儒家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禅宗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道家曰:“清静无为,返璞归真。”那些甘愿淡泊,意出尘外,志趣高远的人们像山中涌出的清泉一样从来不曾断绝。他们如仙鹤一般清瘦的身影一直出现在那云烟环绕的田野、林泉间……
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布衣清庐躬耕于陇亩。他精通音律,平日好念《梁父吟》,常以琴瑟鼓之。又以管仲、乐毅自比。后来刘备三顾茅庐于此,他出山辅佐,终成为乱世当中的一代良相。
“少无世俗韵,性本爱山丘”的东晋诗人陶渊明辞官后归隐故里,过着躬耕自资,“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生活。从而写下了诸多影响深远的田园诗。
诗人王维卜居辋川,归隐山水田园之间。与孟浩然并称为“王孟”,成为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
北宋哲学家、易学家邵雍年少有志,读书隐居于苏门山百泉之上。邵雍少时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宋史·邵雍传》:“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邵雍一生不求功名,过着隐逸的生活。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十分敬仰他,常与之饮酒作诗,并买园宅供他居住,但他依此过着耕种自给的生活,名其居曰“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
北宋哲学家、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的张载曾讲学于关中横渠。他依靠着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整日讲学读书,“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半夜坐起,取烛以书……”张载讲学的地方前身为崇寿院,他年少时曾在此读书,晚年隐居后,一直在此兴馆设教。他逝世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将崇寿院改名为横渠书院。
明代有王守仁“悟道龙场”,民初有蓝川先生布衣自足,讲学于芸阁书院……
纵观自古以来有着自身成就且影响后世深远者,无不是恬淡素朴,耕读田园修身有为之博学志士。他们都保留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宝贵的精髓。
其实,天地之间就是一个大田园,万物之间无不可为耕,无不可为读。所谓耕者致力忘其犁,读者会意忘其卷,是乃耕读于天地自然之间矣。《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一耕一读于天地之间,就是养德归根于性命之学。因为,道从来就在最平淡之处。
如此,余生只伴南山一窗月光,半壁山房。几亩薄地,种些土豆瓜果,作四季食粮。闲时可于屋檐下品读一卷书、啜饮一杯茶;困时可于竹榻高卧一枕梦、惺忪一镜花;愁来秋雨浅酌一壶酒、一阕词;兴登松石闲看一山远、一轴画。脚踩大地眼望星空,日出而作乃耕,日落而息伴读。静观游鱼徘徊,独看飞鸟往返,仰头云聚云散,俯首花落花开……我自悠然。
正如唐代吕岩所作的一首《牧童》诗中所言“归来饭饱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的那种自在洒脱与闲适。
自沽村家酒,伴读五柳诗。春来满溪花,须堪折一枝。壶中待煮茗,乃取松上雪。夏有野径松,枕石且一眠。
粗茶淡饭之余与友人品茗闲叙,山风欲雨,庭院深几许,橙月朦胧,菊花夜露,鸟不语。松涛静谧,泉韵浅低,只堪听雨、只堪读山……
《问道》编辑部
用户评价
这本《问道·田园耕读》给我带来的冲击,与其说是来自情节的跌宕起伏,不如说是来自一种深沉的生活哲学,一种潜移默化的价值观。我常常在阅读过程中陷入沉思,作者对“道”的理解,并非是什么玄而又玄的理论,而是就体现在那一方方田园的耕耘与一卷卷古籍的诵读之中。他没有回避耕读生活中的艰辛与平凡,反而将其描绘得有声有色,正是这些平凡的日常,构成了生命的底色,也孕育着最深刻的真谛。我惊叹于作者如何能将如此朴素的生活描绘得如此富有哲理,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对生命本源的探求,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深刻感悟。书中的那些人物,他们的言行举止,看似简单,却蕴含着长久的智慧。他们如何面对风雨,如何珍惜点滴,如何从书中汲取力量,又如何将这份力量融入到日常的劳作中,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是否过于追求速成的、表面的东西,而忽略了那些需要时间沉淀、需要耐心耕耘才能收获的珍宝。这本书,就像一面古老的镜子,照出了我内心深处对真实、对宁静的渴望,也指引我看向那些被我忽略的、却又至关重要的生命意义。
评分这是一本让我沉醉其中的书,它不是用激烈的冲突和跌宕的情节来吸引我,而是用一种温润如玉的文字,描绘出一种深邃而宁静的生活哲学。《问道·田园耕读》让我看到了,原来生活可以如此贴近土地,如此回归本源。书中的人物,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的生活简单而充实,充满了劳动带来的满足感,也充满了阅读带来的精神上的富足。我被这种“耕读”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它是一种身体力行地去感受自然,去与自然和谐共处,同时,又是一种用知识和智慧来滋养心灵,来提升自我的方式。我能够感受到,作者笔下的人物,他们并非逃避现实,而是选择了一种更贴近生命本质的生活态度。他们从土地中汲取力量,从古籍中获得启迪,这种内在的力量,让他们能够从容地面对生活的风雨,能够从平凡中发现不凡。我开始反思,在追逐所谓“成功”的道路上,我们是否过于功利,是否忽略了内心的平和与精神的丰盈?这本书,就像一位智者,在我耳边轻语,告诉我,真正的富足,并非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充实与宁静。
评分《问道·田园耕读》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是一种久违的平静,一种对生命本源的追寻。作者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在远离尘嚣的田园中,人们如何通过辛勤的耕耘与土地建立联系,又如何通过诵读古籍与智慧相遇。这种“耕读”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一种对内心世界的关照。我能感受到,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淳朴生活带来的踏实感,也能体会到在繁忙的农事之余,捧卷阅读时的那种精神上的富足。书中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描绘,也尤为细腻。他们可能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他们的每一次耕耘,每一次读书,都饱含着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我仿佛能看到那些在田埂上辛勤劳作的身影,听到他们低声吟诵诗句的声音,感受到他们在那份宁静中获得的智慧与力量。这是一种非常接地气的“问道”,它不缥缈,不虚幻,而是深深扎根于泥土之中,扎根于平凡的生活之中。
评分初翻开《问道·田园耕读》,一股难以言喻的宁静便扑面而来,仿佛我已置身于那个遥远的、被时光遗忘的田园。作者用细腻入微的笔触,勾勒出一方朴实而充满诗意的土地,那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浮躁的追求,只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以及那份源自土地的厚重与淳朴。我仿佛能闻到泥土的芬芳,听到虫鸣鸟叫,感受到微风拂过脸颊的温柔。书中的人物,无论是勤劳耕作的农人,还是那些寄情山水、在田园中寻求解脱的隐士,都活灵活现,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开始反思自己身处现代社会中,被各种信息和欲望裹挟,早已丢失了多少与土地、与自然最本真的连接。书中所描绘的“耕读”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返璞归真的智慧。耕种,是与土地的对话,是收获的喜悦;而读书,则是与古圣先贤的交流,是心灵的滋养。这种双重的耕耘,让生命变得丰盈而有深度。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深入其中,去感受这份久违的宁静,去学习这份古老的智慧,去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看看是否能从中汲取力量,在纷繁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宁静的栖息地。
评分《问道·田园耕读》这本书,像一股清流,涤荡了我内心长久以来的浮躁与不安。我读到的,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力量,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在远离尘嚣的田园中,人们如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何通过耕种与土地建立深厚的连接,又如何通过读书与古圣先贤对话。这种“耕读”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一种对内心世界的关照。我能想象到,在那个宁静的环境中,人们的脚步会变得舒缓,他们的目光会变得深邃,他们的内心会充满一种踏实的宁静。书中对于人物情感的刻画,也尤为真挚动人。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但他们之间的亲情、友情,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都如同田园中的一草一木,真实而又充满生命力。我被这种朴素的情感所打动,它让我意识到,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往往就隐藏在最平凡的日常之中。这本书,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否过于沉溺于短暂的感官刺激,而忽略了那些能够滋养灵魂的、需要长期耕耘才能获得的满足感。
评分初次翻阅《问道·田园耕读》,便被其所营造的宁静氛围所深深吸引。作者以一种温婉而有力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田园画卷。我仿佛置身于那片淳朴的土地,感受着自然的韵律,聆听着生命的低语。书中所呈现的“耕读”生活,并非是简单的劳作与阅读,而是一种深刻的人生哲学,一种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智慧。我被书中人物的纯粹所打动,他们用双手耕耘着土地,用勤劳换取收获,同时,又在书本中汲取精神的养分,丰富着内心的世界。这种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滋养,让他们的生命散发出一种独特的光芒。我开始反思,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我们是否已经离这种最本真的生活太远?我们是否过于看重物质的堆砌,而忽略了精神的滋养?《问道·田园耕读》,就像一股清泉,滋润了我干涸的心灵,让我重新审视了“生活”的真正含义,以及如何在忙碌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力量。
评分这本《问道·田园耕读》让我领略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姿态。它不是那种贩卖焦虑、鼓吹成功的鸡汤文,也不是那种天马行空的幻想小说,而是一种对生活最本真状态的回归与探索。我看到了在田园中,人们如何用双手与土地对话,用辛勤的汗水换取丰收的喜悦;我又看到了他们如何用智慧与古人对话,从文字中汲取精神的养分,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耕”与“读”的结合,在我看来,是一种完美的平衡,它让身体与心灵都得到了滋养,让生命既有根基,又有高度。我被书中那些人物的韧性所打动,他们面对自然界的挑战,面对生活的起伏,总能保持一种平静而坚韧的态度。他们不是在对抗,而是在顺应,在与自然融为一体,在从古老的智慧中汲取化解难题的力量。我深切地感受到,作者并非只是在描绘一个理想化的田园生活,而是通过这种描绘,试图向读者传达一种深刻的人生哲理:真正的强大,并非来自外在的征服,而是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智慧的积累。这本书,让我重新思考了“成长”的意义,它并非总是向前奔跑,有时,停下脚步,回归本源,在耕读中沉淀,也是一种更深远的成长。
评分《问道·田园耕读》这本书,仿佛是一剂良药,治愈了我内心深处的浮躁和不安。我从中读到了一种对生命本真的尊重,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作者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田园生活中那些朴实无华的细节,从播种到收获,从日出到日落,每一个场景都充满了生命的气息。我仿佛能闻到泥土的清香,听到虫儿的低语,感受到阳光洒落的温暖。书中人物的“耕”与“读”,并非是简单的劳作和阅读,而是一种与土地的深度对话,一种与古圣先贤的精神交流。这种双重的耕耘,让他们的生命变得更加丰盈和深刻。我被书中人物的韧性所打动,他们面对自然的挑战,面对生活的起伏,总能保持一种平静而坚韧的态度。他们不是在对抗,而是在顺应,在与自然融为一体,在从古老的智慧中汲取化解难题的力量。这本书,让我重新思考了“成长”的意义,它并非总是向前奔跑,有时,停下脚步,回归本源,在耕读中沉淀,也是一种更深远的成长。
评分这本书,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将我带入了一个远离尘嚣的、充满诗意的田园世界。《问道·田园耕读》所传递的,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人生哲学。我被作者对于“道”的理解所深深吸引,这种“道”并非高不可攀的理论,而是就体现在那一方方土地的耕耘,和那一卷卷古籍的诵读之中。我仿佛能闻到泥土的芬芳,听到虫鸣鸟叫,感受到微风拂过脸颊的温柔。书中的人物,无论是勤劳的农人,还是寄情山水的隐士,都活灵活现,他们的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开始反思自己,身处现代社会,被各种信息和欲望裹挟,早已丢失了多少与土地、与自然最本真的连接。《问道·田园耕读》,让我重新审视了“耕”的意义,它是与土地的对话,是收获的喜悦;也让我体会了“读”的深度,它是与古圣先贤的交流,是心灵的滋养。这种双重的耕耘,让生命变得丰盈而有深度。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更深入地去感受这份久违的宁静,去学习这份古老的智慧,去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看看是否能从中汲取力量,在纷繁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宁静的栖息地。
评分《问道·田园耕读》带给我的,是一种心灵上的洗礼,一种久违的温暖。我读到的是一种对生活的虔诚,一种对自然的敬畏,一种对知识的渴望,这些看似简单的元素,在作者的笔下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面。我能感受到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淳朴生活带来的踏实感,也能体会到在繁忙的农事之余,捧卷阅读时的那种精神上的富足。书中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描绘尤为细腻,他们可能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他们的每一次耕耘,每一次读书,都饱含着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我仿佛能看到那些在田埂上辛勤劳作的身影,听到他们低声吟诵诗句的声音,感受到他们在那份宁静中获得的智慧与力量。这是一种非常接地气的“问道”,它不缥缈,不虚幻,而是深深扎根于泥土之中,扎根于平凡的生活之中。我开始反思,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我们是否已经离这种最本真的生活太远?我们是否过于看重物质的堆砌,而忽略了精神的滋养?这本书,就像一股清泉,滋润了我干涸的心灵,让我重新审视了“生活”的真正含义,以及如何在忙碌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力量。
评分看得此书,人望出尘
评分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
评分还没来得及看
评分有趣可读
评分正版全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
评分正版!不错!
评分看得此书,人望出尘
评分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正版全新
评分还没来得及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