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王德威作为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在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方面具有较深造诣,特别是在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方面富有开创性意义。
2.开篇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曾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一条新径。
内容简介
《想象中国的方法》是哈佛大学学者王德威颇具代表性和开拓性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论文集。他从狎邪、科幻、公案、谴责、翻译等晚清小说谈起,探讨晚清文学的开创性,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著名论断;通过合观鲁迅、沈从文的作品以展现中国写实文学的美学与道德尺度之间的对话,通过《骆驼祥子》颠覆性的闹剧手法来展示“人道主义写实作家”老舍对现实主义的对抗,借此研究现代小说名家与现实主义的关联;同时以张爱玲为引,呈现了女作家以写实为基础却又独创一“鬼蜮世界”的独特想象。二十世纪以来,小说记录并反映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现象。小说中的涕泪飘零、嬉笑怒骂,看似与中国命运无甚攸关,却往往反映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少为人注意的真切现实。本书将叙事理论与历史议题相连接,希望借此扩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
作者简介
王德威,生于1954年,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在台湾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校任职。现为美国哈佛大学学者。著有《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当代小说二十家》等。
目录
新版序
序:小说中国
辑一
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寓教于恶——三部晚清狎邪小说
贾宝玉坐潜水艇——晚清科幻小说新论
《老残游记》与公案小说
“谴责”以外的喧嚣——试探晚清小说的闹剧意义
“说话”与中国白话小说叙事模式的关系
翻译“现代性”——论晚清小说的翻译
辑二
从“头”谈起——鲁迅、沈从文与砍头
“母亲”,你在何方?——论巴金的一篇奇情小说
荒谬的喜剧?——《骆驼祥子》的颠覆性
做了女人真倒楣?——丁玲的“霞村”经验
半生缘,一世情——张爱玲与海派小说传统
辑三
从老舍到王祯和——现代中国小说的笑谑倾向
女作家的现代“鬼”话——从张爱玲到苏伟贞
原乡神话的追逐者——沈从文、宋泽莱、莫言、李永平
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力与“张派”作家的超越之路
潘金莲、赛金花、尹雪艳——中国小说世界中“祸水”造型的演变
华丽的世纪末——台湾?女作家?边缘诗学
辑四
历史?小说?虚构
现代文学史理论的文、史之争——以近代中国政治小说的研究为例
现代中国小说研究在西方
想象中国的方法——海外学者看现、当代中国小说与电影
世纪末的中文小说——预言四则
精彩书摘
《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我所谓的晚清文学,指的是太平天国前后,以至宣统逊位的六十年,而其流风遗俗,时至“五四”,仍体现不已。在这一甲子内,中国文学的创作、出版及阅读蓬勃发展,真是前所未见。而小说一跃而为文类的大宗,更见证了传统文学体制的巨变。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推陈出新、千奇百怪的实验冲动,较诸“五四”,毫不逊色。然而中国文学在这一阶段现代化的成绩,却未尝得到重视。当“五四”“正式”引领我们进入以西方是尚的现代话语范畴,晚清那种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现象,反倒被视为落后了。
晚清文学的发展,当然以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为高潮。仅以小说为例,保守地估计,出版当在两千种以上。其中至少一半,今已流失。这些作品的题材、形式,无所不包:从侦探小说到科幻奇谭,从艳情纪实到说教文字,从武侠公案到革命演义,在在令人眼花缭乱。它们的作者大胆嘲弄经典著作,刻意谐仿外来文类,笔锋所至,传统规模无不歧义横生,终而摇摇欲坠。以往“五四”典范内的评者论赞晚清文学的成就,均止于“新小说”——梁启超、严复等人所提倡的政治小说。殊不知“新小说”内包含多少旧种子,而千百“非”新小说又有多少诚属空前的创造力。
而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看,晚清文人的大举创造或捏造与制造小说的热潮,亦必要引起文学生态的巨变。这是一个华洋夹杂、雅俗不分的时期,而读者不论有心无心,也乐得照单全收。中国现代文学的大规模量贩化、商业化,非自今始。称小说为彼时最重要的公众想象领域,应不为过。借着阅读与写作小说,有限的知识人虚拟家国过去及未来的种种,而非一种版图,放肆个人欲望的多重出口。比起“五四”之后日趋窄化的“感时忧国”正统,晚清毋宁揭示了更复杂的可能。
晚清的最后十年里,至少曾有一百七十余家出版机构此起彼落;照顾的阅读人口,在二百万到四百万之间。而晚清最重要的文类——小说——的发行,多经由四种媒介:报纸、游戏、刊物、杂志与成书。中国最早的报纸《申报》(1872—1949)于1870年,即有名为《瀛寰琐记》的文学专刊出版,发表诗文说部创作或翻译。到了1892年,由韩邦庆(1856—1894;《海上花列传》作者)一手包办的《海上奇书》出版,是为现代小说专业杂志的滥觞。同时,在标榜“游戏”及“清闲”的风月小报上,小说也觅得一席之地。这些刊物可查者仍有32种之多;晚清红极一时的作者如吴趼人(1866—1910)、李伯元(1867—1906),都是由此起家。而在梁启超提倡“新小说”的热潮后,更有30余家小说出版社,以及21种以“小说”为名的期刊出现。其中最著名的,即所谓《新小说》《月月小说》《绣像小说》《小说林》“四大”小说杂志。
晚清也是翻译文学大盛的时代。阿英早已指出晚清的译作不在创作之下;近年学者陈平原就此统计,一八九九至一九一一年间,至少有六百一十五种小说曾经译介至中国。狄更斯、大小仲马、雨果、托尔斯泰等均是读者耳熟能详的名字。至于畅销作家,则有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感伤奇情作家哈葛德,以及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名列前茅。
但我们对彼时文人“翻译”的定义,却需稍作厘清:它至少包括意译、重写、删改、合译等方式。学者如史华兹(Schwartz)、夏志清及李欧梵曾各以严复、梁启超及林纾为例,说明晚清译者往往借题发挥,所译作品的意识及感情指向,每与原作大相径庭。不仅此也,由着这些有意或无意的误译或另译,晚清学者已兀自发展出极不同的“现代”视野。以此类推,晚清作者对传统古典的新奇诠释,也是另一种以志逆意的“翻译”。
西洋文学的影响,一向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主要关目。此一方面的研究,亦犹待加强。但就在作者、读者热烈接受异国译作,作为一新耳目的蓝本时,传统说部早已产生质变。当《荡寇志》(1853)成为太平天国时期,清廷及太平军文宣战争的焦点时,小说与政治的主从关系,迈入了新的“技术”模式。当《品花宝鉴》以男女易装的观点,混淆异性及同性恋爱的界限时,小说与情色主体的辩证,也变得益发繁复。几乎所有经典说部均在此时遭到谐仿。这也许是作者自甘颓废、惫懒因袭的征兆,但更可能是他们不耐传承藩篱,力图颠覆窠臼的信号。
不仅此也,清末重被发掘的稍早作品,沈复的《浮生六记》及张南庄的《何典》,更具有在文学传统以内另起炉灶的意义。《浮生六记》描摹情性自主的向往、《何典》夸张人间鬼蜮的想象,对二十世纪作家的浪漫或讽刺风格,各有深远影响。《何典》依循以往话本小说生鲜活泼的世俗叙述,并点染极具地域色彩的吴语特征,自然可视为“五四”白话文学的又一先导。凡此皆说明“新小说”兴起前,中国说部的变动已不能等闲视之。西方的冲击并未“开启”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是使其间转折,更为复杂,并因此展开了跨文化、跨语系的对话过程。这一过程才是我们定义“现代性”的重心。
……
前言/序言
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 目录 第一章:穿越历史的迷雾——中国历史的叙事建构 1.1 史学传统的演变与“正史”的生成 1.2 地方志、笔记小说中的“民间史”视角 1.3 现代史学观念的引入与中国历史书写的转型 1.4 历史的“再现”与“建构”:叙事的力量 第二章:虚构的时空织锦——中国小说的创作实践 2.1 从志怪、传奇到章回体:小说叙事形式的演进 2.2 小说中的“想象”与“写实”:人物、情节与主题的塑造 2.3 文人小说、世情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差异与融合 2.4 现代小说浪潮:西方叙事技巧与中国本土传统的碰撞 2.5 晚明小说中的“异化”与“反思” 第三章:叙事的多重奏——历史与小说的互动交织 3.1 历史事件在小说中的变形与再演绎 3.2 小说对历史认知的塑造与影响 3.3 历史人物在小说中的“陌生化”与“再创造” 3.4 叙事模式的迁移:历史叙事中的小说化倾向,小说叙事中的历史化意识 3.5 批判性叙事:质疑与重估历史 第四章:想象的疆域——关于“中国”的文化建构 4.1 经典文本中的“中国”形象 4.2 图像、艺术与“中国”的视觉想象 4.3 语言、概念与“中国”的意义体系 4.4 身份认同的生成与流变 4.5 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想象 第五章:叙事的未来——当代中国文学与历史观的再探索 5.1 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趋势 5.2 “后真相”时代与历史叙事的挑战 5.3 新媒体与叙事形式的变革 5.4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叙事 5.5 想象与反思:通往更深邃理解的路径 --- 正文 第一章:穿越历史的迷雾——中国历史的叙事建构 中国历史的叙事,宛如一条蜿蜒流淌的长河,承载着千百年的兴衰更迭,也镌刻着无数王朝的功过是非。然而,这条长河并非自然流淌的纯粹客观记录,而是经过一代代史官、文人、甚至普通民众的精心编织与诠释。本章将深入探讨中国历史叙事的建构过程,揭示其背后蕴含的复杂逻辑与深刻含义。 1.1 史学传统的演变与“正史”的生成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自《尚书》的“书言事”以来,便奠定了以纪事为核心的传统。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官修史书——“正史”——成为叙述国家历史的主流。从《史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抱负,到《汉书》的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模式,再到《后汉书》、《三国志》的精炼与聚焦,历代史家在前人基础上不断探索与创新,试图以更为系统、权威的方式记录国家的过去。 “正史”的编纂,其目的并非仅仅是客观还原历史的真相,更蕴含着政治伦理、王朝合法性论证的强大能量。史官们在叙事中,往往遵循着“春秋笔法”,通过对史事的褒贬、详略, subtly 地传达着统治者的意志与价值观。例如,对亡国之君的“恶评”或对开国之君的“溢美之词”,都是叙事建构的重要手段。这种叙事逻辑,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认知。 “正史”的生成,也伴随着严谨的考证与史料的筛选。史官们需要查阅大量的官方档案、诏令、奏章,并结合口述、碑刻等材料,力求叙事的真实性。然而,这种真实性本身,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史官个人立场、以及社会观念的制约。因此,“正史”固然是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基石,但其叙事背后隐藏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也必须被我们审慎地辨析。 1.2 地方志、笔记小说中的“民间史”视角 相较于“正史”的宏大叙事与政治意图,“地方志”和“笔记小说”则提供了更为丰富多样的“民间史”视角。 “地方志”,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的史书,通常记录着当地的风土人情、地理沿革、人物传记、灾荒记载等。虽然其篇幅和影响力不及“正史”,但它以微观的视角,填补了国家史书的空白,展现了中国广阔地域内社会生活的细节与地方特色。许多在“正史”中被忽略的普通人、小事件,在地方志中得以保存,成为研究社会史、民俗史的宝贵资料。 “笔记小说”,则更是将叙事的主体从朝堂转向了街巷,从帝王将相转向了士人、商贾、乃至市井百姓。这些以笔记形式流传下来的篇章,内容包罗万象,既有神怪志异、轶闻趣事,也有人事纠葛、社会风俗的白描。虽然许多笔记小说带有浓厚的虚构色彩,但其中折射出的社会现实、人情世态,以及人们的普遍情感与道德观念,却为我们理解历史的“另一面”提供了独特的窗口。它们以更为鲜活、生动的语言,展现了历史的温度与人性的复杂,是对“正史”理性叙事的有力补充。 1.3 现代史学观念的引入与中国历史书写的转型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史学观念的传入,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等著作,引入了科学实证、进化论等新思想,鼓励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 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书写开始发生深刻的转型。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受到挑战,新的史学体例不断涌现。史学研究的范围也空前拓展,从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拓展到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多个领域。同时,以科学方法为指导,对史料进行严谨的考证、辨伪,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环节。 学者们开始运用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对历史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例如,王国维通过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将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数千年,将文献记载与考古证据相结合,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梁启超等学者,积极倡导“新史学”,强调历史应服务于现实,启迪民智,促进国家富强。 这种转型,不仅改变了历史叙事的语言和逻辑,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方式,将中国历史的研究推向了更为科学、客观、多元的轨道。 1.4 历史的“再现”与“建构”:叙事的力量 在深入探讨中国历史叙事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区分“历史的再现”与“历史的建构”这两个层面。 “历史的再现”,是历史学家试图尽最大可能地接近历史真相,通过严谨的考证与分析,将过去的事实还原出来。这需要对史料进行细致的解读,理解其产生的语境,并力求客观公正地呈现。 然而,任何叙事都无法完全摆脱“建构”的痕迹。“历史的建构”,是指我们在叙述历史时,无法避免地会受到自身所处时代、文化背景、个人价值观念以及叙事目的的影响。我们选择讲述哪些故事,如何讲述,关注哪些人物,强调哪些事件,这些选择本身就构成了对历史的“建构”。 例如,在不同时代,人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解读可能截然不同。唐朝人对安史之乱的叙述,可能侧重于政治动荡与民族融合;而现代历史学家,则可能更关注其对社会经济、人口结构、以及文化交流的长远影响。这种“建构”并非简单的歪曲,而是对历史意义的不断再诠释与再发现。 因此,理解中国历史的叙事,需要我们既要看到史学工作者在“再现”历史真相上的努力,也要认识到“建构”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叙事的力量,在于它不仅传递信息,更重要的是,它塑造着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影响着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并最终指向我们对未来的想象。 第二章:虚构的时空织锦——中国小说的创作实践 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艺术史,也是一部反映时代变迁、人心浮动的生动画卷。从早期零散的志怪笔记,到结构宏大的章回小说,再到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中国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与丰富的想象力,构建了一个又一个虚构的艺术时空,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欲望、思考与梦想。 2.1 从志怪、传奇到章回体:小说叙事形式的演进 中国小说的早期形态,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志怪”与“传奇”。《山海经》、《搜神记》等作品,以神怪异事为题材,充满了奇幻色彩,展现了古人对未知世界的想象与敬畏。这些作品篇幅短小,叙事松散,但它们奠定了中国小说中“虚构”的基石。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与“传奇”开始兴盛。“志人小说”如《世说新语》,记录士人的言行风尚,以精炼的语言展现人物的个性与智慧。而“传奇”,如唐传奇《李娃传》、《莺莺传》,则开始走向更为复杂的情节与更为鲜活的人物塑造,在叙事结构上有了初步的发展,为后世小说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唐宋以后,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通俗小说的创作也日渐活跃。宋元话本,作为说书人的底本,篇幅渐长,结构也更加完整,开始出现一些初步的“母题”与“情节模式”。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小说迎来了其黄金时代,涌现出大量结构宏大、内容丰富的章回体小说。这些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以其宏大的叙事框架、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的情节设计,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章回体小说的叙事结构,往往以“回”为单位,每一回都有相对独立的情节,又服务于整体的叙事线索。这种结构,使得叙事能够延展得更长,人物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展现,情节也能够更加跌宕起伏。作者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描写,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以及对人生哲理的探讨,构建了一个个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世界。 2.2 小说中的“想象”与“写实”:人物、情节与主题的塑造 在中国小说创作中,“想象”与“写实”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常常交织融合,共同塑造着小说的人物、情节与主题。 “想象”,是中国小说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从神话传说中的奇幻生物,到传奇故事中的侠肝义胆,再到章回小说中的情节转折与人物命运的安排,想象力始终是中国小说创作的重要驱动力。这种想象力,既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也是对现实世界的观照。它能够突破时空的限制,呈现出更为广阔、更为深刻的艺术图景。 “写实”,则是中国小说另一条重要的创作脉络。许多小说,特别是世情小说,力求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刻画人物的性格,揭示人性的复杂。例如,《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下文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了辛辣的讽刺,《醒世姻缘传》则细致地描绘了市井生活与家庭关系。 人物的塑造,是中国小说中最具魅力的部分。小说家们通过对人物的外貌、语言、行动、心理的描写,以及人物之间的互动,构建出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既有作者的理想寄托,也有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性格特征。例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其敏感、多愁善感,既是艺术想象的产物,也触及了许多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 情节的设计,是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中国小说善于运用巧合、冲突、悬念等手法,使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聚义过程,充满了戏剧性的冲突与巧妙的安排。而《三国演义》中无数场精彩绝伦的战争描写,更是将想象力与历史的宏大叙事相结合。 主题的探讨,使中国小说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无论是对国家兴衰的忧思,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对人生际遇的感叹,还是对爱情、亲情的描摹,都使小说超越了单纯的娱乐功能,成为承载社会思考与人生智慧的艺术载体。 2.3 文人小说、世情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差异与融合 中国小说史上,存在着文人小说、世情小说与通俗小说等不同的类型,它们各有特点,又常常相互影响、彼此融合。 “文人小说”,通常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创作,语言典雅,意境深远,注重艺术技巧与思想内涵。唐传奇、明清的“拟话本”及一些“才子佳人”小说,都带有文人小说的色彩。它们往往关注士人的情感世界、人生境遇,或寄托作者的理想情怀。 “世情小说”,则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对市井生活、人情世故进行细致入微的描绘。明清的《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是世情小说的代表。它们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风貌,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阴暗面。 “通俗小说”,则以其广泛的受众基础和更为直白的叙事风格而著称。宋元话本、明清的“公案小说”、“侠义小说”等,都属于通俗小说的范畴。它们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善于抓住读者的兴趣,但也常常在艺术性上稍显逊色。 然而,这种分类并非绝对。许多作品同时兼具不同类型的特点。例如,《红楼梦》虽然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但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与精湛的艺术技巧,使其超越了简单的“文人小说”范畴,同时其对贾府兴衰的描绘,又充满了世情小说的现实感。 这种差异与融合,丰富了中国小说的艺术面貌,也使得小说在不同社会阶层与文化群体中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与接受。 2.4 现代小说浪潮:西方叙事技巧与中国本土传统的碰撞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西方现代小说思潮与叙事技巧的引入,给中国小说创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西方小说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思潮,以及其在人物心理刻画、情节结构设计、视角运用等方面的技巧,深刻影响了中国作家。例如,鲁迅借鉴了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创作了《呐喊》、《彷徨》等小说,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先河。巴金、茅盾、老舍等作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西方小说的营养,创作出了一批反映时代、反映现实的优秀作品。 然而,中国现代小说并非全盘西化。中国作家在借鉴西方叙事技巧的同时,也努力将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审美情趣与叙事经验融入其中。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人物塑造方式、以及对意境的追求,都在现代小说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延续与发展。 这种碰撞与融合,使得中国现代小说既具有了现代性,又保持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它既是对西方文学的借鉴,也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传承与创新。中国小说,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展现出了新的生命力。 2.5 晚明小说中的“异化”与“反思” 晚明时期,是中国小说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作品,在“想象”与“写实”的结合上,呈现出一些独特的“异化”与“反思”的倾向。 “异化”,体现在作品中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以及对人性的复杂性的深入挖掘。例如,《金瓶梅》中对潘金莲、西门庆等人物的刻画,突破了传统道德的束缚,展现了人性的贪婪、欲望与扭曲。《醒世姻缘传》中,对传统性别观念的颠覆,以及对社会不公的讽刺,也显露出强烈的“异化”色彩。 “反思”,则体现在作品中对人生、社会、乃至政治的深刻思考。晚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解放,使得人们开始质疑传统的权威,反思人生的意义。《红楼梦》虽然创作于清代,但其对封建大家族衰败的描绘,对青春美好的毁灭,以及对人生无常的感叹,却与晚明时期的一些思潮有着内在的联系。 这些“异化”与“反思”,使得晚明时期的许多小说,在艺术上更加大胆、深刻,在思想上更具批判性。它们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迷茫、挣扎与思考,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性提供了珍贵的文学佐证。 第三章:叙事的多重奏——历史与小说的互动交织 历史与小说,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形式,却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构建起中国人理解世界、认识自我的独特图景。本章将深入探讨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互动交织,揭示它们之间复杂的共生关系。 3.1 历史事件在小说中的变形与再演绎 历史事件,是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库。然而,当历史事件被纳入小说的叙事框架时,它们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形与再演绎。 例如,《三国演义》虽然以历史上的三国时期为背景,但其中许多情节、人物形象,都经过了作者罗贯中的艺术加工与再创作。关羽的忠义勇武被放大,诸葛亮的智慧被神化,曹操的奸雄形象被固化。这些变形,并非仅仅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娱乐需求,更是作者为了突出主题、塑造人物、以及传递某种价值观而进行的有意为之。 历史事件的“变形”,往往体现在对事件的因果链条的重塑,对人物动机的重新解读,以及对事件最终结局的模糊或强化。小说家们并非历史学家,他们关注的更多是故事性、人物的命运以及情感的张力。因此,历史事件在小说中,往往被提炼、简化,或者被赋予更为戏剧化的色彩,以更好地服务于小说的整体叙事。 这种“再演绎”,使得历史事件在小说中,呈现出一种新的生命力。它们不再是冰冷的史实,而是被赋予了情感、意义与象征,成为读者能够感知、理解并产生共鸣的艺术形象。 3.2 小说对历史认知的塑造与影响 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易懂的叙事形式,其对大众历史认知的塑造与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许多读者,特别是缺乏专业历史知识的普通民众,往往是通过小说来接触和理解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例如,《三国演义》的影响力之深远,使得其中塑造的许多人物形象,如诸葛亮、关羽,成为了中国人心中不可磨灭的英雄符号,甚至影响了人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真实认知。 小说所传递的历史观,往往带有鲜明的立场与价值判断。例如,许多历史小说倾向于宣扬忠君爱国、替天行道的价值观,塑造正面英雄形象,批判奸臣恶人。这种叙事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教化作用,但也可能简化历史的复杂性,固化片面的历史认知。 随着时代的发展,小说对历史的解读也发生了变化。一些现代历史小说,开始挑战传统的历史叙事,从更微观、更人性的角度去审视历史事件与人物,引发读者对历史的重新思考。例如,一些小说会关注战争中的普通士兵,或者描写历史事件中被忽略的边缘人物,从而呈现出更为丰富、多维的历史画面。 3.3 历史人物在小说中的“陌生化”与“再创造” 历史人物,是小说创作的另一重要源泉。然而,当历史人物被纳入小说的叙事时,他们便不可避免地会经历“陌生化”与“再创造”的过程。 “陌生化”,是指小说家们试图打破读者对历史人物的既有认知,从新的角度去审视他们。例如,一些小说可能会描绘历史人物的另一面,揭示他们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或者将他们置于意想不到的情境中,从而产生一种“陌生感”。 “再创造”,则意味着小说家们在保留历史人物基本身份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小说的需要,对其性格、经历、动机进行虚构与填充。例如,杜撰人物的内心独白,设定其与小说中虚构人物的互动,或描绘其在小说设定的特定情境下的反应。 这种“陌生化”与“再创造”,使得历史人物在小说中,获得了新的生命。他们不再是教科书上僵化的符号,而是变得有血有肉,充满情感与复杂性。这种艺术加工,虽然可能与历史事实存在差异,但却能够使人物更加鲜活,更具艺术感染力,并引发读者对人性和历史的深入思考。 3.4 叙事模式的迁移:历史叙事中的小说化倾向,小说叙事中的历史化意识 在历史与小说的互动中,还存在着一种有趣的现象:叙事模式的迁移。 “历史叙事中的小说化倾向”,是指在历史学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借鉴小说的叙事技巧,以增强历史叙事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例如,在描写历史事件时,运用生动的语言,设置悬念,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使历史叙事更加具有故事性。这种“小说化”的趋势,并非是对历史真相的背离,而是为了更好地吸引读者,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历史。 “小说叙事中的历史化意识”,是指小说家们在创作时,越来越重视对历史背景的尊重与考证,努力使小说中的情节、人物、环境与历史真实相契合。一些小说家,在创作历史小说时,会进行大量的史料研究,力求在虚构的情节中,注入历史的真实感。这种“历史化”的意识,使得小说更加具有深度与厚度,能够引发读者对历史的关注与思考。 这种叙事模式的迁移,表明历史与小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处于一种动态的互动之中。它们相互借鉴,相互启发,共同丰富了中国叙事艺术的宝库。 3.5 批判性叙事:质疑与重估历史 在历史与小说的互动中,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是“批判性叙事”的兴起。这种叙事,不再仅仅是对历史的简单呈现或美化,而是积极地质疑与重估历史。 批判性叙事,体现在对传统历史叙事的挑战,对被遮蔽的真相的挖掘,以及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重新解读。例如,一些小说会聚焦历史中的受害者,揭示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痛苦与挣扎,从而颠覆传统的英雄史观。另一些小说,则会从多角度、多视角展现历史事件,展现其复杂性与矛盾性,引导读者对历史产生更深的思考。 这种“批判性叙事”,对于打破固有的历史认知,促进历史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它鼓励我们不盲从权威,不沉溺于过去的辉煌,而是以更加理性和审慎的态度,去审视历史,从中汲取智慧,警醒未来。 第四章:想象的疆域——关于“中国”的文化建构 “中国”,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政治实体,更是一个深邃而复杂的文化符号,它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迁,在无数的想象与叙事中不断被建构、被重塑。“想象的疆域”一章,将深入探讨“中国”这一概念的文化建构过程,揭示其背后蕴含的多元视域与时代印记。 4.1 经典文本中的“中国”形象 中国经典的文学、哲学、历史文本,构成了早期“中国”形象的基石。从《诗经》中对风土人情的描绘,到《论语》中对仁义礼智信的阐释,再到《史记》中对王朝更迭的记载,这些文本共同勾勒出一个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家国天下为价值取向的“中国”轮廓。 《尚书》中的“华夏”,《周礼》中的“天下”,《尚书·尧典》中的“四海之内,咸戴元功”,都体现了早期中国统治者对于国家疆域与政治秩序的想象。这些文本,通过对“中央之国”的定位,以及对周边民族的“化外”或“羁縻”的处理,构建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地理观念。 《论语》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将个人品德的修养与国家治理紧密联系起来,塑造了一个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国”形象。而《道德经》中的“道法自然”,《庄子》中的“逍遥游”,则提供了另一种关于“中国”的精神寄托,一种超然物外、追求精神自由的想象。 《史记》等正史,则通过对帝王将相的生平事迹的叙述,构建了一个以历史为载体、以王朝兴衰为脉络的“中国”叙事。它们强调秩序、正统与合法性,塑造了一个以强大中央集权为特征的政治“中国”形象。 这些经典文本,通过语言、观念、价值判断的不断重复与强化,为“中国”这一概念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在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国人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4.2 图像、艺术与“中国”的视觉想象 除了文本叙事,“中国”的视觉想象,也同样丰富且多元。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艺术形式,通过其独特的视觉语言,将抽象的“中国”具象化,并传递出不同的文化意涵。 山水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门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其精细的笔触,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展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市井“中国”。而王蒙的《溪山行旅图》,则以其宏伟的山峦、渺小的人物,营造出一种天人合一、壮丽雄浑的自然“中国”意境。这些山水画,不仅是对自然景色的描绘,更是对中国士人心灵境界的寄托,是一种将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中国”想象。 佛教艺术,如敦煌壁画、龙门石窟等,将外来的宗教信仰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佛教“中国”形象。佛陀的慈悲、菩萨的庄严,以及飞天的曼妙,都成为“中国”文化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典建筑,如北京故宫、苏州园林等,则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展现了“中国”的秩序感、对称美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宫殿的威严,园林的精巧,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哲学。 这些视觉艺术,通过直观的图像,将“中国”的审美情趣、哲学理念、社会生活等多重面向呈现出来,与文本叙事相互补充,共同构建起我们对于“中国”的丰富想象。 4.3 语言、概念与“中国”的意义体系 语言,是承载与构建文化的最重要载体。汉语的特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体系,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意义建构。 汉字的象形、指事、会意等造字方法,使得汉语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例如,“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核心概念,在汉语中有着明确而深刻的表达,它们构成了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核心。 “天人合一”、“阴阳五行”、“道法自然”等哲学概念,则构成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基石,它们影响着中国人对宇宙、生命、社会的理解。 “家国天下”的观念,将个体与家庭、国家、天下紧密联系起来,塑造了一种强烈的集体主义与家国情怀。“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则强调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 语言的模糊性与灵活性,也为“中国”的意义建构提供了空间。例如,“中国”一词的内涵,既可以指代一个地理疆域,也可以是一个文化概念,甚至可以是一种身份认同。这种多义性,使得“中国”的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下,不断被重新阐释与丰富。 4.4 身份认同的生成与流变 “中国”身份认同的生成与流变,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过程。它并非天然存在,而是通过历史的进程、文化的传播、以及个体的经验而不断形成的。 在古代,“中国”的身份认同,更多地与地域、文化、语言等因素相关联。生活在中原地区,使用汉字,遵循儒家礼仪,被认为是“中国人”。而边疆民族,则往往被视为“蛮夷”。 随着民族融合与国家疆域的变迁,这种身份认同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元朝、清朝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使得“中国”的疆域范围大大拓展,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与身份认同的挑战。 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得“中国”身份认同更加明确和强化。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这种身份认同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它需要与多元文化相适应,另一方面,它也需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 “中国人”的身份,既是血缘的传承,也是文化的认同,更是对“中国”这一复杂概念的共同想象与实践。 4.5 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想象 当“中国”被置于跨文化语境中时,它便会成为一种被“他者”观看的对象,并在此过程中,产生新的“中国”想象。 西方对“中国”的想象,经历了从“东方神秘主义”到“龙的传人”,再到“中国威胁论”等不同阶段。这些想象,既有对中国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的赞叹,也有对中国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的误解与偏见。 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崛起,以及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力度加大,“中国”的跨文化想象也日益多元与复杂。它既包含了对他者的观察与解读,也反映了中国自身在与外部世界互动中的自我认知与价值输出。 这种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想象,既是对“中国”概念的拓展与丰富,也是对我们自身文化的反思与审视。它提醒我们,在理解“中国”时,必须兼顾内外的视角,警惕刻板印象,寻求更为真实与全面的认知。 第五章:叙事的未来——当代中国文学与历史观的再探索 时代在变,社会在发展,叙事的方式与内容也在不断演进。当代中国文学,正以其独特的视角与方法,对历史进行着再探索,并不断拓展着“想象的疆域”。本章将探讨当代中国文学在历史叙事方面的最新趋势,以及其面临的挑战与未来走向。 5.1 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趋势 当代历史小说,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展现出新的创作趋势。 微观叙事与个体命运的关注: 相较于宏大叙事,当代历史小说更倾向于关注历史事件中的个体命运,挖掘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选择与生存。例如,对战争中的士兵、政治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或改革开放中的普通人的刻画,都展现出对历史的温情与人性关怀。 叙事视角的多元化: 打破单一的宏大叙事视角,采用多元化的叙事角度,如女性视角、边缘人群视角、甚至非人视角,来呈现历史。这使得历史的解读更加丰富、细腻,也更加贴近真实。 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一些作家不再满足于简单地复述历史,而是积极地对历史真相进行追问,质疑传统的历史叙事,探讨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与争议性。这种反思,往往带有对社会现实的关照,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忧思。 类型化的融合与创新: 将历史叙事与科幻、悬疑、魔幻现实主义等类型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叙事形式。例如,一些作品在历史背景下融入科幻设定,探讨历史与科技的互动;另一些作品则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历史事件的荒诞与象征意义。 5.2 “后真相”时代与历史叙事的挑战 “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为历史叙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爆炸、真假难辨的媒介环境,使得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认知变得更加复杂。 历史虚无主义的风险: 面对海量信息,一些人可能倾向于对所有历史叙事都持怀疑态度,甚至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的价值与意义。 碎片化信息的误读: 社交媒体等平台传播的历史信息往往是碎片化的,容易被断章取义,导致对历史事件的误读与片面理解。 情感宣泄取代理性思考: 在“后真相”时代,情绪化的表达往往比理性分析更容易获得关注,这可能导致历史讨论走向极端,缺乏建设性。 当代中国文学,在应对这些挑战时,需要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用严谨的史料考证支撑叙事,用深刻的思想洞察引导读者,同时也要警惕过度煽情或迎合大众情绪的倾向。 5.3 新媒体与叙事形式的变革 新媒体的兴起,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叙事的形式与传播方式。 互动式叙事: 网络文学、短视频等形式,允许读者更直接地参与到叙事中,甚至影响叙事的走向。这种互动式叙事,为历史故事的传播带来了新的可能。 多模态叙事: 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多种媒介形式的融合,使得叙事更加生动、立体。例如,一些历史纪录片或基于历史题材的短剧,能够更直观地呈现历史场景。 碎片化传播与即时性: 新媒体的传播特点,使得信息传播更加碎片化和即时性。这要求叙事者在短时间内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并以简洁、有力的方式传达信息。 然而,新媒体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如信息过载、浅层阅读等,这要求叙事者在追求形式创新的同时,也要注重内容的深度与思想性。 5.4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叙事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叙事正面临着走向世界的机遇与挑战。 文化输出的努力: 中国作家、出版机构积极推动中国文学走向国际,通过翻译、版权合作等方式,将中国的历史故事、文化内涵介绍给世界。 跨文化理解的障碍: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可能存在差异。如何克服语言、文化、历史认知上的障碍,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是重要的课题。 “中国故事”的国际化表达: 如何用国际读者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是叙事者需要思考的问题。这涉及到叙事方式、价值观的转化与融合。 5.5 想象与反思:通往更深邃理解的路径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叙事的形式如何创新,想象与反思,始终是理解历史、认识“中国”的根本路径。 以想象力穿越时空: 想象力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通过想象,我们可以重现历史场景,感受人物情感,从而对历史产生更深刻的体悟。 以反思精神审视历史: 反思,是对历史的理性辨析与批判。它鼓励我们不盲从,不偏信,而是以开放的姿态,去审视历史的得失,汲取教训,为未来提供启示。 文学的独特价值: 文学,以其独特的方式,将历史的宏大叙事与人性的复杂情感相结合,展现了历史的温度与深度。它能够触及读者的灵魂,引发共鸣,并最终促成对历史更深邃的理解。 当代中国文学,在继承与创新中,不断探索着历史叙事的未来。通过不断的想象与反思,我们有望构建出更加丰富、多元、深刻的“中国”叙事,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过去,也更好地塑造我们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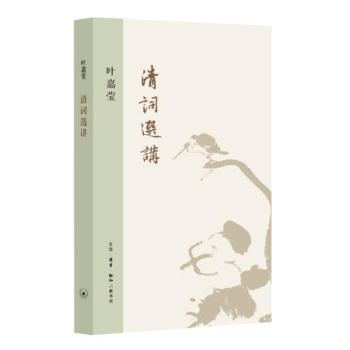


![小桔灯(冰心后人监制,冰心研究会会长、冰心文学馆馆长推荐。)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74774/577335a4N5062460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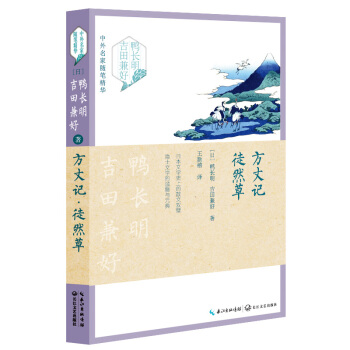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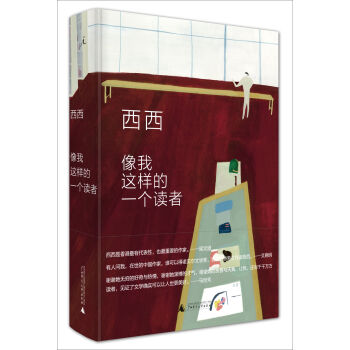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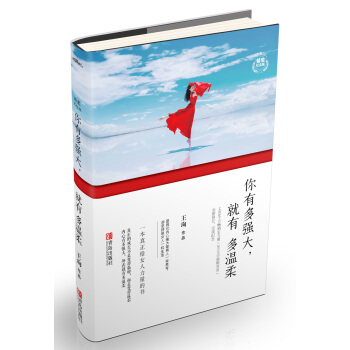
![众声 [The Soun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30149/586efabfN7393925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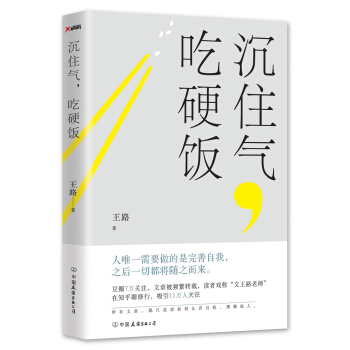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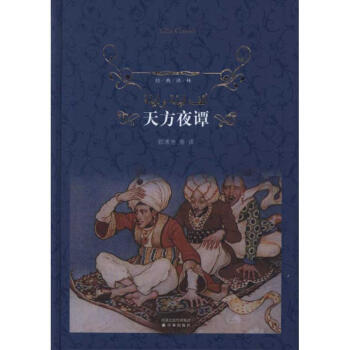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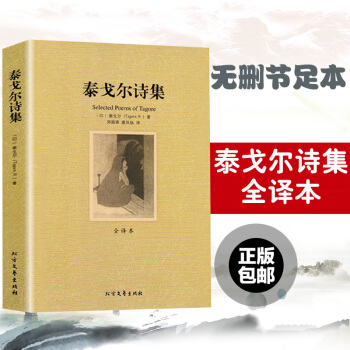
![新黑猫警长:真假黑猫警长(注音 全彩 图画书)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47754/rBEhVVNXFZcIAAAAAB-Ab8oJ6TcAAMdQwOYnPkAH4CH943.jpg)
![新黑猫警长:恐龙总动员(注音 全彩 图画书)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47758/rBEQYVNXFaMIAAAAAB-iqkdNt2oAAE8vwONwCgAH6LC54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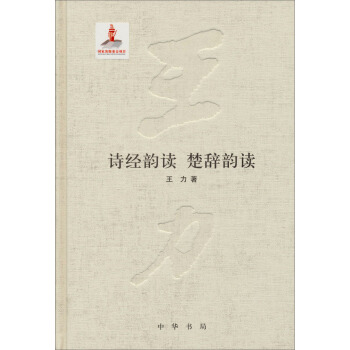
![“双桅船名家经典读本”:银河铁道之夜(外国卷)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95094/540031d4N51cf8b9e.jpg)
![夏洛书屋(第三辑):夜鸟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99904/53f404e2N0ab684c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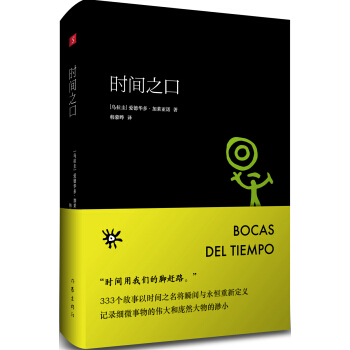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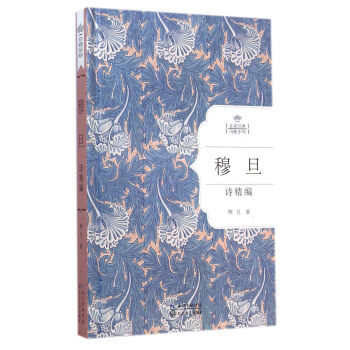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7-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23855/5656d0b5N8b4dc74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