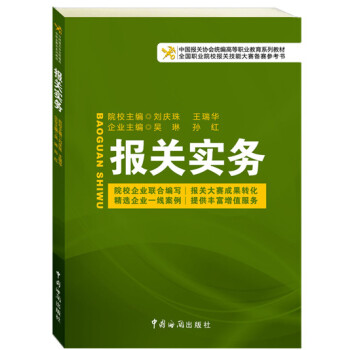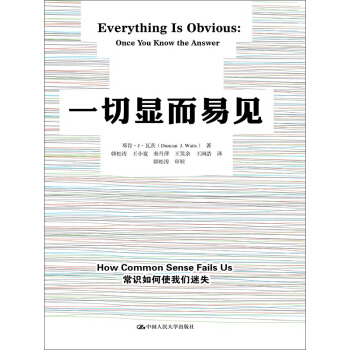![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瑰丽人生 [Lives of the Laureates]](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13229/58577c96N3ed01348.jpg)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瑰丽人生》是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为题的小传的合集,每一篇都是当事者亲自现身面对无数听众讲述其心路历程。虽然,这二十三位获奖者并非都是研究相同的领域,但却都强调知识的累积,以及同行、师生间相互脑力激荡的重要性。经济学专业读者固然会对这些得奖者之重要贡献的来龙去脉兴味盎然,就是外行人虽可能不明其内涵,却仍可获得新知的脉动。
内容简介
《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瑰丽人生》描述了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贡献,虽然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领域并不相同,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领域为读者揭开了经济学数十年来发展的脉络。书中同时也记录了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史,也为读者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对经济学的认识以及对整个经济学科及经济学各领域的评判。
作者简介
罗格·斯宾塞,圣安东尼奥三一大学经济学教授。
大卫·麦克弗森,圣安东尼奥三一大学经济学教授。
精彩书评
对于任何一个想寻求经济学真谛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再合适不过了。还有什么能比探寻世界上伟大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和灵魂更好的呢?
——格里高利·曼昆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目录
前言(第6版)
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R.Klein)
肯尼斯·阿罗(Kenneth J.Arrow)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
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
弗兰克·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Buchanan)
罗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
威廉·夏普(William F.Sharpe)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
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Sckoles)
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
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Jr��)
詹姆斯·海克曼(James J.Heckman)
弗农·史密斯(Vernon L.Smith)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Prescott)
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
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
埃里克·马斯金(Eric S.Maskin)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彼得·戴蒙德(Peter A.Diamond)
后记 感悟大师人生
致谢
精彩书摘
感悟大师人生
三一大学编写这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系列演讲,一个重要的目的是通过传记,更准确说是自传,帮助我们了解现代重大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轨迹。这23个人的演讲,都围绕着“我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之路”这一主题来提供相应素材。
后记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确定共同主题,让获奖者自述他们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独到见解。这些追忆往事包括:对现实事件的严密性和关联性的渴求,老师及学者对获奖者发展历程的关键影响,必要的学术交流与活跃的学术环境,以及他们生命中际遇的好运和意外。多数获奖者认为,他们的研究项目大部分都没有事先计划,只是通过不断地交流观念,才逐渐形成一套思想。当然,也有例外。我们主要从获奖者在三一大学的演说中攫取材料,以概括这些主题。第二部分评估了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获奖者的个人经历,对于了解现代经济学的思想潮流是否重要。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对此给出明确的答案。人们无法观察也无法用任何方式模拟不存在的事实——没有这些个人及其独特的人生经历,经济学思想会怎样发展。尽管不能对这一难题给予确定回答,但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应该被忽略。这23篇演讲文呈献了丰富的素材,促使我们对传记在经济学思想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做出详尽而周密的思考。
同一主题与不同言论
很少有人从小就期待或渴望成为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是如此。他们进入经济学殿堂主要是受老师、学者的影响,或者因为知性挑战和经济学的严密性,或者因为认为经济学与现实生活的种种问题有关联。以下四个例子,是几位获奖者自述如何将爱好投向了正式的经济学训练:
我想,有不少孩子希望长大后当经济学家或教授……从初次接触《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起,我就被经济学吸引住了。和许多同时代的经济学者一样,我之所以会对这门学科着迷,原因有二。其一,经济理论是一项迷人的知性挑战,与数学或下棋很相似。我非常喜欢分析和逻辑论证……其二,通过经济学研究,显然可以了解经济大萧条和它给全球政治走势带来的可怕影响,甚至提出解决之道……由于有了凯恩斯,经济学让我充分领略到两个世界的极致。(詹姆斯·托宾)
大二的第一学期,我选了会计学及微观经济学两门必修课。前者其实就是完全不动脑筋的死记,令我深感厌恶。但微观经济学完全不同,它理论严谨、前后关联、结构完整、逻辑清晰。我感受到了其中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我随即在第二学期转为主修经济学,从此不再回头。这是幸运之神的第一次眷顾。有时回想起来,我都会不自觉冒出一身冷汗——假如当时选读的是现代会计学和制度经济学,那么现在会发生什么事儿?(威廉·夏普)
选择科罗拉多学院就读比事先预料的复杂得多……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学了一门雷·维尔纳教的经济增长选读课……我读了李嘉图、斯密和阿瑟·刘易斯的著作……那位教授还把他的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这本书我至今还保存着)借给我看,算是开小灶。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本书使我懂得,经济学也可以像物理学一样严谨,是一门经验科学……同时,它表明通过显示性偏好理论,经济学具有经验内容。我在社会科学中看到了我在奥本海姆的课堂上第一次体会到的硬科学内容。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符合我受通识教育的趣味……听了三年级的选读课后,我决定今后以经济学为业……我研究科学与研究社会科学是并行不悖的。(詹姆斯·海克曼)
我领略了数学、物理以及工程学不打折扣的严密性。但在四年级的时候,我选了一门经济学的课,发现经济学很让人着迷——可以实在地学到一些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及其他的什么主义所做断言的经济学原理上的依据吗?我不太知道,但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对专业的经济学感到好奇后,我就到加州理工的图书馆翻阅相关的书籍, 碰巧看到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那年稍后的时候,我又看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对前者来说,经济学可以做到与物理学一样,那是很清楚的;但对后者来说,经济学看起来是一种推理的方式而不太像物理学。我还订了一份《经济学季刊》,某卷的头一期有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写的一篇论工程生产函数的论文。这样经济学又像工程学了。这些最初的印象在我随后几十年的思想中是怎么改变的,我已经没有头绪了。 (弗农·史密斯)
对关联性进行阐述是这些演讲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前面老一辈诺贝尔获奖者托宾的引述表明,是大萧条激起了他对经济学的兴趣。而托宾和其他获奖者则强有力地支持这样的观点:
凯恩斯对周遭笼罩着的错误进行全面颠覆,发起一场鼓舞年轻人的经济学圣战。真理得彰之后我们将获得自由,同时也可以充分就业……当真实世界的事件与争端,把各种必须理解和解答的谜题摆在我们面前时,经济学知识将得到发展。(詹姆斯·托宾)
1932年可谓经济学家的绝妙时期。经济学就像睡美人,正等着新方法、新典范、新能手和新问题的复苏之吻。科学又如寄生虫:病人越多,生理学和病理学上的进步就越大,而由病理学又可以发展出治疗疾病的新方法。1932年是经济大萧条的谷底,从这片腐霉的土壤中,迟迟长出了今天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学科新苗。(保罗·萨缪尔森)
很快,再过几年,多活跃的经济学者恐怕也没人对20世纪30年代有清楚的记忆。那一代因深感有必要了解经济大萧条而投身经济学领域的经济学者,马上就要退休了。在今天大部分中、青年宏观经济学者的眼里,“景气循环”是一个轻度变异、自我相关性不大、稳定而随机的过程,依循着一个大体令人满意的趋势产生。这种观念架构,和我在这个专业领域的成长背景下形成的架构,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罗伯特·索洛)
虽然大萧条早已远去,但寻求与现实事件的关联研究依然是后来诺贝尔奖得主的重要课题。埃德蒙·费尔普斯针对当时缺乏关联分析、几乎不考虑现实人们的行为及不确定性的主流观点,用他的研究做出了别树一帜的回应。例如:
然而在阅读哈耶克的《价格与产品》(1935年第二版次)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我感觉到,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虽然在某些方面还算吸引人,且可能起一定作用,但是完全摒弃了现代经济理论所强调的信息不完全与知识不完善,并代之以某一新方法或方法论,这是不正确的。直觉上我认为(可能凯恩斯也会说),抽象出来的新凯恩斯模型疏忽了“人”的作用——这样,将不存在有别于真理的各种信念,也不存在与真实情况不同的预期,没有精神激励、挑战、问题的求解、创造力,也就没有所谓的发现。(埃德蒙·费尔普斯)
加里·贝克尔是把研究社会问题带入关联性研究的几位得奖者之一:
然而在普林斯顿的高年级阶段,我渐渐失去对经济学的兴趣,开始想我应该做些别的什么。经济学对我来说,太过形式化了……经济学看来无法帮助我理解那些我有兴趣的问题:不平等、阶级、尊严以及类似的那些对社会很重要的问题……我仍然不愉快,因为对我来说,经济学家在课本及别的地方所讲的东西与我想谈论的东西脱节了……(在芝加哥)米尔顿·弗里德曼对我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影响最大。上他的研究生价格理论课太令人振奋了,我巴不得他的课一周上两次……他的课使我明白了经济学是一件工具而不只是一种聪明学者玩的游戏……(经济学)这门了不起的课程表明我原来的想法是不对的。我们确实可以研究经济学并且以非常严格的方式来研究,同时又可以讨论重要的问题。(加里·贝克尔)
以上引述,展现了贝克尔是如何在经济学的关联领域受弗里德曼所启蒙。芝加哥大学很多学生都会提及弗里德曼的魅力对他们人生的影响。这是人格使然。但包括弗里德曼在内,没有一个诺贝尔得奖者所获得的声誉能超过他们的学术贡献。像贝克尔,还远未能以伟大导师或魅力个体的形象被世人接受。迈伦·斯科尔斯、詹姆斯·布坎南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亦是如此:
上麦克马斯达大学显然是个幸运的选择。因为麦克马斯达是所很小的学校,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专业的麦克伊夫教授,在我学习期间同我走得近,他指导我阅读和理解许多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及斯蒂格勒的当代理论……因为我喜欢经济学,一直没有放弃回头经商的计划。我决定读商学院而不是法学院。尽管我家里想我读其他学校,比如哈佛大学,但我只想去芝加哥大学,那是斯蒂格勒及弗里德曼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地方。(迈伦·斯科尔斯)
本人并不像某些同僚那样,是“天生的经济学家”,而且我也不是“演化”成为经济学家的。相反,我是“看到光”之后,才突发了知识领域的全盘转变……我确确实实是在弗兰克·奈特的影响下转变的。可以说他是全心全意在传达这样的信念:不论在科学的学术领域之内或之外,都不存在其信息值得被捧到至高无上的神。每件事、每个人、不论何时何地——一切都可以公开地接受批评与挑战。我们在道义上有责任找出自己的结论,即便有时这意味着公开检验你所信奉的知识宗师。(詹姆斯·布坎南)
通过这次合作,我终于明白了当时完成论文答辩后鲍伯所提出的问题。他是在告诉我,要运用动态经济理论构建总体现象模型。也由于这次合作,我成了鲍伯的学生,并逐渐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回归到这场讲座的主题,鲍伯其实是在我经济学家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件占尽天时地利的幸运之事。
理论与测量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重要性,是指导我进行研究的原则。我逐渐得出结论:宏观经济学领域根本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实际中寻找到有关经济运动的政策不变法则。我曾读过鲍伯的评判文章,知道结论中还需要点其他东西。因此,我不再教授当时所谓的宏观经济学,而是开始利用动态均衡模型来研究鲍伯所实践的总量经济学。(爱德华·普雷斯科特)
尽管这类怪事时有发生,可我仍然觉得数学是一门分外迷人的科目,如果不是偶然间踏足经济学课程,听了伟大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的信息经济学讲座,我很可能成为一名数学家。那时我并不知道阿罗是何许人,当然也不知道信息经济学是干什么的,但我认为那门课至少应该有所裨益。阿罗的讲座都是即兴创作。他似乎是在从办公室到教室途中,才想到了他要谈论的东西,有时甚至啥都没想到。不过在即兴讲座中,他往往灵感迸发。他的讲座主题有点儿像大杂烩。其中涉及课程名称所示的信息经济学,还涉及一些团队理论,他用一个单元讲讲规划程序,再讨论讨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而课程最精彩的,也是改变了我人生发展方向的部分,是莱昂尼德·赫维奇对机制设计理论的研究。(埃里克·马斯金)
托宾强调,他读研究生时教授们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同时他也暗示在课堂之外学到了很多东西:
回想起来,当初教授们几乎把大部分的教育责任留给我们自己。他们希望我们能自学并与同学相互切磋,我们的确也做到了。教授把我们视为学术研究过程中的伙伴,而不是所谓的“徒弟”。我认为,如今的研究院教育,太注重于将一大堆固定的教材灌输给学生,然后测验他们对所传授知识的掌握程度如何。(詹姆斯·托宾)
几乎所有获奖者都认同一个特定的工作环境,通常为大学经济学系(但并非全部如此),是他们演变为经济学家的关键因素。斯蒂格勒、克莱因和夏普尤其同意这一点:
所以,如果想了解当代经济学成果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获得的,就必须深入探究当代学者求学和工作的情况。这些条件并不等同于创造力,然而却是创造力得以发挥不可或缺的条件……
说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有充分理由,一方面因为它关切人类社会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另一方面则因为如果不能处在适宜知识探讨的环境,那么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将很难有所建树。(乔治·斯蒂格勒)
20世纪40年代末的芝加哥大学可谓人才济济,如此强大的阵容在经济学界恐怕再难一见。我们这群亲密的伙伴当中,先后诞生了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下一代考列斯委员会任职的研究人员(部分在芝加哥大学,部分在耶鲁大学)里,又出现了两位。我们通力合作,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统计学理论、经济学理论和各种现有资料,专门研究一项课题——为美国经济构建整体计量经济模型(继30年代丁伯根模型的第二轮尝试)。在进行了四五年的集中研究之后,这个工作团体的成员陆续离开,奔往各自新的学术前程。(劳伦斯·克莱因)
1956年的兰德公司是个非常特别的组织……员工可以自由上下班,工作时间有相当大的弹性。办公室的大门永远敞开着,大家要展开各种广泛议题的知识交流——这是必需的,另外每人每周得有一天时间可以进行纯属自己兴趣的研究。
那段时光令人振奋。兰德的工作主要包括系统分析、运作研究、电脑科学和应用经济学等。在兰德我们使用的第一批电脑中,有一部就是冯纽曼设计的。丹立格(George Dantizig)那时正在摸索线性规划。一些杰出的学术界大师也在兰德担任顾问。在这里,大家习惯了互相直呼其名。假如有人对实用理论感兴趣,那20世纪50年代的兰德公司就是最佳的工作场所。(威廉·夏普)
获奖者在演讲中总会提到运气的作用。毫无疑问,强调运气好,部分是多数获奖者谦虚的表达。显然,天赋与努力相结合是必需的,尽管不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充分条件。他们通常说的所谓“运气”,是指在职业生涯的发展历程中,经常遇到一些不可预测或意外事件。不难想象,这些不确定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在他们早期的发展轨迹上给他们的未来带来决然不同的命运。弗里德曼和贝克尔的经历能清楚地证明这一事实:
当我回忆起个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历程,“纯粹的偶然”在关键时刻所扮演的角色总是令我深有感触……回顾个人的经验与发展过程,我发现自己走过的道路是由一连串幸运的意外所决定的。(米尔顿·弗里德曼)
我很快认识到,在人力资本领域需要做的有很多……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还没有理论基础……我开始尝试构思一套粗略的理论基础来充实研究的理论内容……我却完全不知道会往哪个方向走……这又是一个运气起作用的例证……当我开始认识到这一理论框架可以整合众多个人收益中的可观察现象和规律,收益的职业差别,以及就业时,我既感到惊异,又兴奋至极。(加里·贝克尔)
钻研历史需要进行海量的细节研究,虽然经济学同样需要研究,可研究细节真不适合我的性格。而且,历史主要关注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在你书籍的最后一章讨论为什么会发生那种事,但这通常涉及的是“什么”,而非“为什么”。我想寻找更多的“为什么”。所以我被吸引到了经济学领域,这真的很幸运——那种你能在任何事业有成者的人生经历背后发现的幸运。对我来说,我遇到一位相当出色的导师(比尔·诺德豪斯,现在在耶鲁),他教了我一门极好的课程:自然资源经济学专业课……一切就这么顺利发展下去,经过比尔·诺德豪斯的推荐我进了研究生院。我喜欢的东西竟然也是我相当擅长的东西实在太好了,但至关重要的是,我有幸在恰当的时间遇见了恰当的人……
在麻省理工学院,我再度清楚地了解到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研究风格。幸运之神又让我遇上了另一位伟大的导师,这一次是已故的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 Dornbusch),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杰出的国际宏观经济学家,有人会认为他是过去三十几年来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宏观经济学家。这位伟大的老师以他独特的工作方式激励着我们所有人。(保罗·克鲁格曼)
研究计划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关于这一点,获奖者的感受不一而足。从贝克尔的例子来看,他早期尝试性介入人力资本理论时,对最终如何发展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多数获奖者同样强调了他们的研究并非宏伟的设计或了不起的远见,倒是因为市场的激烈竞争才产生了相关理念。譬如布坎南、萨缪尔森和克鲁格曼的例子:
当然我也知道,我个人的研究出版记录,可能会被解读为一个讲究方法论、重视规范性的个人主义的作品,其潜在目的一直是要以更具哲学性的观点来支持个人自由。但是,主观地回想一下,在我工作的过程中,似乎从未有意识地采取这种态度。整个学术生涯中,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我都在致力于澄清一些模糊或混淆的观念;对经济学者、社会科学家与哲学家看法的疏漏之处,我也设法研究清楚。如果说这些努力有什么自觉的动机,那就是纯粹享受创造思想观念的过程,享受将现实反映于最终的文字著述所带来的乐趣。(詹姆斯·布坎南)
对于注重科学界大人物或大成就的观念,我一直并不苟同。老农夫都会一边朝池塘吐口水一边说:每滴水都有助益。我们应该为自己面对的最急迫问题竭尽全力,之后就算遭遇收益递减,尽力做好该做的事仍是最佳策略。何况,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撞上熊彼特式的创新或达尔文式的突破,状态又回到了收益递增的阶段……
科学家就和“斯密主义”的生意人一样,既贪婪又争强好胜。然而他们追逐的并不是物质享受,甚至不是金钱本身,或者一般人所讲的权力。学者求的是“名”……是在同行——他们敬重的也希望赢得对方敬重的同行之间的名誉。(保罗·萨缪尔森)
那时我注意到自己正在创造一种体式,所以我详细记录了我二十几年前的研究规则。请看我制定的四项研究规则:聆听外邦人说话;质疑问题;敢于碰钉子;简化,再简化!(保罗·克鲁格曼)
托马斯·谢林指出,他确立研究方向,很大原因是别人的建议和要求。
其次,我所做的每件事几乎都是由机遇所激发的,并不是我去寻求这些机遇,而是它们找上了我;我做的许多事情,包括一些我相当满意的事,都是因为接受了别人的建议或邀请。(托马斯·谢林)
道格拉斯·诺斯、弗兰克·莫迪利亚尼和托宾,这三位获奖者则选择更为有条不紊、计划明确的研究之路。诺斯很早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莫迪利亚尼从不随俗主流,而托宾关心的是自己所处时代的重大问题。
从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的那一天起,我就清楚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一开始我就在研究,是什么因素造成了经济的富裕或贫困。在我看来,只有先弄明白了这一点,然后才能谈如何改善经济的绩效。探索经济绩效的最终根源,对我来说是一段漫长而充满意外的旅程——从马克思主义转变到认知科学;但正是这项持久不变的目标,一直指引并塑造了我的学术生涯。(道格拉斯·诺斯)
回顾个人的贡献,我找到一条统一的脉络:我喜欢与时代主流背道而驰,挑战当时所谓的正统观念。这些正统思想认为古典学派已经过时:说富人的收入中用来储蓄的部分比穷人的高;或者说绩优的有价证券利率比股本回报率低,因此负债融资的成本比较低;等等。我很期望在未来能继续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是我不想对未来的方向做过多思考。我只愿顺其自然,随时准备着一遇到有趣的事,便能投入其中。(弗兰克·莫迪利亚尼)
对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选择什么问题来研究。如果只是从文献的缺陷之处寻找研究的主题,通常会事倍功半;更糟糕的是,可能因为只注意了文献,反而忽略那些更具研究价值也更重要的问题。最优秀的经济学者,都是从周遭的世界中找出研究的题目。(詹姆斯·托宾)
我阅读课程的不同主题时,并非只想着教授那些文章或书本章节,我还想找到我要研究的课题。这就触发了从为上课准备教材转变为创作成一篇好论文。我把这一改变归功于精心为敏锐、专注的学生准备课程的过程。这意味着我正在思考的不只是应用数学,更是经济学……我一直喜欢拓展自己的教材,而不是照本宣科,只教现成论文里的内容。很多人担心教学工作会挤掉研究时间,但我的经历却表明这两者能相辅相成。事实上,当我的教学工作减少时,我的研究也几乎放慢了速度。(彼得·戴蒙德)
经济学的重要突破,不会发生在真空地带。即便没有某个特殊经济学家的贡献,一些主要的经济学发展也能产生。但有些贡献是非常独特的——极为明确地指引了经济文献的未来之路。至于其他的研究科目,其对经济学的确切贡献会随着时间不断地发展。以下的引用可以佐证这些可能性:
在科学的世界里,重复发现其实是司空见惯的事……由不同诱因所引致的相关领域的发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一些疑难问题。这些发展既然公之于众,那么各方学者都能加以运用,重复发现也就不足为怪了。对于一项新的发现,能够成为第一位发现者或跻身首批发现者之列,当然会令自己满足。不过至少就一般均衡理论来讲,显然即使没有我的投入,它的发展也不会另有不同。(肯尼斯·阿罗)
进一步的研究之后,我写了《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最终于1972年发表在《经济理论杂志》上。这篇论文精心构建了这样一个经济的理论模型,其中动机、机会以及每一个经济主体的信息都清楚地予以说明。预期是理性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正如弗里德曼的AEA演说一样,在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长期的替代关系。但这一模型也包含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关性,然后这一相关性被广泛地解释为是那种替代关系存在的坚实证据。我感到我第一次理解了,为什么费尔普斯与弗里德曼两人都是对的,即他们认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在长期内不存在替代关系;以及为什么计量经济学家的检验却一直反驳这种“自然率”观点。
为了给出这个模型,我把我的技术手段都用尽了:这不是一篇好读的论文,写的时候也不轻松。模型借鉴了我和拉平关于劳动供给的观点,以及我和普雷斯科特在写《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时发展的理性预期表述……我很容易就看出这篇论文受费尔普斯、拉平、普雷斯科特及卡斯的影响,但把这些影响合并起来是新的,也令人震惊:1970年还没有人这样研究宏观经济学。这篇论文给我带来了声誉。(罗伯特·卢卡斯)
这里有一个问题:《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这本书是阐述的博弈论吗?如果是,那么是什么使它成为博弈论方面的书籍?……
不过在当时我并不是那样想的——我就没有想到这一层——但从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评论中不难看出,他们认为那本书写的就是博弈论。而现在我发现,书里写的都是有关个人相对于他人选择所做出的调整或预期,以及相互协调的需要与时机:正式的合作,或对指令、规章的服从……现在我可以做出结论,这就是写的博弈论。我认为(或者界定),博弈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各种情境的分析。“囚徒困境”难道不是一种情境吗?选择的逻辑固然是博弈论的核心,而且博弈论的关键——这里我再次想到了矩阵的发明——往往是查明在什么情况下,选择会有些令人费解,或是有疑问,或是具有挑战性,并确定在某一情况下会有多少种不同的可能。(詹姆斯·谢林)
本章“感悟大师人生”所述内容,深刻洞察了经济学思想发展和进化的全过程,相信其他学科思想的演进也与之类似。脱离老师的重要帮助、学术气氛、探索现实事件的紧密性与关联性,以及现代经济学思想演变的偶然因素,人们就无法感悟这些讲稿所会演的人生。这些经验之谈中至少表明一个迹象:个人经历很重要。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话题。
……
前言/序言
本书摘录了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23位经济学者的职业生涯自传,他们具有三个共同特点:第一,都是经济学家;第二,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三,都曾前往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在三一大学里讲述自己的故事。
诺贝尔经济奖并非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本人设立的。1901年根据其遗嘱设立的奖项,有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以及和平奖这五类。诺贝尔希望这些奖项的设立能够奖励那些在这几个行业做出特殊贡献的学者,而不是杰出人物。因此在自然科学领域,奖励是针对重大的“发现”“发明”和“改进”。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在建行300周年庆典上又开设了一项新奖: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伯恩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金(以下简称诺贝尔经济学奖)。该项奖项的设立遵照原诺贝尔奖的颁奖标准执行。按照瑞典中央银行的评选原则,“该奖项将每年颁发给那些在经济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而其贡献的重要性一如诺贝尔在遗嘱中所述”。[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这一系列自传性演讲中所传播的思想,也正是本书的资深编辑威廉·伯烈特(William Breit)所要表达的思想。他花了大部分学术生涯进行研究、教学,并写出了当代杰出美国经济学家的生活和思想。[2]这种对人物的生平及其学术研究过程之间的关联性的恒久兴趣,自然而然地使他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为杰出经济学家提供一方这样的论坛。在那里,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用任何他们认为适宜的形式,围绕“我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之路”这一主题,发表自传性质的演讲。这样的论坛,不仅可以记录丰富的经济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科学的发展方向和性质;而且更主要的目的,则是为某一理论的科学发现提供重要的资料来源。
一个原创想法由萌芽到最终被同人接受,其过程是鲜为人知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实质内容,有多少反映了理论创造者的实际生活?有影响力的教育工作者群体在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思想家在探讨问题时,有多大程度是受到自身背景的影响,又有多大程度是受到所处时代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影响?是哪些力量使他们获得了那么深刻的见解?简单地说,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能够发现某项研究内容,并且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的?把这一系列演讲编辑成书的主要目的,正是希望帮助读者们解答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邀请谁来演讲呢?显然,预算和时间限制了邀请函的数量,所以入选人名单基本要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获得诺贝尔奖时名单上的该经济学家应任教于美国的大学;二是名单上的经济学家所研究的领域力求广泛,以期充分代表经济学不同的研究领域、分析方法和意识形态。从1983年我们开始策划这项活动时,共有12位诺贝尔奖得主符合第一个条件,其中有一人因病未能接受我们的邀请。依照第二个条件进行严格筛选后,人数减少为8名,很庆幸只有一人谢绝了邀请。
本书第1版中的内容是,1984~1985年度应邀来三一大学演讲者的自传性讲稿。这项方案的成功促使卡尔加德校长允许将这一系列讲座举办下去。
在紧接最初演讲系列面世后的3年里,有3位美国经济学者相继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位是1985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弗兰克·莫迪利亚尼,第二位是1986年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第三位是1987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他们全都接受邀请出席了演讲会,讲述他们取得学术界最高荣誉的历程。这些讲稿加录在1990年出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心路历程》第2版中。
越来越多的诺贝尔奖得主接受邀请前往三一大学进行演讲。第3版发表于1995年,第4版发表于2004年,而后又于2009年出版了第5版。
第6版《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瑰丽人生》新添了4篇文章,分别来自:埃里克·马斯金(2007年共享获奖)、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年共享获奖)、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共享获奖)及彼得·戴蒙德(2010年共享获奖)。估计随着在三一大学发表演讲的诺贝尔奖得主持续增加,未来的版本可能将会制成两卷,以便将被删除的演讲稿恢复。
为了在本书中加进上述的4篇新稿,出版商只好决定删掉先前版本的4篇文章,分别是阿瑟·刘易斯、罗纳德·科斯、约翰·萨尼和克莱夫·格兰杰的演讲稿。
对于许多获奖者来说,做这个演讲并不容易。有些人不愿意公开畅谈自己的思想成就,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一位受邀者所说:“我不知道发表这个演讲,是该矜持些还是可以海阔天空、夸夸其谈。这事儿还真有点儿压力。”此外,他们大部分人的专业研究领域技术性极高,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很难理解。可是他们又被要求,就自己的贡献向社会大众进行一场通俗易懂的讲座,这使一部分演讲变得更为困难。比如保罗·萨缪尔森和肯尼斯·阿罗的科学文稿,其中涉及大部分数理经济学领域的内容;劳伦斯·克莱因和詹姆斯·海克曼等人,则注重统计技术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这些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都习惯使用他们学科的专业术语来表达自己的见解。
不过读者会发现,在每篇文章里,发言者都成功地传达了他在经济学领域所做贡献的性质和意义(本书的文章按照他们在三一大学系列讲座中的顺序编排)。真难以想象,要把握阿罗“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的精髓,最轻松的方式竟然是聆听(或者阅读)他本人的现身说法。想要学习有关计量经济学“模型构建”的概念,在哪儿还有比克莱因文章里阐述的更为明确?而乔治·斯蒂格勒精彩诠释的“信息论”,会让每一个对这项成果丰硕的创新感兴趣的人清楚领略其理论要旨。最近几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的讲座也都如此。事实上,各个演讲者都能把原本晦涩难懂的内容说得清清楚楚。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演讲每次都获得了空前成功。听众规模庞大,而且都十分赞赏这些讲座。一些获奖者甚至不远万里前来三一大学进行演讲。广大师生同这些经济学家进行了各种非正式的会晤。在小型招待会上、在餐厅里、在喝咖啡之际、在私人住宅共进晚餐时,学生和教师都有机会和这些20世纪、21世纪最有声望的经济学家进行交谈。尽管他们作为学者声名显赫,有时还显得个性强烈,但他们都态度谦逊、平易近人,给几乎所有与他们接触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举办这一系列讲座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即告诉我们,大部分当代经济学界的顶尖人物都有其身为普通人的一面。
回顾这些讲座的内容,人们会对存在于当代经济学巨流中的分支纵横感到惊奇。读者将会发现:这些支流常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交错开去,观点截然不同的思想者往往师承同一位导师。运气、毅力加上辛勤工作,在科学知识的成功创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重要地,特别敏锐的读者会发现,这些自传性文章还揭示了作者的某些人格特质,可能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总而言之,这个系列讲座综合反映了美国当代经济思想的丰富多彩和深刻性。
除了编后记,该版次的《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瑰丽人生》以彼得·戴蒙德的演讲作为结尾,于2013年4月交付发行。而三一大学系列演讲的编制仍在继续,乃是一项持续发展的事业。想要关注其后一系列报告的读者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http: // www�眛rinity�眅du/nobel。该网站提供了系列讲座的年表,以及每位获奖者在三一大学演讲的摘录。
在第3版出版之前,系列演讲中的两名获奖者已经离开了我们:在1984年系列演讲创办时发表演讲的W�毖巧�·刘易斯和乔治·斯蒂格勒,两人均于1991年去世。另外于第4版出版前,有3位获奖者也相继过世:约翰·萨尼(卒于2000年)、詹姆斯·托宾(卒于2002年)和弗兰克·莫迪利亚尼(卒于2003年)。不幸的是,自上一版本出版后,获奖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于2006年去世。
谨以此书献给与世长辞者。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充满了质感,简约而大气,散发着一种沉静的智慧光辉。拿到手中,厚实的分量让我对接下来的阅读充满期待。我一直对那些能够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思想家们充满好奇,他们的理论如何孕育,他们的研究过程又是怎样的跌宕起伏。我猜想,这本书一定不仅仅是罗列枯燥的经济学原理,而是会深入挖掘这些伟大的头脑背后,那些鲜活的、充满人情味的故事。想象一下,那些在象牙塔里沉思的学者,如何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力量;那些在数据和模型中遨游的头脑,又如何在生活的琐碎和灵感的迸发之间找到平衡。我尤其好奇,在诺贝尔奖的光环之下,他们是否也曾经历过迷茫、挫折,甚至是不为人知的挣扎。这本书,或许能为我们揭开这些经济学巨匠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让我们看到他们作为凡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身上那种不屈不挠、追求真理的精神。光是想到这一点,就足以让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书页,踏上这段探寻瑰丽人生的旅程。
评分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于知识的科普,它更像是一本关于如何追求卓越、如何坚持理想的励志指南。在阅读过程中,我被每一位经济学家的坚韧不拔所深深感染。他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无数次的质疑、失败和重塑。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提出的某个理论在当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坚持不懈地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证,最终才获得了学界的认可。这种面对困境时的勇气和对学术的忠诚,是我从书中收获到的宝贵财富。我开始思考,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遇到挑战时,是否也能拥有同样的决心和毅力。这本书让我明白,真正的“瑰丽人生”,不仅仅是获得多少荣誉,更是经历了怎样的磨砺,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以及对人类知识和社会的贡献。它鼓励我以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确定性,去追求属于自己的那份“瑰丽”。
评分我一直对那些能够洞察事物本质、引领时代潮流的思想家们抱有极大的敬意,而这本书恰好满足了我对这群“大脑中的巨人”的强烈好奇心。它不仅仅是一份名单的罗列,而是一次深入人心的探索之旅。作者似乎拥有某种魔法,能够将那些可能显得严肃枯燥的经济学理论,化为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我仿佛看到了那位在贫困中成长,却凭借过人才智改变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学者;也仿佛听到了那位在战乱年代,依然坚持进行思想探索的智者。书中所描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学术成就,更是他们面对时代洪流时的思考、他们在个人生活中的取舍,以及他们对人类社会进步所做的贡献。这种多维度的呈现,让我对“经济学奖得主”这个身份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它让我看到了,在每一个闪耀的桂冠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段曲折却又充满力量的人生篇章,这本身就是最动人的“瑰丽”。
评分坦白说,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印象,大多停留在那些抽象的理论模型和复杂的数学公式上。我以为这是一本“高冷”的书,会充斥着艰深的学术术语,难以企入。然而,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它以一种极其人性化的视角,将这些经济学大师们的生活经历、个人情感、甚至是一些小小的癖好都娓娓道来。我惊叹于作者的叙事能力,能够将如此庞杂的知识体系,用如此引人入胜的故事串联起来。读到其中一位经济学家,他不仅在学术上有着卓越的成就,生活中还是一位热爱音乐的艺术家,这种跨领域的才华让我由衷钦佩。另一位则因为对某个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而将毕生精力投入到相关的研究中,这种使命感令人动容。这本书让我深刻体会到,伟大的成就往往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世界的深刻理解,而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运行的学科,本身就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充满了温度和人情味。
评分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经历了一场思想的洗礼,也仿佛与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深度对话。书中对每一位经济学家的生平、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其理论的深远影响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我特别被其中一位经济学家的故事所打动,他并非出身名门,而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对经济现象的敏锐洞察,一步步走上学术巅峰。他的理论不仅改变了我们理解市场运行的视角,更在实际政策制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书中没有回避他们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争议,反而将这些挑战视为他们思想淬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坦诚的态度,让我觉得这些伟大的学者更加真实可感。我还在书中看到了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碰撞与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经济学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一个不断发展、自我修正的动态学科。这本书不仅拓展了我的知识边界,更激发了我对经济学领域更深层次的思考,让我看到了理论的力量如何塑造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
评分在京东买书很方便,正版图书,性价比高!以后还会再买的~
评分一如既往的好
评分参考书,还算很不错的。
评分参考书,还算很不错的。
评分书已经收到,质量还不错,慢慢再看吧
评分经典。。。。。。
评分很好,买来慢慢看哈
评分一如既往的好
评分包装完整,印刷质量很好,发货也很快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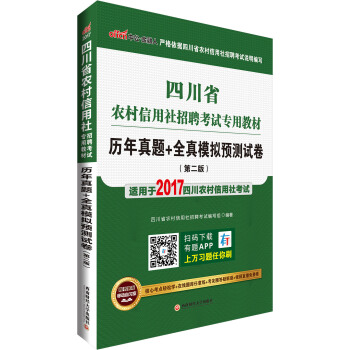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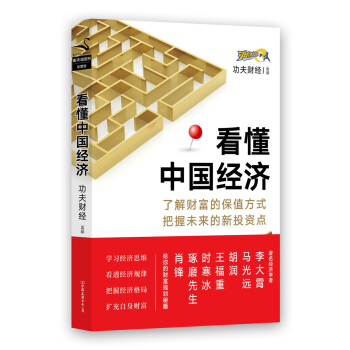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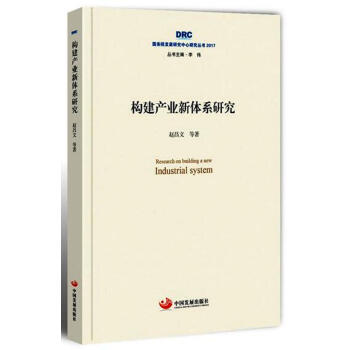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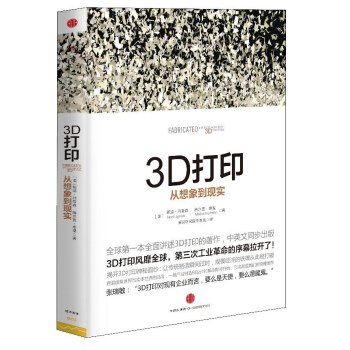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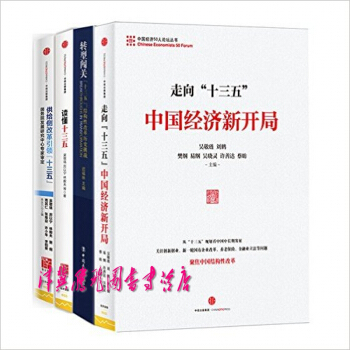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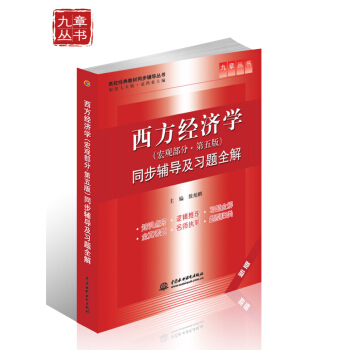
![世界主要经济体战后经济发展丛书:战后经济发展之路(美国篇) [The Development Way of Post-War Economic Americ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095392/rBEHaFBmrp8IAAAAAACexpcG-xIAABk-ALO7fUAAJ7e21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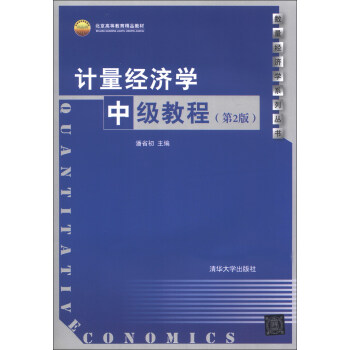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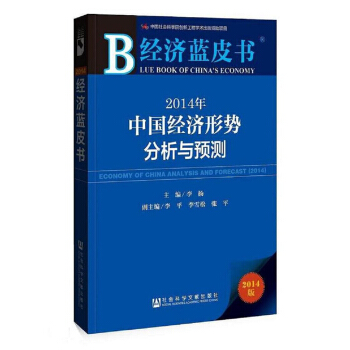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57363/rBEbSlNx8isIAAAAAAHlnmOSej8AAAopABlcogAAeW2144.jpg)
![风险导向内部审计 [Risk-Based Auditing]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62041/537b2079Nc4d61a8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