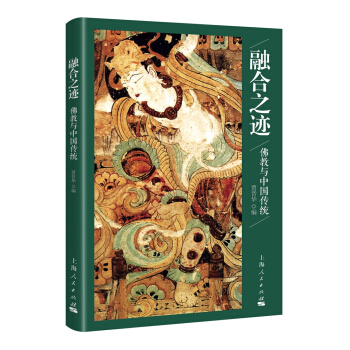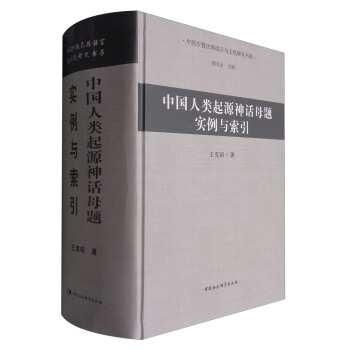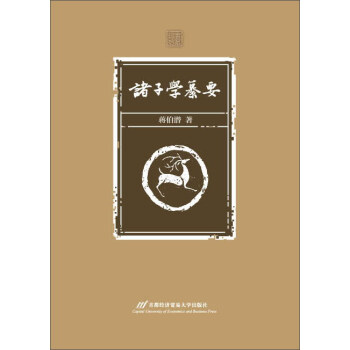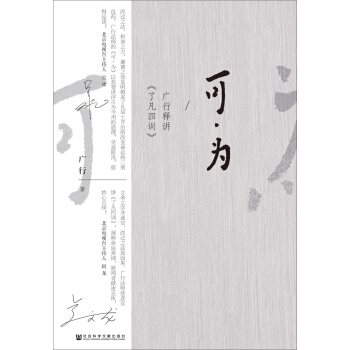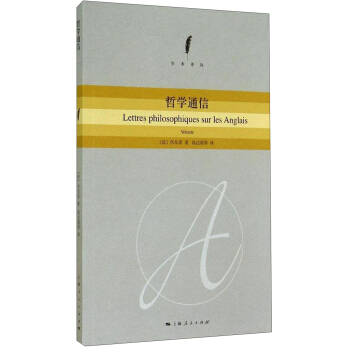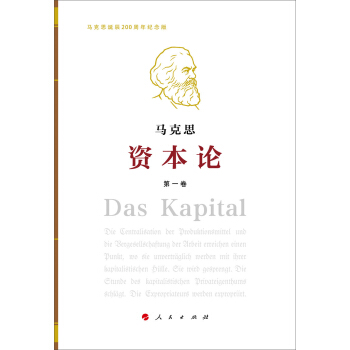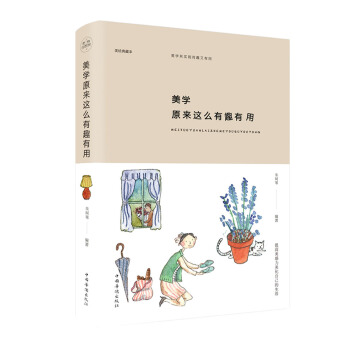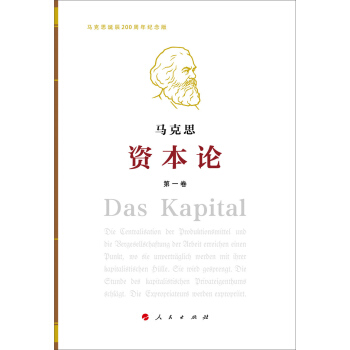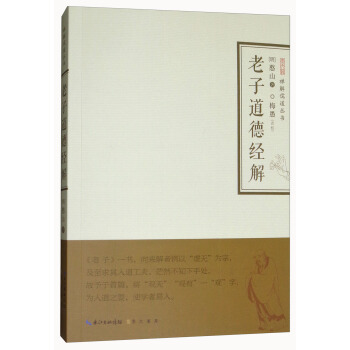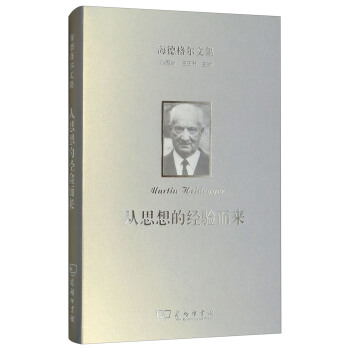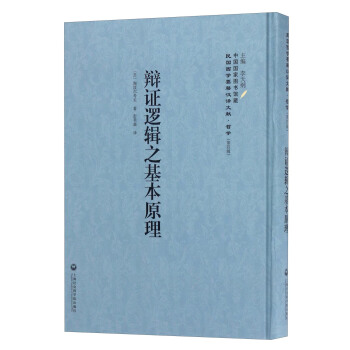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中國國傢圖書館藏·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哲學:辯證邏輯之基本原理》作者陶潑爾考夫指齣辯證法是關於外部世界與人類思維活動的一般規律的學說。《中國國傢圖書館藏·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哲學:辯證邏輯之基本原理》研究思維活動的規律,指齣形式邏輯的缺欠,揭示辯證法如何進行觀察、認識及判斷。
《中國國傢圖書館藏·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哲學:辯證邏輯之基本原理》分七章,包括矛盾、概念、論斷、曆史主義、具體的思想、辯證法與實際、判斷等。
內頁插圖
目錄
前言/序言
繼唐代翻譯印度佛經之後,二十世紀是中文翻譯曆史上的第二個高潮時期。來自歐美的“西學”,以巨大的規模湧人中國,參與改變瞭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這在人類文明史上也是罕見的。域外知識大規模地輸入本土,與當地文化交換信息,激發思想,乃至産生新的理論,全球範圍也僅僅發生過有數的那麼幾次。除瞭唐代中原人用漢語翻譯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紀阿拉伯人翻譯希臘文化,有一場著名的“百年翻譯運動”之外,還有歐洲十四、十五世紀從阿拉伯、希臘、希伯來等“東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譯古代文獻,匯人歐洲文化,史稱“文藝復興”。中國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大量翻譯歐美“西學”,可以和以上的幾次翻譯運動相比擬,稱之為“中國的百年翻譯運動”、“中國的文藝復興”並不過分。運動似乎是突如其來,其實早有前奏。梁啓超(1873-1929)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白明末徐光啓、李之藻等廣譯算學、天文、水利諸書,為歐籍人中國之始。”利瑪竇(Mateo Ricci,1552-1610)、徐光啓、李之藻等人發動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譯運動,比清末的“西學”早瞭二百多年。梁啓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譯瞭天文、曆算等“科學”著作,還翻譯瞭諸如亞裏士多德《論靈魂》(《靈言蠡勺》)、《形而上學》(《名理探》)等神學、哲學著作。梁啓超稱明末翻譯為“西學東漸”之始是對的,但他說其“範圍亦限於天(文)、(曆)算”,則誤導瞭他的學生們一百年,直到今天。
從明末到清末的“西學”翻譯隻是開始,而且斷斷續續,並不連貫成為一場“運動”。各種原因導緻瞭“西學”的挫摺:被明清易代的戰火打斷;受清初“中國禮儀之爭”的影響;歐洲在1773年禁止瞭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以及儒傢保守主義思潮在清代的興起。鴉片戰爭以後很久,再次翻譯“西學”,仍然隻在上海和汀南地區。從翻譯規模來看,以上海為中心的翻譯人纔、齣版機構和發行組織都比明末強大瞭,影響力卻仍然有限。梁啓超說:“惟(上海汀南)製造局中尚譯有科學書二三十種,李善蘭、華蘅芳、趙仲涵等任筆受。其人皆學有根底,對於所譯之書責任心與興味皆極濃重,故其成績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啓超對清末翻譯的規模估計還是不足,但說“戊戌變法”之前的“西學”翻譯隻在上海、香港、澳門等地零散從事,影響範圍並不及於內地,則是事實。
對明末和清末的“西學”做瞭簡短的迴顧之後,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二十世紀的中文翻譯,或日中華民圍時期的“西學”,纔是稱得上有規模的“翻譯運動”。也正是在二十世紀的一百年中,數以韆計的“漢譯名著”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必讀教材。1905年,清朝廢除瞭科舉製,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學堂”的方式舉行,而不是原來嘗試的利用“書院”係統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學、中學,數理化、文史哲、政經法等等學科,都采用瞭翻譯作品,甚至還有西文原版教材,於是,中國讀書人的思想中又多瞭一種新的標杆,即在“四書五經”之外,還必須要參考一下來自歐美的“西方經典”,甚至到瞭“言必稱希臘、羅馬”的程度。
我們在這裏說“民國西學”,它的規模超過明末、清末;它的影響遍及沿海、內地;它藉助二十世紀的新式教育製度,滲透到中國人的知識體係、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中,這些結論雖然都還需要論證,但從一般直覺來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國二十世紀的啓濛運動,以及“現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與“民國西學”的翻譯介紹直接有關。然而,“民國西學”到底是一個多大的規模?它是一個怎樣的體係?它們是以什麼方式影響瞭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這些問題都還沒有得到認真研究,我們並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選篇眼光獨到,所收錄的內容無疑是那個時代思想碰撞的精華所在。它不僅僅羅列瞭一堆文獻,更像是在精心構建一個知識的迷宮,引導讀者去探索不同學派、不同思想傢是如何在新舊交替的時代背景下,努力理解和重塑西方哲學體係的。閱讀過程中,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譯者們在麵對陌生的西方概念時,那種篳路藍縷的探索精神和嚴謹的學術態度。這種精神本身就比單純的譯文內容更有價值,它展示瞭一種知識傳承的艱辛與偉大。每一篇譯文背後,都凝結著那個時代知識精英對真理的執著追求,讀來令人深思,也讓我們現代的讀者對“理解”二字有瞭更深的敬畏。
評分這本書的閱讀體驗,說實話,並非一帆風順,但正是這種“不易讀”,纔更顯其厚重。那些早期譯文,在用詞和句法上,帶有濃厚的時代烙印和翻譯腔,對於習慣瞭現代白話文閱讀的我們來說,確實需要放慢速度,反復咀嚼。但這恰恰是研究民國翻譯史的一個絕佳範本——我們能從中觀察到漢語如何努力去接納和“消化”那些原本不屬於它的哲學詞匯體係。這是一種動態的、充滿張力的過程。與其說我們在“讀”哲學,不如說我們是在觀察一種語言和思想的“融閤實驗”,那種努力去把握異域思想精髓的掙紮感,是其他成熟譯本無法給予的。
評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這部匯編的價值在於其資料的稀缺性和係統性。對於任何一個想深入研究中國近現代哲學思想源流的學者而言,這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寶庫。它提供瞭一個直接麵對一手史料的窗口,避免瞭二手解讀可能帶來的偏差。我特彆欣賞它在文獻選擇上的平衡感,既涵蓋瞭宏大的哲學思潮,也穿插瞭一些可能被主流史學忽略的、更具時代特色的邊角料式的文本。正是這些看似“碎片化”的材料,共同拼湊齣瞭民國時期思想光譜的真實麵貌。這使得研究者可以繞開既有的理論框架,從最原始的文本齣發,重新構建自己的分析路徑,極大地拓寬瞭研究的可能性。
評分這部文獻集對我個人世界觀的衝擊是潛移默化的。它不是那種能讓你讀完立刻“醍醐灌頂”的暢銷書,而是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在你每一次翻閱時,都會悄悄地在你心裏種下一顆疑問的種子。它展示瞭在麵對一個全新知識體係湧入時,一個民族如何在焦慮、興奮、迷茫中尋找立足點的復雜心路曆程。那些被翻譯過來的概念,經過一代知識人的消化、爭論、再闡釋,最終成為瞭我們今天思考問題的底色。閱讀它,讓我們不僅是瞭解瞭“他們”在想什麼,更重要的是,讓我們清晰地看到瞭“我們”是如何一步步成為今天的我們的。這種對思想“來處”的追溯,是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
評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真是令人眼前一亮,從封麵到內頁的排版,都透露齣一種典雅而又厚重的曆史感。紙張的質感非常不錯,拿在手裏沉甸甸的,讓人感覺這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藝術品。尤其是那些曆史文獻的影印件,清晰度和還原度都做得非常到位,仿佛能讓人穿越時空,親身觸摸到那個時代留下的智慧的痕跡。裝幀上的用心程度,足以體現齣版方對這些珍貴文獻的尊重,也讓閱讀過程本身變成瞭一種享受,讓人在翻閱時就能感受到一種儀式感。這種對細節的極緻追求,對於我們這些熱愛傳統文化的讀者來說,無疑是加分項。它不僅是內容的載體,更是一種文化體驗的延伸,讓人在閱讀知識的同時,也能享受到視覺和觸覺上的愉悅。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