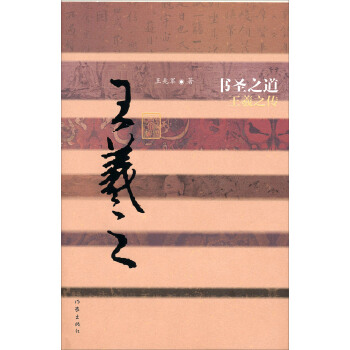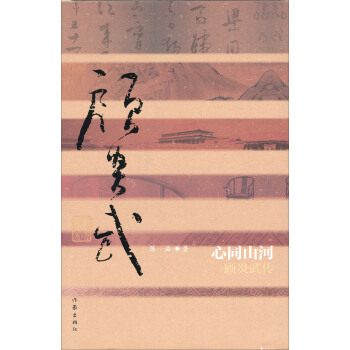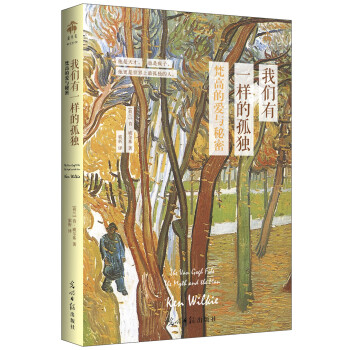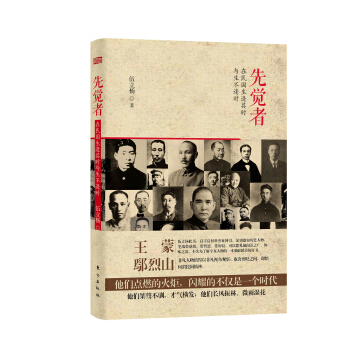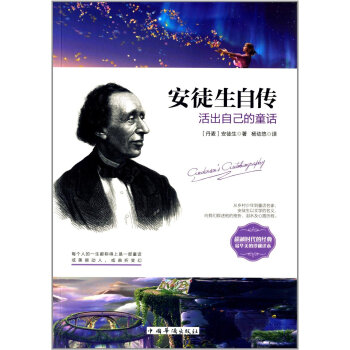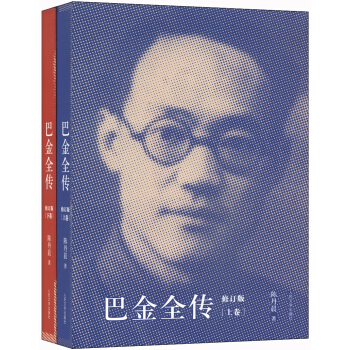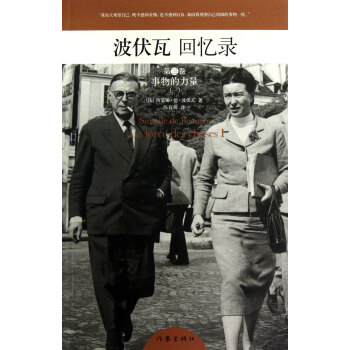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法国存在主义者、女权主义理论先驱、著名小说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其中以小说杰作《一代名流》、被奉为“女权主义圣经”的理论著作《第二性》及篇幅巨大的回忆录尤为光彩夺目。西蒙娜·德·波伏瓦无疑是20世纪法国一位伟大的回忆录作家,其四部主要回忆录的巨大规模与篇幅,至今无人出其右。其即:《西蒙娜·德·波伏瓦回忆录》之《第一卷:端方淑女》(1958)、《第二卷:岁月的力量》(1960)、《第三卷:事物的力量》(1963)与《归根到底》(1972)。这四部回忆录所具有的圣西蒙式的历史社会价值,只有像波伏瓦这样既是文学家又是社会活动家、“介入者”的作家兼斗士才能提供。此外,还有三部回忆录或自传性作品,与前四大部回忆录构成一个编年史般的整体。本书为《波伏瓦回忆录(第3卷)》。作者简介
作者:(法)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c de Beauvoir)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20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存在主义学者、文学家。波伏瓦一生著作甚丰,其中以荣获龚古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名士风流》、被奉为女权主义圣经的理论著作《第二性》和鸿篇巨制的四卷本《波伏瓦回忆录》最为突出。20世纪50年代,波伏瓦访问中国,遂有《长征》(1957)问世。其他重要作品有《女宾》《他人之血》《存在主义与民族智慧》等。
陈筱卿,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享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人事部考试中心专家组成员。翻译出版法国名家名著多部,达八百多万字,有:拉伯雷的《巨人传》、卢梭的《忏悔录》、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纪德的《梵蒂冈地窖》、罗曼·罗兰的《名人传》、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法布尔的《昆虫记》和雅克·洛朗的《蠢事》等。
目录
序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精彩书摘
我们解放了。孩子们在街头巷尾欢唱着:我们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
结束了,他们完蛋了。
我一直在嘀咕:结束了,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又都开始了。莫里斯夫妇的美国朋友瓦尔贝格开着吉普车带着我们在市郊游玩。多年来,我这还是头一次乘车郊游。我又在午夜之后,在9月的清凉之中游荡。一家家小酒馆早早地打了烊,但是当我们离开鲁梅里酒店的露天座或在“蒙塔纳”那烟雾缭绕的红色恐怖之地时,我们见到了人行道、长条椅和马路。屋顶上有一些狙击手,当我猜想到自己头顶上方有人充满仇恨地在警戒着的时候,我的心情沉重极了。一天夜晚,我们听见警报声响起: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飞临巴黎上空;几枚V-1飞弹落在巴黎郊外,炸毁了一些楼房。通常消息极其灵通的瓦尔贝格说,德国人已经制造出一些十分可怕的秘密武器。我听闻,不禁心头又害怕起来。但是,欢乐很快便扫清了我心中的阴霾。我们日日夜夜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喝酒、闲逛、欢笑,庆祝我们的解放。所有像我们一样庆祝解放的人,无论远近,都成了我们的朋友。大家如同兄弟姐妹一般狂欢畅饮!笼罩在法兰西上空的密布愁云消散了。一些身着咔叽布、嚼着口香糖的大兵的出现,表明人们又可以跨海越洋了。这些大兵走起路来吊儿郎当,常常跌跌撞撞地沿着人行道和地铁站台走着,嘴里还哼着小调、吹着口哨;晚上,他们在酒吧里迷迷瞪瞪地跳着舞,还大声狂笑,露出雪白的牙齿,对于德国人毫不同情而又不喜欢牧歌的热内,在鲁梅里酒店露天座上大声嚷嚷,说这帮身着军服的平民毫无教养,而德国占领者身穿绿色和黑色“甲壳”,也不是好东西!可我却觉得,这些年轻的美国人的自由散漫却正体现出自由:我们毫不怀疑,这个自由也属于我们,他们将把它传播到全世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完蛋之后,佛朗哥和葡萄牙的萨拉扎尔被驱逐之后,法西斯主义将在欧洲被清除干净。法国按照全国抗敌委员会的章程,正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相信,我们国家在经历了这么大的灾难之后,是会在没有新的动荡的情况下,去实现其彻底的结构性重组的。《战斗报》的刊头语表达出我们的希望:“从抵抗走向革命。”
这一胜利抹去了我们往日的种种失败,它属于我们,它展示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执政的那些人是曾经程度不同地直接参加过抵抗运动的抗敌人士,我们都认识他们。我们在报章和广播中的那些负责人中有许多朋友:政治已经变成一种家庭事务,我们希望参与其中。加缪在9月初的《战斗报》上撰文说:“政治不再与个人分离,它是一个人向其他人在直接演讲。”向其他人演讲是我们搞写作的人的任务。战前,很少有知识分子试图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而所有的知识分子——或者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未能了解自己的时代,而且,我们最敬重的那个阿兰,竟然堕落了。我们应该接着去完成这一使命。
现在,我明白我的命运是与所有的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自由、压抑、幸福和痛苦是与我密切相关的。但是,我说过我并无哲学方面的雄心壮志。萨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里,打算对存在继续作一个全面的阐述,而这种存在是依赖于他自身的处境的。他必须确定自己的位置,不仅是通过抽象推理,而且要通过一些实践的选择。因此,他以比我更加激进的方式投身行动。我们总是一起讨论他的态度,而且有的时候,我还会影响他。但是,正是通过他,我才了解到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及其微妙之处。在这个方面,为了谈我们,我就必须要谈他。
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感到应该接近共产党,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党的否定态度与我们的无政府主义不谋而合。我们希望资本主义失败,不过,我们希望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不要剥夺我们的自由。正因为如此,萨特在1939年9月14日的日记里写道:“我现在正在纠正社会主义,如果我需要纠正它的话。”可是,1941年,在他组建一个抵抗团体的时候,他将两个词——社会主义和自由——组合起来命名他的这个团体。战争让他有了一个决定性的变化。
首先,战争让他发现了其历史性。而这一发现让他十分震撼,让他终于明白,尽管自己在谴责既定秩序,但却与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冒险者都有其保守的地方:为了塑造自己的形象,为了在未来的世界里设计自己的奇思妙想,他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萨特从骨子里都想投入写作的冒险之中去,自幼年时起便一心想成为一个大作家,并荣获不朽的荣光,希望子孙后代为其自身目的,不断地好好利用本世纪的遗产。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始终忠实于他二十岁时的那种“对立的审美观”:他不遗余力地揭露这个社会的种种弊端,但是他并不希望颠覆这个社会。突然之间,一切都分崩离析了,永恒被击得粉碎:他又在一个幻想的往昔和一个阴暗的未来之间飘来荡去。他在用他那“真实性”的道德进行自我保护:从自由的观点来看,如果我们通过一个计划去看待所有的形势的话,那么它们都是可以挽救的。这种解决办法与禁欲主义十分贴近,因为环境除了迫使我们屈服之外,往往并不允许有其他的超越。萨特很憎恶内心的那些小诡计,所以他不可能长期地用口头的抗议去掩饰自己的被动屈从。他很清楚,他并非生活在绝对之中,而是生活在过渡之中,所以应该抛弃“存在”,决心“行动”。他的这一转变过程因往昔的外在变化而变得很容易。他要想,他要写,他最最关心的是抓住意义这个关键。但是,在海德格尔之后,他在1940年读了圣艾克絮佩里的书,致使他深信,“意义”只有通过人的行动才能呈现于世,因为实践优于思考。在“荒唐的战争”期间,他就跟我说过——他甚至在写给布里斯·帕兰的一封信中也如是说——和平一旦恢复,他将会搞政治。
被俘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会了他懂得互相关怀;他没有丝毫的沮丧,反而高高兴兴地参加到集体的生活中去。他憎恶特权,因为他的傲岸要求他通过自身的才智在世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他是个无名之辈,无人知晓,但他从零开始,踏踏实实地去做每一件事,从中取得成功,获得极大的满足。他结交了一些朋友,把自己的观点灌输给他人;他组织活动,动员集中营里所有的人在圣诞节的时候,排演了他自己写的一部反德国人的话剧——《巴里奥纳》,深受欢迎。患难与共、志同道合化解了反人道主义的矛盾。其实,他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因为它展示的是人的一种本性;但是,如果人必须塑造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一项任务能够激起人的激情了。此后,他便不再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立起来,而是要将它们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将通过构建一个符合自己希望的未来的方法客观地去改变形势,而不是通过主观地承受限定的形势以实现自己的自由。这个未来根据他所向往的民主原则,就是社会主义,只有这个他曾害怕迷失于其中的社会主义才能去除他的这块心病。现在,他既看到了人道主义的唯一机遇,也看到了自我实现的条件。
《社会主义与自由》的失败给萨特上了现实主义的一课,他只是在稍后才在全国阵线里与共产党员们一起做起严肃的工作来。
1941年,我曾说过见《岁月的力量》。——原注,共产党人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十分不满,他们曾散布流言蜚语,说萨特是通过当德国人的走狗才赎买到自己的自由的。1943年,他们想要统一行动。确实,据说有一份出自共产党人之手的宣传册,是在法国南方印刷的,萨特的名字上了一份黑名单,夹在夏多布里昂和蒙泰朗二人之间;他把它拿给克洛德·摩根看,后者立即大声嚷道:“真可悲!”随后,二人就再没提过此事。萨特同共产党抵抗运动成员的关系非常友好。德国人走了,他便希望继续保持这种友好关系。右翼的思想家们用所谓的精神分析法去解释他与共产党的这种结盟。他们将这归之于他的放任或自卑情结、他的心怀不满、他的幼稚、他对宗教的怀念。简直是胡说八道!共产党身后有广大群众,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共产党才能取得胜利;另外,萨特现在明白,他同无产阶级的关系将使他对自己进行彻底的考虑。他以前一直把无产阶级看做是一般的阶级;但是只要他想通过文学创作达到绝对,那他的存在在别人看来只不过是次要的了。他在发现自己的历史性时也发现了自己的依赖性,不再有永恒的存在,不再有绝对的存在;他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希冀的那种普遍性,只有能在世上体现它的芸芸众生可以赋予他。他已经在考虑以后要表达的东西了1952年,在《共产党人与和平》中表述了。——原注:对事物的真正的观点就是与自己所持有的观点彻底决裂之后的观点;刽子手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可受难者却不容置疑地在承受自己的痛苦和死亡,压迫的真相集于被压迫者一身。萨特正是通过被剥削者们的眼睛了解了自己:如果被压迫者们抛弃他,那他就将囿于他那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圈子里。
我们对苏联的友谊之情毫无保留;俄国人民的牺牲证明了他们自己的意志在他们的领导人身上得到了体现。因此,在各个领域想同共产党合作都是很容易的。萨特并不打算加入共产党。首先,他太独立,特别是他同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大的分歧。他当时认为,辩证法取消了他的个性;他相信“有血有肉地”直接接触事物的那种现象学直觉。尽管坚持“实践”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很早以前便想着手写一部有关伦理道德书的既定计划。他仍在追求“存在”。他认为,按伦理道德去生活,就是想要达到一个绝对有意义的存在模式。他不愿意放弃——他从未放弃过——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所提出的否定、存在、内在、自由的概念。他反对共产党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坚持维护人的人性范畴。他希望共产党人能容许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存在;他试图借助于他向他们借来的工具从资产阶级手中将人道主义夺回来。他在运用资产级文化观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反过来将资产阶级文化列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我们出身于中产阶级,但我们想要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架桥铺路。”见《活着的梅洛-庞蒂》。——原注在政治方面,他认为同情者们应该在共产党外扮演反对派在其他党派内部所扮演的角色:既支持又批评。
P3-7
前言/序言
我曾经说过,我为什么在《端方淑女》之后,决定继续写我的自传。当我写到巴黎解放时,我已经筋疲力尽,搁笔不写了。我需要弄清楚,我的这项工作是否有意义。好像是有意义的。但是,在我重新拿起笔来之前,我却又犹豫起来了。一些朋友、一些读者都在激励我继续写下去,他们说:“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您现在写到哪儿了?您得写完它,我们等着往下看哪……”但是,外界,包括我自己,对此并不以为然:“写这个为时尚早:您现在阅历不够,还没到写自传的时候……”还有人说:“还是等到能和盘托出的时候再写不迟:有一些东西现在又说不清,避而不谈又会造成误解。”还有人说:“像缺乏退一步看问题的能力。”甚至有人还说:“在您的小说中,您已经将自己表现得够充分的了。”凡此种种,均皆有理,但我别无选择。无论是心态平和还是思绪纷繁,由于老之将至所造成的麻木使得我难以掌控住主题,同为青春不再,已近垂暮。我想让自己的血液在这一叙述之中流动起来,我想全身心地积极地投入到这中间去,而且要在所有的问题消弭之前,充分地剖析自己。也许确实是为时过早,但明天肯定是为时过晚了。 有人还对我说:“您的故事嘛,尽人皆知了,因为自1944年起,它已经被广而告之了。”但是,这些广为人知的东西只不过是我个人生活的一个侧面,既然我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消除一些误解,那么我便觉得有必要如实地叙述一下我的人生。由于我以前更多地卷入到政治事件之中,所以我将更多地谈到这些事件。但是,我的自传并不会因此而过多地受到个人情感的左右;如果说政治是“预见现实”的艺术的话,那么,作为一个非政治家,我将分析的正是这个不可预见的现实。我每天所经历的历史,其方式犹如我自身的主体发展一般,是一种独特的冒险。 在我要谈的这段时期,所涉及的是实现自我,而非修身养性。虽然我接触过一些人,看过一些书籍、电影,也有过一些邂逅,总体而言,对我都是有所助益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们并非全都是对我不可或缺的。当我回忆起这些往事时,往往是我的记忆的随意性在主导着我的选择,而我的选择并不必然涉及一种价值判断。另外,我不再赘述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描述过的一些经历(比如我的美国之行和中国之行),而是更加详细地叙述我的巴西之旅。当然,这样处理必然会让该书失去平衡,可是,只好如此了。不管怎么说,对该书同对前一部分作品一样,我并不要求它成为一部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就像一幢别墅的花园里的一个雕塑,枯燥乏味。“艺术作品”系收藏家的术语,系欣赏者的术语,而非创作者的术语。我将永远不会想到说拉伯雷、蒙田、圣西蒙或卢梭完成了一些艺术作品。如果大家拒绝给我的自传贴上这一标签的话,我并不在意。不,我的自传并不是一部艺术作品,而是我激情、失望、激荡的生活。我并不想附庸风雅,我是在叙述自己的生活。 这一次,我也将尽量少地去删节。我往往会感到很惊讶的是,人们总在谴责传记作家写东西很拖沓冗长,但是,如果他的作品让我感兴趣的话,我仍旧会手不释卷;如果他的东西让我觉得厌烦了,我甚至连十页都看不下去。我从来就不会因自我欣赏而去描绘天空的颜色和水果的滋味。在叙述他人的生活时,我将会浓墨重彩地叙述他的所谓的琐碎之事,如果我知道的话。这些琐碎的细节不仅能让我们了解一个时期和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且,通过这些没什么意义的琐碎细节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经历的真相。它们显示的正是它们自身,把它们写到自传中去的唯一原因就是,它们确实存在,这就足够了。 尽管我的矜持也适用于这后一部自传(当然,想要毫无遗漏地叙述一切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些评论家已经在指责我的轻率了。第一个开始这么有所保留地写的人并不是我:我宁愿自己剖析自己的过去,而不愿把这个任务留给别人。 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我先前的作品还是下了工夫的:这是一种真诚,它并非源自于自负,也不是源自于自己糟践自己。我希望我能保持这一优点。三十多年来,在我与萨特的交往中,我一贯是如此行事的。我每天观察自己,既不感到羞愧,也不感到自负,如同我观察自己周围的事物一样。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并非是装腔作势,而是由我认识他人、包括认识我自己的方式方法使然。我相信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责任,但是,不管它们有多么重要,我们所存在于其中的这个范畴却是难以描述的,能够描述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在我看来,我觉得我是一个客体,我是一种结果,而与这种评价的功过是非的见解无关。如果回首往事,如果一种行为看起来或多或少地值得赞扬,或导致遗憾的话,那么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我所关心的更多的是理解,而不是评判。我宁可剖析自己,而不愿忘乎所以,因为我忠实于事实远胜于对自己的形象的关切:这种对事实的执著可以从我的人生经历中得到答案,但我对此并不感到得意扬扬。总而言之,由于对自己并无任何的评判,我也就对坦率地谈论自己的生活和我本人不会有什么抵触,至少当我把自己置于我自己的世界之中时就是如此。也许当我的形象投射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中——比如心理分析专家的世界中时——可能会让我感到窘迫或尴尬。但是,只要我在为自己画像的话,那我可是毫不畏惧的。 当然,诸位读者必须理解我们所说的“客观公正”。一个共产党人、一个戴高乐派,对于这些年的描绘会大不相同;同样,一个小工、一个农民、一个上校、一个音乐家,其各自的看法也是大相径庭的。但是,我的观点、信念、憧憬、趣味、介入,是公开声明了的,它们构成了我的真实面貌,我也正是根据它们来描述自己的。当然,我在叙述我的过去时,总是尽量地做到客观公正。 同前一本书一样,这本书也要求诸位读者的合作。我依照先后次序在描述我的发展的每一时刻,读者们一定得耐心地读完它,不要半途而废,否则将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比如,有一位评论家就说,萨特喜欢格维多·雷尼,理由是他十九岁时就喜欢上后者了。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而这一错误的产生缘于心怀叵测,可我却并不想小心翼翼地去提防这种险恶用心。相反,我的这本书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会激发这种丑恶心灵的内容,所以它必然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否则我就会颇觉沮丧了。同样,如果这本书没能让人感到兴趣的话,我也会感到失望。因此,我要声明,本书的真实性并不在于书中的某一个地方,而是存在于它的总体叙述之中。 有的读者已经指出,我的《岁月的力量》中存在着许多小的错误,而且有两三处还挺严重的。我已经很细心了,但是,百密一疏,我肯定在很多地方给弄错了,不过,我再次声明,我绝没有故意歪曲事实。用户评价
购买这本书,更多的是源于一种长久以来对波伏瓦这个名字的敬意和好奇。她的思想,尤其是《第二性》所带来的冲击,至今仍是女性主义研究中不可逾越的里程碑。然而,我始终觉得,理解一位思想家的核心,除了理论著作,更需要深入了解其个人生活和心路历程。这部回忆录,特别是它的第三卷,对我而言,就是一块通往波伏瓦内心世界的珍贵钥匙。我渴望从她的笔下,读到她如何将抽象的哲学理念融入到具体的生命体验中,如何在现实的困境中探索自由与责任的边界,又如何在人际关系中处理爱情、友情和思想的交织。我猜想,其中必然会有关于她与萨特之间深刻而复杂的精神伴侣关系,关于她参与的社会运动和政治思考,以及她作为一名女性在那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和奋斗。这本书的设计风格朴素而典雅,封面上那略带沧桑的肖像,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她的人生故事,引人入胜。
评分我一直对那些能够穿越时空,与伟大的灵魂对话的书籍情有独钟,而波伏瓦的回忆录无疑就是这样一部著作。我曾读过她关于哲学和文学的论述,那些严谨的逻辑和犀利的观点至今仍让我受益匪浅。这次拿到的是她的回忆录,而且是其中的第三卷,这让我充满好奇。我非常想知道,在她波澜壮阔的人生旅程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经历和感悟被记录下来。或许是她在写作和哲学研究上的突破,或许是她与萨特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关系,又或许是她对当时社会风貌的细致观察和独到见解。我预感,这会是一部充满智慧的光芒,同时又饱含人间烟火气的作品。我期待着在字里行间,重新认识这位传奇女性,去理解她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她在时代浪潮中如何坚持自己的信念。这本书的纸张和排版都十分考究,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仿佛握在手中的是一段珍贵的时光。
评分这次入手的是波伏瓦回忆录的第三卷,单是拿到书的重量和触感,就让我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期待。我一直认为,波伏瓦不仅仅是一位哲学家,更是一位用生命书写思想的实践者。她的作品,总能将宏大的哲学命题拉回到个体生存的真实境遇中,引发人深思。而回忆录,更是直接触及到了她灵魂的脉络。第三卷,我想象中会包含她人生中更为成熟和深刻的思考,或许是对过往的回顾和反思,又或许是对未来方向的探索。我尤其想了解她如何在激荡的时代背景下,保持独立的思想,又如何在爱情、友情和事业之间寻找平衡。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简洁却不失力量,仿佛预示着内容同样充满力量。我迫不及待地想翻开它,去感受波伏瓦独特的叙事风格,去倾听她最真挚的声音,去理解她非凡的人生轨迹。
评分这部作品的封面设计就透露着一种沉静而有力量的气息,封面上波伏瓦的肖像,眼神中带着一丝洞察世事的睿智,又有一丝对过往的留恋。拿到手的时候,就能感觉到纸张的质感,厚实而温润,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这是一种久违的阅读体验,让人忍不住想立刻沉浸其中。我尤其期待能够深入了解波伏瓦在特定历史时期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和她个人的思考。作为一位对二十世纪女性主义思潮有着浓厚兴趣的读者,我一直将波伏瓦视为重要的思想启蒙者。她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文字,总能引发我关于存在、自由、社会性别角色等一系列深刻的哲学思考。我相信,在这一卷的篇幅里,她定会以她一贯的坦诚和深刻,为我们描绘出那个时代女性生活的图景,以及她如何在其中寻找自我定位和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希望这本书能像她之前的著作一样,既有文学的温度,又有思想的深度,让我能在阅读中获得知识的滋养,也能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评分拿到这本《波伏瓦回忆录(第3卷)》,让我有一种与一位智者对话的预感。我一直欣赏波伏瓦的思想深度和她对自由与责任的深刻洞察,她的存在主义哲学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启发。但是,纯粹的理论论述有时会显得有些疏离,而回忆录,则为我提供了一个更具象、更有人情味的角度去理解她。我期待着在这第三卷中,能看到她如何将那些抽象的哲学理念,融入到她丰富而曲折的人生经历中。或许是她在创作过程中的挣扎与突破,或许是她与身边重要人物的情感纠葛,又或许是她对社会变革的观察和思考。我希望通过阅读,能够更立体地认识这位女性,感受她的喜怒哀乐,理解她的选择与坚持。这本书的装帧设计,传递出一种内敛而丰富的气质,与波伏瓦一贯的风格十分契合,让我对内容充满了美好的想象。
评分波伏娃(1908——1986)于1908年1月9日出生于巴黎比较守旧的富裕家庭,父母均是天主教徒,但她从小就拒绝父母对她事业和婚姻的安排,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父亲的律师工作受到影响,全家生活困顿。因此,波伏娃的少女时代是在枯燥闭锁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波伏娃酷爱读书,性格沉稳,14岁时突然对神失去了虔诚的信仰。波伏娃生活和创作的核心建立在令人惊骇的反叛性上。波伏娃头脑明晰、意志坚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好奇心。当她还是名不见经传的穷教师时就开始写作,决心成为名作家。由此她终身不断努力,勇往直前,沿着成功之路成为了20世纪思想界的巨星。
评分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感到应该接近共产党,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党的否定态度与我们的无政府主义不谋而合。我们希望资本主义失败,不过,我们希望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不要剥夺我们的自由。正因为如此,萨特在1939年9月14日的日记里写道:“我现在正在纠正社会主义,如果我需要纠正它的话。”可是,1941年,在他组建一个抵抗团体的时候,他将两个词——社会主义和自由——组合起来命名他的这个团体。战争让他有了一个决定性的变化。
评分19岁时,她发表了一项个人 "独立宣言 ",宣称 "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在当时法国的第一高等学府巴黎高师读书时,她与萨特、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这些影响战后整个思想界的才子们结为文友。在通过令人望而生畏的教师资格综合考试时,波伏娃的名次紧随萨特排在第二。她和萨特相识后,两人有共同的对书本的爱好,有共同的志向,成为共同生活的伴侣,但终生没有履行结婚手续。这两个有志于写作的人彼此维护着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一起工作一同参加政治活动。他们住在不同的地方,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隐私权,但每天都见面,常共同工作或是边喝威士忌边交换意见,而且常常一起外出旅行。并互相尊重对方与其他人的性关系,但两人建立在互相尊重,有共同信仰基础上的爱情非常强烈,萨特去世后波伏娃写了《永别的仪式》,是对和萨特共同生活的最后日子的痛苦回忆,流露出强烈的爱情。纵观波伏娃的一生,萨特可以说是她最深爱、最尊重的人物,不过,两人也都有被其他异性吸引的时期。
评分波伏娃将存在主义哲学和现实道德结合在一起,写过多部小说和论文,她的小说《名士风流》获得了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小说的主题在于说明知识分子不能为革命和真理同时服务,两位主人公的革命目的和方法虽然不同,但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都失败而牺牲了。此外她还写过多部小说如《女宾》,《他人的血》,《人不免一死》, 以及论文《建立一种模棱两可的伦理学》,《存在主义理论与各民族的智慧》,《皮鲁斯与斯内阿斯》等,提出道德规范与存在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她一直被人们视为是第二萨特。
评分这一胜利抹去了我们往日的种种失败,它属于我们,它展示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执政的那些人是曾经程度不同地直接参加过抵抗运动的抗敌人士,我们都认识他们。我们在报章和广播中的那些负责人中有许多朋友:政治已经变成一种家庭事务,我们希望参与其中。加缪在9月初的《战斗报》上撰文说:“政治不再与个人分离,它是一个人向其他人在直接演讲。”向其他人演讲是我们搞写作的人的任务。战前,很少有知识分子试图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而所有的知识分子——或者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未能了解自己的时代,而且,我们最敬重的那个阿兰,竟然堕落了。我们应该接着去完成这一使命。
评分女生可以看看,比较有意思吧
评分西蒙娜.德.伏娃一生写了许多作品,如:《第二性》是她获得世界性成功的一部巨著,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意志、智慧的一本书,被誉为女人的“圣经”,成为西方女人必读之书。西蒙娜。德。伏娃的《第二性》是人类求索中的女性哲学,向所有的读者,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提示了当代妇女面临的问题:生命的自由、坠胎、卖淫和两性平等。既是当代妇女问题的探寻,也是历史与永恒的品味。波伏娃还将自己作为 "一种特殊的女性状态 ",在四卷本回忆录中 "暴露给世人 "。她用卢梭《忏悔录》式的笔调坦诚率真地剖析自己。尽管《第二性》曾经使她遭受到恶毒狂怒的攻击,而诸如 "性贪婪 "、"性冷淡 "、 "淫妇 "、 "慕雄狂患者 "、 "女同性恋者 "等恶骂之声仍不绝于耳。但是,这一切不能阻止她将自身作为反传统、追求个体独立的典范,不加粉饰和修改地奉献出来。1955年9月,也就是波伏娃47岁的时候,她和萨特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联袂来到中国访问了两个月,两年后发表了《长征》一书。
评分很好。
评分波伏娃传记,还不错哦,都瘦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改变命运:奥朗德自述 [Changer de desti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81089/rBEhWlHt5mcIAAAAAAG2rbP0LKAAABS6ANSpSoAAbbF25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