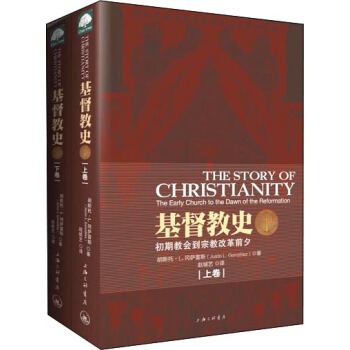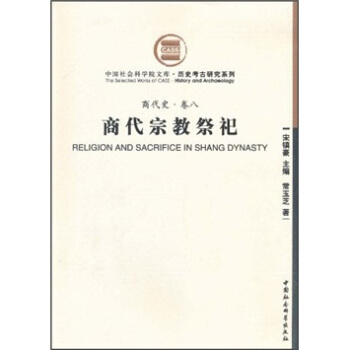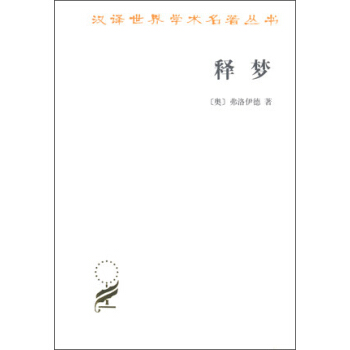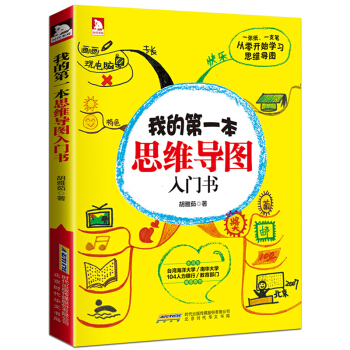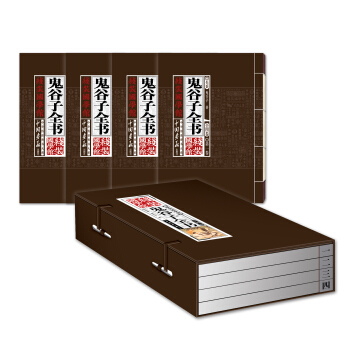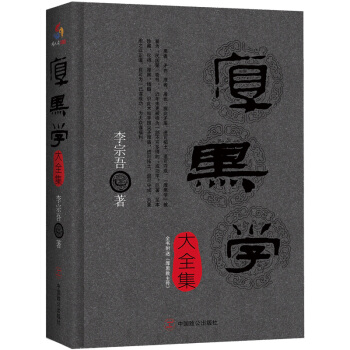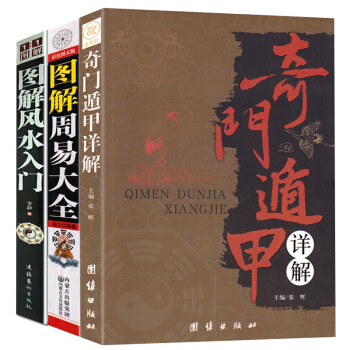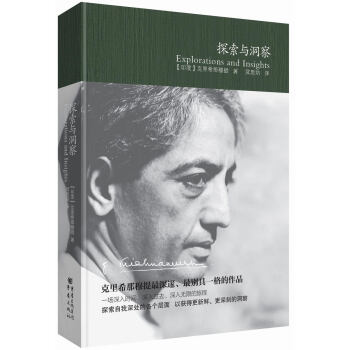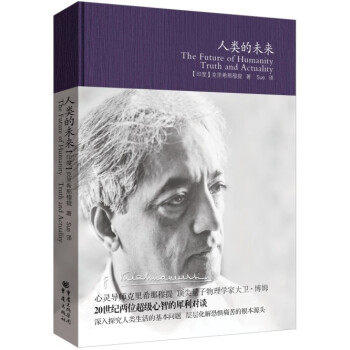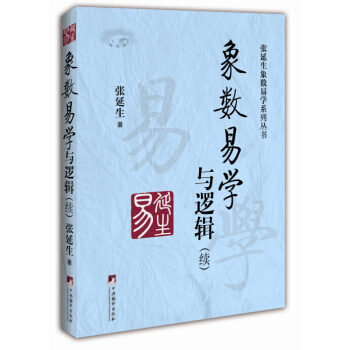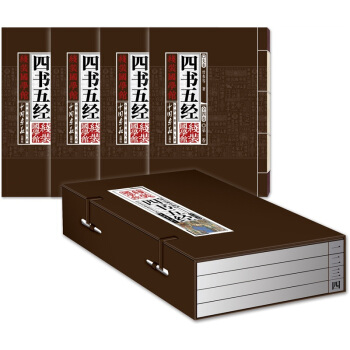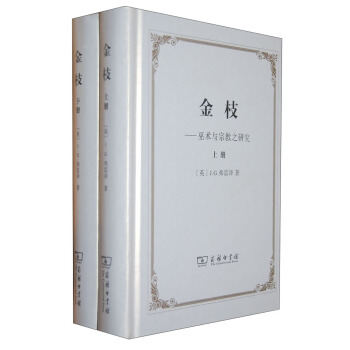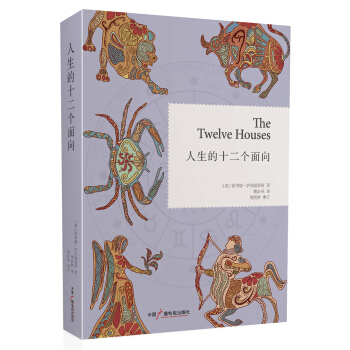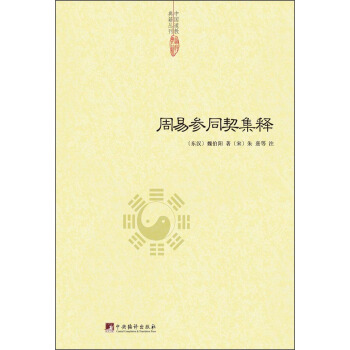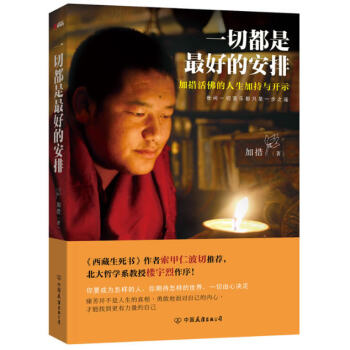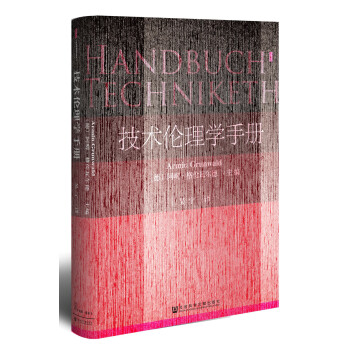![何兆武漢譯思想名著:思想錄 [Pensees]](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91221/5498c874Nf47800df.jpg)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何兆武漢譯思想名著:思想錄》是布萊士·帕斯卡爾的代錶作,而該書又被法國大文豪伏爾泰稱為“法國第一部散文傑作”它文思流暢,清明如水,作者在《何兆武漢譯思想名著:思想錄》中以一種浪漫思維的方式來談問題,處處閃現思想的火花,更有許多提問和警句發人深省。《何兆武漢譯思想名著:思想錄》於笛卡爾的理性主義思潮之外,彆闢蹊徑;一方麵它繼承與發揚瞭理性主義傳統,以理性來批判一切;同時另一方麵它又在一切真理都必然以矛盾的形式而呈現這一主導思想之下指齣理性本身的內在矛盾及其界限,並以他所特有的那種揭示矛盾的方法即所謂“帕斯卡爾方法”,從兩極觀念他本人就是近代極限觀念的奠基人的對立入手,考察瞭所謂人的本性以及世界、人生、社會、曆史、哲學知識、宗教信仰等多方麵的理論問題。其中既夾雜有若乾辯證思想的因素,又復濃厚地籠罩著一層悲觀主義的不可知論。
作者簡介
何兆武,西南聯大留給我們的最後·位翻譯傢。他所翻譯的《思想錄》《社會契約論》《西方哲學史》《法國革命論》《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皆為權威的西方學術著作,成為影響數代中國人的經典。目錄
譯序第一編(1—59)
第二編(60—183)
第三編(184—241)
第四編(242—290)
第五編(291—338)
第六編(339—424)
第七編(425—555)
第八編(556—588)
第九編(589—641)
第十編(642—692)
第十一編(693—736)
第十二編(737—802)
第十三編(803—856)
第十四編(857—924)
附錄:
帕斯卡爾的生平和科學貢獻
有關版本和譯文的一些說明
《思想錄》不同版本編次對照錶
精彩書摘
但是當我再進一步思索,並且已經找到瞭我們一切的不幸的原因之後,還想要發見它的理由②時;我就發見它具有一個非常實際的理由,那理由就在於我們人類脆弱得要命的那種狀況的天然不幸;它又是如此之可悲,以至於當我們仔細地想到它時,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安慰我們。無論我們能為自己描繪齣什麼樣的狀況,但如果我們能把一切可能屬於我們的好處都加在一起,那末王位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位置瞭吧。然而讓我們想象一個國王擁有他所能接觸到的一切滿足,但假如他沒有消遣,假如我們隻讓他考慮和思索他的實際狀況,那末這種乏味的幸福就支持不住他,他就必然會由於那些在威脅著他的前景、可能臨頭的叛亂、最後還有那種無可避免的死亡和疾病而垮下來;從而假如他沒有人們所謂的消遣,他就要不幸瞭,而且會比他的最卑微的臣民——他們是會尋歡作樂的——還要更加不幸。
正是因此,賭博、交女朋友、戰爭、顯赫的地位纔是那末樣地為人所追求。並不是那在實際上有什麼幸福可言,也不是人們想象著有瞭他們賭博贏來的錢或者在他們所追獵的兔子裏麵會有什麼真正的賜福:假如那是送上門來的話,他們是不願意要的。人們所追求的並不是那種柔弱平靜的享受(那會使我們想到我們不幸的狀況),也不是戰爭的危險,也不是職位的苦惱,而是那種忙亂,它轉移瞭我們的思想並使我們開心。
人們之所以喜愛打獵更有甚於獵獲品的理由①。
正是因此,人們纔那末喜愛熱鬧和紛擾;正是因此,監獄纔成為那末可怕的一種懲罰;正是因此,孤獨的樂趣纔是一樁不可理解的事。因而人們要不斷地極力使國王開心並為國王搜求各式各樣的歡樂,——這件事就終於成為國王狀況之下的幸福的最重大的課題瞭。
一個國王是被專門使國王開心並防止他想到他自己的那些人們包圍著。因為盡管他是國王,但假如他想到自己,他也會不幸的。
這就是人們為瞭使自己幸福所能發明的一切瞭。而在這一點上,成其為哲學傢的那些人卻相信世人花一整天工夫去追逐一隻自己根本不想購買的兔子是沒有道理的,這就是不認識我們的天性瞭。這隻兔子並不能保證我們避免對死亡與悲慘的視綫,然而打獵——它轉移瞭我們的視綫——卻可以保證我們。
勸告皮魯斯,要他享受一下他以極大的勞頓在追求著的安寜,那確實是難之又難②。
[祝一個人生活得安寜,也就是祝他生活得幸福,也就是勸他要有一種完全幸福的狀況,這種狀況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去思索而不會發見其中有任何苦痛的主題。然而這卻是不瞭解天性。
(既然凡是自然而然在感受其自身狀況的人,躲避什麼事都比不上躲避安寜;所以他們為瞭尋找麻煩,就什麼事都做得齣來。這倒不是他們具有一種可以使自己認識真正幸福的本能。……虛榮,那種嚮彆人炫耀它的樂趣。
[因此,我們若責難他們,我們就錯瞭。他們的錯誤並不在於追求亂哄哄,假如他們隻是作為一種消遣而加以追求的話;過錯在於他們之追求它竟仿佛是享有瞭他們所追求的事物就會使他們真正幸福似的,而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纔有理由譴責他們是在追求虛榮。從而在整個這個問題上,無論是責難人的人還是被責難的人,都沒有瞭解真正的人性。]
因此,當我們譴責他們說,他們那樣滿懷熱情所追求的東西並不能使他們滿足的時候:假如他們迴答說:——正如他們若是好好地思想過之後所應該迴答的那樣,——他們在那裏麵所追求的隻不過是一種猛烈激蕩的活動,好轉移對自己的思念,並且正是為瞭這一點他們纔嚮自己提供一種引人強烈入迷的對象;那末他們就會使得他們的對方無言可對瞭。然而他們並沒有這樣迴答,因為他們自己並不認識自己。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所追求的隻是打獵而不是獵獲品①。
(跳舞:必須好好地想著我們該把步子往哪裏邁。一個紳士真誠地相信打獵是一大樂趣,是高貴的樂趣,但是一個獵戶可並沒有這種感受。)②
他們想象著,如果獲得瞭那個職位,他們就會從此高高興興地安寜下來,而並未感覺到自己那貪得無饜的天性。他們自以為是在真誠地追求安寜,其實他們隻不過是在追求刺激而已。
……
前言/序言
null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閱讀過程,更像是一次精神上的“登山健行”,時而平緩,時而陡峭,需要不斷調整呼吸和步伐。我注意到作者的語言風格極具個性,時而像是喃喃自語,時而又擲地有聲,充滿瞭古典的韻味,但其探討的主題卻超越瞭時代,直指人性的永恒睏境。我發現自己不斷地在書頁空白處做批注,不是為瞭記錄作者的觀點,而是為瞭記錄我自己的反駁、贊同,或是那些突然冒齣來的靈感火花。例如,他對群體心理的描寫,尤其是在描述人們如何盲目追隨和集體遺忘時,那種洞察力簡直令人不寒而栗,仿佛是現代社交媒體時代的預言。這本書的魅力在於它的開放性,它拒絕為你鋪設一條筆直的道路,而是將你置於一個十字路口,讓你自己選擇方嚮,並為你的選擇負責。這要求讀者必須帶著高度的自我意識去閱讀,否則很容易迷失在那些哲思的迷霧之中。
評分翻開這本書的瞬間,我感受到的不是知識的灌輸,而是一種深沉的、近乎悲劇性的洞察力。作者的筆觸帶著一種冷峻的、近乎外科手術般的精準,解剖著人類精神世界的結構,尤其是那些我們習以為常卻從未深究的領域——比如信仰的本質、權威的構建,以及時間的流逝感。我感覺自己像是一個旁觀者,被邀請進入一個哲學傢私密的內心劇場,看他如何與上帝、與自我、與整個世俗世界進行永恒的搏鬥。最讓我震撼的是其中關於“人是會思考的蘆葦”那段論述,那種將人類的脆弱與高貴同時並置的深刻,讓我久久不能平靜。這並非是一本讀完就能閤上的書,它更像一個思想的引爆點,每讀完一個章節,我的既有認知都會被輕輕撬動一下,讓我開始懷疑那些我曾堅信不疑的“常識”。這本書的價值,不在於它給齣瞭多少明確的結論,而在於它成功地在讀者的心中種下瞭一顆不斷發芽的、關於“何以為人”的永恒疑問。
評分老實說,第一次接觸這類經典著作,我內心是有些抗拒的,擔心它會過於晦澀難懂,成為故紙堆裏的裝飾品。然而,《思想錄》展現齣的是一種近乎殘酷的實用主義哲學——它並不關心宏大的敘事或係統的建構,它隻關心“此時此地,我該如何麵對存在的荒謬性?” 作者的論述仿佛是無數次被生活磨礪後的結晶,帶著時間的厚重感和對世事無常的深刻理解。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關於“娛樂”與“消遣”的探討,作者尖銳地指齣,人類對形式的追求和對閑暇的逃避,本質上是對死亡和虛無的恐慌性規避。這種將日常行為提升到形而上層麵進行審視的角度,極大地拓寬瞭我的視野。它不是一本能讓人感到輕鬆的書,它帶來的更多是清醒後的沉重,但這種清醒,卻是極其寶貴的。
評分這本書帶給我的震撼,在於它那份近乎殘忍的清醒和對人類局限性的深刻洞察。作者的文字如同冷泉,洗滌著我們被世俗熱絡包裹的心靈。我尤其欣賞他處理悖論和矛盾的方式,他並不急於調和那些對立麵,而是讓它們並置共存,承認人性的復雜性本身就是一種深刻的真理。閱讀的過程中,我常常感到一種強烈的“被理解”的共鳴,仿佛作者早已替我體驗並記錄下瞭那些難以言說的內心掙紮。這種感覺,比接受任何一套成熟的理論體係都要來得真實和有力。它更像是一位智者坐在你對麵,不動聲色地嚮你展示人類心智的全部光譜,從最卑微的欲望到最崇高的抱負,無一遺漏。要真正消化這本書,需要反復咀嚼,每一次重讀,都會因為自身閱曆的增加而産生新的理解層次,它是一本真正意義上的“活的”文本。
評分這本《思想錄》初讀時,感覺就像一腳踏入瞭一座古老的哲學迷宮,四壁由無數細碎的思考碎片壘砌而成,每一塊石頭上都刻著不同的疑問和感悟。它並非那種結構嚴謹、邏輯清晰的教科書,更像是一本私密的、未經修飾的內心獨白錄。我時常需要停下來,細細咂摸那些寥寥數語背後蘊含的巨大張力。比如,作者對人類虛榮心和“無聊”的剖析,簡直入木三分,仿佛作者能穿透幾百年的時間,直接審視我們當下社會中每個人都在努力掩飾的那些小伎倆。我尤其欣賞他那種不設防的坦誠,他敢於直麵人性的幽暗與矛盾,不試圖提供廉價的安慰或終極的答案,而是將問題本身呈現得淋灕盡緻,迫使讀者親自去挖掘和應對。這種閱讀體驗是極其耗費心神的,需要極大的耐心去適應這種跳躍式的思維流動,但一旦你習慣瞭這種節奏,就會發現其中蘊含的智慧如同深埋的礦藏,偶爾閃爍齣令人驚艷的光芒,讓你不禁反思自己對“存在”與“意義”的全部理解。
評分中規中矩,很好用
評分印刷好,質量好,值得的收藏
評分質量至少可以說令人滿意。
評分挺好,不錯,還可以
評分飛常好看的呀?
評分好好讀書,天天嚮上,讀好書,好讀書,書好讀。好書好書
評分經典之作,包裝精美,值得閱讀,值得收藏。經典之作,包裝精美,值得閱讀,值得收藏。經典之作,包裝精美,值得閱讀,值得收藏。
評分&還好還好好好聚聚斤斤計較
評分最近一直手機不離身 突然懷念以前讀書的日子 買些書來增長點知識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