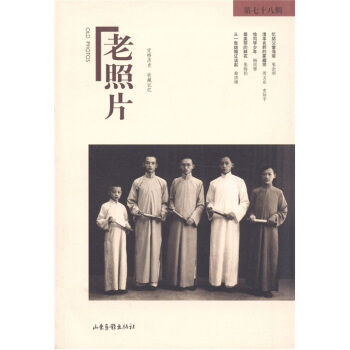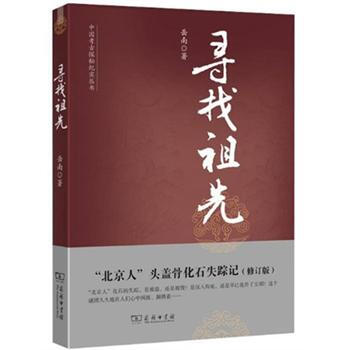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他们从山上来,终却不知飘向何方?他们带来了另类的文化,带给了中国历史一片崭新气象……在绵延至今的人类文明长河中,中国唐朝曾以其宽容开放的胸襟、颠覆传统的个性,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然而又有谁知道,在这颗绮丽璀璨的名星绽放之前,曾有过一个神秘的民族,默默地把自己的能量注入了她的血液。为什么唐太宗能够毫无顾忌地打破汉族正统观念,欣然接受少数民族送他的“天可汗”尊号?也正是因为他身上流着这个民族的血!李唐王朝与这个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李唐王朝是由这个民族与汉族的混血家族建立的。我
内容简介
他们金发碧眼,他们黄帝族系遗失在异域的支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个不同于黄种人的民族。他们具有白种人的相貌特征:金发碧眼。他们继匈奴之后第二个称霸蒙古草原,他们永不言败,建立过多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甚至在中国历史辉煌的盛唐文明中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印记!他们就是鲜卑人。
公元630年,唐太宗欣然接受了北方民族送给他的“天可汗”尊号。“天可汗”是北方民族对统治者的敬称,对以正统自居的古代中原王朝来说,接受这一称谓无疑意味着降低了自己的身份。然而唐王朝却依然我行我素,不以为忤,这是为什么呢?有学者考证,唐王室具有明显的鲜卑血统。中国历史上辉煌的盛唐王朝,竟是鲜卑与汉族的混血家族建立的。
从唐太宗欣然接受北方民族送他的“天可汗”尊号,到盛唐社会流行的“胡音胡骑与胡妆”,充分说明了鲜卑文化在唐朝社会无处不在。原来鲜卑人已经在盛唐文明中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鲜卑,这个击匈奴之后第二个称霸蒙古草原的民族,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建立政权多的民族,曾经上演过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剧,爆发出令世界为之震颤的力量。
如今,鲜卑作为一个民族已经随风消逝,但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金发碧眼的炎黄子孙。
内页插图
目录
引子 巍巍兴安岭:东亚文明发展的动力源第一章 兴安岭的第一个主人:被称为“东胡”的人们
一、秦开与长城:东胡与匈奴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原动力
二、退守鲜卑山:一次并不成功的西进
三、赤髯碧眼老鲜卑:具有白种人特征的“炎黄子孙”
第二章 仰天长啸:蒙古草原的第二个主人
一、接管蒙古草原:200年踯躅迁徙后的“意外”收获
二、千呼万唤始出来:鲜卑第一英雄檀石槐
三、暗杀:低成本肢解鲜卑帝国的新尝试
第三章 目标锁定中原:东部鲜卑的南向之路
一、顽固坚持旧传统的反面教材:昙花一现的段部
二、学习汉文化的新途径:趁乱吸纳汉族流民的慕容廆和他的前燕政权
三、短暂复国:真命天子慕容垂和他的跳蚤子孙们
四、延续了东胡祖脉的匈奴人:退回大山的宇文部
第四章 入乡随俗:淹没于河西走廊的西部鲜卑
一、仙人指路:锐意东进的秃发鲜卑
二、崛起于乱世:在向西退却中建国的乞伏鲜卑
三、慕容部的近亲:坚持游牧的吐谷浑
第五章 天狼西向:远走中亚的厌哒人
一、白匈奴:从蒙古草原走出的第二头狼
二、幸运的波斯人:拒绝推倒多米诺骨牌的厌哒帝国
三、次大陆的梦魇:厌恶佛教的征服者
四、速兴速亡:被自由散漫毁掉的中亚霸主
第六章 打开南北朝历史的出口:最后走出兴安岭的拓跋部
一、千古之谜嘎仙洞:苍茫林海,何处是我家?
二、从鲜卑山到呼伦湖畔:蜕变、新生、成熟中的拓跋人
三、神兽传说:这就是鲜卑吗?
四、“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充满血腥的拓跋祖先世系
第七章 北魏:一个性格裂变的王朝
一、立贤还是立长?——面对亡国之痛的困惑
二、北魏平城时代:拓跋珪的早期统治
三、赐死太子:拓跋宏锐意推进的汉化改革
四、“六镇”:无法调适的文化裂变
五、江山破碎:激进改革无法医治的后遗症
第八章 胡气满长安:盛唐气象的历史因缘
一、向老子求救:鲜卑化李唐皇室的无奈选择
二、文化上的南北朝:中国区域格局的划时代转变
三、胡音胡骑与胡妆:大唐盛世的新时尚
尾声 留在故乡的人们
精彩书摘
第八章 胡气满长安:盛唐气象的历史因缘在鲜卑人自己的政权灭亡以后,作为一个民族,鲜卑人逐渐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久居中原与汉族杂处,他们慢慢地与汉族融为一体。除了慕容、长孙、独孤这样明显的鲜卑姓氏之外,似乎他们并没有留下任何标志性的文化因素,就是这些鲜卑人的姓氏也演变为典型的汉族复姓。但如果我们认真解析继鲜卑人之后兴起的盛唐王朝,则会发现,鲜卑人已经在盛唐文明中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印记。鲜卑人在融入汉族的过程中,也将自身的文化融入汉族文明,对汉族文明是改革、是发展,推动着中原文明的进步。中华文明历五千年绵延不绝,与其能不断得到来自北方民族的新鲜血液的补充有着直接关系。
鲜卑人不仅在文化上影响了盛唐,历史学家们甚至发现,唐皇室明显具有鲜卑人血统,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盛唐王朝,竟是鲜卑人与汉族的混血家族建立的。
一、向老子求救:鲜卑化李唐皇室的无奈选择
按照正史中的说法,唐王朝的皇室李氏家族出自陇西,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是陇西成纪人(今甘肃秦安)。李渊的七世祖李暠,就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割据河西的西凉政权的创立者。在最讲究门第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方四大名门世家为崔、卢、李、郑,但其中的“李”姓指的是赵郡李氏,而不是陇西李氏。为抬高自己的门第,在唐朝初年,皇室也曾一度自称出于赵郡李氏。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的先世要么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要么是赵郡李氏的“假冒牌”。但根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赵郡李氏的显著支派的活动范围,不出原常山郡,其微弱支派也有在巨鹿居住的,但都与陇西没有关系。
据说李暠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十六世孙,可是世家大族重视的是文官而非武将,将家世追溯到抗击匈奴一辈子也未能获得封侯的李广,不见得能给李氏增加什么光彩。
来自于陇西的李氏并不是传统的世家大族,即使在其夺取帝位以后,在老牌世家的眼中也还只是一个“暴发户”。这些魏晋以来的名门望族甚至以与李唐皇室通婚为耻辱。为了弥补自家出身低的不足,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就命大臣高士廉、韦挺等人重新排定全国世家大族的等级,写成《氏族志》一书。高士廉等人没有明白李世民的用意,在书的初稿中,还是将山东世族黄门侍郎崔干定为第一等。李世民看过后大为不满,对高士廉等人说:“我现在要重新确定族姓等级,目的是要提高当朝官员的社会地位,为何还要把崔氏列为第一!现在确定等级,不必考虑各家族几代以前的门第,只以现在的官职高下作为划定等级的依据。”高士廉等人虽对原书进行了修改,将皇族陇西李氏列为第一,后族长孙氏列为第二,但还是不得不把崔氏列为第三。
但这种事需要社会至少是世家大族的普遍认同,并不是皇帝的一纸命令就可以改变的。李世民新刊定的《氏族志》,传统的高门大族都不屑一顾,他们虽然嘴上不敢说,但心中仍旧蔑视陇西李氏。
为改变这种状况,皇室不得不下功夫为自己寻找一个更富有号召力的祖先。于是,李氏将其始祖由李暠上溯到李广,再上溯到先秦道家学派的始祖、后来被道教奉为太上老君的老子李耳,宣称唐高祖李渊是李耳的五十六代孙,唐太宗李世民是李耳的57代孙。
在中国的姓氏发展史中,李姓的历史并不十分古老,其出现不会早于周代。《姓解》即说:“周之前未见李氏。”传说老子的母亲怀胎长达81年,最后在李树下割左腑而生老子。如果将在母腹中的时间记入其年龄的话,老子出生时就已经81岁了,所以传说老子生下来头发就是白的。传说中没有提到老子的父母是谁,只是说他“生而指李树,故为李姓”。如此看来,在老子之前是没有“李”这个姓的。
可是《史记》中明确记载,老子是楚国苦县人,也就是今河南鹿邑县人,他的后裔何时迁入陇西成纪却又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了。
关于李姓的起源还有另一个传说。东夷族首领皋陶,曾在尧、舜时代担任大理之职(掌管刑法的官),于是以官名为姓氏,称“理”氏。因为在古字中“理”与“李”相通,所以后来改写为李氏。但是,李家是不可能将始祖上溯到东夷人皋陶的,编造家谱本来是为了炫耀门第,如果反而由此将自己归入“夷狄”之流,岂不是得不偿失?所以,李家也只能将老子拉来作为本家族的始祖了。
改认祖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李渊开始经过了六代皇帝,直到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才正式完成了这个过程。唐玄宗下诏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并宣布李暠的后裔都被视为李唐的宗室皇亲。始祖李耳、世居陇西,也就成为李唐皇室家谱的正统说法。目前已经发现的李唐宗室的墓志,如:淮安靖王李寿,虢王李凤,越王李贞,汝南公主李字,长乐公主李丽质,永泰公主李仙蕙,懿德太子李重润,潞王李贤,云麾将军李思训,这些人的墓志上都称其是“陇西狄道人”,可见这种编造的家谱已经成为李唐宗室对外的统一口径。
不仅李唐皇室自称陇西李氏,在整个唐代,凡是李姓,要显示其门第的高贵,也都要假称为陇西李氏,以便与皇室拉上关系,成为“皇亲宗室”。这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时尚,以至有些来自天竺、大食、波斯的外国人的后裔,在被赐姓李氏之后,也都想办法攀附陇西李氏。
按照李唐皇室的正统说法,西凉李暠共有10个儿子,其中李歆(字士业)为西凉后主,也就是唐皇室的祖先。
李飜-李 宝-李冲
李暠
李歆-李重耳-李熙-李天锡—李虎-李昺-李渊-李世民
照这样看来,李冲与李熙是同一祖父的堂兄弟,血统十分接近。在北魏太和年间,李冲宗族十分显贵,当时的世家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比,他们一系为陇西显贵望族,但他们并不承认李熙这一族是同族兄弟。由此看来,李唐皇室自称是西凉李暠之后,虽然这个门第不够辉煌,但很可能也是冒充的。
另外,陈寅恪先生发现,李熙的父亲李重耳的经历,与史书中记载的李初古拔的经历几乎一模一样,很可能李重耳就是李初古拔,也就是说,李唐王室可能是李初古拔的后裔,而不是西凉李暠的后裔。
自李熙之孙李虎开始,李唐皇室祖先的事迹才开始清楚起来。李虎,字文彬,陇西成纪人,曾是北周宇文泰手下大将,后被封为柱国大将军、太尉、尚书左仆射、陇西郡公,并赐姓大野氏。至隋文帝杨坚在北周执政时,允许其复姓李。李虎生有八子,李昺为小儿子,这就是李渊之父,李世民的祖父。
可是,如果李唐皇室不是出自陇西李氏,他们究竟是出自何族呢?
据释彦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记载,唐代僧人法琳曾当着李世民的面,对李家出自老子、属于陇西李氏的说法加以驳斥:“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法琳明确指出,唐皇室的李氏不是出自老子,也不是陇西李氏,而是拓跋达阇改汉姓的产物,李家是拓跋达阇的后裔。由此看来,李家祖上竟是鲜卑人,其鲜卑语的姓氏为拓跋,与北魏皇室同姓。如果此说成立,我们倒可以将唐王朝看成了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的复兴了。
我们在史书中还可以发现,李渊的祖父李虎有兄名“起头”,有弟名“乞豆”,起头之子名“达摩”,显然,这些都不是汉语名字。如果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是对的,李氏始祖真的是李初古拔的话,这也不是汉语名字。这无疑提醒我们,法琳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否则他也不会当着皇帝的面指斥皇族出自鲜卑人,这毕竟是要冒被杀头的风险的。
如果真如法琳所说,李氏出自鲜卑人,我们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就要有一个新的认识了。北魏不再是鲜卑人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此后鲜卑人不仅又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还统一了全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自439年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之后,至1911年清王朝灭亡以前,除了明王朝统治下的267年时间以外,主宰中国政坛的都是北方民族。
当然,说李唐皇室出自鲜卑人,目前还只是部分历史学家的推测,远不足以形成定论,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但说李唐皇室具有鲜卑人的血统,则是无可置疑的。
李世民的祖父李昺的妻子独孤氏,是鲜卑名将独孤信的女儿。
独孤信,本名独孤如愿,武川镇(今内蒙武川西南)人,祖籍云中。其祖先伏留屯曾任部落大人,到独孤信的祖父俟尼时,举部迁往武川。俟尼去世后,独孤信的父亲独孤库继任部落酋长,其妻费连氏也出身于鲜卑贵族之家。独孤信相貌俊美,精于骑射。在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后,独孤信归属西魏,因战功受封为八大柱国之一,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大臣。
独孤信共有六子七女。长女嫁给了北周明帝,生周宣帝;小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杨坚,生隋炀帝杨广;四女儿就是李昺的妻子,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因为他的女儿中出了三位皇后,而且是不同朝代的皇后,还各自都有儿子继承了皇位,独孤信也被称为“三朝国丈”、“中国第一岳父”。
李世民的外祖父窦毅也是鲜卑人,在北周为八大柱国之一。窦氏是其汉姓,其鲜卑语的姓氏为纥豆陵氏。李世民的外祖母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宇文氏,而建立北周的宇文氏被认为出自东部鲜卑三部之一的宇文部,是鲜卑化的匈奴人,在北魏统治期间,他们已经被视为鲜卑人了。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与李渊的婚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得上是比武招亲。窦毅让人在家门上画了两只孔雀,谁能在百步外射两箭,每箭射中一只孔雀的眼睛,就招谁女婿。结果是,前来应试的几十人中,只有李渊两箭都射中了。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其父系血统是否出自鲜卑人姑且不论,就其母系而言,他至少存在一半的鲜卑族血统。而唐代最伟大的君主李世民,其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四位当中,除祖父的族属难以确定之外,其他三位都肯定是鲜卑人,李世民的身上至少有四分之三的鲜卑族血统。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是鲜卑人,可以肯定,在李唐的前三位皇帝中,鲜卑族的血统在逐渐增强。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结构安排是极其巧妙的,它就像一棵参天大树,根基是深厚的地理与气候分析,主干是关键的军事与政治演变,而枝叶则是社会风俗、宗教信仰和法律制度的细致展开。我常常会停下来,反复揣摩作者对特定历史节点的论述,比如鲜卑族南迁的必然性,书中给出的解释远比以往我读到的任何版本都要具有说服力。它将经济地理、气候变化与军事战略紧密地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严密的逻辑链条。更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作者在探讨鲜卑统治下的赋税和土地制度时,展现了极强的专业性,这部分内容往往是其他历史作品会一带而过的。书中对于“州郡制”在北方的适应性改造,以及如何平衡游牧贵族与汉族士人的利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直接关系到一个帝国的长期稳定。读完这些分析,我深切体会到,一个政权的建立固然需要武力,但其延续则依赖于精密的制度设计。这本书为我理解古代王朝的治理难题,提供了全新的工具箱。
评分读完这本厚重的《鲜卑帝国》,我最大的感受是,它成功地挑战了我对传统“中原史观”的一些固有认知。这本书的视角非常独特,它没有将鲜卑视为仅仅是中原王朝的对立面或入侵者,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欧亚大陆交流网络中进行考察。作者在论述中融入了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异域文献的交叉对比,使得整个叙事框架显得极为坚实和具有说服力。比如,书中对柔然、匈奴等周边族群的相互影响有着精辟的论述,这让我意识到,鲜卑的崛起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整个北方草原民族生态系统调整的结果。其中关于“汉化”与“保持本色”之间那微妙的张力,作者的处理尤为精彩。它不是简单的“同化”或“被同化”,而是一种充满张力的选择与适应。我特别喜欢作者对于文化精英阶层如何平衡两种身份认同的刻画,那份内心深处的撕扯和最终的融合,读来令人唏嘘。全书的语言风格偏向于学术的严谨,但又穿插着富有感染力的史诗感,使得即使是复杂的政治经济分析,也显得清晰而引人入胜。
评分老实说,我很少能在一本历史著作中找到如此清晰的时代脉搏感。《鲜卑帝国》不仅是一部关于过去的书,它似乎也在和我们当下的世界进行某种对话。作者在行文的收尾部分,对鲜卑文明在中华文明长河中的最终“消融”与“贡献”进行了富有哲理性的反思,这让我受益匪浅。它探讨了文化身份的流动性与持久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没有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而是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思考空间。阅读过程中,那些鲜卑语的名字、陌生的神祇、异域的风物,在作者的笔下变得不再遥远和陌生,反而有了一种亲近感,仿佛我们现代人也能从中找到某种历史的共鸣。这本书的排版和装帧也相当精良,字体适中,注释清晰,便于查阅,这对于深度阅读者来说是极大的福音。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兼具学术深度、叙事魅力和思想高度的杰作,它彻底刷新了我对“鲜卑”这个历史符号的认知。
评分这本《鲜卑帝国》简直是历史爱好者的一场饕餮盛宴!我原本以为这只是一部枯燥的年代史,没想到作者的叙事功力如此了得,将那个遥远而又充满活力的时代描绘得栩栩如生。初读,最让我震撼的是它对早期游牧民族社会结构的深入剖析,那种深入骨髓的文化差异感,让人仿佛亲身站在了广袤的草原上,感受着铁蹄与风沙的洗礼。作者没有简单地罗列事件和人名,而是巧妙地穿插了大量的侧面描写和细节考证,比如不同部落间复杂的血缘关系、祭祀仪式的神秘色彩,甚至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工具和食物,都经过了细致的打磨。阅读过程中,我多次被那些充满力量感的历史瞬间所吸引,比如铁弗的崛起、拓跋氏的融合与转型,这些都不是教科书上那种扁平化的描述,而是充满了人性挣扎和时代洪流的复杂画卷。尤其是对于鲜卑人如何从四散的部落逐渐凝聚成一个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帝国”的过程,作者展现了惊人的洞察力,那种由内而外的变革力量,远比单纯的军事征服来得深刻和持久。这本书不仅仅是在讲述“谁打败了谁”,更是在探索一个强大文明的诞生与演变,读完后对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的理解,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评分说实话,我最初是抱着怀疑的心态翻开《鲜卑帝国》的,因为市面上关于这个时期的作品汗牛充栋,很容易陷入窠臼。然而,这本书在处理人物群像方面,展现出了令人惊喜的细腻和深度。它并没有把历史人物塑造成道德的化身或纯粹的恶人,而是展现了他们作为复杂个体的挣扎与决策。比如,对于某位关键的拓跋君主在关键时刻的几次重大战略转向的分析,作者没有急于下定论,而是细致地还原了当时的朝堂气氛、各方势力的掣肘以及他个人的性格弱点,这使得人物形象瞬间丰满起来。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描述战争场面时所采取的克制手法,它不像一些通俗历史那样追求场面的宏大和血腥,而是侧重于展现后勤补给的难度、不同兵种之间的协同作战效率,以及战争对基层社会结构造成的长期影响。这种“由下而上”的视角,让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独角戏,而是无数普通人生存图存的缩影。这本书的史料运用非常扎实,引用的注释和考证工作量是惊人的,但阅读体验却流畅自然,这得益于作者高超的叙事节奏把控。
评分有帮助质量好丰富内容
评分这个书是经典书籍,买下收藏,以后再看看。
评分这系列的都很好,,很不错,,,值得看
评分不错的书,概括了鲜卑族的历史。
评分至于为什么外族最终都被汉族同化,我觉得所谓的汉族文化只是很不重要的一方面,或者干脆只是幌子,真正重要的是汉族的制度能很好地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而让他们稳定地把皇位坐下去。(比如本书中提到的,鲜卑人汉化之后才开始世袭制度等等。)咋没见哪个外族以及汉族人自己去崇敬思想和理论对统治阶级毫无利益的庄子呢?谁规定只有孔子才叫“文化”?
评分总以为彩图太多的书不严肃,不过,这是一本还算严肃的彩图书。
评分好评!
评分李世民的母亲是鲜卑人已经众所周知,如果李氏家族本身也是鲜卑人,那就太颠覆了。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强盛的王朝是汉族人建立的,当然,汉族人在唐朝过后估计也消失得差不多了。
评分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老照片(第85辑) [Old Photo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135587/rBEHalDBZOgIAAAAAADSBNmpqP4AADK4QC1lakAANIc81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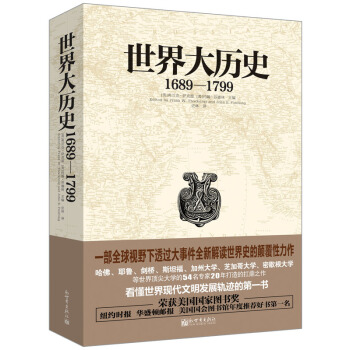
![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 [Fatal Purity:Robespierr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38214/54c21b14Naecc64ac.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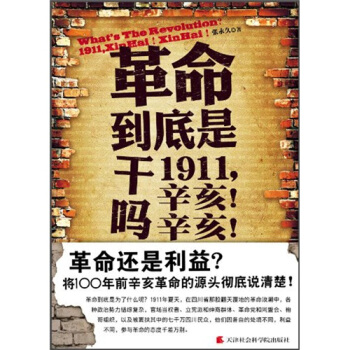
![老照片(第87辑) [Old Photo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10242/rBEQWVFnhi8IAAAAAAkiR4Pz0FAAAD9IQH6CN8ACSJf55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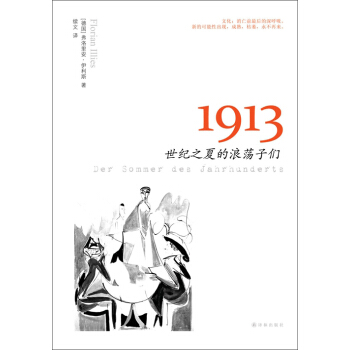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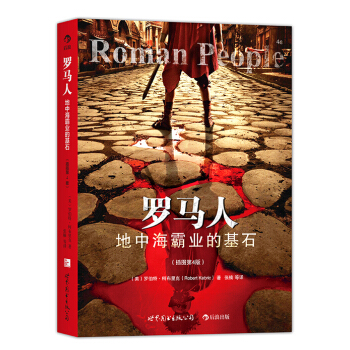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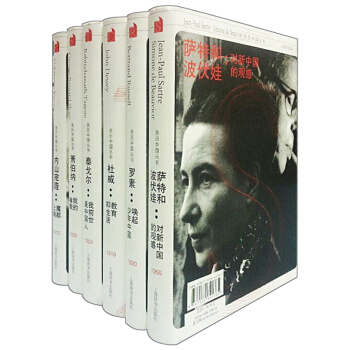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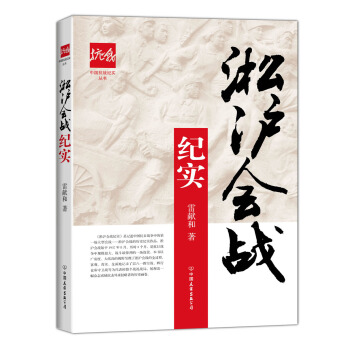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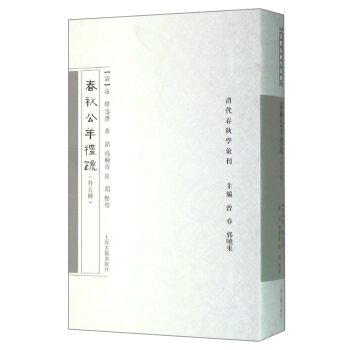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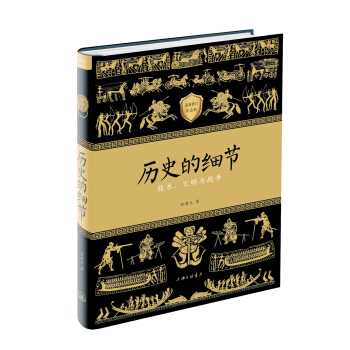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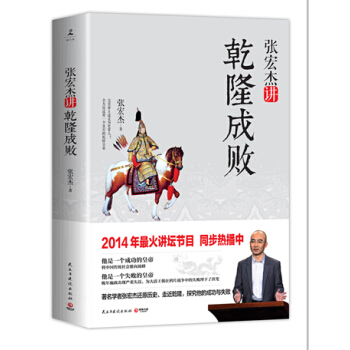
![一口气读完大宋史 [A VERY SHORT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109630/b2cbe69f-c4cc-4df5-b1da-b384e60c316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