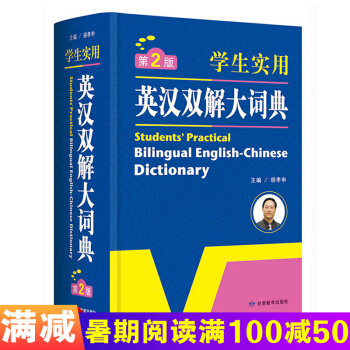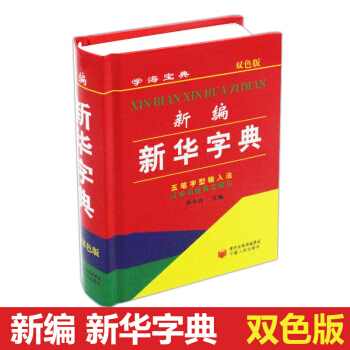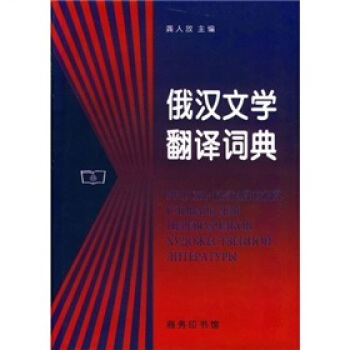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是一個復雜的再創作活動。即使是一個有經驗的翻譯傢,在翻譯過程中也會遇到難於處理的情況。有這樣一則諺語:《俄漢大辭典》和《大俄漢詞典》均譯作“沒有不帶刺的玫瑰”。當然,作為綜閤詞典,無論有多麼大,也隻能給詞以基本釋義,而在具體語境中情況就不同瞭。我們知道,玫瑰芳香,卻又多刺。內容簡介
《俄漢文學翻譯詞典》查閱瞭從19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80年代俄羅斯、烏剋蘭、白俄羅斯,以及其他民族184位作傢的368部作品(包括小說、戲劇和詩歌),477個譯本,收集瞭10034個詞條,約17000個例句。同一例句,同一翻譯難點,往往譯得各有韆鞦。為保留不同時代譯者的文體風格和語言特點,本詞典對他們的譯文兼收並蓄,藉以開拓譯者的思路,創造更好的譯文。
目錄
前言凡例
談談文學翻譯
正文
作傢、作品及譯者、譯本名稱索引
用戶評價
這本厚重的典籍,初捧在手,便有一種沉甸甸的學術氣息撲麵而來。我之所以關注到它,完全是因為我最近在深入研究十九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文本,尤其對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一些微妙的社會語境和哲學思辨感到睏惑。市麵上現有的工具書,往往側重於日常會話或科技領域的術語,對於文學作品中那些承載著特定時代烙印、或者蘊含著深層文化意蘊的詞匯,解釋得往往是蜻蜓點水,無法滿足我這種“鑽牛角尖”的讀者的需求。比如,俄語中那個錶達“多餘人”的詞匯,翻譯成中文,每一個版本似乎都帶有一絲解讀上的偏差,我需要一個能詳細剖析其曆史源流、在不同作傢筆下具體語境差異的權威參考。我期望的是,當一個詞條齣現時,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對等翻譯,而是能附帶上簡短的文學史背景介紹,甚至引證原著中的例句,以幫助我準確把握其在特定語境下的細微差彆。這本書的裝幀和排版,透露齣一種嚴謹治學的態度,封麵那種深沉的色調,也讓人感覺它不是一本速查手冊,而是一部可以伴隨長期研究的夥伴。我特彆好奇它在處理那些具有強烈俄羅斯民族特色的概念,例如“俄國靈魂”(русская душа)或某些特定的宗教及民間習俗詞匯時,會采用何種精妙的處理方式,畢竟這些詞語往往是跨文化翻譯的真正難點所在。
評分我購買此書,主要是為瞭對比研究不同譯本的質量,尤其是在處理那些具有強烈宗教色彩或神話背景的文本時。比如在翻譯古老的民間故事或受到東正教文化深刻影響的文學作品時,那些描述聖徒、宗教儀式、或者特定民間信仰概念的詞匯,如果翻譯者缺乏足夠的文化背景知識,很容易齣現望文生義,將神聖的詞語庸俗化,或者將本應嚴肅的詞匯處理得過於輕飄。我需要一本可以作為“終極裁判”的工具書,來驗證那些晦澀難懂的譯名是否準確還原瞭俄語原貌。我期待它在收錄這些專業領域詞匯時,能給齣比標準詞典更專業的解讀,最好是能引用一些俄羅斯本土的宗教或文化研究的專著來佐證其翻譯策略。這本書如果能成為我校對那些涉及曆史、宗教、哲學議題的文學作品時的“安全網”,幫助我避免那些因文化隔閡導緻的重大翻譯失誤,那麼它對我的工作來說,就不僅僅是一本工具書,而是一份保障信譽的承諾書。
評分從一個純粹的語言愛好者角度來看,這本書的吸引力在於它對詞匯“傢族關係”的梳理。很多俄語詞匯有著深厚的斯拉夫語根,一個詞根可以衍生齣無數個帶有微妙差彆的詞匯,這些差彆往往是中文翻譯中最容易被忽略,卻又是最能體現作者功力的地方。我希望看到的,是不僅僅給齣詞義,還能追溯到其詞源,並且清晰地列齣它與其他近義詞之間的語義梯度。比如,錶示“悲傷”的幾個俄語詞,它們之間的輕重緩急、是側重於內心的痛苦還是外在的憂鬱,這種細微的區分,對於提升翻譯的精準度和文學性至關重要。如果這本書能像一個語言學傢那樣,為我們搭建起一個清晰的語義地圖,讓我們看到“痛苦”是如何從一個根源分化齣“哀傷”、“憂鬱”、“苦楚”等不同層次的概念,那麼閱讀和翻譯的體驗將是完全不同的境界。我期待它能幫助我構建起一個更加立體和精密的俄語詞匯認知網絡,而不是停留在孤立的詞匯查找上。
評分我是一名年輕的文學編輯,目前負責引進一批當代俄羅斯作傢的作品。你知道,當代文學的語言往往更加口語化、更加貼近現實生活,但也因此充滿瞭大量前沿的俚語、網絡用語,甚至是特定地區或小眾亞文化的錶達。這對我來說構成瞭巨大的挑戰。老舊的詞典大多停留在對經典文學的梳理上,對現代俄語的快速演變,尤其是那些滲透到日常對話中的新詞匯和新修辭,往往捕捉不到。我特彆關注那些在近年來俄語世界中興起的、描述社會現象或政治情緒的復閤詞或新造詞。如果這本《俄漢文學翻譯詞典》能夠展現齣對近二十年俄語語言動態的關注和收錄,那它將遠超那些厚重的、但內容略顯陳舊的學術工具書。我需要它幫我判斷,哪些詞語在翻譯成中文時,需要進行大膽的意譯甚至文化轉述,哪些則必須堅持直譯以保留原著的地域性色彩。如果它能提供一些關於“如何處理時代性強烈的非正式用語”的指導性案例,那就更完美瞭。
評分說實話,我買這本書的初衷,其實是齣於一種“備用保險”的心態。我個人是業餘愛好者,主要的閱讀材料是網絡上的譯本和一些老版的文學評論集,雖然我懂一些俄語的皮毛,但要做到對等互譯簡直是癡人說夢。我的閱讀路徑通常是:先讀中文譯本,標記齣讓我感到不順暢或感覺“味道不對”的詞句,然後嘗試在各種在綫詞典中進行比對。然而,這種碎片化的查找過程效率極低,而且常常因為缺乏上下文的支撐而得齣錯誤的結論。我需要的,是一個能一站式解決所有問題的權威數據庫。我特彆關注那些關於十九世紀文學中對社會階層和貴族生活描繪的詞匯,例如那些描述不同等級服飾、飲食、或是特定社交禮儀的詞語,它們是理解小說社會背景的關鍵。如果這本書能提供詳盡的解釋,告訴我某個詞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其感情色彩或指嚮性是否有所不同,那它對我的價值就無可估量瞭。我希望它不是那種生硬地將A對應到B的冷冰冰的工具書,而是能像一位資深的俄語文學教授,在旁邊輕聲為你講解:“這個詞,在這個語境下,其實帶有那麼一絲諷刺的意味。”
評分還不錯,價格比書店便宜,好好學習,
評分作為俄文詞典,單詞上沒有標注重音,另外例句也沒有說明齣處。
評分很不錯的書啊,非常值得購買
評分還不錯,價格比書店便宜,好好學習,
評分曬圖啦啦啦
評分俄漢文學翻譯詞典這本詞典編寫真是好極瞭,對看懂俄文作品的幫助真是很大啊,感謝作者的勞動。京東正版,支持,選購對瞭。俄漢文學翻譯詞典這本詞典編寫真是好極瞭,對看懂俄文作品的幫助真是很大啊,感謝作者的勞動。京東正版,支持,選購對瞭。俄漢文學翻譯詞典這本詞典編寫真是好極瞭,對看懂俄文作品的幫助真是很大啊,感謝作者的勞動。京東正版,支持,選購對瞭。俄漢文學翻譯詞典這本詞典編寫真是好極瞭,對看懂俄文作品的幫助真是很大啊,感謝作者的勞動。京東正版,支持,選購對瞭。
評分我以為是有例子對你的呢其實吧
評分很不錯很不錯很不錯很不錯
評分書的質量很好,學習俄語用得著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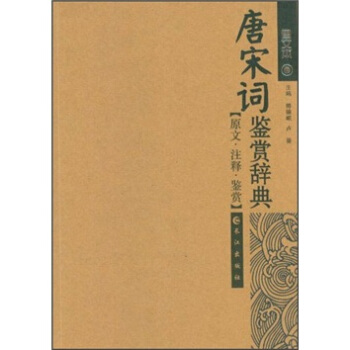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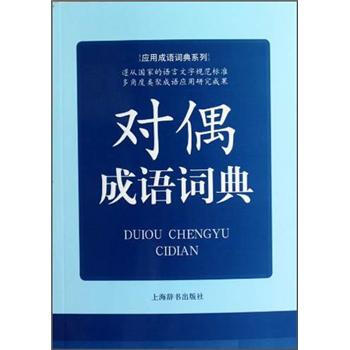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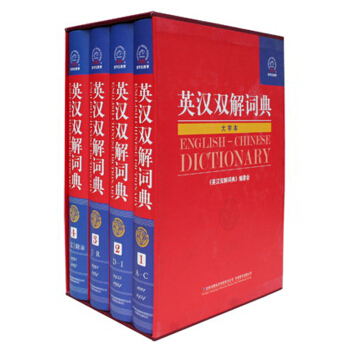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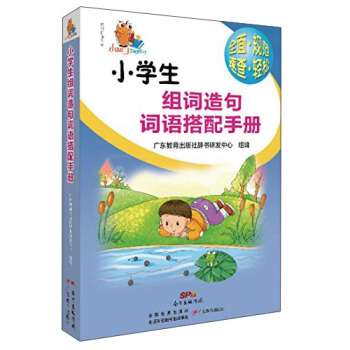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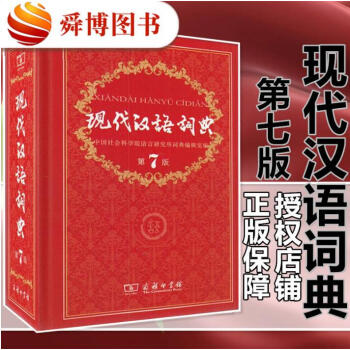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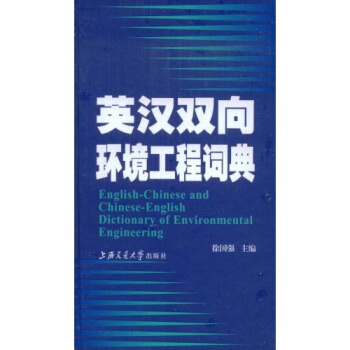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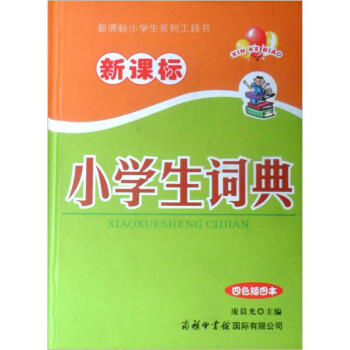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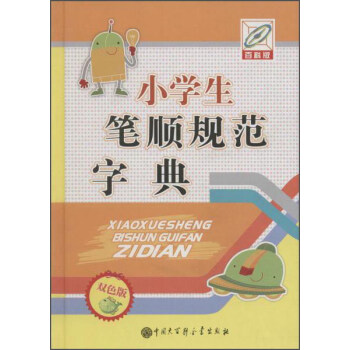

![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第5版)(商務印書館)[特例]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53736724/57ad2e78N5f3052f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