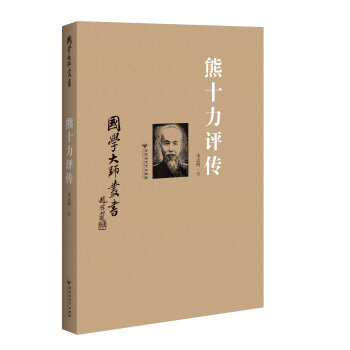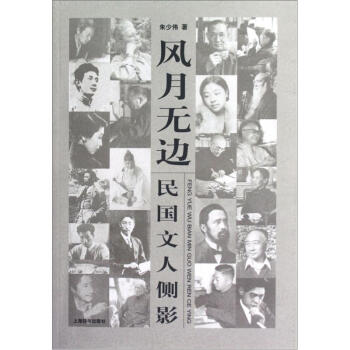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民国文人系列·风月无边:民国文人侧影》以茅盾、巴金为代表的海派文学,以蔡楚生、袁牧之为代表的海派电影,以田汉、于伶为代表的海派话剧,以周信芳、盖叫天为代表的海派京剧,以吴湖帆、刘海粟为代表的海派书画.以庞莱臣、张葱玉为代表的海派收藏,以赵超构、徐铸成为代表的海派报业,以黄炎培、陶行知为代表的海派教育等,可谓是少长成集、群贤毕至、英才辈出、大师云集,形成了人才高地和精英舞台。目录
序康有为:种菜闭门吾将老
黄宗仰:儒释同致殷忧国事
庄蕴宽:时代潮流不可拂
孙毓修: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
欧阳竞无:穷老苍茫一卷经
梁启超: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
黄炎培:坚持素食几十年
于右任:为办报三次蒙难
鲁 迅:在病逝前还关心《译文》
杨明斋:万里拓荒,一身是胆
朱少屏:青年当与世界通声气
苏曼殊:亦僧亦俗多才多艺
夏丐尊:要把这本书全部翻译出来
李大钊: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
李汉俊:用“新时代丛书”巧周旋
李 达:“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
陈望道:真理总是不胫而走的
郭沫若:铁佛披金色相黄
徐悲鸿:运用“禅”的智慧搞创作
林语堂: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
毛泽民:上海书店是极要紧的阵地
茅 盾:要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
郁达夫:拔剑光寒倭寇胆
徐志摩:我的诗魂的滋养全得靠你
杜重远:重新把这火炬撑着
田 汉:欲打破文坛的惰眠状态
郑振铎:工作万不能就此终止
瞿秋白:同胞起来,救国最要紧
老 舍:字纸篓子是我的密友
张大千:墨落能生万壑云
阿 英:冒险出版《西行漫画》
冰 心:大海赋予了宽阔的胸怀
夏’衍:必当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
梁思成:艰辛寻觅唐代木结构建筑
杭稚英:宁可穷困也不给日商绘画
沈从文:创作似建“小庙”
丁 玲:它一定会流传到全世界
巴 金:我不过在旁边呐喊助威
戴望舒:你的梦开出花来了
郭大力:在破庙里研读《资本论》
臧克家:一人双手编《文讯》
施蛰存:开辟一条创作的新蹊径
潘汉年:无躲入象牙之塔里的资格
邵洵美:搞出版“赔完巨万家产”
叶浅予:古稀尝叹路崎岖
赵朴初:同张射日弓,待看乾坤转
张乐平:我的作品还没有成熟
季羡林:对佛教研究始终锲而不合
聂 耳:一九三四年是我的音乐年
穆时英: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
苏 青:常是为着生活而写作
汪曾祺:从西南联大走出的作家
张爱玲: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
跋
精彩书摘
借住盛家的“辛家花园” 一九一四年六月,康有为抵达申城,很快相中“辛家花园”(今新闸路一0一0号中华新村),便立即租赁,年租金为一千四百四十银元(约折合今人民币十万元)。 “辛家花园”原为犹太商人辛溪所拥有,后来破产被以发售彩票的方式拍卖,易主盛宣怀,但一般市民仍习惯沿用旧称。该园占地十亩,围墙呈红色,进门即迎长约三十米的木桥,过桥有走廊贯穿两个亭子,廊边近水处可坐着垂钓;园内曲径纵横,林木茂盛,花卉遍地,一派江南田园风光。康有为对矗立的两座宫殿式楼房挺满意,分别起名为“游存楼”和“补读楼”;他还在花园里搭起凉棚,种植瓜果,饲养了大龟、海豹、澳洲袋鼠等观赏动物。 康有为和家眷在“辛家花园”过了八年悠闲的隐居生活。在此期间,康有为遇到一件极为伤感的事,就是他那年仅二十四岁的三太太何旃理突患腥红热,不幸病故。为纪念英年早逝的爱妾,康有为找到暂宿“辛家花园”的徐悲鸿,请这位青年画家依据遗照绘了她的油画肖像。同时,康有为还怀着深情写下了绵绵千言的《金光梦》词,其中云:“浓艳凝香带叶妍,粉痕墨晕态犹鲜。而今落尽残红后,读画题诗更惘然。一枝浓艳发遗香,剩粉残笺空断肠。色相华严常示现,殿将画谱拾群芳。”曾有评论说,这首爱情悲歌堪称康有为诗中的“绝品”,虽不似自居易的《长恨歌》那样有名,那样感人,但也是和血带泪的倾诉,是至真至诚的表述,一字一句都流露了真情实感。 一直租赁盛家住宅终究不太方便,亦非长久之计,于是康有为决定迁出 “辛家花园”。嗣后,盛宣怀之妻把该园捐献给佛门,后来改建为里弄。相传系康有为当年亲手种植的几棵广玉兰树,迄今仍在原址亭亭玉立。自建“ 游存庐”和“莹园” 一九二一年春,康有为在上海愚园路置地十亩,仿“辛家花园”的风格,造起豪华的园林式住宅“游存庐”,他的《游存庐落成》诗充分表达出自己乔迁新居的喜悦:“自有天游入非想,默存独乐始于今。”数年后,康有为还利用这里的沿街房屋开办了天游学院。 “游存庐”的主要建筑,是中西合璧的楼房“延香堂”,两层共十间屋,楼上楼下均有走廊;另有传统形式的平房“三本堂”,其名源于《荀子· 礼论》的“天为生之本,祖为类之本,圣为教之本”。此外,园内有座古色古香的“竹屋”,它形似附近简照南(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创办人,与康有为长相往来)宅院中的“茅庐”,外面饰翠竹、内部系木质,康有为常在这里会友;园内还挖了一个曲折的大池塘,上架两座木桥,水面可划船;挖池起出的泥土则堆成一座假山,山腰分布着茅亭;各处种植樱花四百株、桃花四百株、红梅数十株和开绿花的梨树,以及菊花、玫瑰等,并有葡萄架、紫藤棚;还饲养了一些观赏动物,如金鱼、孔雀、猴子、麇鹿、驴子等。 翌年,康有为想享受郊野之趣,遂于上海杨树浦临江之处筑“莹园”,并按江南田园格局设计,简单中显现水乡农夫躬耕田野、安居乐业之意境。 “莹园”落成之日,康有为很早就起身,他仰视茫茫苍穹,又凝视被晨曦撒上金色的江面,不禁吟出《新筑别墅于杨树浦临吴淞江作》诗:“白茅覆屋竹编墙,丈室三间小草堂。剪取吴淞作池饮,遥吞渤海看云翔。种菜闭门吾将老,倚槛听涛我坐忘。夜夜潮声惊拍岸,大堤起步月似霜。”嗣后,康有为和家眷常坐着马车,悠然地去那儿小住,远眺日出东海之美景。 一九一九年初夏,年逾花甲的康有为迎娶杭州船家少女张阿翠为六姨太(一说为七姨太),婚礼在“游存庐”举行时,邀请了不少达官贵人、名流大亨,轰动上海。康有为对张阿翠很宠爱,他不仅亲自为她起大名张光、字明漪,还专门请家庭教师教她读书识字。 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日,康有为过七十岁生日,亲朋好友、门生弟子齐集 “游存庐”。得意门生梁启超赠寿联:“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至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全联集《史记》、《汉书》及《郑康成集》中的句子而成,天然贴切,把康有为比喻为孔圣人,这让一直以“康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煞是喜欢。逊帝溥仪则派徐良从天津送来亲题的“岳峙渊清”匾额和一柄玉如意,作为给康有为的寿诞贺礼;这让他受宠若惊,居然重整前清官服,遥拜天恩,并挥笔写下一份“谢恩折”,让人用小楷誊清,石印千份,分赠前来祝寿的宾客。 不知何故,康有为在“莹园”建成一年后,就把它转让掉;抗战期间,这座别墅毁于侵沪日军的炮火。 “游存庐”也称为“康公馆”,在一九三。年春康家将它出售给浙江兴业银行;该行将原有园林拆除,改建为弄堂式居民楼房四十多栋,定名为“愚园新村”,迄今尚存。……
前言/序言
岁月世事,沧桑红尘。 那曾经的海上民国往事与人物,如今却令人驻足回眸或是缅怀诉说,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情怀与人文的情致。友人朱少伟兄的这本《风月无边:民国文人侧影》,就为我们提供了那个时期翔实生动而又细腻传神的历史信息和人文资源,从而说明我们这座城市的文明记忆依然在延续、人文家底依然被关注。 美国著名的城市学家麦克·黑尔在其《城市社会学》一书中曾说过.一座城市的“现在之未来是在过去中,未来之未来是在现实中”。上海自一八四三年十一月正式开埠后,就开始从封闭性的吴越小城向开放性的沿海城市转型。随着金融、商业、贸易、工业、交通乃至新闻、出版、娱乐业的崛起,上海成为中国近现代意义上最先成熟的城市,使其具有了文化观念上的领先性、思想意识上的开放性与精神取向上的前卫性。也就是说上海的城市结构是中西合璧、变通互补,城市特征是内外兼容、多元互惠,城市生态是五方杂居、移民为主。唯其如此,这座城市能云集并包容了一批精神领袖、思想精英与文化巨子。诚如朱少伟书中所写到的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鲁迅、郭沫若、陈望道、瞿秋白、茅盾、李达、于右任、黄炎培等.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思想库和文化源.打造了中国领先的都市精神之高端平台。如朱少伟在《茅盾:要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中写道:“一九二。年春,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茅盾与陈独秀结识。陈独秀刚由北京抵达申城,正着手在沪继续出版《新青年》杂志,茅盾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茅盾由此亦成为现代文坛最早的党员之一.为他日后的文学耕耘作了精神上的铺垫。由此可见,那个时期的海上文入,大都具有思想的引领和文化的觉悟,从而构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风骨与做派、气度与境界。 一座城市的文化精神,无疑是由人来支撑并展示的,是“包含由文化和有目的的人类行为所造成的状况”。而海派文化精神,既有本土“人的觉醒 ”和“文的自觉”这种传统遗绪,又有欧美“趋时鹜新”和“人性关爱”的那种现代意识,由此构成了我们这座城市最具个性化的都市精神底蕴、最具代表性的都市入文景观,亦见证了这座城市所拥有或具备的原创力和辐射力。“海派文化艺术大系统”或称之为“海派文化艺术圈”,正是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孕育、发展而成,如以茅盾、巴金为代表的海派文学,以蔡楚生、袁牧之为代表的海派电影,以田汉、于伶为代表的海派话剧,以周信芳、盖叫天为代表的海派京剧,以吴湖帆、刘海粟为代表的海派书画.以庞莱臣、张葱玉为代表的海派收藏,以赵超构、徐铸成为代表的海派报业,以黄炎培、陶行知为代表的海派教育等,可谓是少长成集、群贤毕至、英才辈出、大师云集,形成了人才高地和精英舞台。朱少伟的《风月无边:民国文人侧影》,正是对此作了群体的叙事与概括。尽管这本书中的有些人如郭沫若、林语堂、梁思成、沈从文、老舍、冰心等,不属海派文人圈,但他们与上海依然有着相当的地缘、人缘与文缘,他们或是在上海居住过、工作过.或是不少著作是在上海出版,上海成为他们人生旅途中一个重要而温馨的驿站。因此,他们优雅的背影也融入了民国文人的群体侧影中。 为撰写此书,朱少伟兄花了不少时间与精力,探幽抉微、钩沉索引、拾遗补缺,发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从而为海派文化的研究作了添砖加瓦的贡献。对此,我深为敬佩。如果朱少伟还有打算写续集的话,那么如吴昌硕、王一亭、吴湖帆、张元济、史量才、于伶、刘海粟、秦瘦鸥、梅兰芳、柯灵、吴永刚、蔡楚生、袁牧之等,还是值得一书的,从而使之风月无边,群星璀璨。王琪森
二0一二年七月十二日于海上禅风堂灯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让人眼前一亮,封面采用了复古的牛皮纸质感,上面烫金的“民国文人系列”几个大字,古朴又不失雅致。我拿到手的时候,就觉得它不像市面上很多流水线出版的书籍,而是有种精心打磨过的匠心。翻开书页,那略带泛黄的纸张,触感温润,油墨的香气混合着历史的沉淀,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我特别喜欢书中的插图,不是那种华丽的、程式化的绘画,而是用素描或者水墨勾勒出的文人画像,线条简练却神韵十足,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人物的神态,或沉思,或纵情,或落寞,仿佛能透过画纸窥见他们内心深处的波澜。每一个插图都配有简短的文字说明,介绍人物的生平,或者与画作相呼应的经典诗句,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让阅读体验更加立体和富有层次感。我一直对民国时期的文化氛围充满好奇,而这本《风月无边:民国文人侧影》在视觉呈现上,就已经成功地将我带入了那个时代。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可以触摸的艺术品,让人爱不释手,迫不及待地想去探索书中的故事。
评分总的来说,这本书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阅读愉悦和精神满足。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民国文人的书,更是一本关于人性、关于时代、关于情感的深刻解读。作者在处理这些复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展现出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和人文关怀。我非常喜欢书中那种不动声色的幽默感,以及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悯情怀。即使是在讲述一些令人唏嘘的故事时,作者的笔调也始终保持着一份超然,既不过分渲染悲伤,也不刻意制造轻松,而是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其中的韵味。这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让整本书读起来非常舒服,而且余味悠长。我发现,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不仅了解了许多民国文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我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也有了一些新的体悟。那些发生在过去的故事,仿佛也照亮了我当下的生活,让我对人性有了更深的理解,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敬畏。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阅读体验,也让我对“民国文人系列”的其他作品充满了期待。
评分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更像是一次与历史对话的旅程,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启发。它并没有像一些传记那样,按照时间顺序线性叙述文人的生平,而是选取了他们生命中的某个“侧影”,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展现了那些隐藏在宏大历史叙事之外的真实情感和生活片段。我读到一些关于文人之间微妙的情谊,那些难以言说的暧昧,或是因为思想分歧而产生的疏离,都写得非常到位。这些“侧影”并非是对他们才华的简单颂扬,而是深入到他们内心深处,展现他们的挣扎、迷茫、甚至是脆弱。我发现,即便是在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时代,这些伟大的灵魂也同样会经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会为生计发愁,会为情感烦恼,会与时代格格不入。这种“去神化”的描写,反而让我觉得他们更加鲜活,更加真实,也更加贴近我的生活。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文人”这个群体,不再仅仅是书本上的名字,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个体,他们的命运与那个时代紧密相连,他们的选择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真是太令人惊喜了!我一开始还担心它会像很多历史类的书籍一样,充斥着枯燥的史实和过于学术的辞藻,但事实证明我的顾虑是多余的。作者的笔触非常细腻,仿佛是一位老友在娓娓道来,用一种非常平和、亲切的语调讲述着那些发生在民国文人身上的故事。他的叙述中没有刻意的煽情,也没有夸张的戏剧化处理,而是将人物置于那个时代的洪流中,展现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我尤其欣赏作者对细节的捕捉,那些不经意的生活片段,比如一杯清茶,一封信笺,一场雨,都能被他赋予独特的意境,进而折射出人物的性格和当时的社会风貌。读起来丝毫不会感到费力,反而有一种读小说的流畅感,却又比小说多了几分历史的厚重感和真实感。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叙事方式,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引,与书中的人物一同经历悲欢离合,感同身受。这种成熟的叙事功力,是很多作家毕生追求的目标,能在这本书中体验到,实在是一种幸运。
评分这本书带给我的,是一种温和的、却又深刻的思考。我曾以为民国文人都是一群生活在象牙塔里的艺术家,他们的生活充满诗意和浪漫,但这本书却打破了我的这种刻板印象。它让我看到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另一面,看到了他们在乱世中的生存智慧,看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作者并没有回避他们生活中的困顿与无奈,也没有刻意美化他们的情感纠葛,而是以一种非常坦诚的态度,将那些不那么“完美”的侧面也呈现出来。这种真实的力量,反而更加打动人心。我从中看到了他们面对困境时的坚韧,看到了他们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光芒,也看到了他们在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对抗时的无奈。这种对人性的深入挖掘,让我对那个时代有了更立体、更复杂的认识。这本书让我明白,历史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而个体也同样如此,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既是弄潮儿,也可能是被浪涛拍打的孤舟。这种深刻的洞察,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评分民国文人的风采令人钦佩
评分正版图书,送货速度快,好
评分一般般的图书真是一般般
评分非常好的书,值得买,包装也好
评分碑帖临习,就我的经验,可分为三个层次:“眼到”、“手到”、“心到”。其中后两个层次是当前认识比较模糊的地方;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势必影响到以后的创作水平。 先来谈谈“眼到”这一层次即是唐代孙过庭所谓的“察之者尚精”。对法帖中字的用笔、结构、章法要详察细审,既要在静态上把握笔画形态,又要在动态上理解点画间的呼应关系。南宋姜夔在《续书谱》中说:“字有藏锋出锋,粲然盈楮,顾其首尾相应,上下相接为佳。后学之士,随所记忆,图写其形,未能涵容,皆支离而不相贯穿。”在结构上既要看到线条本身在空间中的安排,又要对空白的分布予以重视。清笪重光《书筏》说:“黑之量度为分,白之虚净为布。”即是指出要懂得空间分布之理。而在整体章法上,要注意原法帖的字间行距,欹正关系,润燥疏密等因素。古人讲求章法要“变而贯”,“如织锦之法,花地相间须要得宜。”在这一阶段主要解决的是观察能力的提高,要能看出法帖的微妙之处。许多临习者只得粗枝大叶,整体看去,似乎与原帖相去不远,但在细微处则失之甚多,这和抄书并无区别。前人妙处往往就在一笔一画,甚至一个小动作之中,就如同美人之美亦常在一颦一嗔之间一样。所以王僧虔说:“纤微向背,毫发死生。”姜夔说:“夫临摹之际,毫发失真则神情顿异,所贵详谨。”这时的眼睛要像放大镜,能够将常人注意不到的细节放大。能否做到“眼到”决定了能否“手到”,因此临习者不能盲目机械地照临,应多读帖,多观察。 “手到” 这一境界是在临帖过程中最具基础性的环节。孙过庭说:“心不厌精,手不厌熟”,所谓“手到”不仅是指临得形似,而且要神似,要做到形势相似,下笔自然要缓慢但要写出神气来,则非熟练迅速(相对而言)不可。而二者又是一对矛盾。务必精熟,才能迟速有度。所以古人说:“迟以取妍,速以取劲。先必能速,然空能迟。若素不能速而专事,则无神气;若专事速,又多失势。”在拳学中,“手到”是极关键的,在双方对搏时,一旦得机,须身快手到,才能中敌,不然战机即失。这说明了技术准确性的重要性。事实上,“手到”的境界对于一个学书法的人来说,可谓是难途了。在众多临习者中,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太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临习之初,未能做到“眼到”的境界;二是心态浮躁,临摹功夫尚未下到。这和习太极拳技击一样,如果连拳架都不能达以精熟准确,何谈实战?当前许多临习者对于“拟之者贵似”这一句格言的认识相当模糊,一个“似”字其中所包含的意义远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关于“心到”的境界,理应算达到了临帖的最终要求。但反观当代不少书法创作者在提及他们的临帖经历时都说临过多少多少帖目,某帖目临过多少遍,甚至过百遍。但其所创作的作品中,都难以看到他们从中吸收了多少精髓。最常见的两种情况,一种是有的书写者提到自己曾临《兰亭序》等“二王”帖多年,但在其作品中并无半点“二王”的神韵。如果从创造动机上根本就不想吸收“二王”的营养,那当然另当别论;但既然花了时间去临“二王”,为何连捕风捉影的意思都没有呢?另一种情况是虽然在创作中体现了所学的某些形式因素,但流于程式化,缺乏变通,更无论神韵二字。以上疑问使得笔者开始想到关于临帖的“心到”问题。“手到”虽然标志着临帖已到精熟准确之境,但事实上,仍然处于技术层面,未能真正捕捉到原帖作者心灵深处的生命律动。所谓“形神兼似”也还不过是在笔墨外在形式上的深刻理解,虽然做到这一步已经很难得,但要想对创作起到精神层面的深刻影响,则必须“心到”——去触动前人在挥毫时撩拨性灵的心弦。就像六祖惠能之于达摩,直通心性,而后可言悟道。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乎达情,书不妄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创作的最高境界是“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那么临摹的最高境界也当如此。要想达到这一点,则须要更多地在精神层次上去体会探求。具体到《兰亭序》则不能仅仅追求其形式上的逼肖,而应在充分了解魏晋社会文化大背景及王羲之本人思想个性的基础上,熟读《兰亭》内容,把此文中的思想感情移植到自己的心灵深处,深味那魏晋时代士人独有的心灵“药酒”,试图让这酒的余味渗入你的历史悠思当中去。当你仿佛已听到王羲之等人对人生的咏叹时,或许你将不再处处拘泥于《兰亭》帖某笔某画的固定形态,而达到心手双畅的高境界。唐张怀瓘在《书断》序中说:“若乃思贤哲于千载,览陈迹于缣简,谋猷在觌,作事粲然,言察深衷,使百代无隐,斯可尚也。及夫身处一方,会情万里,标拔志气,黼藻性灵,披封睹迹,欣如会面,又可乐也。
评分付出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
评分民国文人系列·风月无边:民国文人侧影
评分碑帖临习,就我的经验,可分为三个层次:“眼到”、“手到”、“心到”。其中后两个层次是当前认识比较模糊的地方;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势必影响到以后的创作水平。 先来谈谈“眼到”这一层次即是唐代孙过庭所谓的“察之者尚精”。对法帖中字的用笔、结构、章法要详察细审,既要在静态上把握笔画形态,又要在动态上理解点画间的呼应关系。南宋姜夔在《续书谱》中说:“字有藏锋出锋,粲然盈楮,顾其首尾相应,上下相接为佳。后学之士,随所记忆,图写其形,未能涵容,皆支离而不相贯穿。”在结构上既要看到线条本身在空间中的安排,又要对空白的分布予以重视。清笪重光《书筏》说:“黑之量度为分,白之虚净为布。”即是指出要懂得空间分布之理。而在整体章法上,要注意原法帖的字间行距,欹正关系,润燥疏密等因素。古人讲求章法要“变而贯”,“如织锦之法,花地相间须要得宜。”在这一阶段主要解决的是观察能力的提高,要能看出法帖的微妙之处。许多临习者只得粗枝大叶,整体看去,似乎与原帖相去不远,但在细微处则失之甚多,这和抄书并无区别。前人妙处往往就在一笔一画,甚至一个小动作之中,就如同美人之美亦常在一颦一嗔之间一样。所以王僧虔说:“纤微向背,毫发死生。”姜夔说:“夫临摹之际,毫发失真则神情顿异,所贵详谨。”这时的眼睛要像放大镜,能够将常人注意不到的细节放大。能否做到“眼到”决定了能否“手到”,因此临习者不能盲目机械地照临,应多读帖,多观察。 “手到” 这一境界是在临帖过程中最具基础性的环节。孙过庭说:“心不厌精,手不厌熟”,所谓“手到”不仅是指临得形似,而且要神似,要做到形势相似,下笔自然要缓慢但要写出神气来,则非熟练迅速(相对而言)不可。而二者又是一对矛盾。务必精熟,才能迟速有度。所以古人说:“迟以取妍,速以取劲。先必能速,然空能迟。若素不能速而专事,则无神气;若专事速,又多失势。”在拳学中,“手到”是极关键的,在双方对搏时,一旦得机,须身快手到,才能中敌,不然战机即失。这说明了技术准确性的重要性。事实上,“手到”的境界对于一个学书法的人来说,可谓是难途了。在众多临习者中,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太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临习之初,未能做到“眼到”的境界;二是心态浮躁,临摹功夫尚未下到。这和习太极拳技击一样,如果连拳架都不能达以精熟准确,何谈实战?当前许多临习者对于“拟之者贵似”这一句格言的认识相当模糊,一个“似”字其中所包含的意义远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关于“心到”的境界,理应算达到了临帖的最终要求。但反观当代不少书法创作者在提及他们的临帖经历时都说临过多少多少帖目,某帖目临过多少遍,甚至过百遍。但其所创作的作品中,都难以看到他们从中吸收了多少精髓。最常见的两种情况,一种是有的书写者提到自己曾临《兰亭序》等“二王”帖多年,但在其作品中并无半点“二王”的神韵。如果从创造动机上根本就不想吸收“二王”的营养,那当然另当别论;但既然花了时间去临“二王”,为何连捕风捉影的意思都没有呢?另一种情况是虽然在创作中体现了所学的某些形式因素,但流于程式化,缺乏变通,更无论神韵二字。以上疑问使得笔者开始想到关于临帖的“心到”问题。“手到”虽然标志着临帖已到精熟准确之境,但事实上,仍然处于技术层面,未能真正捕捉到原帖作者心灵深处的生命律动。所谓“形神兼似”也还不过是在笔墨外在形式上的深刻理解,虽然做到这一步已经很难得,但要想对创作起到精神层面的深刻影响,则必须“心到”——去触动前人在挥毫时撩拨性灵的心弦。就像六祖惠能之于达摩,直通心性,而后可言悟道。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乎达情,书不妄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创作的最高境界是“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那么临摹的最高境界也当如此。要想达到这一点,则须要更多地在精神层次上去体会探求。具体到《兰亭序》则不能仅仅追求其形式上的逼肖,而应在充分了解魏晋社会文化大背景及王羲之本人思想个性的基础上,熟读《兰亭》内容,把此文中的思想感情移植到自己的心灵深处,深味那魏晋时代士人独有的心灵“药酒”,试图让这酒的余味渗入你的历史悠思当中去。当你仿佛已听到王羲之等人对人生的咏叹时,或许你将不再处处拘泥于《兰亭》帖某笔某画的固定形态,而达到心手双畅的高境界。唐张怀瓘在《书断》序中说:“若乃思贤哲于千载,览陈迹于缣简,谋猷在觌,作事粲然,言察深衷,使百代无隐,斯可尚也。及夫身处一方,会情万里,标拔志气,黼藻性灵,披封睹迹,欣如会面,又可乐也。
评分值得推荐,非常不错的选择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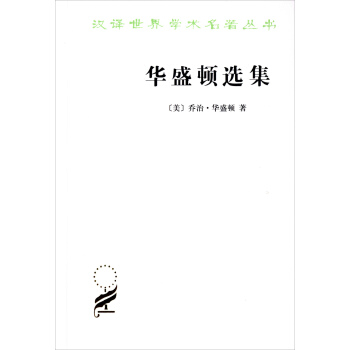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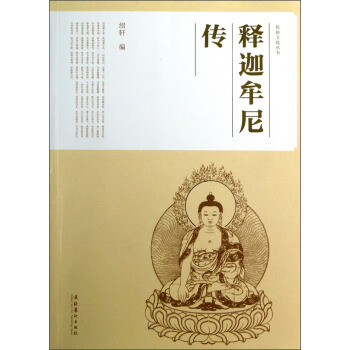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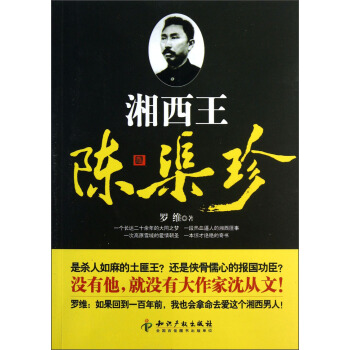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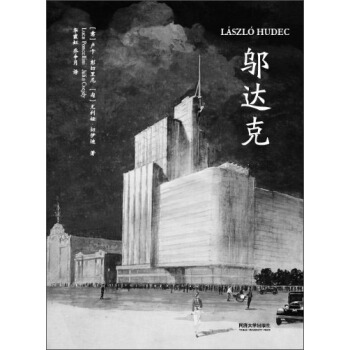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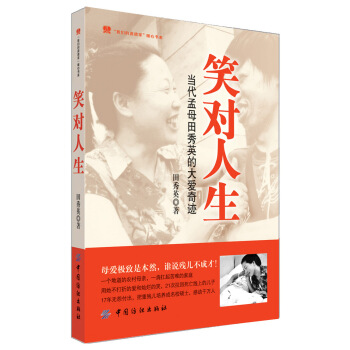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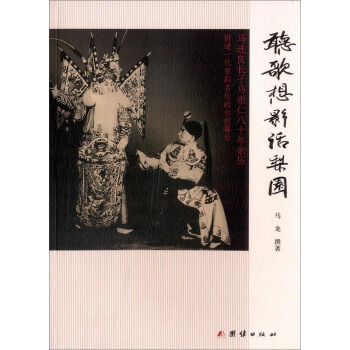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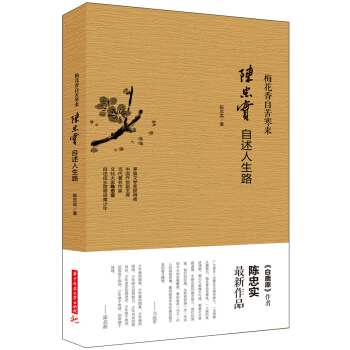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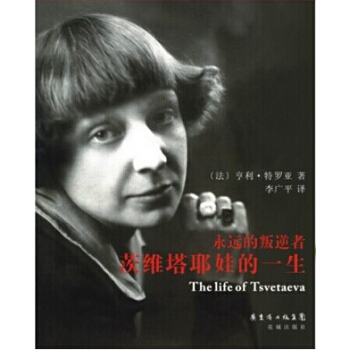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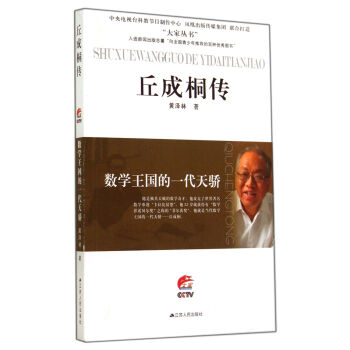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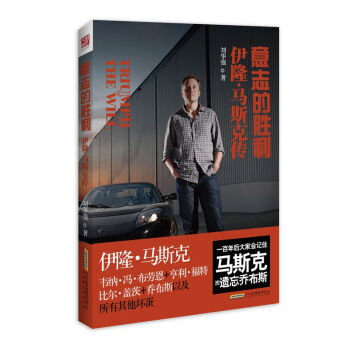
![涵芬香远译丛·尼克松:孤独的白宫主人 [President Nixon Alone in the White Hous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98623/54992c45N589d098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