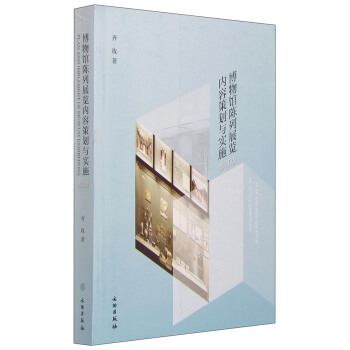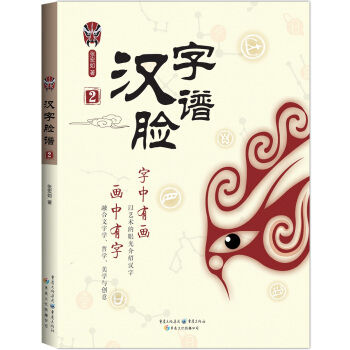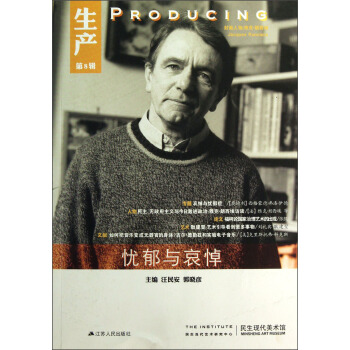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生产(第8辑):忧郁与哀悼》是目前国内介绍欧美新学一个最前沿的阵地。虽然它的译文常常值得商榷,虽然它的版权一直模糊不清,但是它的价值,尤其是对那些渴望了解欧美新思 想的内地读者来说所具有的价值,不容抹杀。内容包括哀悼与忧郁症、哀悼及其与躁狂性抑郁状态的关系、论悲悼剧与悲剧、与他人的归属关系等。目录
专题:忧郁与哀悼哀悼与忧郁症
哀悼及其与躁狂性抑郁状态的关系
论悲悼剧与悲剧
与他人的归属关系
心理分析:消除抑郁的方法
心灵的诞生:忧郁、矛盾、愤怒
抵制左派忧郁
哀悼残存
《情绪精神紊乱:忧郁及抑郁论文集》前言
清算死者:雅克·德里达的哀悼政治学
对米歇尔·福柯的追悼
人物: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
关于政治的十个论点
民主意味着什么?
美学异托邦
审美革命及其后果
电影的眩晕
民主、无政府主义与今日激进政治:雅克·朗西埃访谈
论文
福柯论国家治理艺术的出现
艺术
耿建翌:艺术引导看到更多事物
文献
如何把音乐变成无器官的身体?吉尔·德勒兹和实验电子音乐
用户评价
我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更像是一次与作者进行的私人化、高强度的对话。这本书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安慰或解决方案,它只是忠实地记录了人类面对某些终极命题时,那种无助、但又不得不直面的姿态。它像一面高清晰度的镜子,反射出的是读者内心深处那些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关于脆弱与消逝的角落。读完后,我的感受不是“理解了什么”,而是“被触碰了哪里”。这本书的价值,或许不在于它提供了多少知识,而在于它迫使你重新审视自己与世界、与时间、与自我的关系。它留下的是一种持久的、微弱的震颤,而不是轰轰烈烈的结论。它成功地在你心灵的壁炉旁,燃起了一堆需要小心看护的、幽暗的火苗。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简直是一次视觉上的冒险,那种沉甸甸的质感,拿在手里仿佛能感受到作者那些复杂心绪的重量。封面那种带着些许做旧感的色彩搭配,配合上锐利而又内敛的字体,成功地营造了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疏离感。我特别喜欢它在排版上的考究,字距和行距的把握恰到好处,让阅读过程本身就成了一种冥想的体验。纸张的选取也很有心,不是那种光滑刺眼的铜版纸,而是带着微弱纹理的哑光纸,每一次翻页的沙沙声都像是为接下来的文字做着铺垫。这样的用心,让这本书不仅仅是文字的载体,更像是一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初次上手时,我甚至不忍心立刻打开阅读,而是先沉浸在这种物质形态带来的心理预期之中。它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需要被尊重的气息,让人在阅读前就不自觉地放慢了呼吸。这种对实体书制作工艺的极致追求,在当今这个电子书盛行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和难得。
评分从语言风格来看,作者无疑是一位文学上的“炼金术士”,他将那些通常被认为“阴暗”或“晦涩”的词汇,通过精妙的组合,提炼出了近乎水晶般透明的表达。我注意到他频繁地使用古典修辞手法,比如反讽和借代,但这些手法绝非炫技,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他想要揭示的那个核心的虚无感。例如,他对“希望”这个词的处理,不是直接否定,而是用一系列关于“希望的形态”的描述,最终指向其本质的空洞性,这种迂回的叙事策略极具欺骗性和感染力。他的句式长短交错,有的如长长的河流般绵延不绝,蕴含着无尽的叹息;有的则短促有力,像被瞬间截断的闪电。这种语言上的动态平衡,为全书注入了一种内在的音乐性,即使是晦涩的内容,读起来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韵律感。
评分我尝试着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切入这本书的文本,但很快发现,它似乎拒绝被单一的理论框架所束缚。作者在探讨人性困境时,常常游走在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边界地带,但又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抽身,留下一个开放的、令人不安的悬念。我尤其欣赏那些充满张力的句子结构,它们如同精密的机械装置,将抽象的情感具象化为可以触摸的实体。例如,其中有一处描述“记忆的腐蚀性”,那种将时间流逝比拟为化学反应的精准性,让人脊背发凉。它不是简单地描述悲伤,而是试图解构悲伤的内部运作机制,就像一个冷酷的生物学家在观察一株正在枯萎的植物。整本书的论述逻辑并非线性的推进,更像是多棱镜折射下的光斑,需要读者不断地在不同的角度间切换,才能拼凑出作者试图描绘的那幅破碎的图景。读完一章,我常常需要停下来,让那些密集的、具有穿透力的词汇在脑海中完成消化。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感是极其独特的,它更像是一部慢镜头电影,而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或论著。作者似乎对“暂停”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迷恋,大量的留白和重复的意象被精心布置在文本的关键节点。在描述人物的内心挣扎时,这种缓慢感被放大到了极致,使得每一个细微的情绪波动都被拉长、被剖析,甚至显得有些冗余,但正是这种“过度”的详尽,反而构建出一种令人窒息的真实感。我发现自己开始学着去适应这种节奏,从快速获取信息的阅读习惯中抽离出来,转而沉浸于文本所营造的那个缓慢流逝的时间场域里。这要求读者具备极大的耐心,也要求读者愿意放弃那种寻求即时满足的阅读期待。它不是用来消遣的读物,更像是一次对时间感知力的深度校准。
评分这样看来,就不难理解威廉斯为何会在《漫长的革命》第二部分将触角伸及教育、大众报刊、标准英语等等驳杂的内容了,因为这些都属于文化范畴,承载着活生生的当代体验。纵横捭阖的威廉斯的确不负英语系社会学家的名号,各种分析数据详实、论述细致。后世的文化研究者们无不将此奉为典范,但更重要的是后来者仿佛大梦初醒般也学着将古老的文化概念砸了个粉碎,并且糅合了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各派理论武器,在“文化”的旗号下全面进击日常生活:爵士、摄影、电影以致于肥皂剧、橄榄球和男人的体味。大学教师布置的作业也与时俱进地不再局限于《追忆逝水年华》或《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老友记》和《星际迷航》也可以毫不费劲地套用各种西马、酷儿或后殖民理论。讽刺的是,文化研究飘洋渡海之后,美国的后辈批评家及大学生们并不屑于将伯明翰元老们放入神龛,因此仔细阅读威廉斯著作的学生反而凤毛麟角。事实上,如果他们抛开那些研究人如何与汽车做爱的著作,转而仔细阅读威廉斯的这部著作就会发现他是个多么冥顽不灵的“新左派”,霍尔和莫利的著作都比他更带劲。为什么?因为他写来写去都是关于阅读:报纸、小说、歌谣集或戏剧。
评分这位特立独行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曾被同行讥刺为“误闯了英语系的社会学家”,他出身于威尔士乡间普通铁路工人家庭,对阿诺德-利维斯式精英主义感到深深厌恶,是以与高贵冷艳的剑桥总显得格格不入。他的名声也并不依赖这古老的文化堡垒,而更多地源于朋友霍加特、霍尔等人于1964年组建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因此,从执教牛津大学成人教育开始,他就怀抱着反叛那些高雅文化垄断的夙愿,于是自创出文化社会学的思路来挖掘产生这些作品的文化土壤,即那些“具体表现我们可称之为社会的共同意义的东西”,他坚持认为批评家不该只看见伟大的艺术,“而必须跟各种各样的艺术打交道”(《漫长的革命》,P40)。因为这些也许是拙劣的作品也能够传达不同个体所分享的共同意义,只有全面地分析各种作品才能完整地把握人们当时活生生的经验。所以,他关注报纸、铁路书店卖的畅销小说、各种廉价的小册子,并以此为基础热情地分析着它们与宪章运动之间的种种关联,以勾勒出一个时代的民众最鲜明的“社会性格”和“感觉结构”。
评分这位特立独行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曾被同行讥刺为“误闯了英语系的社会学家”,他出身于威尔士乡间普通铁路工人家庭,对阿诺德-利维斯式精英主义感到深深厌恶,是以与高贵冷艳的剑桥总显得格格不入。他的名声也并不依赖这古老的文化堡垒,而更多地源于朋友霍加特、霍尔等人于1964年组建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因此,从执教牛津大学成人教育开始,他就怀抱着反叛那些高雅文化垄断的夙愿,于是自创出文化社会学的思路来挖掘产生这些作品的文化土壤,即那些“具体表现我们可称之为社会的共同意义的东西”,他坚持认为批评家不该只看见伟大的艺术,“而必须跟各种各样的艺术打交道”(《漫长的革命》,P40)。因为这些也许是拙劣的作品也能够传达不同个体所分享的共同意义,只有全面地分析各种作品才能完整地把握人们当时活生生的经验。所以,他关注报纸、铁路书店卖的畅销小说、各种廉价的小册子,并以此为基础热情地分析着它们与宪章运动之间的种种关联,以勾勒出一个时代的民众最鲜明的“社会性格”和“感觉结构”。
评分东西很好,快递也不错,趁活动便宜买的
评分狼西埃也许最好被描述为一名“当代批判理论家”,确切来说这恰恰是因为他的作品跨越了如此之多的探究领域,鉴于其彻底跨学科的本质,且就他本人一直抵抗任何对他思想的范畴化而言的。也就是说,把本书中收录的作家带到一起的那个泛泛的头衔(即当代批判理论家)抓住了朗西埃思想——它无疑是完全批判且理论化的——的大部分趣味,同时又不会把他的计划限制在任何特定的学科领域之内。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这些人的思想往往停留在某个分类之中(以某个学科为依托)——不一样,朗西埃的作品“避开了分类(elude[d] classification)”[1],这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写作跨越了如此之多的领域:从劳工和思想史延伸到美学,从民主到文学,从政治学到电影。朗西埃的教育和早期接受的训练是按惯常的轨道进行得。和阿尔都塞与德里达一样,朗西埃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生于1940年;和德里达与福柯一样,朗西埃进而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在阿尔都塞的指导下学习。朗西埃对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作出了贡献,但他的论文没有收入该书的英译本。1968年的五月事件对他的思想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但是,和他时代著名的法国批判理论家不一样,朗西埃对阿尔都塞的偏离使他走向了档案研究。朗西埃所谓的历史研究在英语批判理论界并没有得到关注,这些文本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才被译为英文。尽管朗西埃五十多年来出版了许多著作,加伯利埃尔·洛克希尔(Gabriel Rockhill),在2004年的著作中,依然可以准确地把他描述为一个“在英语世界仍然有待全面聆听”的人。[2]然而,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在过去十年间朗西埃的作品迅速成为重新思考政治以及把“美学”计划拓展到“纯粹艺术”的领域之外的重要资源之一。
评分发货速度快,产品质量还好
评分一本好书就像一个好老师。。。赞一个
评分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曾无奈地说:1984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没来,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来了。前者是高压的集权社会;后者是宛在天堂的“自由世界”。环顾我们生存的当下,仿佛置身于赫胥黎所预言的世界,一个宁愿看电视说书人讲论语也不愿翻开《论语》的世界;一个对新版红楼女演员的关注远大于《红楼梦》本身的世界;一个被选秀、肥皂剧、粉丝萦绕的“娱乐至死”的世界。在一些人看来,无论这一切是多么琐碎无聊,有选择的权利就意味着自由。敏锐的阿多诺在世纪初就愤怒地批判了这种“虚假的自由”,但之后如火如荼的文化研究却把阿多诺贴上“精英主义”的标签打发回了德国老家。再回首,正如伊格尔顿所调侃的,如今大学生都扎堆在图书馆里“勤奋地研究着像吸血鬼迷信、挖眼睛、电子人,淫秽电影这样耸人听闻的题目。”(《理论之后》,P4)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切都拜当年名震一时的伯明翰学派所赐,而挥舞着“文化”的板斧砍向文学、艺术等高雅文化的始作俑者就是雷蒙德·威廉斯。继《文化与社会》之后,他的名著《漫长的革命》为霍尔、赛义德等人带来了缪斯女神的璀璨微笑。最近细读此书中文版却意识到,如果威廉斯有幸迈入满目苍夷的二十一世纪,他一定会感慨:这不是我想要的!
评分这书市面上很少有京东有货所以赶紧买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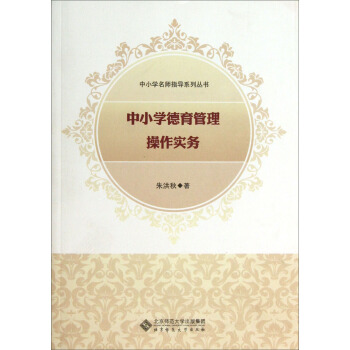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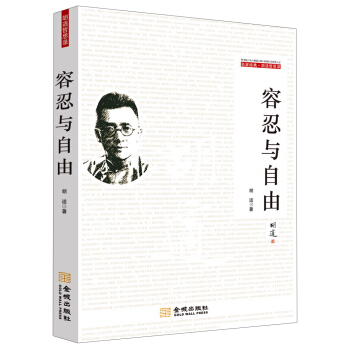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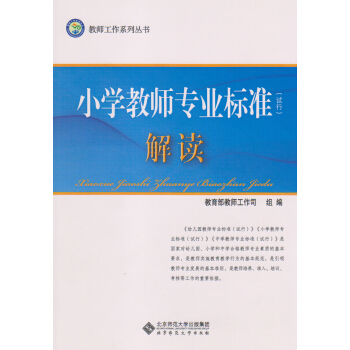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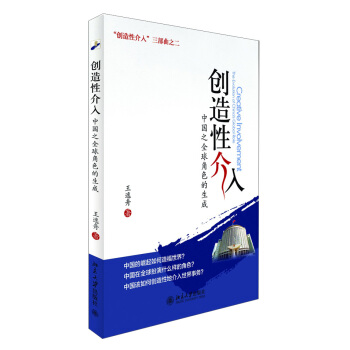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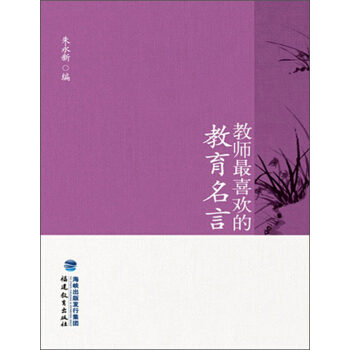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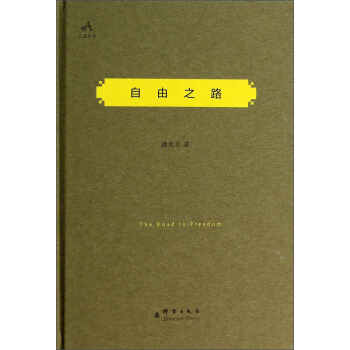
![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4版) [Blue Book of China's Media Report on Development of China's Media industry(2014)]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56106/rBEbR1NqEqgIAAAAAAOokT5g3HkAAAHdwBIs5QAA6ip99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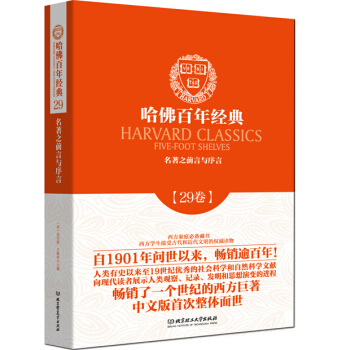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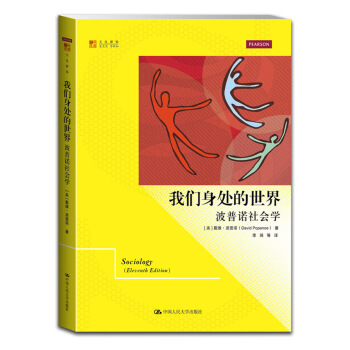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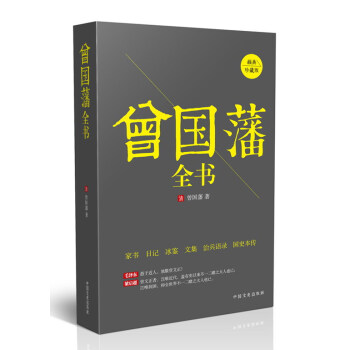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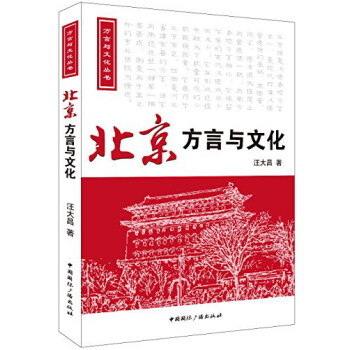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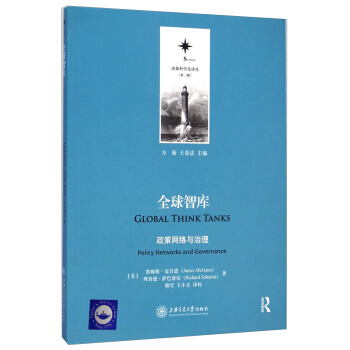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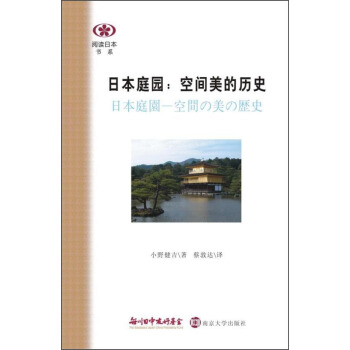
![培生书系·学前教育精品译丛:幼儿园教师技能大全(原书第9版) [Skills for Preschool Teacher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95864/559628d3N6b6f495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