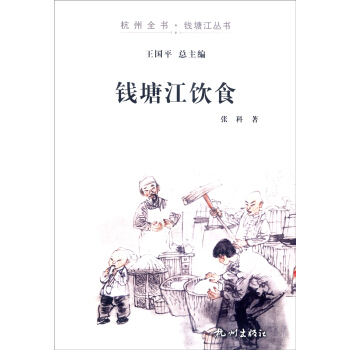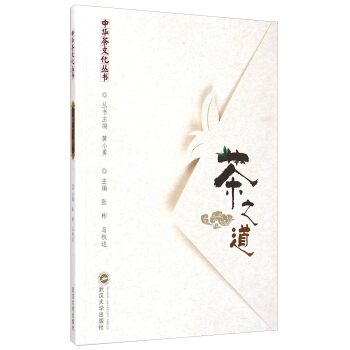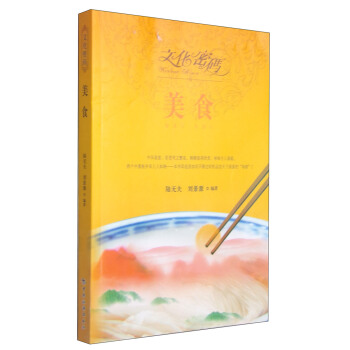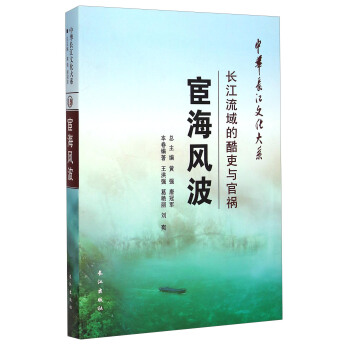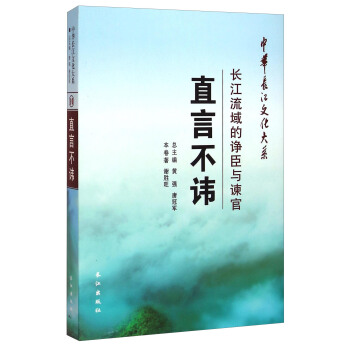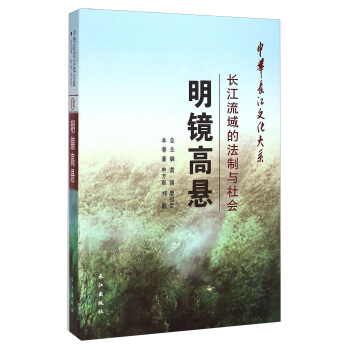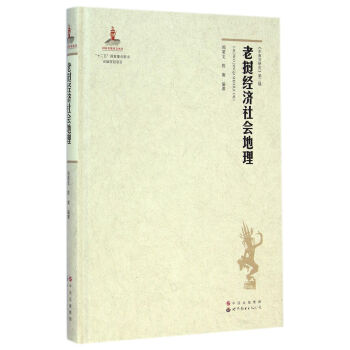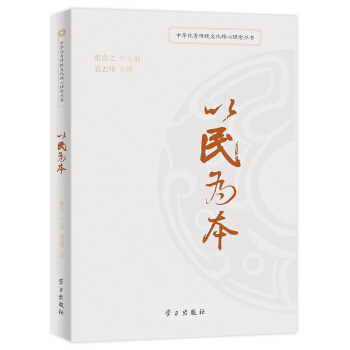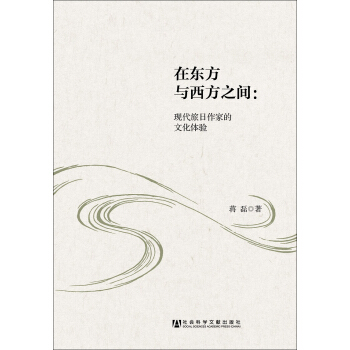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清末民国时期以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为代表的旅日作家,形成了特殊的创作群体。旅日活动不仅让他们接触到现代思想,更获得了异域文化体验。本书试图从异质语言的冲突和转换、旅日作家的风景体验、都市文化观察和日常生活体验等几个崭新的角度回望清末民国时期的“旅日潮”,探察这些文化体验究竟有何特质,解答“日本体验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发生”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探究文学视野下的“旅行文化”是如何呈现的。本书认为,旅日活动中所呈现出的诸多文化现象,体现了中日文化之间、东亚文化与欧美文化之间的多元对话。现代旅日作家的文化体验,可谓跨越了“东方”和“西方”的现代性体验。作者简介
蒋磊,男,1983年生,四川成都人。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就职于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目前从事现当代文艺思潮和文化研究。近年在《文艺研究》《文艺争鸣》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目录
绪 论/001第一章 “对照性发明”: 旅日作家的语言体验/015
第一节 遭遇“日本语”:旅日作家的“笔谈”经验/020
第二节 日语的移植与旅日作家的文化身份/025
第三节 旅日作家的“混杂性”用语/034
第二章 风景的多元取向:旅日作家的风景体验/041
第一节 多重书写:风景描写的语言转向/044
第二节 从“诗意的风景”到“图像的风景”:风景描写的视觉转向/052
第三节 时空的重组:“闲暇的风景”与“轨道的风景”/061
第四节 旅日作家与现代“文化风景”的诞生/072
第五节 樱花与富士山:在东方风情与日本主义之间/080
第三章 “杂交的空间”:旅日作家的都市文化体验/097
第一节 东京新景观:民族情绪的触媒/100
第二节 “东京新感情”:都市里的男男女女/110
第三节 都市的向心力与离心力:旅日作家的“都市梦”与“反都市”/121
第四节 日本都市:作为“杂交文化”和“第三空间”的场所/129
第四章 旅日作家日常生活的现代性经验/145
第一节 日常生活的文明观:旅日作家的“清洁”体验/150
第二节 在“和风”与“洋风”之间:服饰与饮食的现代发明/163
余 论 旅日作家的文化体验与东亚现代性/179
参考文献/189
附 录/206
后 记/212
前言/序言
绪 论一 “东方”与“西方”的起源
近代以来的思想著作和文学作品中,有关“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争论寻常可见,而一些学术研究的学科分类也以此为依据,例如“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东方美学”与“西方美学”等。那些有关文化交流问题的报刊文章和言论,尽管在整体上呈现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似乎又总是可以归结到“‘东方’还是‘西方’?”这一大问题的框架下,表现为对此问题的不同解答。无论是“西化派”(如陈独秀、胡适)、“国粹派”(如杜亚泉、梁漱溟),还是“折中调和派”(如梁启超),都是在“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提出各自观点的。即便是后来出现的一些试图“超越东西方”的文化论,也不得不在反思“东西方文化观”的基础之上来展开论述。因此可以说,“东方”与“西方”,是近现代中国思想界的一大研究主线,是我们论及文化问题之时无法绕开的话题。
但显而易见的是,所谓“东方”或者“西方”,各自都不是铁板一块,“东方”或“西方”内部的文化差异性,其复杂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因此,“东方-西方”这种过于宏大、壁垒分明、粗疏笼统的描述方式,并不能反映多元文化的真实样态。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在后殖民主义所创造的理论语境中来看待这一问题时,为我们所惯用的“东方-西方”话语更招致质疑和反省,因此,为打破“东方-西方”的思维模式,将文化交流问题引向更深的层次,首先需要对“东方”与“西方”进行一番谱系学的考察。
那么,“东方”与“西方”的观念,是自来就有的吗?这对概念究竟源起于何时,又因何成为近代国人世界观的基本构架呢?它在20世纪思想讨论中的广泛使用,反映了什么样的政治含义?它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各种表述方式,体现了怎样的历史嬗变过程?
由于“东方”与“西方”概念的产生和流变总是涉及跨越了国界、洲际的异域经验,因而对于以上种种问题的解答,就可以从多重的视角出发,如中国本土的视角、西方的视角、日本的视角等。本书针对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互动的历史,将采用“东亚”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问题。
鸦片战争以前,“中华帝国居于世界之‘中心’的位置”,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自我想象和定位。尽管“中国”的国家意识未必出现得很早,而普遍自称“中国人”,也是较为晚近的事情,但自视为文明之正统、天下万国之核心的意识,无论在汉民族掌权的汉唐、宋明时期,还是元朝、清朝等少数民族统治时代,都清晰可见,这一点,从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古地图中即可看出。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中国历史上,但凡统治力量难以触及之地,一概视之为蛮夷僻壤,理应向天朝称臣纳贡。因此,只有“中”的自我感受才是中国人世界观的主流意识,所谓“东方”“亚洲”“东亚”的概念,在彼时的中国人那里是极为淡漠的,而“西方”的观念也不如“外夷”之感更为强烈。
这种地理和政治双重层面上的自我意识,基于自古以来逐渐确立的“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不过,这种“华夷秩序”并不总是为周边国家和地区所认同,它常表现为中华帝国一厢情愿的政治要求,而“朝贡体系”也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在近古时期的东亚地区,这种以中华帝国为文明中心的格局出现了瓦解的迹象。明亡以后,朝鲜出现了蔑视清朝政府、自视为中华文化正统的思想,而日本江户时代的“古学”和“国学”家们,更提出“华夷变态”之说,认为清代的中华帝国已经逐步走向衰败,由“华”沦为“夷”,而日本则应该成为真正的“华”,甚至世界的中心。
随着前近代及近代以来欧美列强对亚洲各国的入侵,“华夷秩序”彻底被打破,日本幕末思想中的“华夷变态”观真实地发生了,从此以后,“东方”“亚洲”“亚细亚”“东亚”“亚东”“东洋”之类的概念开始逐步取代天朝中心观。在成书于1840年代的《海国图志》中,虽然言明作书的目的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仍然将异域诸邦皆称为“夷”,但又以“夷图、夷语”作为著书凭据之一。在实际书写中,魏源摒弃了“天圆地方”的旧说,强化了“宇宙之大、南北极上下之浑圆”的天文地理观,并描述了四海万国并存的状态,从而不自觉地消解了天朝中心论。在《海国图志·阿细亚洲》的描述中,中国的位置被明确地放在了亚细亚的东南方。到了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在《马关条约》中承认朝鲜“独立”,标志着“华夷秩序”的最终瓦解。而“东方”“亚洲”“东亚”等观念正是作为“华夷秩序”崩溃以后的替代品出现的,相应的,“西方”也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重视,成为近代以来挥之不去的“他者”的阴影。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提出下列疑问。
第一,自近代以来,尤其是清末民初时期,分别有哪些历史因素参与了中国人东西方观念的创造?日本的崛起,在这一文化变局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而自古承袭而来的天朝中心观,又是如何向“东方”观转变的?
“东方”和“西方”,不仅仅是地理学上的一种命名,还是各种政治、经济、历史和社会文化观念所生产出来的一种“知识”。作为知识生产物的“东方”,凝合了西方殖民者对亚洲的观察视角、日本国家主义的政治野心、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变形,它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政治意味的空间,反映了以欧洲、日本和中国为主的多重历史视角。而相应的,“西方”则暗示了“东方”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西方”是对“东方”的拯救者、奴役者、文化闯入者、资源征用者,总而言之,是“东方”的对应之物。于是在近现代史著作中,便出现了这样的叙述模式:近代“东方”逐步衰弱之时,似乎正是“西方”勃兴、扩张的大好年代;而当“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趋于没落之时,仿佛恰好带来了“东方”的复兴之机。
欧洲思想对于“东西方”文化观的产生,起到了最为直接的作用。可以说,正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强势兴起,才产生了“东方”的观念。不过,如果完全将“东方”纳入西方思想的体系中,认为“东方”乃“西方”的生产物,则过于简单化。实际上,“东方”不仅是与“西方”相伴而生的一个“西方的观念”,同时还是近代亚洲国家的自我生产物,是近代中华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相交碰的产物,它的实际发生过程,远比欧洲对亚洲的所谓“冲击-反应”模式来得复杂。
而在这之中,近代日本可谓横亘在欧洲和亚洲之间、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一块难以消化的骨头,始终无法被纳入“东方-西方”的叙述框架中。日本是“东亚”观或“东方”观的大力鼓吹者,近代日本的“脱亚论”或“兴亚论”,都是在对欧洲与亚洲、西方与东方的比对中产生的。随着日本军事的扩张、野心的膨胀,日本思想者所鼓吹的“大东合邦论”(樽井藤吉,1893)、“亚洲一体论”(冈仓天心,1902)等,又逐渐被赋予了“日本主义”的含义,日本通过“东方”观和“东亚”观的构建试图将自己塑造为亚洲的盟主,这其中潜藏着幕末以来的“华夷变态”思想;但同时,这种“亚细亚的优等生”意识,又是在对西方的尊崇过程中形成的,带有强烈的西方殖民主义色彩。
对于“东方”与“西方”的建构,除了欧洲的视角、日本的视角以外,自然还有中国的视角。在面对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入侵之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空前高涨,“东方”因含有对“西方”的反抗意识而被强调,也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派生物。因此,近代以来关于“东方”和“西方”的论述包含了多重的意义,成为一个充满着竞争的意义“场域”,在其中,诸多相异甚或对立的“东西方”论展开了角逐,集中表现于20世纪初叶发生在中国思想界的数次东西方文化论战之中。
第二,既然“东方”是一个复杂、多义的地缘政治生产物和文化建构物,那么在晚清到“五四”期间的中国人眼中,“东方”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否已经具有所谓的“东西方观”或东方主义意识?这种东方主义意识有着怎样的特点和知识构成?
当传统的华夷秩序因全球政局的动荡而崩溃以后,中国人并没有一头扑进“世界”的怀抱,简单地将自己定位为“世界”的一员。这是因为,部分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不无警觉地意识到,所谓“世界”有时不过是为西方人所单方面规定的“世界”罢了。因此,直至“西学”大兴的“五四”时期,中国都没法抛弃“国粹”的旧癖,多有抱残守缺、以中华文化为傲者。而正是由于对中华文化的自尊自傲,当中国人在战争和留学、流亡风潮中史无前例地与日本、朝鲜等国大规模接触时,他们无法将深受中国影响的日本与“西方列强”等而视之,更无法忘掉朝鲜的“藩属国”位置。甚至在面对南亚、东南亚诸国时,他们也时常发出文化的共通感,将其视为中华文化的辐射地。
由于儒家文化圈的亲缘性以及“同文同种”的观念,近代中国人终究无法彻底消除与日本、朝鲜的文化连带感和民族亲近感,也由于佛教文化模糊的影响范围,印度文化也常被视为亚洲文明的代表,被纳入“东方”的阵营中来看待。针对这些思潮和观念,自然又产生了以“西化”或“新文化”为旗帜,试图解构“东方”的思想,愈加拉大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距离。
其实,无论是认同“东方”还是拒斥“东方”,无论是“复兴东方”还是“崇尚西方”,都意味着对中、日、朝以及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诸国的关系重组,意味着“华夷秩序”崩溃之后,中国人不断寻求着自身在世界秩序中的重新定位。于是,当近代中国人走出国门,去获取异域经验、想象崭新世界之时,或者当大批的异域来客,怀着各种不同的目的进入中国,与中国人发生文化触碰之时,对于中国人文化身份问题的思考就总是伴随在他们的交流过程之中。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东亚,聚焦于日本,观察近代中国人的日本体验(这种体验包括旅日体验、日本人来华交流和对日想象等多个层面)时,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人的东西方观,是在一种奇异的交流模式中产生的——由于日本是近代学人学习西方的前站,也是现代中国思想的源发地之一,中国人一方面的确是通过与日本这一文化近亲相交碰来想象“东方”、构建东方意识的,但另一方面,恰恰由于明治末期的日本已经是学西的“优等生”,是一个严重西化的地域,中日之间这种不对等的交碰随时随地被掺入了某种西方意识或“世界意识”。中国人试图通过对“东方”的强调来对抗“西方”,但十分诡谲的是,“东方”本身就带有西方思想的色彩,而同处亚洲的日本又是近代中国的殖民者之一,这导致中国人的东方意识从一开始就带有自我否定的意味。
可以看到,日本人是在较为主动的国际境遇中建构其东方观、亚洲观的,其东方主义论调或有西方思想的背景、或源于日本本土,但无论哪种情况,皆出自日本人自身的需要;而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人却是在被动的接受中形成东方意识和亚洲意识的,这种意识或是对日本思想的回应,或出于对传统文化的怀旧,偏偏绝少属于中国学人的原创。
第三,由以上问题还可衍生出另一问题,即当时中国人的东西方观,究竟是通过哪些具体途径被建构起来的?
从东亚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这些途径主要包括战争、留学、流亡、游历、想象和来华事件。
甲午中日战争造就了近代中国与日、朝两国的首次大规模接触,也是中国的日本观、日本的中国观以及朝鲜的中日观发生剧变的转折点,它必然影响了各国东西方观的形成转变,这反映在战争前后的一些文学作品中;而晚清至“五四”时期的几次大规模留日学潮,以及志士文人的流亡及游历、访问,造成了更大规模的文化交碰,许多人正是在这些活动中发现“东方”和“西方”的,这在“留学生文学”、“流亡文学”和“游记文学”中,多有体现。此外,一些身居国内者,也依然可以通过印刷媒介对异域展开想象,或者通过对泰戈尔等人来华事件的观察,来建构其东西方观。
在这之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百年前中国的“旅日潮”。清末至抗战前夕几次大规模的旅日活动,对中国的政治变革、思想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参与了对近代国人文化观念的塑造。日本这一特殊地域中,中国学人获取了中华文化以外的文化体验,这种体验既是新鲜的,又是怀旧的,既是“东洋风”的,又是“欧美化”的,从而建立了复杂而暧昧的东西方文化观。他们通过日本想象,强化了“东方”和“西方”,但同时,近代日本所具有的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文化属性,又使得旅日活动获得了超越“东方-西方”模式的跨域经验,使日本成为“作为方法的日本”。
这样奇特的文化体验,集中反映在现代旅日作家的文学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本书的研究目标,正是试图在清末至抗战前夕丰富的文学作品中,理清东西方意识的踪迹,并分析这种东西方文化观的特质,指出其形成要素。
在这之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日常语言、异域风景、近现代都市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体验与东西方文化观的联系。对于旅日学人来说,日本只是快速有效获取西方知识的中介,因而日本本土思想对旅日学人的意识塑造作用是不大的(但并非没有)。由于当时留日者以学习理、法、商、工、农、医等西洋技艺为主,对日本社会思想的关注相对较少,所以留日学人更多的是被“西化”而非“日化”。因此,相对于化为文字典籍的上层思想来说,日常语言交流、风景观察、都市生活和日常生活细节对留日学人的影响,则显得更为直接而广泛。从这些角度出发,来探讨旅日学人的文化境遇,呈现他们在西方、东方、日本等多元观念冲击中的复杂反应,较之纯粹思想层面的影响研究,更为全面而真实。
二 何谓“旅日”?
思想文化交流史未必都是由跨域经验所构成的。如果立足于本土,通过口传或印刷媒介,也能够对外来思想进行了解和摄取。因此,以“旅行”方式进行的跨域活动,就和一般意义上的思想传播、文化交流活动区分开来,具有其独特的文化交流方式。
旅行(Travel,包括行游、旅游、观光、行旅等),是人类文明史上世代相承的文化现象。荣格甚至将旅行的冲动归结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孔子携弟子周游列国,庄子遨游于山林水泽之间,都是文人旅行活动的早期表现;司马迁遍游名山大川、边疆风土,方能积累起丰富的写作材料;李白、苏轼都曾浪迹天下、飘游四海,故而于诗文中体现出开阔的视野与高尚的人文情怀;明清山水画的兴盛,与朱耷、石涛和扬州八怪的游历密切相关。阿倍仲麻吕遣唐,鉴真和尚东渡,马可·波罗东来,耶律楚材西去,是历史上留学之旅、宗教之旅、商人之旅和战争之旅的典型代表。
对于上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圈之间的旅行活动,根据不同的标准,可有多种划分方式。而对于现代旅日作家的旅行活动来说,将其大致分为留日、游日、流日、访日四类,较为符合史实。
首先是留日者。盖因于1896~1937年间四次留日热潮,留日者在旅日作家中人数最多,较重要的留日作家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田汉、张资平、李叔同、丰子恺、成仿吾、夏衍、欧阳予倩、巴金、滕固、穆木天、不肖生等。他们在政策鼓励和宣传下,以学习为目的,通过公派或私费的方式留学日本。对于这些留学生来说,问学、求知自然是旅日活动的主要目的,但是实际上,“留学”又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校教育或知识阅读过程,留学生长期旅居海外,海外生活必然构成他们的人生经验,参与了他们文化观念的构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留日作家最初大多都不以学习文学为留学目的。即便一些人在兴趣转向文学之后,他们对于日本文学的阅读,以及从当时日本文艺思潮那里所受的影响也都十分有限。这样一来,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他们的日本生活经历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其次为游日者,即以观光游历或调养身心为主要目的的旅日者,代表人物有徐志摩、俞平伯、闻一多、庐隐、萧红、蒋光慈等。对于他们来说,风景游览和日常生活体验更是旅日的主要目的。
再次有流日者,即因历次革命运动、政治打压等各种原因流亡日本者,也不在少数,知名者有梁启超、郭沫若、茅盾等。
最后还有访日者,即因公委派或学术出访者,有章太炎、曹禺等,数量较少,但仍是旅日作家群体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尽管旅日作家赴日的目的不尽相同,但在这一作家群体的个人经历中,在他们涉及日本体验的文字描述中,普遍存在着一些相似的文化现象:旅日作家的文学创作多有对日语的创造性运用,而一些特殊的日语词汇也引发了中日之间的冲突;日本的风景在进入旅日作家的视野,并被写入旅日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总是在一些有着现代特征的独特视角中被“发现”的;旅日作家对日本都市生活的各种反应,体现出“杂交文化”场所中都市人的精神结构裂变;旅日作家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清洁卫生、穿着打扮和饮食习惯等问题,引发了他们对于日本文化矛盾而暧昧的情绪;而当旅日作家即将离别日本之时,或久别岛国生活之后,又常生发出对这段经历的怀念之情。
因此,以“语言”、“风景”、“都市”和“日常生活”为关键词,本书将着重从四个方面来展开论述,将关注点集中在既有的文学史叙述所忽略掉的一些历史细节上,以期从旅日作家日常性的文化感知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问题,揭示以旅日作家为代表的近现代中国人,在跨域交流中所面临的种种文化前途的选项,以及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不同愿景。
身处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旅日作家,他们的所思所感,他们的文学书写,反映出怎样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呢?一方面,与明清文人和文学相比,某种前所未见的、可称之为“现代性”的经验已经在清末民国时期的旅日作家群体中发生,并广泛反映在旅日文学的书写之中;但另一方面,这种介乎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体验又和欧洲思想背景中的“现代性”具有颇多相异之处,其特质远非“现代性”一词所能涵盖。
更为复杂的是,由于这种独异的现代性体验产生自欧美文化、中华文化和日本文化相互缠绕的“混杂”场所之中,故其产生、嬗变的过程始终具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多重线索。例如,一方面,近现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中,始终掺入了欧洲人的视角,即以欧洲文化中“文明与野蛮”的判断标准来看待日本。但另一方面,在某种特殊的文化情境中,这种“欧洲的标准”似乎又可以被搁置一边,取而代之以传统中华文化的视角。反过来讲,近现代旅日中国人的西方观同样复杂多变:有时他们对西方文化推崇备至,理由之一便是“西方文化推动了日本的崛起”,有时他们又对欧美文明表示不屑、鄙夷乃至憎恨不已,其原因则变成了“西方文化使日本一步步堕落,与中华文化渐行渐远”。而当一些旅日中国人在日本的游历途中,因意外发现了“古代中国”的文化遗产而惊喜不已的时候,他们称赞日本、鄙薄西方的思维逻辑又变成了“日本继承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西方文化终究无法征服东方人的心灵”。
由此可见,近现代中国人对于欧美文化、日本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认识常呈现矛盾而多变的特点,各地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常被置于“悬搁”的位置来加以讨论,因不同文化情境的需要而产生不同的判断。本书旨在从现代旅日作家的文化体验中,解读这种多重视角相交织,并不断建构自身的文化观念,从而勾勒出所谓“东亚现代性”的雏形。
用户评价
《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现代旅日作家的文化体验》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一场关于“看见”与“被看见”的深刻旅程。我一直以为,自己对日本的了解,已经足够多了,通过影视、文学作品,甚至是短暂的旅行。但这本书,让我明白,那仅仅是冰山一角。书中那些旅日作家们,他们以一种近乎雕琢般的细腻,捕捉到了那些最隐秘的文化肌理。我特别被其中关于“无言”的描写所打动。日本文化中,很多情感和沟通,并不需要直接的语言表达,而是通过眼神、肢体语言,甚至是沉默来传递。这种“无言”的艺术,在我们习惯了直抒胸臆的文化里,显得尤为珍贵和难以捉摸。书中一位作家,她描述了自己在一次与日本朋友的交流中,因为不理解对方的“暗示”,而导致了一场小小的误会,但正是这场误会,让她开始真正去体味,日本文化中那些微妙的情感界限。这让我想到,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懂”了,但实际上,只是停留在最表层的理解。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鼓励我们去“放下”自己已有的认知,去重新“学习”如何去“感受”和“解读”。它让我意识到,文化是一种活生生的体验,而不是一套僵化的规则。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好像拥有了一双新的眼睛,能够看到那些曾经被我忽略的细节,能够听见那些曾经被我忽略的声音。
评分这本书带来的震撼,是那种细水长流却又直击心灵的力量。我一直以为,所谓的“文化融合”或者“跨文化交流”,都应当是某种程度上的趋同,是两个不同文化体在碰撞中相互学习、相互靠拢的过程。但《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现代旅日作家的文化体验》所展现的,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和 nuanced。它探讨的并非简单地“学习”对方的习俗,而是那种更加内化的、甚至有些颠覆性的过程。我看到书中一些作家,他们最初可能带着猎奇的眼光,试图去理解日本的茶道、花道,或者那些看似繁复的礼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观察变得越来越深入,逐渐触及到这些文化现象背后所承载的深层哲学和价值观。比如,那种对于“留白”的艺术追求,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体现,但日本文化中的“留白”似乎带有一种独特的寂静与内省的意味。书中对这种“留白”的解读,让我开始反思我们自己文化中“填满”的习惯,以及这种习惯背后可能隐藏的焦虑。更让我着迷的是,作者们并非完全被日本文化所同化,他们依然保留着自己原有的文化印记,并且在新的文化体验中,这些印记被重新审视,甚至焕发出新的光彩。这种“在…之间”的状态,既不是完全属于东方,也不是完全属于西方,而是一种全新的、属于作者自身存在的空间。这让我想到,真正的文化体验,或许不是去“成为”另一个文化的人,而是去“理解”另一个文化,然后在这种理解中,重新认识和定义自己。这本书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让我们看到这种“跨越”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对个体精神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
评分这本书,我必须承认,它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阅读的愉悦,更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审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能够接纳不同文化的人,但《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现代旅日作家的文化体验》这本书,让我看到了,真正的跨文化体验,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和深刻。书中那些旅日作家们,他们不仅仅是记录者,更是探索者,他们试图去理解日本文化中那些最难以捉摸的部分,比如“寂静”的价值,比如“和”的意义,比如“侘寂”的美学。这些概念,在我自己的文化背景中,可能并没有直接对应的词汇,因此,理解起来也格外有挑战。我被书中关于“侘寂”的描绘深深吸引,这种对不完美、不完整、稍纵即逝之美的欣赏,与我们追求完美、永恒的文化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书中一位作家,她如何从一件破碎的陶器中,看到了人生的哲理,这种对“残缺”的接纳和升华,让我对“美”有了全新的定义。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展示异域风情,更是引导读者去思考,我们自己的文化,是如何塑造了我们的认知,以及我们是否能够跳出固有的框架,去拥抱更广阔的世界。
评分这本书,我不能简单地用“喜欢”或者“不喜欢”来概括,它带来的冲击和思考,远远超出了简单的个人喜好范畴。我在阅读过程中,时常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仿佛那些一直以来困扰我的,关于跨文化交流的困惑,在这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答。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就是“身份的重塑”。我看到,当一个来自西方(或者说非东方)的作家,长时间生活在日本,他的身份认同会经历一个怎样的流动和变化。他可能不再是那个纯粹的“西方人”,但也无法完全成为一个“日本人”。他所处的,是一种“中间地带”,一种“暧昧”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充满挑战和不安的,但书中的作家们,却从中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和创造力。我尤其欣赏书中对“和”的解读,这种对和谐、对融洽的极致追求,体现在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它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礼貌,更是一种深层次的、对于社会关系的考量。当我们习惯了西方文化中那种直接、坦诚的沟通方式,去面对日本文化中那种委婉、含蓄的表达时,所产生的碰撞是巨大的。书中对这种碰撞的描绘,既写实又充满哲思,让我开始反思,我们自己的沟通模式,是否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记录,更是引导读者去思考。它让我明白,文化体验并非一场单向的“学习”过程,而是一个双向的“对话”和“转化”的过程。
评分这本书,我只能说,它是一本“颠覆”之书。它颠覆了我过去对“文化”的认知,颠覆了我对“旅居”的理解,甚至颠覆了我对自己文化身份的看法。我曾以为,去体验异国文化,无非是学习一些新的词汇,尝试一些新的食物,或者参加一些当地的节日。但《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现代旅日作家的文化体验》这本书,向我展示了,真正的文化体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书中那些旅日作家们,他们不仅仅是观察者,更是参与者,是感受者。他们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灵,去丈量日本文化的深度。我特别被书中关于“礼貌”的探讨所打动。日本的礼貌,是一种近乎极致的追求,它不仅仅是表面的客套,更是一种对他人的尊重,对“不给他人添麻烦”的重视。这种“礼貌”,在我们的文化中,可能被视为一种必要的社交技巧,但在日本,它似乎已经融入了民族的血液。书中的作家们,他们如何在这个“礼貌”的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理解这种“礼貌”背后的深层含义,这让我思考良多。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打破了“东方”与“西方”的简单二元对立,而是在两者之间,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一个属于个体体验和深刻反思的空间。
评分《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现代旅日作家的文化体验》这本书,是一场关于“看见”与“被看见”的深刻旅程。我一直以为,自己对日本的了解,已经足够多了,通过影视、文学作品,甚至是短暂的旅行。但这本书,让我明白,那仅仅是冰山一角。书中那些旅日作家们,他们以一种近乎雕琢般的细腻,捕捉到了那些最隐秘的文化肌理。我特别被其中关于“无言”的描写所打动。日本文化中,很多情感和沟通,并不需要直接的语言表达,而是通过眼神、肢体语言,甚至是沉默来传递。这种“无言”的艺术,在我们习惯了直抒胸臆的文化里,显得尤为珍贵和难以捉摸。书中一位作家,她描述了自己在一次与日本朋友的交流中,因为不理解对方的“暗示”,而导致了一场小小的误会,但正是这场误会,让她开始真正去体味,日本文化中那些微妙的情感界限。这让我想到,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懂”了,但实际上,只是停留在最表层的理解。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鼓励我们去“放下”自己已有的认知,去重新“学习”如何去“感受”和“解读”。它让我意识到,文化是一种活生生的体验,而不是一套僵化的规则。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好像拥有了一双新的眼睛,能够看到那些曾经被我忽略的细节,能够听见那些曾经被我忽略的声音。
评分我必须说,《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现代旅日作家的文化体验》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对“文化”这个词的固有认知。我一直以来,对于文化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表象层面,比如饮食、服饰、节日等等。我认为,了解一个文化,就是去学习它的这些外在表现形式。但这本书,尤其是书中那些旅日作家们,他们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向我展示了文化的核心,是深埋在人们的思维方式、情感模式,甚至是潜意识里的东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有一位作家,她花了大量的篇幅去描述她在日本生活中,如何不断地感受到“空气感”的差异。起初我并不理解,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这种“空气感”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日本社会对于“察言观色”、“不给别人添麻烦”的重视,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似乎总是笼罩着一种微妙的、需要用心去体会的“气场”。这种“气场”在我的母国文化中,可能并不那么明显,甚至有时会被视为一种疏离。但通过这位作家的细腻描绘,我开始理解,这种“空气感”背后,是对个体尊重和集体和谐的一种追求。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对其他文化的误解,就源于我们用自己固有的文化滤镜去解读,而忽略了对方文化内在的逻辑和价值观。书中这些作家,他们敢于放下自己的预设,去倾听、去感受、去思考,最终才能够触及到文化最真实的内核。这种勇于自我挑战的精神,让我非常钦佩,也让我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审视自己是如何被自己的文化所塑造的。
评分《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现代旅日作家的文化体验》这本书,在我翻开第一页的那一刻,就如同打开了一扇通往平行世界的大门。不是那种科幻小说里光怪陆离的设定,而是关于现实世界中,当一个拥有截然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深入踏足另一个文化土壤时,内心所经历的微妙而深刻的转变。我一直对“文化冲击”这个词有着模糊的认识,以为它仅仅是语言不通、风俗习惯差异带来的表象困扰。然而,读完这本书,我才明白,文化体验的深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它不仅仅是关于“看”和“听”,更是关于“感受”和“内化”。书中那些旅日作家们,他们的文字并非简单地记录下日本街景的斑斓,或是传统艺能的精致,而是通过他们独特的视角,捕捉到了那些隐藏在日常表象之下的文化肌理。我尤其被书中关于“物哀”的探讨所打动,这是一种我从未在我的母国文化中找到对应词汇的情感,它是一种对生命短暂、事物易逝的敏感而又温柔的感怀。作者们如何用他们的笔触,将这种难以言喻的情绪,在字里行间缓缓铺展开来,让我沉浸其中,仿佛也经历了一场关于时间与存在的哲学沉思。这本书并非枯燥的学术论文,而是充满了个人化的观察与情感共鸣。读着读着,我仿佛置身于京都的古巷,感受着微风拂过樱花的轻柔;又仿佛置身于东京的繁华街头,体味着现代都市的快节奏与疏离感。这种多维度的文化呈现,让我在阅读的同时,也在不断审视自己的文化身份,反思那些被我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观。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打破了“他者”与“自我”的界限,让我在阅读他人的文化体验时,也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我”是谁,以及“我”是如何被塑造的。
评分《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现代旅日作家的文化体验》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是一种智识上的启迪,更是一种情感上的洗礼。我曾以为,所谓的“文化差异”,无非是语言、习俗的不同,但这本书,让我明白,真正的文化差异,是思维模式、价值观、甚至是对生命本质的理解上的差异。我尤其被书中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比所吸引。在我的母国文化中,集体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我们习惯于强调“我们”,而很少去强调“我”。但在日本文化中,这种“集体”的边界,似乎更加微妙和复杂。书中的作家们,他们是如何在理解和适应这种“集体”的同时,又不失自己独立的个体意识,这让我非常好奇。他们的笔触,既有对日本社会“规则感”和“秩序感”的细腻描绘,也有对个体在其中挣扎、寻找自我空间的深刻反思。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体验,让我对“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它既是约束,也是支撑;既是限制,也是可能。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停留在现象的描述,而是深入到文化的根源,去探究那些看不见的、却又影响深远的内在逻辑。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文化”这个词,有了全新的认识,它不再是一个标签,而是一个动态的、充满生命力的存在。
评分这本书,我只能用“惊艳”来形容。它以一种极其个人化、却又普遍适用的方式,探讨了文化体验的深度与广度。我一直认为,文化是深植于土壤中的,是民族性格的体现。但《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现代旅日作家的文化体验》这本书,让我看到了文化是如何通过个体的“旅居”和“体验”,被重新解读、甚至被“重塑”的。书中很多段落,都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仿佛我就是那个身处异乡,努力理解和适应的旅人。我被书中对于“季节感”的描绘所深深吸引,日本的四季分明,不仅仅是气候的变化,更是渗透在人们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乃至精神状态中的一种深沉感受。这种“季节感”,在我们一些文化中,可能被简化为气候的冷暖,但在这里,它变成了一种哲学,一种对生命循环的体悟。我看到,作家们是如何将这种季节感,融入到他们对日本社会、对人情世故的观察中。他们的文字,不是冰冷的分析,而是充满情感的流淌,让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文化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这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让我们看到,当东方与西方两种文化在个体身上发生碰撞和融合时,会产生怎样的火花。这种火花,既有冲突,也有和谐,更有最终的升华。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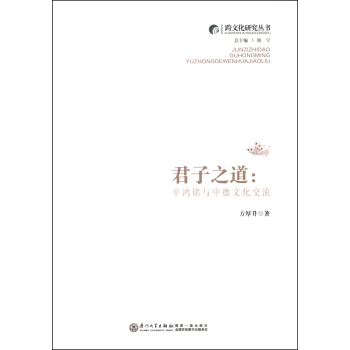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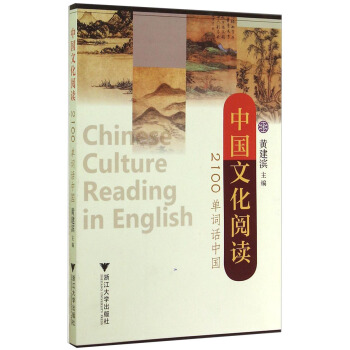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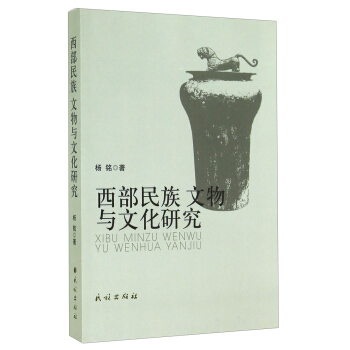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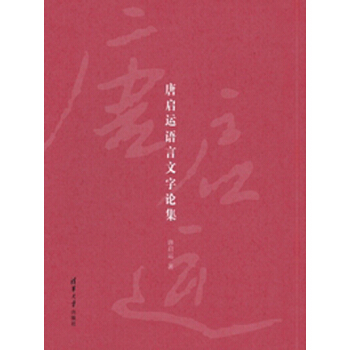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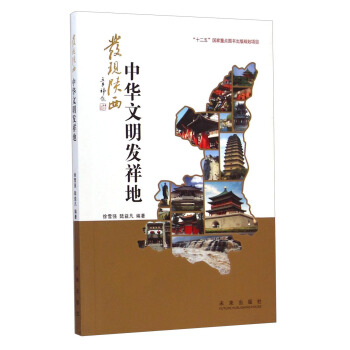
![中国红:梅兰竹菊 [Plum Blossom,Orchid,Bamboo and Chrysanthemum]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25964/55189feeN5469b91f.jpg)
![中国红:民间玩具 [Folk Toy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25971/55189fefN1e7e9c92.jpg)
![中国红:中国名湖(名胜古迹篇) [Famous Lakes in Chin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26094/55189ff6Nb0315a60.jpg)
![中国红:中国姓氏 [Chinese Surnam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26314/55189ffcNc57a7e6e.jpg)
![当代思想前沿系列·凤凰文库:文化模式批判 [Culture Modes Criticism]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27748/551bcce7N4097680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