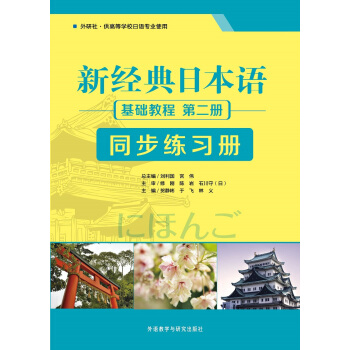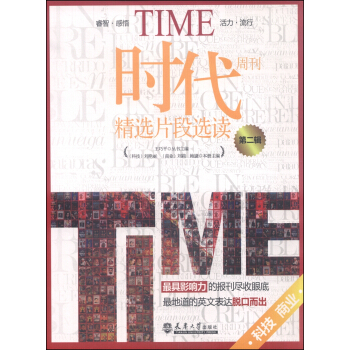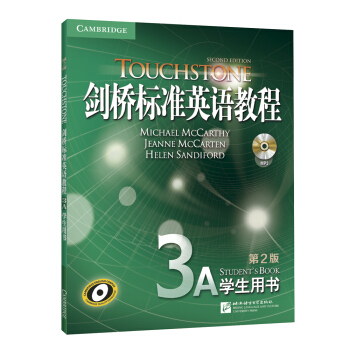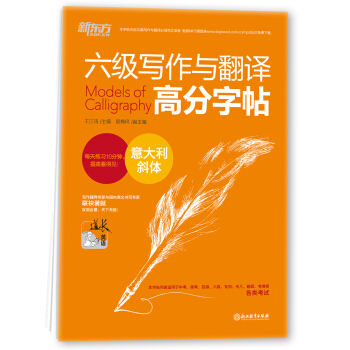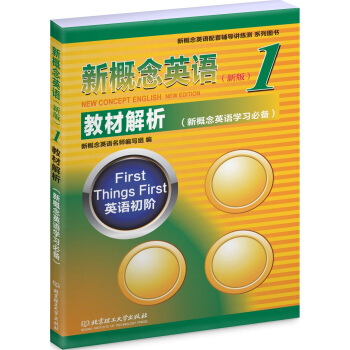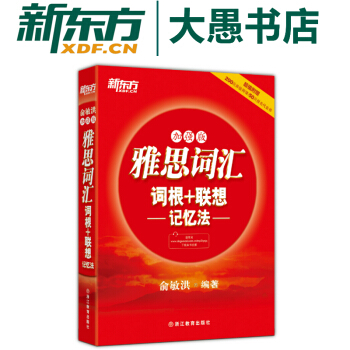![济慈诗选(精装版)(英诗经典名家名译) [Selected Poems of John Keats]](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66534/582d4de2N52e2ee6c.jpg)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学生,一般读者英诗经典精装升级,知名译者冰心、江枫、屠岸、杨德豫经典译本,“诗人外交家”李肇星倾情作序推荐,双语对照排版精美。带你感受诗歌韵律之美。
“美的,就应该是有力量的。”——济慈
在英国浪漫主义辉煌的“七姊妹星团”(彭斯、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雪莱、布莱克、济慈)中,济慈出生晚,生命短。但他的光越来越强,到今天,已超过了其他六颗星。他的诗作充满辽阔高远的想象、自然瑰丽的语言和摄人心魄的力量,不断唤起人们内在的激情和渴望。
拜伦于19 世纪在意大利名声很大,特别是在意大利爱国者中间成功地享有声誉;雪莱在意大利的声誉稍逊于拜伦。济慈当年在意大利没有得到爱国者的称赞,也没有得到诗人们的尊敬,但是今天济慈已被认为是上述三位诗人中之的伟大者。欧金尼奥?蒙塔莱(Eugenio Montale,1896—1981)把济慈列入“至高无上的诗人”之中。(蒙塔莱是意大利20 世纪的伟大诗人,1975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意大利罗马“济慈、雪莱纪念馆”(济慈临终故居)
内容简介
《济慈诗选(精装版)》精选济慈负盛名的6首颂、48首十四行诗、11首抒情诗和1首叙事诗,译文选用了国内获好评的屠岸译本。译者屠岸先生是著名诗人、翻译家。2001年,他因《济慈诗选》译本2001年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彩虹奖;2010年,获全国翻译行业高荣誉奖——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济慈是屠岸喜爱的诗人,他曾评论济慈:“如果天以借年,他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是难以逆料的。但是人们公认,当他二十四岁停笔时,他对诗坛的贡献已大大超过了同一年龄的乔叟、莎士比亚和弥尔顿。”
作者简介
济慈(1795—1821),英国诗人,浪漫主义诗派的杰出代表,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在英国的大诗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比济慈的出身更为卑微。”他英年早逝,在短短7年的诗歌创作生涯中(济慈在18岁之前没有写过诗),济慈创造了那么多充满想象力、气势磅礴、直指人心的作品,足以使他进入世界上“伟大的人的行列”。
精彩书评
一百多年来,济慈的声誉与日俱增,如今且远在浪漫派诸人之上。——余光中
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是浪漫主义的创始者;拜伦使浪漫主义影响遍及全世界;雪莱透过浪漫主义前瞻大同世界。但他们在吸收前人精华和影响后人诗艺上,作用都不及济慈。——王佐良
如果天以借年,他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是难以预料的。但是人们公认,当他二十四岁停笔时,他对诗坛的贡献已大大超过了同一年龄的乔叟、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屠岸
目录
(一)颂
怠惰颂
赛吉颂
夜莺颂
希腊古瓮颂
忧郁颂
秋颂
(二)十四行诗
咏和平
致查特顿
致拜伦
写于李·亨特先生出狱之日
“ 哦,孤独!如果我和你必须同住”
“多少诗人把光阴镀成了黄金”
给一位赠我以玫瑰的朋友
接受李·亨特递过来的桂冠
致姑娘们——她们见我戴上了桂冠
“对于一个长困在城里的人”
给我的弟弟乔治
初读恰普曼译荷马史诗
“刺骨的寒风阵阵,在林中回旋”
一清早送别友人们
给我的两个弟弟
致海登(一)
致海登(二)
厌于世人的迷信而作
蝈蝈和蟋蟀
致柯斯丘什科
给G. A. W.
“啊!我真爱——在一个美丽的夏夜”
“ 漫长的严冬过去了,愁云惨雾”
写在乔叟的故事《花与叶》的末页上
初见额尔金石雕有感
献诗——呈李·亨特先生
咏大海
咏勒安得画像
“英国多快乐!我感到由衷满意”
坐下来重读《里亚王》有感
“ 我恐惧,我可能就要停止呼吸”
给——
致斯宾塞
人的季节
访彭斯墓
写于彭斯诞生的村舍
致艾尔萨巨岩
写于本·尼维斯山巅
致荷马
“为什么今夜我发笑?没声音回答”
咏梦——读但丁所写保罗和弗兰切斯卡故事后
致睡眠
咏名声(一)
咏名声(二)
“如果英诗必须受韵式制约”
致芳妮
“ 白天消逝了,甜蜜的一切已失去!”
“亮星!但愿我像你一样坚持”
(三)抒情诗·歌谣·其他
死
睡与诗
致爱玛
咏美人鱼酒店
仙子的歌
雏菊的歌
“你到哪儿去,德文郡姑娘?”
罗宾汉——给一位朋友
诗人颂
幻想
冷酷的妖女
(四)叙事诗
圣亚尼节前夕
精彩书摘
Written in Disgust of Vulgar Superstition
The church bells toll a melancholy round,
Calling the people to some other prayers,
Some other gloominess, more dreadful cares,
More hearkening to the sermon’s horrid sound.
Surely the mind of man is closely bound
In some black spell, seeing that each one tears
Himself from fireside joys and Lydian airs,
And converse high of those with glory crowned.
Still, still they toll, and I should feel a damp,
A chill as from a tomb, did I not know
That they are dying like an outburnt lamp;
That ’tis their sighing, wailing ere they go
Into oblivion; that fresh flowers will grow,
And many glories of immortal stamp.
24th Dec. 1816
厌于世人的迷信而作
教堂的钟声阵阵,阴郁地敲响,
召唤人们沉湎于另一种祈祷,
另一种幽冥,更加悲惨的烦恼,
专注于倾听布道者可怖的宣讲。
无疑,人的头脑已经被捆上
恶毒的符咒;只见他们都抛掉
炉边的欢悦,舍弃温雅的歌调,
跟心地高尚的人们断绝来往。
钟声不停地敲响,我感到阴凉——
那是坟里的寒气;我岂不明白
那些人如残灯将灭,正挨近死亡;
他们一声声叹息着,哀唤着,走向
永远的沉沦;——而世上鲜花会盛开,
壮丽不朽的事物会接踵而来。
‘Bright star! Would I were steadfast as thou art’
Bright star! Would I were steadfast as thou art—
Not in lone splendour hung aloft the night
And watching, with eternal lids apart,
Like nature’s patient, sleepless eremite,
The moving waters at their priestlike task
Of pure ablution round earth’s human shores,
Or gazing on the new soft-fallen mask
Of snow upon the mountains and the moors;
No—yet still steadfast, still unchangeable,
Pillowed upon my fair love’s ripening breast,
To feel for ever its soft fall and swell,
Awake for ever in a sweet unrest,
Still, still to hear her tender-taken breath,
And so live ever—or else swoon to death.
1819
“亮星!但愿我像你一样坚持”①
亮星!但愿我像你一样坚持——
不是在夜空高挂着孤独的美光,
像那大自然的坚忍不眠的隐士,
睁开着一双眼睑永远在守望
动荡的海水如教士那样工作,
绕地球人类的涯岸作涤净的洗礼,
或者凝视着白雪初次降落,
面具般轻轻戴上高山和大地——
不是这样,——但依然坚持不变:
枕在我爱人的正在成熟的胸脯上②
以便感到它柔和的起伏,永远,
永远清醒地感到那甜蜜的动荡:
永远倾听她温柔地呼吸不止,
就这样永远活下去——或昏醉而死。
前言/序言
意切情深信达雅
——序《英诗经典名家名译》
上小学前,爷爷就教导我要爱劳动,爱念诗。“劳动”是让我拾粪、浇菜、割驴草……“诗”是学念他一生中读过的唯一“诗集”《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等。我还算听话,常下地帮着干零活,偶尔也念诗。上中学后喜出望外地得知,最早的诗歌便是俺乡下人干重活时有意无意发出的“哎哟、哎哟”之类的号子声。老师说,这是鲁迅先生发现的。后来糊里糊涂考进北大,便懵懵懂懂向冯至、李赋宁、闻家驷等老师学习一些欧洲国家的诗歌。
大约十二天前,我正准备出访东欧和中亚时,北大、北外、党校三重校友兼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指示我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即将付印的《英诗经典名家名译》写篇序言。基于上述背景,我竟不自量力,欣欣然应允,飞机起飞不久就边拜读边写体会了。
一看目录,我在万米高空立即激动不已。译者全是令我肃然起敬又感到亲切的名字。
冰心是我初中时代的“作家奶奶”,我工作后曾专门找借口去拜访她在福建的故居。袁可嘉半个世纪前应邀从南大到北大讲英国文学史,我是自己搬着凳子硬挤进去旁听的幸运学生之一。王佐良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教授英国诗歌的。同学们爱听他的课,他大段引用原文从不看讲稿,我们常觉得他的汉语译文会比原文更精彩……穆旦、屠岸、江枫、杨德豫等我未曾有幸当面请教,从他们的作品中却受益良多,感激恨晚。
前辈翻译家们追求“信、达、雅”。落实这“三字经”却并非易事。
第一,在丰富多彩、良莠不齐的英文诗林中,译者要有足够高的先进理念和真知灼见去发现和选择思想水平高的作品。国产千里马尚需伯乐去认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诗就更需要了。看诗的高下、文野,境界和情感永远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国《诗经》历久不衰,首先因为里面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样政治上合民心的诗句,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样传递真情的佳句。这套诗集选了许多跨世纪思想性极强的好诗。如雪莱《普罗米修斯的解放》中的警句:“国王、教士与政客们摧毁了人类之花,当它还只是柔嫩的蓓蕾……”今天读起来仍发人深省。如莎士比亚在其第107 号十四行诗中将和平与橄榄树的葱郁有机相连,上承两千多年前中国先哲“和为贵”的真谛,下接联合国大会此时此刻的紧急议题。这样的诗自然有人爱,有人信。
第二,诗源于生活。诗作者和译者都最好与百姓血肉相连。马克思曾与诗友调侃:诗人也得吃饭,别奢望写诗写饿了上帝会把盛着面包的篮子从天堂递下来。这套诗选中有许多生活气息浓醇、情意真切的诗。如出身佃农的彭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后写的政治讽刺诗:“我赞美主的威力无边!主将千万人丢在黑暗的深渊……”,“……阔人们日子过得真舒泰,穷人们活得比鬼还要坏!”,“……有的书从头到尾都是谎言,有的大谎还没有见于笔端。”写实和预言都相当准确。
第三,译文要忠实于原作,自身又要通畅、简洁、优美。这套诗集中,英文原作都是名符其实的经典。读诗最好读原文,但世界上大约有三千种语言,一个人会用来读诗的语言肯定少得可怜。为开阔视野、加强交流、增进友谊,读外国诗大多还得靠翻译。这套诗选中的译者都治学严谨,都酷爱祖国和外国优秀文化,译文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杰出成果。他们把拜伦的奔放、纪伯伦的靓丽、济慈的端庄、布莱克的纯真、华兹华斯的素净、叶芝的淡定、狄金森和弗罗斯特的质朴译得惟妙惟肖。读这样的译作,哲学上可受启迪,美学上可得滋润。这有益于读者的身心健康,能满足青年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能为有关专家的进一步研讨提供方便。
不妨说,这套诗集中外皆宜,老少咸宜,会书中两种语文或其中一种的人皆宜。
李肇星
2011 年9 月14 日至25 日自乌兰巴托(意为“红色勇士”)上空经莫斯科、明斯克(“交易地”)、塔什干(“石头城”)飞阿拉木图(“苹果城”)途中。
用户评价
对我而言,这本诗集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作品范畴,它更像是一个精神上的锚点。在现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信息碎片化的今天,能够拥有这样一本可以随时“逃离”现实、进入纯粹审美世界的载体,是极其宝贵的。它不迎合潮流,不追求时髦,只是安静地矗立在那里,用古老而永恒的语言提醒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依然存在着超越物质的、深刻的、能够抚慰人心的美。每当我感到心绪不宁或灵感枯竭时,我都会随意翻开其中一页,总能被某一句精准捕捉到某种复杂情绪的诗句所击中,仿佛瞬间被理解,被治愈。这份跨越时空的共鸣,是任何电子阅读器都无法比拟的实体书独有的魔力。
评分真正触动我的,是它所承载的对“美”与“短暂”的永恒追问。这些诗篇,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呈现,其核心精神始终围绕着那种对完美瞬间的追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生命消逝的深刻洞察。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的感悟浮现。年少时读,或许只被那种热烈奔放的激情所感染;而今再品,却更能体会到字里行间那份潜藏的忧郁与对“Immortality”(不朽)的渴望。这种成熟的、带着一丝哀伤的美感,是其他许多诗人作品中难以寻觅的独特气质。它不回避痛苦,却选择将痛苦包裹在最华丽、最精致的语言外衣之下,形成了一种极具张力的对比,让人在品味美好的同时,又对时间的无情保持着清醒的认知。这是一种哲学的深度,而非肤浅的抒情。
评分从装帧的细节来看,这份精装版在纸张的选择上也颇为考究,它的纸张有一定的厚度和柔和的质感,即便是长时间阅读,眼睛也不会感到明显的疲劳,这对于沉浸式阅读长篇叙事诗或者大量短诗集来说,至关重要。我留意到,很多细节之处,比如章节之间的留白,都处理得非常得当,使得版面呼吸顺畅,避免了拥挤感。这种对阅读体验的体贴,往往体现了一家优秀出版社对经典文学应有的尊重。它鼓励你慢下来,去细细品味每一个逗号和每一个句子的停顿,而不是囫囵吞枣地快速浏览。这种细致入微的考量,无疑提升了整本书的价值,使其不只是一本“读物”,更像是一件可以珍藏的艺术品,值得反复摩挲和把玩。
评分这本诗集初拿到手时,那种沉甸甸的质感就让人心头一动,精装的封面设计典雅又不失庄重,一看就知道是下了功夫的用心之作。我一向偏爱这种有分量的实体书,指尖摩挲着微微凸起的烫金字样,仿佛能隔着纸张感受到文字本身散发出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我尤其欣赏出版社在装帧上体现出的对原作的尊重,它不是那种流于表面的华丽,而是一种内敛的、恰到好处的精致,让人在翻阅时便能心平气和地沉浸到那个遥远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年代去。每次打开它,都会有一种仪式感,仿佛要进行一场与伟大灵魂的秘密对话。这样的版本,放在书架上本身就是一种赏心悦目的点缀,更重要的是,它预示着内页的翻译和排版也必然是经过精心打磨的,让人对即将展开的阅读之旅充满了期待与敬畏。
评分阅读过程中,我被那种流畅而又饱含韵律感的译文深深吸引住了。好的译本绝不只是简单地将原文的意义转述过来,它更像是为原作在另一种语言的土壤中重新播种、精心培育的过程。这位译者的功力显然是深厚的,他成功地捕捉到了济慈诗歌中那种特有的“感官的丰饶”——那种对色彩、气味、声音和触感的极致描摹。读到那些关于夏日午后、关于秋日收获的诗句时,我几乎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成熟果实的甜香,感受到阳光温暖地洒在皮肤上的那种慵懒与满足。译文没有流于直白的叙述,而是巧妙地运用了中文里那些富有张力的词汇,使得那些跨越了时空的意象依然鲜活如初,这对一个非英语母语的读者来说,简直是莫大的幸运和享受,极大地降低了理解门槛,却又不失原作的艺术高度。
评分很满意
评分这书真的不错,值得购买。
评分此用户未填写评价内容
评分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评分质量保证,书正版,没问题,一直喜欢
评分好书啊
评分装帧啊纸张啊都一级棒可惜自己英语水平太菜
评分经典
评分价格便宜,质量很好,藏起来慢慢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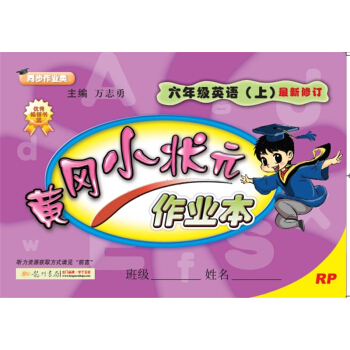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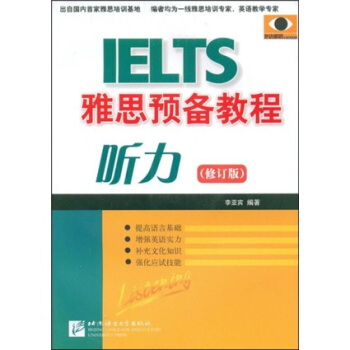
![6500词床头灯英语学习读本:娜娜11(英汉对照) [Nan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234414/76c3353a-a50e-48ba-8110-86c3cc630ae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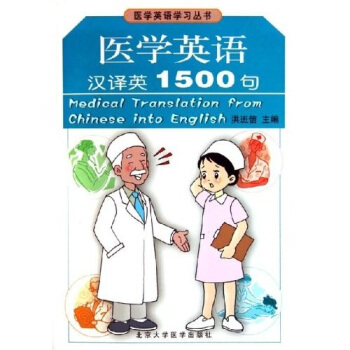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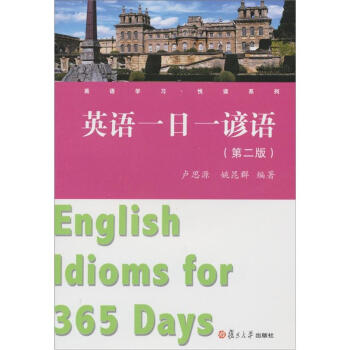

![在彼处:大使演讲录(精装本) [When I Was There:Selected Speeches of Fu Ying]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130679/53a7b8eeN85016f1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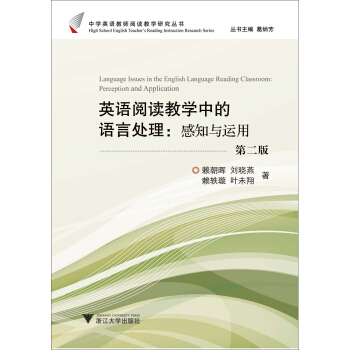
![高中英语阅读教学设计 [Reflection & Research on Classroom Teaching of English Reading]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78773/53a37c9fN215d21a5.jpg)
![新东方ACT考试指定培训教材:ACT备考策略与模拟试题 [Barron's ACT, 17th Edi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54830/543e42d7N17a4995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