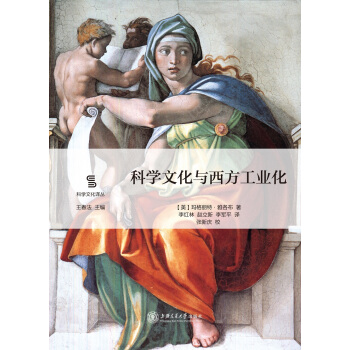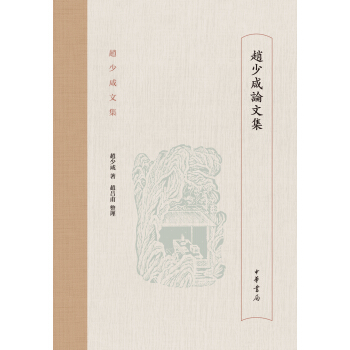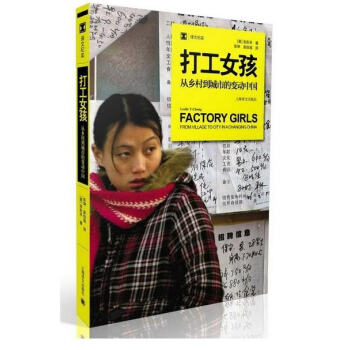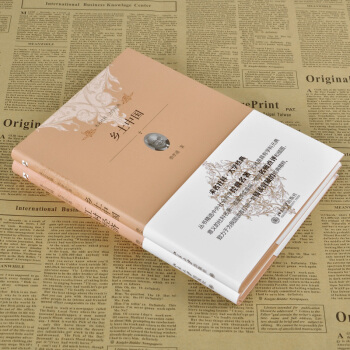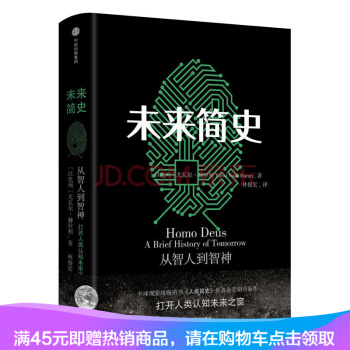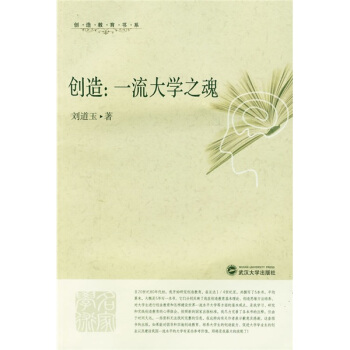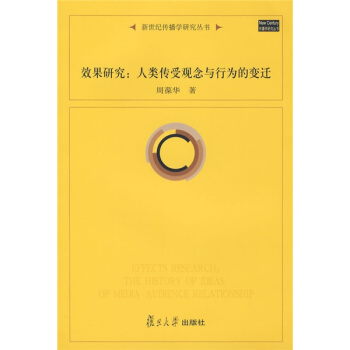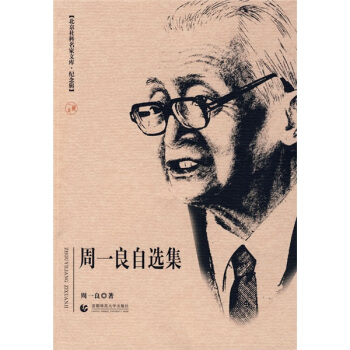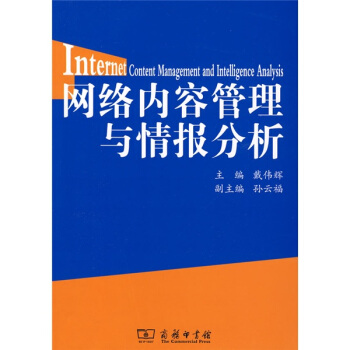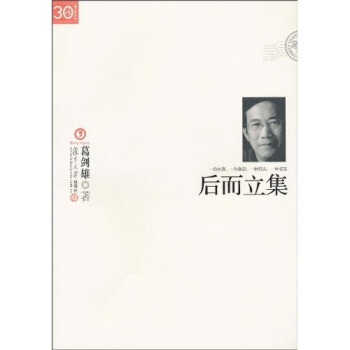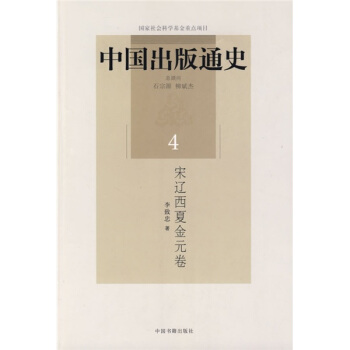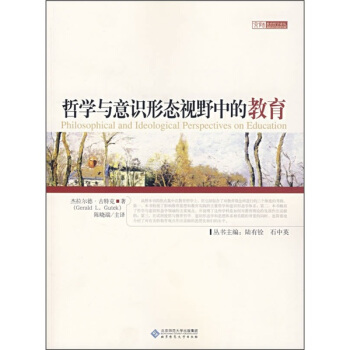![新资本主义的文化/理查德·桑内特作品集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101140/58d9d26fNb465b450.jpg)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社会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师生及社会上具有人文图书阅读兴趣的读者与哈贝马斯、阿伦特齐名的研究公共生活的社会思想家
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艺术和城市管理学等众多研究领域集大成者
黑格尔奖、格尔达?亨克尔奖、特森诺奖等学术奖项获得者
《匠人》作者理查德?桑内特又一力作
内容简介
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分析了传统工业资本主义和当今处于全球化转型中的资本主义之间的重大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工作伦理已经渐趋改变;稳定的传统科层式大型企业逐步被新经济条件下的小型化企业所代替;重视熟练技艺(所谓匠人)和成就的传统价值观让位于更加注重潜能和才华的价值观;所谓的“无用的幽灵”正缠绕着专业人士和手工业工人;消费和政治的界线正在消亡。
新经济在摆脱僵化静态的科层组织的“铁笼”的同时,理应给个人提供一种新的自由模式,但桑内特认为并非如此,新经济带来了新的社会和情感创伤,能适应和得益于这种新资本主义文化的只是一部分人。这种新资本主义文化对个人的自我提出了新的要求:越来越要求来自更加简洁意义上的自我,注重潜能而不是已经取得的成就,人们必须轻视甚至放弃以往的经验,努力适应新经济的“改革”要求。
作者简介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曾任纽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目前担任剑桥大学社会学系杰出访问教授,因其在社会学、城市规划研究等方面的杰出贡献,屡获黑格尔奖、斯宾诺莎奖、格尔达·亨克尔奖和特森诺奖等国际奖项。他的主要著作有:《19世纪的城市》(1969)、《阶级中隐藏的伤害》(1972)、《眼睛的良心》(1990)、《公共人的衰落》(1976)、《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1994)、《不平等世界的尊敬》(2003)、《新资本主义的文化》(2006),以及三部小说。
李继宏,200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其学术论文见于《社会学研究》、《人文杂志》、《广东社会科学》等刊物,另译有《小王子》、《与神对话》、《瓦尔登湖》、《追风筝的人》等各种体裁的图书三十余部,曾任英国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访问学者,目前担任加州大学尔湾校区(UC Irvine)英文系客座研究员。
精彩书评
★几乎所有的社会学方而的思想家都对全球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给予高度的关注,但理查德·桑内特无疑是其中很特别的一位,他的研究手段和视角都显得与众不同,他可以说是我们时代*有洞察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新资本主义的文化》一书中,理查德·桑内特用他不一般的广博知识阐述了新的企业文化的变化、不同的道德维度对政治的影响等多方面的内容,他得出的结论是明智且引人深思的,绝对是有可读性的。
他一直在阐述资本主义经济虽然相当成功,但并不令人满意。会有剧烈的震动使它发生裂变吗?理查德·桑内特认为会的。大家来读读这本书吧!
——罗伯特·默顿·索洛(麻省理工大学荣体教授)
目录
前言
导论
第一章 科层组织
第二章 才华和无用的幽灵
第三章 消费的政治
第四章 我们时代的社会资本主义
译后记
精彩书摘
无用的幽灵
导致无用的幽灵威胁到当代社会的因素有三种:全球的劳动力供应,自动化,以及老龄化的管理。每种因素的实质都与其表象不同。
当新闻记者惊呼全球劳动力供应已经使得工作岗位从富裕地区流向贫穷地区时,他们往往会把这种情况归咎于为了降低薪酬而进行的“恶性竞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总是追逐最廉价的劳动力。这种看法有一半是错误的。某种文化选择也起到了作用,所以工作岗位才会离开美国和德国,转移向各个低工资的经济体,那些地方的工人有足够的技能从事这样的工作,有时候从事这样的工作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大材小用。
印度的呼叫中心便是很好的例子。在那些呼叫中心工作的人至少懂两门语言;他们精心锤炼他们的语言技能,以致呼叫者不知道接电话的人是在美国的哈特福德还是在印度的孟买。许多呼叫中心的工人受过两年或以上的大学教育;此外,他们还得到良好的上岗培训。印度的呼叫中心强调“拓展学习”,这使得他们的头脑充满了各种信息,能够快速地回答最多合理常见的问题,从而大大提高呼入电话的数量。那些呼叫中心还给它们的工人上“人力资源技能”培训课,这种培训的目的有许多,其中之一是使他们不会以烦躁的口气回答某个糊涂的呼入者。那些印度工人比西方的呼叫服务工人得到更好的教育和更好的培训(爱尔兰和德国除外,这两个国家的经营标准和印度差不多)。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都很有能力,而他们得到的薪酬确实非常糟糕。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某些已经转移到南方国家的产业岗位中。这里要举的生动例子是墨西哥北部边境上的汽车装配厂。从事那些非常刻板的劳动的往往是拥有很高技能的机械师,他们宁愿离开汽车修理厂来到装配流水线上工作。在墨西哥北部那些美资免税工厂中上班的普通工人本来也许是领班或者工头。
恶性经济竞争最可怕的形象是这样的:许多南方国家的儿童离开家庭和学校,去血汗工厂打工。这个形象也许并没有错,但却是不完整的。劳动力市场也追求廉价的才华。南方国家的雇主和发达国家的雇主相同,也喜欢用牛刀来杀鸡。因为那些被大材小用的工人善于解决问题,尤其是在原有的工作程序出现毛病的时候。
……
前言/序言
导论
半个世纪之前,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传说中那个性交自由、毒品泛滥的年代,许多严肃的激进主义青年将矛头对准了各种社会机构,尤其是那些大型的企业和政府组织,它们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等级森严,铁钳似的牢牢地束缚着个人。1962年发布的新左派奠基文献“呼伦港宣言”同样抨击了国家社会主义和跨国公司,在新左派看来,这两种组织都是科层式的监狱。
历史部分地满足了“呼伦港宣言”起草者的愿望,五年计划、集中的经济控制等社会主义规则早已消失,那些强迫雇员卖命工作、年年供应相同产品和服务的资本主义企业已经成为陈迹。此外,医疗和教育等福利机构的规模越来越小,其形式也不再像过去那么固定。当今的统治者与五十年前的激进分子有着相同的目标:拆分僵化的科层组织。
然而,历史以相反的方式实现了新左派的愿望。我年轻时代的那些叛逆者认为,通过取缔各种社会机构,他们便能创造出各种共同体:直接交往的、团结信任的关系,不断进行协商与不断更新的关系,一个共同体的领域,身处其中的人们会关心他人的需求。这种情况当然没有发生。大型社会机构的分裂使得许多人的生活处于碎化的状态:他们工作的地方更像是火车站,而不是村庄,因为家庭生活被工作中的各种需求弄得失去了方向。迁移是全球时代的标志,人们四处流动,不再固定下来。可是拆分社会机构并没有生产出更多的共同体。
如果你是个怀旧的人(哪个敏感的灵魂不怀旧呢?),你可能会觉得这种情况实在令人惋惜。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亚洲、拉美和西方发达国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财富,这些新增的财富与拆分政府和企业的科层组织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的技术革命也主要发生在那些最少受到集中控制的机构。当然,这种增长的代价非常高昂:加剧了贫富不均和社会的动荡。尽管如此,认为这样的经济爆炸不应该发生想法也是有失理性的。
正是在这里,文化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我说的“文化”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而不是艺术意义上的。既然人们所生活在其中的机构已经四分五裂,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实践行动才能够让人们团结起来呢?我这代人曾经苦苦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倡导小规模共同体的价值观。共同体并非惟一的文化粘合剂,最明显的证据是,城市中的陌生人尽管彼此并不认识,却生活在共同的文化里。但支持性文化的问题不仅仅与规模有关。
在不稳定的、分碎的社会环境中,只有一类人能够如鱼得水。这个理想的男人或者女人不得不应付三个难题。
第一个与时间有关:不停地在任务、工作、地点之间迁移的同时,如何应对各种短期关系和自我。如果机构不再提供长期的框架,个人可能不得不随时修改他或她的“生活叙事”,或者甚至缺乏任何稳定持续的自我认知。
第二个与才华有关:现实的要求不断变化,如何才能培养新的技能,如何才能开发自身的潜能。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在现代的经济中,许多技能不用多久便会过时;在科学技术领域和先进的制造业中,工作人员平均八到十二年便需要重新培训。才华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新出现的社会秩序不利于匠人精神的发扬。所谓匠人精神,指的是将某件事情做到真正精通的态度;这种专注的态度在经济上往往是破坏性的。为了取代匠人精神,现代文化推出优才统治的理念,这种理念更注重潜在的能力,而不是过去的成绩。
第三个难题由此而生。它和放弃有关;那就是如何忘掉过去。最近,某个蓬勃发展的企业的领导人宣称,她的公司里没有人能够端着铁饭碗,过去的成绩并不足以让员工保住自己的职位。要怎样才能积极地回应这种宣言呢?这需要人们拥有一种性格特征,就是看轻一个人已经拥有的经验。拥有这种性格特征的人就像贪心的消费者,不停地追求新玩意,抛弃那些虽然旧然而功能完好的商品,他或她不会敝帚自珍地守护已经拥有的东西。
我想展示的是,社会如何四处寻找这个理想的男人或者女人。我将会越出学者的本分,对这种寻找进行评判。这些以短期关系为取向、专注于潜在的能力、愿意放弃已有经验的自我是一类——说好听点吧——异乎寻常的人。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子的;他们需要持续的生活叙事,他们以某项专长为荣,他们珍惜有过的经历。因而,那些新机构所要求的这种文化理念给许多生活在它们之中的人们造成了伤害。
用户评价
说实话,这本书的阅读体验,非常具有“催人奋进”的讽刺意味。它把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的那些“成功学”口号背后的文化逻辑扒得一干二净,让我们看到,那些鼓吹“自由职业”和“自我实现”的话术,其实是为一种更精细、更无孔不入的剥削披上了华丽的外衣。桑内特没有给我提供一张逃离的地图,但他给了我一双能看穿迷雾的眼睛。比如他对“个人品牌”的解构,让我意识到,这种不断对外展示完美形象的努力,实际上消耗了我们大量的内在资源,这些资源本可以用来建立更深层次的思考和连接。这本书像一剂清醒剂,让人在被高速运转的社会裹挟前,能够停下来问一句: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它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分析,更是对当代主体性危机的一次深刻探问。每次合上它,我都会有一种想要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结构、抵制那种被动接受既定叙事的冲动。
评分理查德·桑内特这位老先生的笔法,总有一种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悲悯交织其中的独特味道。他并非一个愤世嫉俗的批判者,他更像是一个满怀希望,却又深知现实残酷的观察者。他观察到的新资本主义文化,并非是外来的入侵,而是深深内化为我们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判断之中。我印象非常深的一段,是关于“职业生涯即作品”这一观念的消亡。过去,手艺人可以为自己的作品背负一生的声誉,但现在,一切都成了可以被随时“重置”的迭代版本。这种持续的自我重塑的压力,对创造力的扼杀是巨大的。因为真正的创造往往需要沉潜,需要敢于失败的勇气,而新资本主义文化只奖励“立竿见影的成功”。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提醒我们,当我们为了适应系统而不断“优化”自己的时候,我们可能正在亲手磨损掉那些最宝贵的人性光辉。
评分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本书给我的冲击,那就是“疏离”。桑内特描绘了一个充满“连接”的时代,但这种连接却是建立在极度脆弱和功利基础之上的。他笔下的新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人际信任的系统性瓦解。我们被鼓励去建立“网络”(networks),而不是“关系”(relationships)。网络是流动的、可替代的,关系则需要时间和情感的投入。当我读到他分析那种“项目导向型”的团队合作,其背后潜藏的,其实是缺乏真正共同目标的个体联盟时,我瞬间明白了为什么现在很多合作项目结束后,人与人之间那种体面的礼貌很快就会退化为毫无交集的陌生。这种对情感资本耗散的精准描述,让我对周围那些看似热闹实则空洞的社交场景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这本书不仅仅是在讨论经济,它是在讨论我们如何在这套系统里,艰难地维持着一份有意义的人性。
评分《新资本主义的文化》这本书,我读完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真的把我们这个时代里,那种无处不在、却又难以言喻的“文化氛围”给剖析得淋漓尽致。桑内特这位老先生,他不是那种只会空谈理论的学者,他总能从日常生活的微观细节入手,去捕捉那些宏大的社会结构正在如何悄悄地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人际关系。比如,他谈到那种项目制的、非稳定性的工作模式,是如何侵蚀掉我们对于“长期承诺”和“身份认同”的观念。我们不再是为一个工匠般的职业生涯而努力,而是不断地成为一个“自我推销”的个体。这种评价体系,让我们的情感生活和职业抱负都变得极其碎片化,仿佛我们每个人都在永不停歇地进行一场“软性推销”。读到这些地方,我常常会停下来,回想自己过去几年在职场上的漂泊感,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努力,背后竟然有着如此深刻的文化根源。这种洞察力,让人既感到被理解的慰藉,又生出一种被揭示后的焦虑感。这本书提供的,不是简单的答案,而是一整套理解我们当下处境的批判性工具箱。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说实话,不是那种让人一口气读完就放下的小说,它更像是一杯需要细细品味的陈年威士忌,每一页都带着浓烈的思辨气息。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时间”这个概念上的深刻见解。在那个被新资本主义逻辑所主导的社会里,长期规划似乎成了一种过时的奢望,一切都必须是即时反馈、快速迭代的。桑内特没有停留在对这种“效率至上”的表面批判,他深入挖掘了这种时间观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侵蚀。当我们的“自我”被塑造成一个永远在更新软件的App时,我们如何还能保有那种扎根于历史和传统的深度?这种对“肤浅化”的警惕,让我联想到现在社交媒体上那种追求“爆点”和“热度”的文化现象,它与书中描述的经济逻辑,简直是异曲同工之妙。每一次拿起这本书,我都感觉像是在进行一场智力上的拉锯战,它迫使你跳出舒适区,去质疑那些你习以为常的“生活常识”,那种被挑战的感觉,正是好书的魅力所在。
评分原谅我是标题党,不过这个标题很有趣
评分绝对是好书,价格也便宜,很值得一读。
评分绝对是好书,价格也便宜,很值得一读。
评分~~~~~~~~~~~~~
评分很好!很不错啊
评分书不错的,618搞活动买的,适合科普,买的时候价格美丽,所一直就放着了。哎,遗憾的读书的时候常常想起家里的小宝,就是家里的萨摩耶7月6号在义乌义南工业区走丢了,希望这头傻狗有傻福,小宝有好心人养~~
评分新资本主义的文化输出的地方咋办?
评分替朋友下单,评价很好,值得购买!
评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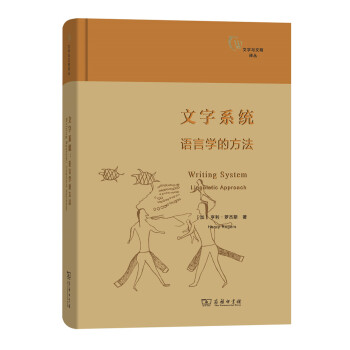
![日本现代思想批判/日本当代文化思想译丛 [日本现代思想批判]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125842/58dc7205N032c65e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