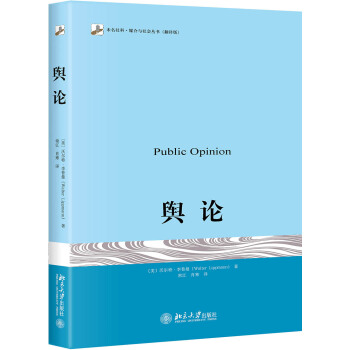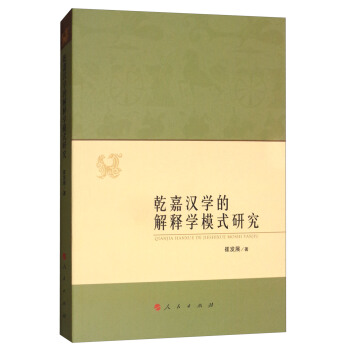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实事求是”是理解乾嘉汉学的一把钥匙,但它绝不仅仅意昧着一种客观的求实态度或考证方法。《乾嘉汉学的解释学模式研究》尝试将“实事求是”作为一个普遍的经学解释学命题进行分析,指出该命题实际上蕴含着考证性、认识论、存在论三个不同的层级。与此相应,该命题既具有一般性的普遍结构,又可以在不同层级上呈现出迥异的特殊结构。由此,对乾嘉汉学进行结构性、模式性分析,就可以宏观考察其利弊得失,进而从中探讨建构中国解释学的有效路径,并适时分析当下复兴传统中的一些需要警惕的问题。
作者简介
崔发展,1978年生,河南兰考人。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四川省第11批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2001年、2004年先后获得四川大学哲学学士、哲学硕士学位,2009年获得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17年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出站。主要从事儒家哲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博士后面上资助各1项。曾主持或参与《中国哲学史经典精读》、《简明中国哲学》、《生活·仁爱·境界:评生活儒学》、《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等著作的编撰工作,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孔子研究》、《鹅湖》、《文化中国》(加拿大)等国内外刊物公开发表论文40余篇。目录
序一序二
导论
第一章 乾嘉汉学与解释学的位置
第一节 说不尽的汉宋
第二节 作为典范的乾嘉汉学
第三节 解释学的位置
第四节 作为焦点问题的“实事求是”
第五节 前期研究综述
第二章 “实事求是”话语的起兴
第一节 黜虚崇实:明清之际宋学话语的失势
第二节 汉宋易帜:官民回归经学的二重奏
第三节 鉴古训今:河间献王作为乾嘉汉学兴起的标杆
第四节 实事求是:乾嘉汉学主盟学坛的就职宣言
第三章 “实事求是”作为经学解释命题的展开
第一节 “实事求是者”:乾嘉汉学的解释主体
第二节 “实事”:乾嘉汉学的解释对象
第三节 “求”:乾嘉汉学的解释方法
第四节 “是”:乾嘉汉学的解释目标
第四章 “实事求是”命题的定性、结构与层级
第一节 “实事求是”的定性问题
第二节 “实事求是”作为经学解释命题的普遍结构
第三节 “实事求是”作为经学考证性命题
第四节 “实事求是”作为认识论命题
第五节 “实事求是”作为存在论命题
第五章 乾嘉汉学的解释学反思
第一节 认识论、方法论的反省:“不为训诂牢笼”
第二节 存在论的启示:“面向事情本身”
第三节 实践论的归属:回应相对主义
结语
附录汉宋之争中的经典解释问题——以阮元对李翱的批评为例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精彩书摘
《乾嘉汉学的解释学模式研究》:二、哲学解释学能否作为一种方法
在《科学时代的理性》的中译本出版之际,伽达默尔在“作者自序”中明确提醒道:“解释学首先就在于它并不是各门科学的一种方法论,而是与人的、社会的存在所具有的根本大法有关。这意味着解释学并非什么方法学说,而是哲学。”①那么,在借鉴哲学解释学时,我们怎么能把一种非方法论的东西拿来作为方法呢?这岂不自相矛盾?
的确,如伽达默尔所言,他的哲学解释学的目的乃是为了理解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理解的存在论事实到底是怎样的,而并非是要揭明理解的步骤或方法,由此,哲学解释学是被明确地定位在本体论的层次上,以致伽氏反复强调说他其实并没有提出什么方法,而只是对“事情本身”的展现。不仅如此,伽氏甚至宣称真理与方法之间的对峙乃是一种不可消除的现实性。②对于伽氏的《真理与方法》所内含的这种对峙,其亲炙弟子帕尔默亦指出:“这《乾嘉汉学的解释学模式研究》的标题包含着一个讽刺:方法并非通达真理的途径。相反,真理逃避遵循方法的人。”③
利科认为,《真理与方法》的“名称本身包括海德格尔的真理概念和狄尔泰的方法概念之间的对立”④。这表明伽氏乃是站在本体论立场上反对方法论、认识论。其实,伽氏并非反对一切方法(论),针对自然科学方法在精神科学领域滥用的现状,或者说,为了维护精神科学领域的真理性,他特意反对那种自然科学方法意义上的“认识论方法学主义”。由此,伽氏才会说《真理与方法》的出发点乃是基于对泛科学化或科学主义的一种对抗。⑤在伽氏看来,人文领域有其自身独特的方法或方法论,如他明确承认其哲学解释学的建立,所依赖的方法论就是辩证法与现象学,而这两种方法已不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了,而是与生存论紧密相关。可见,此二者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来讲的,不可认为伽氏混淆了二者,尤其是这至少充分表明伽氏反对的只是认识论上的方法,而非本体论上的方法。
关于哲学解释学的方法论导向,可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伽氏说:“真理和方法之间对立的尖锐化在我的研究中具有一种论战的意义。正如笛卡尔所承认,使一件被歪曲的事物重新恢复正确的特定结构在于,人们必须矫枉过正。”①由此,既然他之所以强调方法与真理之间的对立,实则是出于不得已的“矫枉过正”的考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间接承认了哲学解释学也有一种方法的使用?且这种使用并不只是所谓的“本体论意义的方法”?②
第二,伽氏曾多次提及“诠释学训练”这一概念,虽然他指出“训练”不同于“方法”,但不可否认其中必然有方法或方法论的意味。③比如伽氏仍旧承认这类训练可以“间接地有益于理解技巧”④,所以,利科的这一识见或许值得重视,其言日:“与海德格尔相比,伽达默尔的研究也标志着从存在论到认识论问题的开端。我正是根据这一点来讨论伽达默尔的贡献。”⑤利科认为,伽氏的哲学解释学其实已有迹象表明他试图从存在论转向认识论。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这只是利科的一家之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伽氏的确有忽略解释学领域中的方法或方法论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利科在修正这一方向上的卓越贡献。因此,我们必须批判地对待哲学解释学,尤其是要充分地意识到它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不足,而乾嘉汉学的工作恰恰也能提供一些反省哲学解释学之局限性的启示。不过,利科的另外一个提醒更需谨记,此即:解释学首先应当是本体论而非方法论,而作为方法的解释学批判必然建立在作为本体的解释传统之上。
……
前言/序言
这些年来,在儒学界、中国哲学研究界,“经典诠释”成为一种学术时尚,不少学人甚至表达了建构“中国式诠释学”的雄心。这固然有中国本土的古典诠释传统的影响,也有外来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的作用,但真正的缘由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时代需求,即寻求“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①。不过,目前为止,“中国式诠释学”的面相还很模糊;不仅如此,还有一种普遍的误解,以为只要是对中国古代文本的解释,那就是“经典诠释”了。总之,“究竟何谓‘经典诠释”依然还是一个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读到《乾嘉汉学的解释学模式研究》这样的著作是一件十分令人高兴的事情。此书是关于乾嘉学术的一种诠释学角度的研究,其宗旨不仅在于从中国传统的经学诠释中辨识出一种别样的“解释学模式”,进而指认出“实事求是”的一般方法论②,更在于由此生长培育出一种中国式的诠释学。
为此,作者首先对乾嘉学术进行了一种坐标式的定位:其纵轴是古今之维,即“汉宋之争”;其横轴是中西之维,即中国传统的“汉学”与西方的哲学诠释学(Diephilosophischehermeneutik)之间的关系。
在中西之维上,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借鉴西方的哲学诠释学来分析中国的乾嘉学术,这是否具有“合法性”?这个问题所牵涉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即近年来哲学界所批评的“以西释中”乃至“汉话胡说”的现象。作者分析论证了以哲学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乾嘉学术这种做法的合法性或合理性,其分析论证是言之成理的。
我自己也曾撰文讨论过这个问题。①简言之,“以西释中”或“汉话胡说”之类的批评,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存在着某种现成在手的、客观实在“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中国经典”和“西方经典”之类的东西。但这个预设前提本身就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诠释者(主体)和被诠释文本(客体)都是由当下的诠释活动给出的,即在诠释活动中获得其新的主体性和新的对象性,亦即是在当下的存在或生活中生成了主体性存在者和对象性存在者。经典是被诠释出来的经典,经典的意义是被诠释出来的意义,而诠释者是被生活给出的,诠释活动乃是当下的一种生活情境。在这个意义上,诸如“借鉴哲学解释学来分析乾嘉汉学”或“以解释学解读乾嘉汉学”这样的提法也是词不达意的、存在者化的表达,因为恰恰是“解读”或“分析”这样的诠释活动给出了所谓“哲学解释学”和所谓“乾嘉汉学”这样的存在者,而这种诠释活动归属于作为存在的生活,即是生活的一种当下显现样式。
用户评价
对于一个对“模式”这个词特别敏感的读者来说,我更关注的是这本书的“通用性”与“独特性”的平衡点。乾嘉汉学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学术现象,其解释模式的构建,必然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这本书的厉害之处,应当在于如何从这个特殊的案例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学原理”。如果它仅仅是把乾嘉学者的治学方法,用解释学的术语重新包装一遍,那就显得有些牵强附会,甚至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嫌。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作者能够有力地证明:这个“乾嘉模式”与其他时期的学术范式相比,在解释文本、理解世界时,究竟有何本质上的区别和优越性(或者局限性)。这是一场关于“如何认识”的深刻对话,它应该能引发我们对当前研究方法论的反思,而不仅仅是对历史细节的缅怀。
评分这本书的名字,让人联想到精妙的构图和深邃的内涵,像一幅需要仔细摩挲才能品出其笔意的工笔画。我常常在想,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实际上是其社会文化心理的折射。乾嘉学派的兴盛,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集体的情感或理性的需求。我希望作者能在文本中描摹出这种“时代精神”是如何被学者们转化为具体的“解释工具”的。比如,在社会动荡或士人情绪压抑的背景下,他们为何会转向对经典文本的“求真务实”?这种务实本身,是否也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或另类表达?如果书中的“解释学模式”不只是冷冰冰的逻辑推演,而是能将学者个体与宏大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展示出学术思想的生命力与温度,那么即便我不是百分之百理解所有的专业术语,也能感受到它扑面而来的历史张力。我期待看到一个充满温度的学术剖析。
评分光是书名就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学院派”气息,这通常意味着严谨、扎实,但也可能意味着相对缺乏趣味性。我最近在关注一些关于知识建构的哲学讨论,非常好奇中国古代的知识生产过程是如何被“解释”的。这本书如果能提供一个清晰的“乾嘉模式”,那无疑是对我们理解传统学术范式的一次重要贡献。我设想,作者或许会对比不同学派在考据、训诂上的差异,然后用解释学的视角去剖析这些差异背后的根本逻辑差异——比如,他们对“原意”的理解有何不同?对“文本权威性”的界定又有哪些细微差别?如果这本书能深入探讨这些形而上的问题,而非仅仅停留在对考据成果的复述上,那么它就具备了超越普通史学专著的潜力,甚至能为当下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一些本土化的理论资源。我希望它能给我带来“原来如此”的惊喜感,而不是“意料之中”的平淡。
评分坦白说,我对这类题目总有些“望而却步”的感觉。你知道,那种专精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学术研究,往往像一个高度精密的仪器,需要操作者具备极高的专业素养才能完全领会其精妙之处。我猜这本书的受众应该主要集中在历史学和文献学领域的研究生和教授们。对于我这样的普通爱好者来说,如果它能用相对清晰、易懂的语言来阐释那些深奥的理论模型,那就太棒了。我最担心的是,作者会不会陷入“学理的自娱自乐”,满篇的术语堆砌,让人读得云里雾里,最后只记住几个名词,却无法真正理解其运作机制。一个成功的学术作品,即便内容再深奥,也应该在结构上做到层层递进,逻辑严密,让读者感受到思维被引导、被提升的过程。如果它能像一位技艺精湛的向导,带领我们穿梭在乾嘉学派的复杂思想迷宫中,指出那些关键的路标,那这本书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评分好的,这是一份模拟读者对一本未读过的图书的评价,旨在展现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体验和视角,且每段的风格和措辞都力求独特,避免被识别为AI生成。 这部书的书名听起来就透着一股学术的厚重感,尤其“乾嘉汉学”和“解释学模式”这两个词的组合,让我立马联想到那些在书斋里耗费毕生精力梳理故纸堆的学者。我个人对清代学术史一直抱有一种敬畏之心,那段时期思想的碰撞和流派的兴起,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如果这本书仅仅是罗列史实、梳理脉络,那未免有些枯燥。我更期待它能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比如,作者是如何将“解释学”这一西方哲学概念巧妙地嵌入到对传统汉学研究范式的分析中去的?这才是真正考验功力的部分。一部好的学术著作,不应只是知识的堆砌,更应当是思想的导航。它应该能帮我们厘清,在面对浩瀚的古代文献时,我们究竟应该采用何种视角、何种工具,才能真正触及文本的精髓,而不是停留在表面功夫。我希望这本书能给我提供一个全新的、富有洞察力的框架,让我能够以一种更现代、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去重新审视那些看似陈旧的学问。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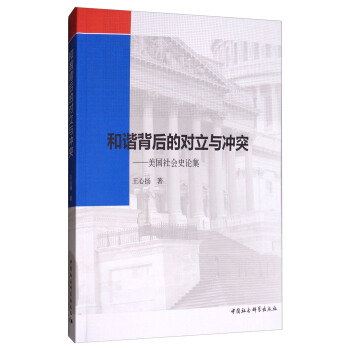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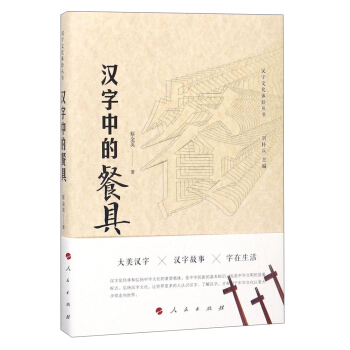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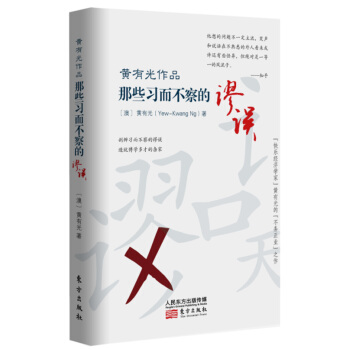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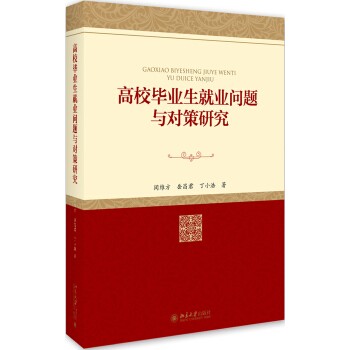
![当代世界媒体(套装上下册) [Contemporary World Medi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44057/5b0289bdN6160a3cc.jpg)

![整合与形塑:地方政务服务机构的运作机制 [Integration with shape: the mechanism of local government servic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44831/5af402ceN76bf91ff.jpg)

![中国路径:双层博弈视角下的气候传播与治理 [Climate Communication and Governance:China's Path]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47975/5b04bc98Nc18346b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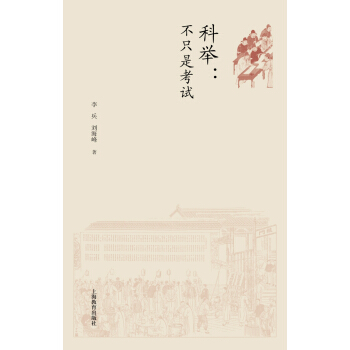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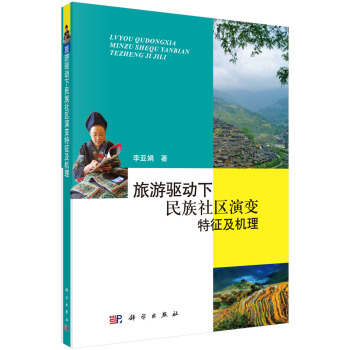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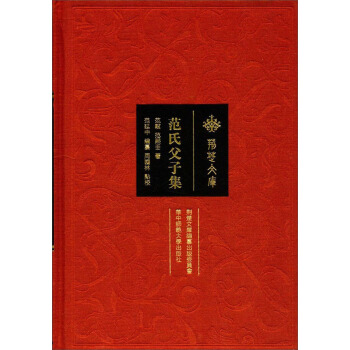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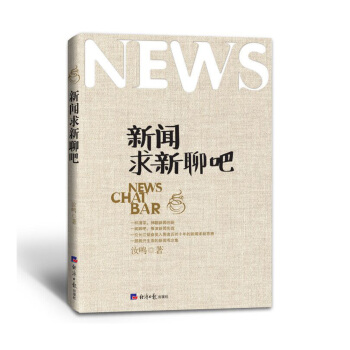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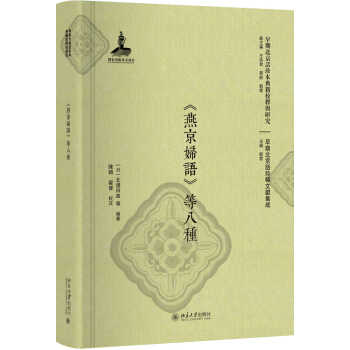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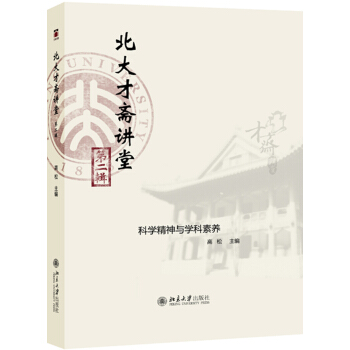

![以书筑城 以城筑梦:深圳书城模式研究/深圳改革创新丛书(第五辑) [Mall of Books,City of Dreams:Research on Shenzhen Bookmall Model]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56801/5b1a4cddN9e3255e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