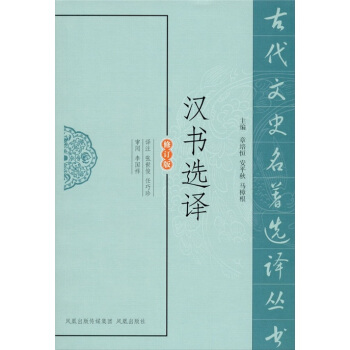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汉书》又称《前汉书》,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史事。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001高帝纪001
苏武传067
张骞传089
东方朔传109
杨恽传139
霍光传155
赵广汉传180
严延年传195
原涉传207
匈奴传218
王莽传239
编纂始末001
丛书总目001
精彩书摘
公元前209年9月,正当陈胜、吴广领导农民起义军冲决着秦帝国的腐朽统治的时候,有两支武装力量在东南部几乎同时崛起。其一是项梁、项羽在吴县杀郡守起义,领着八千江东子弟向北挺进;其一是刘邦在沛县斩蛇起义,然后率领沛县民众攻城略地。起初,刘邦军与项梁军相配合,在江苏、安徽西北部、山东西南部、河南东部辗转作战,打击秦军。项梁死后,项羽北上救赵,抗击秦军主力。刘邦受怀王派遣,出山东西行,横贯河南,没有遭遇特大阻力,从武关攻入关中,结束了秦帝国的反动统治。项羽入关之后,本打算消灭刘邦军,经过鸿门宴上的一番较量,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刘邦不甘心屈居汉中为王,不久便暗度陈仓,还定三秦,出关东征,揭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的历史篇章。
刘邦虽曾一度战败,甚至全军覆没,但很快他又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他以荥阳、成皋为据点,与项羽展开拉锯战,消耗了项羽的有生力量,扩大了战果,形成了对项羽的包围圈。项羽陷于孤立境地,不得不同意中分天下。
成皋之战使刘邦由战略防御变为战略反攻。刘邦终于调动了一切力量在垓下决战中消灭了项羽军。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在复杂激烈的斗争中诞生了。
刘邦知人善任,能听取不同意见,顺应民心,得到民众的支持,这些都是他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值得我们借鉴。
本篇选入刘邦的主要经历和活动,有关的人物和事件一般从略。
高祖①,沛丰邑中阳里人也②,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③,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④,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⑤。已而有娠⑥,遂产高祖。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⑦,美须髯⑧,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宽仁爱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吏,为泗上亭长⑨,廷中吏无所不狎侮⑩。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⑾,时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⑿。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⒀。
高祖常繇咸阳⒁,纵观秦皇帝,喟然大息⒂,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⒃,辟仇,从之客,因家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①,主进②,令诸大夫日:“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③,乃绐为谒曰“贺钱万”④,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⑤。酒阑⑥,吕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后。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箕帚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日:“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卒与高祖。吕公女即吕后也,生孝惠帝、鲁元公主。
用户评价
我最近翻阅了一本探讨晚清“西学东渐”初期思想碰撞的译著,这本书的视角非常独特,它没有聚焦于那些耳熟能详的改革家,而是把镜头对准了那些早期接触西方科技和宗教的中间人物——海关职员、传教士的本土助手以及地方上的开明士绅。这使得整本书的叙事充满了烟火气和现实的张力。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大量未经整理的档案、私人信件和地方志中的零星记载,重建了一个多层次的知识传播网络,让人看到“新知”是如何艰难地渗透到传统社会肌理之中的。比如,书中对火轮船抵达沿海港口时,地方官员的恐慌与好奇心的复杂描绘,既有对未知力量的敬畏,也有对传统体制可能被颠覆的隐忧,描写得极其细腻。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也很有特色,虽然是学术著作,但行文流畅,充满了历史的画面感,完全没有那种枯燥的理论堆砌。它成功地将宏大的历史进程,还原为无数微小的个人选择与挣扎,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在那个剧变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在进行着艰难的文化定位。它让我重新思考“开明”与“保守”这两个标签的复杂性,深刻体会到历史的进步往往是充满矛盾和妥协的。
评分我最近迷上了一套关于魏晋风度的随笔集,名字里带着“潇洒”二字,内容确实也没让人失望。作者的文笔如同山间清泉,泠泠作响,却又暗含深意。他不像那些严谨的史学家,一板一眼地罗列事实,而是用一种近乎于谈笑风生的笔法,描绘了那个时代名士们的风流韵事和精神困境。比如,他写嵇康的《广陵散》,不是简单地介绍这首曲子的历史地位,而是深入挖掘了嵇康在生命最后关头,那种“非汤武而薄周洛”的傲骨是如何通过琴音得以宣泄的。我特别喜欢那种带着强烈个人情感色彩的解读,它让历史人物不再是教科书上刻板的符号,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体。这本书的装帧设计也十分考究,采用了仿宋体的印刷,配合大开本的排版,读起来极其舒服,眼睛一点也不累。虽然书中不乏一些学术性的探讨,但作者总能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其圆融化解,使得即便是对玄学一窍不通的新手,也能窥见一丝“竹林七贤”的清狂与无奈。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成功地架起了一座古典精神与现代心灵之间的桥梁,让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得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去品味那种遗世独立的雅致。
评分这部《史记》的影印本,装帧朴素,纸张略带泛黄的年代感,但印刷质量出奇地清晰,每一个笔画都仿佛能触摸到司马迁当年伏案疾书的力度。初捧此书,便被那份厚重的历史气息所感染。我并非专业的历史学者,对古籍的理解多停留在泛泛的层面,然而这部选本的编排,却巧妙地照顾到了像我这样的“半吊子”读者。它没有一上来就堆砌晦涩难懂的文言,而是精心地挑选了那些叙事性强、人物形象鲜明的段落,像是《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对峙,那种紧张到令人窒息的氛围,即使隔着千年文字,依然能透过纸面扑面而来。尤其是对那些关键情节的注释,做得极为精准到位,不像有些版本,注释多余繁杂,反而打断了阅读的流畅性。这份选本的体例,更像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先生,耐心地为你引路,告诉你哪些地方值得驻足细品,哪些典故需要稍作停顿。我尤其欣赏它在人物评价上的处理,没有过度美化或贬低,而是保留了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让人在阅读故事的同时,也能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读完一遍下来,只觉得胸中块垒郁结,对那个风云变幻的秦末汉初,有了更为立体和鲜活的认知。这不仅仅是一套书,更像是一扇通往那个时代的窗口,让人流连忘返。
评分关于古代小说叙事技巧的研究专著,市面上的很多都侧重于结构分析或者人物原型,但这一本,却独辟蹊径,将目光聚焦在了“场景构建”与“氛围渲染”上。它几乎把章回体小说的叙事空间当作一个可以被解构的对象,来探讨古典作家是如何利用环境描写来暗示人物命运和推动情节发展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它对《红楼梦》中“太虚幻境”描写的分析,作者没有停留在表面的奇幻,而是深入探讨了这种亦真亦幻的空间如何成为曹雪芹表达人生虚无感和宿命论的隐喻场域。书中使用了大量的空间理论和符号学分析,但其行文却异常克制和优雅,大量的例证都是从文本中精准截取的片段,配以精到的评点,让你仿佛跟着作者一起,重新审视那些似曾相识的场景。比如,对“月下独酌”这类经典场景,它会细致分析光影、声音乃至气味的调动,以展示古典叙事在营造情绪上的高超手法。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将我们习以为常的古典叙事,提升到了一个更为精密的学术层面,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之余,也能体会到作者在“如何讲故事”上所下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匠心。读完之后,再去看那些经典片段,总会发现一些之前忽略掉的、潜藏在文字背后的精妙布局。
评分这是一本关于宋代文人画论的精选集,对于长期浸淫在传统艺术领域的人来说,简直是如获至宝。它的厉害之处在于,选取的文本极为专业且聚焦,没有涵盖宋代艺术史的全部面貌,而是精准地锁定了从苏轼到李公麟再到后来的理论家们关于“意境”与“笔墨”的论述。我特意对比了其他几本同类书籍,发现这部选集在对一些核心概念的区分上做得极为细致,比如如何区分“画中有诗”与“诗中有画”的微妙界限,以及“平淡天真”在不同画家身上的体现差异。译注部分的处理,堪称典范——它没有做大段的现代白话翻译,而是采取了对译的模式,将文言原文放在左页,精准的现代学术用语注释放在右页,这样既保留了原文的韵味,又不至于让初学者望而却步。此外,书中还收录了一些宋代书信和题跋的片段,这些零散的文字,往往比系统论述更能体现文人画家的真实心境和创作背景。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更像是在跟一群古代的艺术家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深度对话,每一个字都凝聚着他们对艺术本质的深刻洞察。对于致力于理解宋画精神内核的读者来说,它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深度和广度。
评分物流不想吐槽了,慢出新境界
评分很喜欢。
评分好
评分我前两天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还有去年冬天看张爱玲的《异乡记》。让我深思的是,一个人,他作为小说家的状态和生活底色的比重。老陀当时是被判死刑的,张爱玲去探胡兰成,也正逢战时,兵荒马乱,满地乱孚,应该是心思忐忑,难以聚神才对。而他们的注意力,是马力全开的,不放过一点点残渣。甚至三十年后的《小团圆》里,都楚楚如在目下——她的最爱,她的伴侣,不是胡兰成而是小说。她就是作为一个小说家而活着的,其他的一切,都是补给。她舅舅家的故事被她写成《花凋》。《金锁记》里是她父系的丑事,甚至名字都没换。《易经》《雷峰塔》则干脆把早期小说里的边角料:仆佣、下人,也给血肉丰满扩充写了。小说人格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人的兴趣,而不是急着判断说理,重叙事,更关注事件的质感,喜欢慢慢地体味。评论人格喜欢指点江山,发表意见。这两者没有绝对的分野,只是比重和偏向。 有些人又以评论胜出,私以为鲁迅就是。他的杂文比小说好,刀锋凌厉,气势十足,又多产。韩寒也是,眼睛亮,戾气重,快意恩仇,这种性格,自是杂文最便利。又比如西班牙的蒙特罗,她的《女性小传》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文字紧凑,观点犀利,非常有个人视角,但是她的小说《地域中心》,实在是不忍卒读。桑塔格也是,学术一流,小说平平。这可能和性格有关。写评论的人,好解析,寻根溯源;写小说,更需要还原事件本身和编故事。一个是缜密深究的洞察力,一个是寻求趣味的娱乐性。 同时能把小说和杂文玩溜的,张爱玲算一个,那真是左右开弓的天才。小说文字,要隐蔽、含蓄、肉感,主观低调淡出,精确的全知视角,自抑和克制。杂文需要的是出刀,更骨感,更有观点和火药味。伊简直是文学界的小龙女,周伯通练了一辈子的左右互搏术,人家天生就会。 我前两天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还有去年冬天看张爱玲的《异乡记》。让我深思的是,一个人,他作为小说家的状态和生活底色的比重。老陀当时是被判死刑的,张爱玲去探胡兰成,也正逢战时,兵荒马乱,满地乱孚,应该是心思忐忑,难以聚神才对。而他们的注意力,是马力全开的,不放过一点点残渣。甚至三十年后的《小团圆》里,都楚楚如在目下——她的最爱,她的伴侣,不是胡兰成而是小说。她就是作为一个小说家而活着的,其他的一切,都是补给。她舅舅家的故事被她写成《花凋》。《金锁记》里是她父系的丑事,甚至名字都没换。《易经》《雷峰塔》则干脆把早期小说里的边角料:仆佣、下人,也给血肉丰满扩充写了。小说人格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人的兴趣,而不是急着判断说理,重叙事,更关注事件的质感,喜欢慢慢地体味。评论人格喜欢指点江山,发表意见。这两者没有绝对的分野,只是比重和偏向。 有些人又以评论胜出,私以为鲁迅就是。他的杂文比小说好,刀锋凌厉,气势十足,又多产。韩寒也是,眼睛亮,戾气重,快意恩仇,这种性格,自是杂文最便利。又比如西班牙的蒙特罗,她的《女性小传》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文字紧凑,观点犀利,非常有个人视角,但是她的小说《地域中心》,实在是不忍卒读。桑塔格也是,学术一流,小说平平。这可能和性格有关。写评论的人,好解析,寻根溯源;写小说,更需要还原事件本身和编故事。一个是缜密深究的洞察力,一个是寻求趣味的娱乐性。 同时能把小说和杂文玩溜的,张爱玲算一个,那真是左右开弓的天才。小说文字,要隐蔽、含蓄、肉感,主观低调淡出,精确的全知视角,自抑和克制。杂文需要的是出刀,更骨感,更有观点和火药味。伊简直是文学界的小龙女,周伯通练了一辈子的左右互搏术,人家天生就会。 我前两天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还有去年冬天看张爱玲的《异乡记》。让我深思的是,一个人,他作为小说家的状态和生活底色的比重。老陀当时是被判死刑的,张爱玲去探胡兰成,也正逢战时,兵荒马乱,满地乱孚,应该是心思忐忑,难以聚神才对。而他们的注意力,是马力全开的,不放过一点点残渣。甚至三十年后的《小团圆》里,都楚楚如在目下——她的最爱,她的伴侣,不是胡兰成而是小说。她就是作为一个小说家而活着的,其他的一切,都是补给。她舅舅家的故事被她写成《花凋》。《金锁记》里是她父系的丑事,甚至名字都没换。《易经》《雷峰塔》则干脆把早期小说里的边角料:仆佣、下人,也给血肉丰满扩充写了。小说人格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人的兴趣,而不是急着判断说理,重叙事,更关注事件的质感,喜欢慢慢地体味。评论人格喜欢指点江山,发表意见。这两者没有绝对的分野,只是比重和偏向。 有些人又以评论胜出,私以为鲁迅就是。他的杂文比小说好,刀锋凌厉,气势十足,又多产。韩寒也是,眼睛亮,戾气重,快意恩仇,这种性格,自是杂文最便利。又比如西班牙的蒙特罗,她的《女性小传》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文字。有些人又以评论胜出,私以为鲁迅就是。他的杂文比小说好,刀锋凌厉,气势十足,又多产。韩寒也是,眼睛亮,戾气重,快意恩仇,这种性格,自是杂文最便利
评分这种双面品格的背后则是:知识背景十分复杂,其知识理路的厘清对我是困难的。但还是应当注意到,对于本书来讲,若关涉到方法论,则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该文本之基础的田野调查的方法,这在第四编中有所反思,进一步展示了学者与法律实践者在知识生产关系中的复杂情势,说明了有利于法学知识之生产的结构处于溜流变、不稳定当中);二是作为本著作被写作的方法,即作者构建文本的理论依据。这虽也有所交代,但这种交代十分笼统。考虑到苏力自己所说的,他对西方学术“流露出一种不屑一顾”,只是“利用了驳杂的来自西方的学术理论”来开掘“中国可能开拓的处女地”,我们不得不感到不塌实。例如,尽管强调他所使用的“地方性知识”是受吉尔兹启发的,但与之不同,然而,他实际上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了“知识”这一概念。一种是被强调区别于吉尔兹的、“是交流不经济并因此不一定值得批量文本化的知识”,这实际上离开了文化解释的进路,几近于或就等同于哈耶克的经验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工论(知识的弥散性),在此,“知识”等于“信息”;而另一种则是可交流的、在初步被文本化的知识。这种区分既未被指明,也未被坚持。更重要的是,这种区分的不被指明还隐含了这样的矛盾:如果苏力使用的“知识”一直是第一种意义上的,那么,关于知识的地方性与普遍性的辩解就是多余的。因为,当知识等于信息时,它就可能与这一问题无关。如此,则“知识的地方性”便不足以成为使任何知识具有被理论所重视的正当性之前提。这种“不屑一顾”的做法是否与苏力的建设性方案能够调和呢?仅仅解决知识与其生产机制的关系问题,还不足以使人疑云尽释。并没有试图探询知识在离开其产地之后与其受众的关系。但在另一种方式上,苏力表达了他的情绪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构建了一个“概念法学”作为其批评的对象,尽管这个对象并不明确。对它的最大批评显然是认为它颠倒了知识生产的结构,它欲图以“逻辑的生活替代生活的逻辑”,其实质则是“思想和实践的贫困”。虽然如此,且流露出的感情也极强烈,但是,我们却决不能认为,当法律社会学提交了一份厚重的“作业”时,就自然构成了对概念法学的颠覆。概念法学有它存在的基础,这种基础可能同样是制度性的(德国在这方面享有世界声誉)。它的产生同样是在某种制约结构之中。激情陷于无思之境。,概念法学还有其建设意义。社会学研究离开概念工具也将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到韦伯曾经提醒人们注意在社会学上的“法律”乃与法学上的“法律”不同,那么我们就应该具有更开阔的视界,这种视界既不囿于概念的分析,也不囿于法社会学。也许,把理解成是对中国法学面对中国之不平衡的、有断层的社会现实的不够自觉的批评,更富有启发与警醒意义。正是在对理论的追求与对理论的“不屑一顾”之间的紧张关系上,我们体味到苏力的矛盾心情,但确实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颇具现代性的农村基层司法。这其中,既有科学的冷静,又有“韦伯式”的忧郁。“你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当你听见了第一步空寥的回声。”
评分物流不想吐槽了,慢出新境界
评分很喜欢。
评分好书,但纸张很粗糙
评分意识到“中国的法治不大可能主要依据这套知识来完成”,但是这种知识与其产生机制的关系则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故而,一面勾勒出司法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另一面则试图构建法学知识的生产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欲使法学界从被外来理论支配的地位之下挣脱出来,重新构建法学家与法律实践的知识上的支配关系,改变那种把用舶来品统治中国法学家的结构移置到中国法学家与法律实践者的关系上去的做法。我们也许能够体味到,把将法学家从知识禁锢中“解放”出来这一点作为解决法学知识生产机制本末倒置问题的关键、这一学者的自觉里有多少讽刺的以为和无可奈何。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汪伪政权史话 [A Brief History of the Wang Jinwei Puppet Regim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704420/fa742644-c58c-4ccb-a2fe-21f676ab5d1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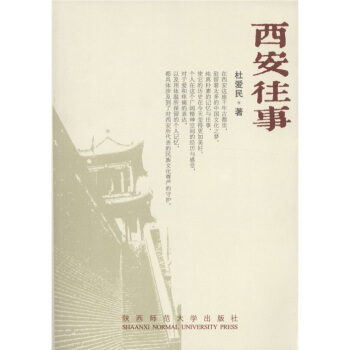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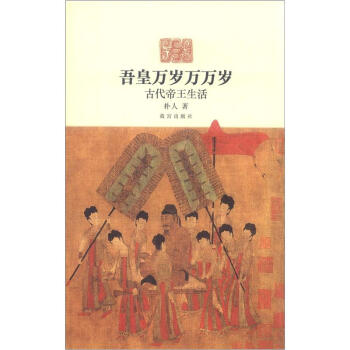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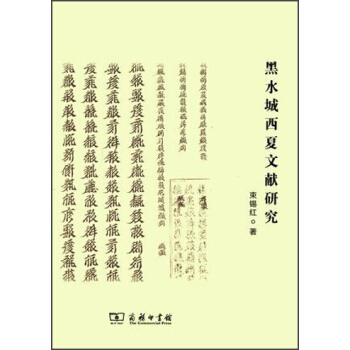
![大象学术译丛:希腊文明中的亚洲因素 [Asianic Elements in Greek Civilisa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79881/547e85b1N63069bd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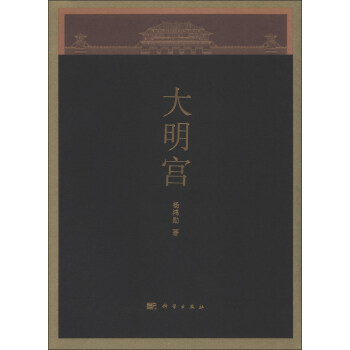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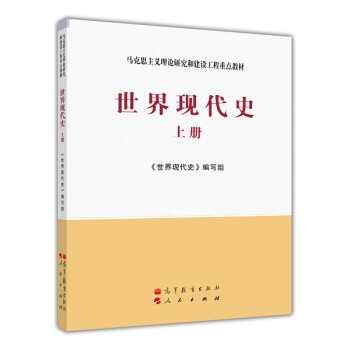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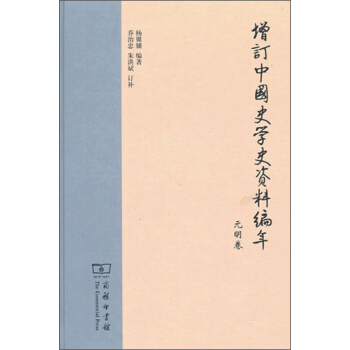
![大明帝国:洪武帝卷(套装上中下册) [The Great Ming Empire I Peculiar Founding Emperor Zhu Yuanzhang(Volume 1)]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04065/rBEhVlMKu84IAAAAAAMQD1ZkLeQAAJETAEythcAAxAn95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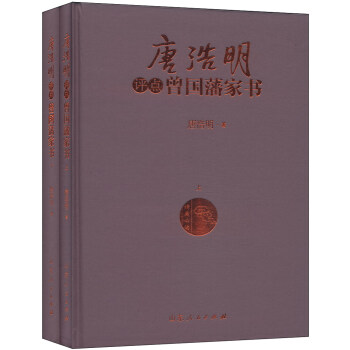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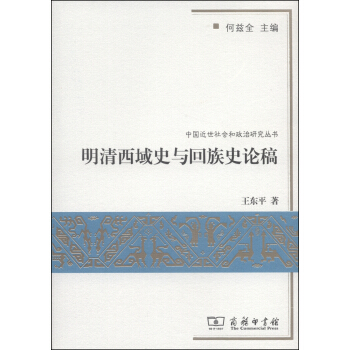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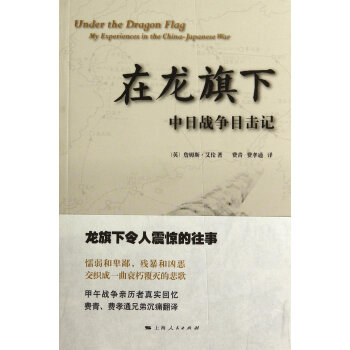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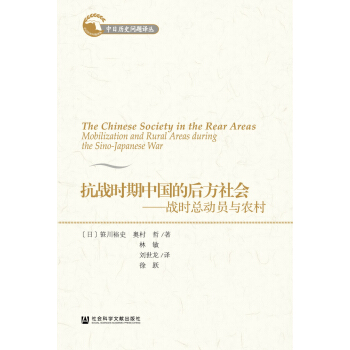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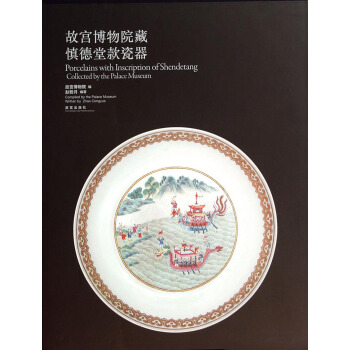


![第三帝国:巴巴罗萨(修订本) [The Third Reich:Barbaross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49811/54d48a8bN22c8c21c.jpg)
![第三帝国:权力的中心(修订本) [The Third Reich: the Center of the Web]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49817/54d48a8bN8706aec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