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修订版)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156072/rBEGF1DtLu8IAAAAAAJgwmxPD5oAABRGwEuv30AAmDa205.jpg)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修订版)》主要内容包括:学科与实践:作为地点、方法和场所的人类学“田野”、“田野科学”之谱系、原型的含义、非正统与霸权:“田野”和“田野调查”的选择性传统、重新解读“田野”:方法论与地点、伊丝梅尔之后:田野调查传统及其未来、定位过去、新闻与文化:瞬间现象与田野传统、美国协会的非洲研究、北美社会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兴起与衰落、人类学和对科学的文化研究:从城堡到木偶人、你不能乘地铁去田野:地球村的“村落认识论”、虚拟人类学家、广泛的实践:田野、旅行与人类学训练等。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在它自认为对于田野概念的恰当的分解和聚合过程中,它是成功的、引人人胜的,在社会科学中间长时期的民族志标准中……它对我们关于目前和将来人类学的方法和文化战略的发展形成挑战。对于任何一个真诚关心民族学和它的继承者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必读的。——约翰·柯莫诺失,芝加哥大学
对人类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批评是直接的、尖锐的,这本书的调子仍然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或者说是破坏建设性的。
——约翰·文森特,巴纳德大学
通过他们对过去和现在的田野思想的深刻的和有刺激性的审查,这本书的贡献之处在于它指出了人类学作为一个概念和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学科努力的方向。我们通常将在争论下一步应该如何的时候参考《人类学定位》这本书。
——乌尔夫·汉纳兹,跨国关系研究写作者
古塔和弗格森这本及时而重要的编著应该被广泛阅读和鉴赏。
——切利·奥特纳,哥伦比亚大学
目录
第一章 学科与实践:作为地点、方法和场所的人类学“田野”一、引言
二、“田野科学”之谱系
三、原型的含义
四、非正统与霸权:“田野”和“田野调查”的选择性传统
五、重新解读“田野”:方法论与地点
第二章 伊丝梅尔之后:田野调查传统及其未来
第三章 定位过去
一、有关人类学的历史
二、田野的概貌
三、置换人类学
……
第四章 新闻与文化:瞬间现象与田野传统
第五章 美国协会的非洲研究
第六章 北美社会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兴起与衰落
第七章 人类学和对科学的文化研究:从城堡到木偶人
第八章 你不能乘地铁去田野:地球村的“村落认识论”
第九章 虚拟人类学家
第十章 广泛的实践:田野、旅行与人类学训练
参考文献
撰稿人介绍
精彩书摘
浓缩于人类学课程中的理论主题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塔式分布顺序还体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概念。尽管很多人认为布朗的社会结构功能主义最终战胜并取代了马林诺夫斯基的个体和生物功能主义,但是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的北美人类学界马林诺夫斯基是胜出者。当布朗待在芝加哥时,他成功地以结构功能主义思想同博厄斯的文化人类学分庭抗礼。后者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从事“文化与人格”研究。但是当我在20世纪50年代末接触美国社会文化人类学时,布朗对社会结构的需要的强调已经被对个体和生物性的人的需要的假设所取代。所有核心理论探讨的都是个体需要被满足的各种方式。心理人类学关注不同育儿方式的过程和结果,它基于一个明确的假设,那就是:所有的儿童都需要被喂养,需要接受生活技能的训练,需要学习劳动本领。主流观点认为亲属研究的是组织结伴和婚配的不同方式,其理论前设为所有的孩子都需要社会认可的父亲。经济人类学研究生存所需要物品的生产和分配。政治人类学基于霍布斯哲学假设,即竞争性的人类需要妥协来避免彼此间的战争。原始宗教的主流则体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即信仰减缓了人们对不确定世界的焦虑感。
对于在美国马林诺夫斯基的个体功能主又为何战胜了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我至少能得出两个原因:第一无疑是政治气候,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冷战,进化论被视同为马克思主义,进化论的拥护者遭到了迅速的挫败甚至迫害。尽管拉德克利夫-布朗既非进化论者也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功能主义的结构观点使得他走入了社会的类型学,这很容易被视为进化主义的进步观(例如福蒂斯和Pritchard在非洲政治体系中提出的政治结构)。尽管拉德克利夫一布朗认同马林诺夫斯基的“社会学的任务在于系统地探究社会制度的本质”,但是他认为这种制度不能离开他们功能性所维持的社会结构而被理解。因而,社会结构必须被分类。他认为我们不能指望通过主观观察直接达到一般性社会学法则或学科的知识,人类社会的复杂多样性必须首先通过某种分类而被简化(1940:xi)。
……
前言/序言
“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经过修订和大家见面了,这套教材是由王铭铭教授策划的,包括国际人类学界在世纪之交前后出版的五种著作,作者也都是蜚声国际的人类学家。考虑到作为一套丛书,这五本书也是各有侧重。从基本概念、人类学概论、学科发展史和理论史到田野工作方法,覆盖了作为文化人类学基础的几个主要部分。然而,选人这套丛书的这些著作又不是简单的教材。如《人类学: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理论实践》一书,是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编写的,领衔作者迈克尔·赫茨菲尔德是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著名教授,没有像通常的《文化人类学概论》那样四平八稳地展开教科书式的讨论,而是用一种反思“常识”的眼光来展开思辨性的讨论。其他几种作品也是可以用作教材但又高于教材之作。这套丛书出版之后,以学术著作难有的速度很快售罄。我们在这一次修订中,将过去改译书名的两本书重新订正,回归本来面目。学术史是学术研究和训练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人类学家的成长道路中,可能会有不同的途径。有些人可以先搜集和积累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或者说对生活的详细观察有所收获,开始觉得有研究的必要,需要解释这些材料。于是乎通过阅读和请教,学习人类学理论,了解不同学派的观点,熟悉不同的理论分析和解释路径,再加上用人类学田野工作和比较研究技术不断改进自己的研究方法,从而成为人类学家;另外一些人,在已经学术制度化的今天主要是从院校中培养出来的。在大学课堂中学习相关的课程,阅读人类学经典著作,听各路名家的讲座,然后再去进行田野工作,进行田野民族志写作,最终完成从学生到人类学家的历程。
……
用户评价
阅读体验上,这本书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略显颠覆性的思想漫游。它挑战了我过去对于人类学“应该是什么样”的预设,尤其是在探讨“田野科学”的边界问题时,作者展现出的那种毫不留情的批判精神,让人不得不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熟悉的那些方法论。这本书的结构安排很巧妙,它并非线性地推进论点,而是在不同议题之间进行跳跃式的对话,仿佛是在邀请读者参与一场复杂的智力博弈。其中关于“知识的地域性”的论述,尤其触动了我。它强调了理论并非是普世的、可以随意移植的“工具箱”,而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之中。这种对“地方性知识”与“全球性理论”之间张力的剖析,对于当前国内正在进行的本土化人类学建构的讨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批判性的参照系。坦白说,初读时需要较大的专注力来消化其中复杂的逻辑链条,但一旦进入状态,那种被学术前沿不断推着走的兴奋感是难以替代的。
评分从阅读的“手感”和内容的“密度”来看,这是一部需要反复品味的经典之作。它不是那种读完一遍就能声称“理解了”的快餐式理论读物,更像是一部理论的“矿藏”,每一次重读都会挖掘出新的矿脉。书中对于“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自我诘问,构成了全书的内在驱动力。作者并没有回避人类学在历史上的殖民主义遗产,而是将其作为重新定位自身使命的出发点。这种诚实的、近乎苛刻的自我审视,反而赋予了这部作品强大的伦理力量。它教导我们,真正的田野工作,不仅是对他者文化的深入体验,更是对自己文化预设的无情解构。我特别欣赏作者处理复杂议题时所展现出的克制与精准,没有浮夸的辞藻堆砌,每一句话似乎都承载着沉甸甸的理论重量,这使得整本书读起来既烧脑,又极具满足感。
评分这部译作的价值,在于它成功地架设了一座桥梁,连接了欧美人类学界最前沿的理论争论与国内学者的知识谱系。它提供的不仅仅是理论工具,更是一种研究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体现在对“边界”的持续质疑上——学科的边界、知识的边界、田野的边界。书中对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地理学甚至政治学)的交叉地带的描绘,清晰地展现了当代学术的融合趋势。它提醒我们,固守纯粹的“人类学”学科壁垒已经不再是明智之举。作者对于“科学”二字所抱持的审慎态度,也值得我们深思:如何在一门充满主观性和解释性的学科中,建立起可被信任的、站得住脚的知识基础?这本书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最终答案,但它所提供的分析框架,无疑是探讨这一核心问题的最佳起点之一。它要求读者跳出舒适区,去拥抱理论的不确定性与研究实践的复杂性。
评分这部新译本的出版,无疑为国内人类学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份及时且极具价值的参考资料。我个人在阅读了前几章后,立刻感受到了其文本的厚重感和理论的穿透力。它不仅仅是对既有学科范式的简单梳理,更像是一次深刻的“自我反思”式的对话。书中对人类学实践中那些潜藏的、往往被忽略的伦理困境和知识生产机制的剖析,令人耳目一新。作者似乎非常擅长于在宏大的理论框架下,精准地捕捉到那些细微的、发生在田野现场的权力运作痕迹。例如,对于“观察者效应”的讨论,书中没有停留在教科书式的描述,而是深入挖掘了研究者自身的社会位置如何不可避免地塑造了他们所“看见”的现实,这种对研究主体性的审视,对于提升我们自身研究的自觉性至关重要。再者,从语言的层面看,译者团队的努力也值得称赞,他们成功地将原本可能晦涩难懂的学术概念,转化为流畅且富有张力的中文表达,使得即便初次接触此类前沿理论的读者,也能比较顺畅地跟上作者的思路,避免了许多译著中常见的佶屈聱牙感。总而言之,它提供了一个审视人类学这门学科“根基”的全新视角,远超一般教材的范畴。
评分这本书的出版,对于那些正处于学术生涯关键路口的年轻学者而言,简直是醍醐灌顶般的存在。它没有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抛出了更多、更深刻的问题,迫使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被主流叙事所边缘化的领域。我对其中关于“技术与身体的交织体”的讨论印象尤为深刻,它超越了传统人类学对“文化”的界定,将目光投向了日益数字化的现代生活图景。作者似乎在暗示,人类学的未来必须学会如何与那些非人类能动者进行有效的对话,而不仅仅是聚焦于传统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跨学科的视野,融合了技术哲学和社会学的深刻见解,使得全书的论证充满了动态的生命力。它不再满足于描述“他者”,而是更专注于描绘“我们自身”在变动的世界中如何成为被理解的对象。那些希望突破传统人类学框架,探索人类学与其他科学如何真正发生实质性对话的同仁们,这本书不容错过。
评分20世纪以来,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开始分离,同时许多人类学家开始转向所谓「文化多元论」观点,并出现许多流派。与人类学同时诞生。 开创了对文化的科学研究,摩尔根,泰勒,巴斯蒂安等提出了文化,社会进化的时间序列,着重文化的纵向发展,也成为进化学派的创始人。18世纪孟德斯鸠等的启蒙思想,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以<<物种起源>>为标志的生物进化学说,18及19世纪的社会进化观等,都是19世纪人类学进化学派的文化,社会进化思想产生的基础。理论进化学派以进化的思想研究人类社会及其文化,认为人类同源,本质一致,有共同心理,因此产生同样的文化,社会发展有共同的途径,由低级向高级进化。泰勒被称为人类学之父,他在<<原始文化>>中提出文化是进化的。摩尔根在<<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中在研究婚姻家庭进化的基础上,建构家庭的发展历史,初步提出了社会进化的问题。在<<古代社会>>进一步全面地发展了社会进化思想,论证了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包亚士首先摒弃了那种选择事实,附会于抽象的进化理论的研究方法,注重实地研究并倾向于所谓功能观点,坚持对任何一种文化进行整体性的考察。他是文化历史学派的主要人物,这个学派在美国文化人类学领域占统治地位。法国社会学派莫斯(Marcel Mauss)和「社会学」学派 一般来说,莫斯和包亚士一样,主张系统地研究社会现象,但方式略有不同。他指出社会是「自我调节」并趋于均衡的系统,系统各要素的作用是保持系统的整合与适应。他启发了後来的功能主义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欧洲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是功能派的代表人物。这派认为,解释人类学事实的唯一途径是说明它在一定文化中正在发挥的功能,因此人类学研究的目标是把握文化整体与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历史的比较方法意义不大。相反,拉德克利夫-布朗(A.R. Radcliffe-Brown)是结构主义的倡导者。这派认为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在於揭示超乎经验事实的系统的本质。文化心理学这派的基本思想是文化决定每个个人的心理构成,反对普遍精神或人类本质的概念。例如潘乃德(Ruth Benedict)在美国西南部研究中发现,印第安人的思维方式或推理方式与其邻近人种完全不同,因此文化决定心理趋向。如今,文化与个性的研究更加广泛,例如对价值体系和民族性格的研究。文化唯物论(Cutural materialism) 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Marvin Harris,1927,)在1979年出版的《文化唯物论》,书中提出文化唯物论的思想。其理论强调生殖的或人口的压力及生态压力对社会文化系统的决定作用。哈里斯认为,人性的生物心理的基本需要(如食物、性、情感等)导致了四种普遍的人类组织层次。文化唯物论》一书也称为是“哈里斯所写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文化人类学还是一门年轻的科学,还没有构成完全一致的理论体系。但是如果人类学家能够避免种族中心主义,并创造出普遍客观化的概念,关於文化的「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评分虽然“最先占有者的权利”要比“最强者的权利”更加真实,但是它也只有在所有权确立之后才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利。任何一个人对于他所需要的东西都拥有天然的权利,但是使一个人成为某种财产的所有者这种积极的行为,就排除了他对于其他的所有东西的所有权。他的那一份一旦被确定,他就必须把自己局限于此,而且他不能再向共同体要求更多的权利。这样,我们便看到了在自然状态下非常脆弱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在政治社会中是如何得到所有人的尊重的。这种权利使我们看清楚的,与其说是哪些东西是别人的,不如说是哪些东西不是我们的。 一般来说,要确定对于任何一块土地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以下所列的条件是必须具备的:第一,这块土地还不曾被任何人居住过;第二,他要求占有的数量不应该超过他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数量;第三,他获得占有权,不是通过一种空洞的形式,而是通过在这块土地上实际地劳动和耕作,这是在缺乏合法名义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其他人尊重的所有权的唯一标志。 可以说,根据需要和劳动赋予“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实际上已经把这种权利扩展到了它所可能达到的最大极限了。人们不应该为这种权利设定一个界限吗?虽然“最先占有者的权利”要比“最强者的权利”更加真实,但是它也只有在所有权确立之后才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利。任何一个人对于他所需要的东西都拥有天然的权利,但是使一个人成为某种财产的所有者这种积极的行为,就排除了他对于其他的所有东西的所有权。他的那一份一旦被确定,他就必须把自己局限于此,而且他不能再向共同体要求更多的权利。这样,我们便看到了在自然状态下非常脆弱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在政治社会中是如何得到所有人的尊重的。这种权利使我们看清楚的,与其说是哪些东西是别人的,不如说是哪些东西不是我们的。 一般来说,要确定对于任何一块土地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以下所列的条件是必须具备的:第一,这块土地还不曾被任何人居住过;第二,他要求占有的数量不应该超过他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数量;第三,他获得占有权,不是通过一种空洞的形式,而是通过在这块土地上实际地劳动和耕作,这是在缺乏合法名义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其他人尊重的所有权的唯一标志。 可以说,根据需要和劳动赋予“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实际上已经把这种权利扩展到了它所可能达到的最大极限了。人们不应该为这种权利设定一个界限吗?虽然“最先占有者的权利”要比“最强者的权利”更加真实,但是它也只有在所有权确立之后才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利。任何一个人对于他所需要的东西都拥有天然的权利,但是使一个人成为某种财产的所有者这种积极的行为,就排除了他对于其他的所有东西的所有权。他的那一份一旦被确定,他就必须把自己局限于此,而且他不能再向共同体要求更多的权利。这样,我们便看到了在自然状态下非常脆弱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在政治社会中是如何得到所有人的尊重的。这种权利使我们看清楚的,与其说是哪些东西是别人的,不如说是哪些东西不是我们的。 一般来说,要确定对于任何一块土地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以下所列的条件是必须具备的:第一,这块土地还不曾被任何人居住过;第二,他要求占有的数量不应该超过他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数量;第三,他获得占有权,不是通过一种空洞的形式,而是通过在这块土地上实际地劳动和耕作,这是在缺乏合法名义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其他人尊重的所有权的唯一标志。 可以说,根据需要和劳动赋予“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实际上已经把这种权利扩展到了它所可能达到的最大极限了。人们不应该为这种权利设定一个界限吗?虽然“最先占有者的权利”要比“最强者的权利”更加真实,但是它也只有在所有权确立之后才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利。任何一个人对于他所需要的东西都拥有天然的权利,但是使一个人成为某种财产的所有者这种积极的行为,就排除了他对于其他的所有东西的所有权。他的那一份一旦被确定,他就必须把自己局限于此,而且他不能再向共同体要求更多的权利。这样,我们便看到了在自然状态下非常脆弱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在政治社会中是如何得到所有人的尊重的。这种权利使我们看清楚的,与其说是哪些东西是别人的,不如说是哪些东西不是我们的。
评分不错,好书
评分[ZZ]写的很好,书本质量不错 内容很精彩 快递很给力 任做新东方的这么多年里,我对自己提出了七句话,作为自己做事情的原则和指导,这七句话是:用理想和信念来支撑自己的精神:用平和与宽容来看待周围的人事:用知识和技能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用理性和判断来避免人生的危机;用主动和关怀来赢得别人的友爱;用激情和毅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用严厉和冷酷来改正自己的缺点。 《新东方·六级词汇词根 联想记忆法(乱序版)》特点:“词根 联想”记忆法--实用有趣,巩固记忆,“乱序”编排--打破常规字母顺序,“真题例句”--仿真环境应用,直观了解考查要点,辨析 “图解记忆”--形象生动,千言万语尽在一图中,“词源”--从起源透析单词释义的演变,加深理解,“模拟练习”--助你真正做到学以致用,500分钟标准美音MP3光盘(支持字幕播放)--标准单,词发音、释义以及例句,配合学习,效果加倍。 任做新东方的这么多年里,我对自己提出了七句话,作为自己做事情的原则和指导,这七句话是:用理想和信念来支撑自己的精神:用平和与宽容来看待周围的人事:用知识和技能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用理性和判断来避免人生的危机;用主动和关怀来赢得别人的友爱;用激情和毅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用严厉和冷酷来改正自己的缺点。 《新东方·六级词汇词根 联想记忆法(乱序版)》特点:“词根 联想”记忆法--实用有趣,巩固记忆,“乱序”编排--打破常规字母顺序,“真题例句”--仿真环境应用,直观了解考查要点,辨析 “图解记忆”--形象生动,千言万语尽在一图中,“词源”--从起源透析单词释义的演变,加深理解,“模拟练习”--助你真正做到学以致用,500分钟标准美音MP3光盘(支持字幕播放)--标准单,词发音、释义以及例句,配合学习,效果加倍。 任做新东方的这么多年里,我对自己提出了七句话,作为自己做事情的原则和指导,这七句话是:用理想和信念来支撑自己的精神:用平和与宽容来看待周围的人事:用知识和技能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用理性和判断来避免人生的危机;用主动和关怀来赢得别人的友爱;用激情和毅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用严厉和冷酷来改正自己的缺点。 《新东方·六级词汇词根 联想记忆法(乱序版)》特点:“词根 联想”记忆法--实用有趣,巩固记忆,“乱序”编排--打破常规字母顺序,“真题例句”--仿真环境应用,直观了解考查要点,辨析 “图解记忆”--形象生动,千言万语尽在一图中,“词源”--从起源透析单词释义的演变,加深理解,“模拟练习”--助你真正做到学以致用,500分钟标准美音MP3光盘(支持字幕播放)--标准单,词发音、释义以及例句,配合学习,效果加倍。 任做新东方的这么多年里,我对自己提出了七句话,作为自己做事情的原则和指导,这七句话是:用理想和信念来支撑自己的精神:用平和与宽容来看待周围的人事:用知识和技能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用理性和判断来避免人生的危机;用主动和关怀来赢得别人的友爱;用激情和毅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用严厉和冷酷来改正自己的缺点。 《新东方·六级词汇词根 联想记忆法(乱序版)》特点:“词根 联想”记忆法--实用有趣,巩固记忆,“乱序”编排--打破常规字母顺序,“真题例句”--仿真环境应用,直观了解考查要点,辨析 “图解记忆”--形象生动,千言万语尽在一图中,“词源”--从起源透析单词释义的演变,加深理解,“模拟练习”--助你真正做到学以致用,500分钟标准美音MP3光盘(支持字幕播放)--标准单,词发音、释义以及例句,配合学习,效果加倍。
评分非常喜欢
评分想到是这么精彩的一本书。我花了两天来读,真让人手不释卷。看到梵高自尽,酸楚的泪水也汨汨而出。尽管我非常爱他,但是我依然不知道,他是那么的纯洁,伟大。世人对他的误解至深,伤害至深。而且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出身于那样的阶层,可以说他是另一个“月亮与六便士”的主角。如果沿着他既有的人生轨迹走下去,他未尝不可以像他的弟弟一样,做一个体面的画商。 他生来便是要做艺术家的。他的生活里容不下虚伪,无情。他是那么的炽热,坦白,他爱的那样赤诚,毫无保留。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在画,因此,当他不能再创作,他的生命便也没有了太大的意义。像大多数天才一样,他奉献给世界的,是不分阶层的博爱和用生命画出的瑰宝;而世界回应他的,却是无尽的挫折,饥饿,疾病,困顿,误解,侮辱,伤害。。。 我几乎可以说,他是属于“人民”的。他始终关怀着世上受着疾苦的大众,他从来没有等级的观念。他描绘农民,工人,最普通的劳动者,“吃土豆的人”。他的播种者的脚步,是那样的坚定有力,大步的在璀璨的麦田里迈步。 而且,他也是非常“精神”的。他的生活里有京东,但是他并不是和别的画家一样,纯粹到京东那里找乐子,满足肉欲。他尊重她们,甚至愿意娶一个年老色衰的京东为妻。讽刺的是,他有那么多的爱,却无法得到世人的回应,给了他些许温情的,竟然是那个被世人同样唾弃的女子。他的有些举动,的确是神圣的,悲悯的,难怪他被矿山上的人称为“基督在世”。在那里,人们不会觉得他疯狂,因为他们知道他爱他们,他为了能让他们好过一点,已经奉献了几乎所有能够奉献的。 让人感动的,是他和提奥之前的兄弟之情。没有提奥的资助和理解,也就不可能有他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兄弟两人就是一体的。没有提奥在背景里默默做着根系,就不可能有他盛放的艺术之花。提奥无条件的支持他,几乎从来没有拒绝过他的请求,总在关键时刻赶到他的身边,为他偿还负债,把他从贫病之中拯救回来。他们之间频繁的通信,已经让这两个灵魂紧紧的结合在了一起。提奥虽然在巴黎过着体面的画商的生活,却无时不刻的关注着他的进展和动态。他在心灵上所有的跌宕起伏,都通过书信让提奥感同身受。是提奥早早看出他身上埋藏的巨大潜力,是提奥细心珍藏了那700多封通信,是提奥把他的习作和画作按时间小心的编排好。所以后人得以完整的追溯梵高的心路历程,能够离这个伟大的灵魂更近一些。生前,只卖出了一副画,价值四百法郎。但我不能说他是不幸的。比起世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做到了极致。即使他后来长寿,能看到自己的画作价钱越来越高,我想,他也会是漠不关心的。他从未因为市场的口味而作画,他也从未为那些脑满肠肥的人作画。虽然,卖画这件事一直在困扰着他,但他的祈求也不过是卖出的画,能够让他自立,不必依赖提奥的资助而生活。对他来说,创造是最重要的。如果什么都不能说,那么他宁肯沉默。如果不能够再创作,那么他宁肯死亡。 我之前不知道的是,他的父母两家都有不少出众的亲戚,他的姓氏在当时荷兰的艺术界鼎鼎有名。可以说他父母这一支是相对比较平淡的。然而,今日只有文森特让梵高这个名字不朽。就像书中说的,他活着,他的爱,他的才华,透过那些灿然的画活着。不管这些画今天值多少钱,它们终究不是某个人的私藏,而能被我这样的普罗大众看到。他的精神,他的爱,他的热望透过那些画震撼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他淋漓尽致的来过这个世界,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熊熊燃烧过。他终于成就了自己,也为这个世界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
评分想到是这么精彩的一本书。我花了两天来读,真让人手不释卷。看到梵高自尽,酸楚的泪水也汨汨而出。尽管我非常爱他,但是我依然不知道,他是那么的纯洁,伟大。世人对他的误解至深,伤害至深。而且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出身于那样的阶层,可以说他是另一个“月亮与六便士”的主角。如果沿着他既有的人生轨迹走下去,他未尝不可以像他的弟弟一样,做一个体面的画商。 他生来便是要做艺术家的。他的生活里容不下虚伪,无情。他是那么的炽热,坦白,他爱的那样赤诚,毫无保留。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在画,因此,当他不能再创作,他的生命便也没有了太大的意义。像大多数天才一样,他奉献给世界的,是不分阶层的博爱和用生命画出的瑰宝;而世界回应他的,却是无尽的挫折,饥饿,疾病,困顿,误解,侮辱,伤害。。。 我几乎可以说,他是属于“人民”的。他始终关怀着世上受着疾苦的大众,他从来没有等级的观念。他描绘农民,工人,最普通的劳动者,“吃土豆的人”。他的播种者的脚步,是那样的坚定有力,大步的在璀璨的麦田里迈步。 而且,他也是非常“精神”的。他的生活里有京东,但是他并不是和别的画家一样,纯粹到京东那里找乐子,满足肉欲。他尊重她们,甚至愿意娶一个年老色衰的京东为妻。讽刺的是,他有那么多的爱,却无法得到世人的回应,给了他些许温情的,竟然是那个被世人同样唾弃的女子。他的有些举动,的确是神圣的,悲悯的,难怪他被矿山上的人称为“基督在世”。在那里,人们不会觉得他疯狂,因为他们知道他爱他们,他为了能让他们好过一点,已经奉献了几乎所有能够奉献的。 让人感动的,是他和提奥之前的兄弟之情。没有提奥的资助和理解,也就不可能有他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兄弟两人就是一体的。没有提奥在背景里默默做着根系,就不可能有他盛放的艺术之花。提奥无条件的支持他,几乎从来没有拒绝过他的请求,总在关键时刻赶到他的身边,为他偿还负债,把他从贫病之中拯救回来。他们之间频繁的通信,已经让这两个灵魂紧紧的结合在了一起。提奥虽然在巴黎过着体面的画商的生活,却无时不刻的关注着他的进展和动态。他在心灵上所有的跌宕起伏,都通过书信让提奥感同身受。是提奥早早看出他身上埋藏的巨大潜力,是提奥细心珍藏了那700多封通信,是提奥把他的习作和画作按时间小心的编排好。所以后人得以完整的追溯梵高的心路历程,能够离这个伟大的灵魂更近一些。生前,只卖出了一副画,价值四百法郎。但我不能说他是不幸的。比起世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做到了极致。即使他后来长寿,能看到自己的画作价钱越来越高,我想,他也会是漠不关心的。他从未因为市场的口味而作画,他也从未为那些脑满肠肥的人作画。虽然,卖画这件事一直在困扰着他,但他的祈求也不过是卖出的画,能够让他自立,不必依赖提奥的资助而生活。对他来说,创造是最重要的。如果什么都不能说,那么他宁肯沉默。如果不能够再创作,那么他宁肯死亡。 我之前不知道的是,他的父母两家都有不少出众的亲戚,他的姓氏在当时荷兰的艺术界鼎鼎有名。可以说他父母这一支是相对比较平淡的。然而,今日只有文森特让梵高这个名字不朽。就像书中说的,他活着,他的爱,他的才华,透过那些灿然的画活着。不管这些画今天值多少钱,它们终究不是某个人的私藏,而能被我这样的普罗大众看到。他的精神,他的爱,他的热望透过那些画震撼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他淋漓尽致的来过这个世界,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熊熊燃烧过。他终于成就了自己,也为这个世界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
评分非常喜欢
评分跟他讲了安排到今天发货,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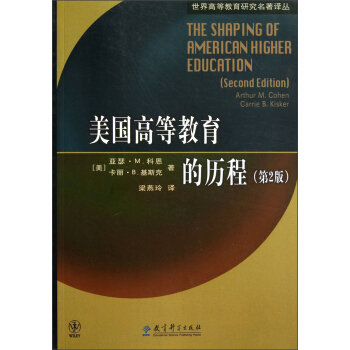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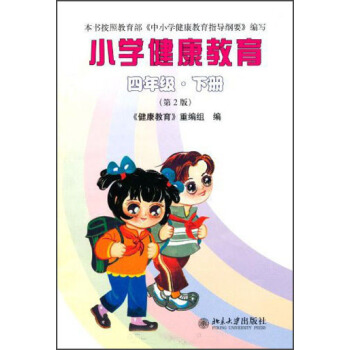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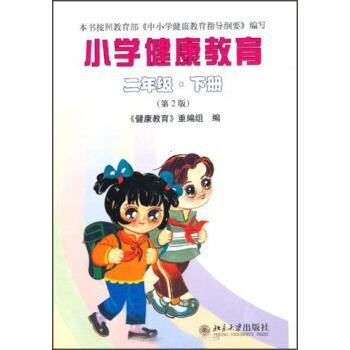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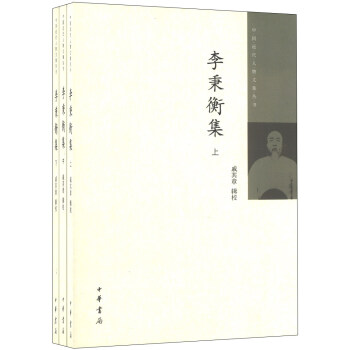
![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3):资料分析 [Reseach Methods on Social and Bahavior ScienceⅢ:Data Analysi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97930/rBEhWlIR5HIIAAAAAAHheBCkjxYAACNswJ2Od0AAeGQ514.jpg)
![国际汉语教师培养与培训丛书:国际汉语语法与语法教学 [International Chinese Grammar and Grammar Teaching]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323206/564a82aaN8156103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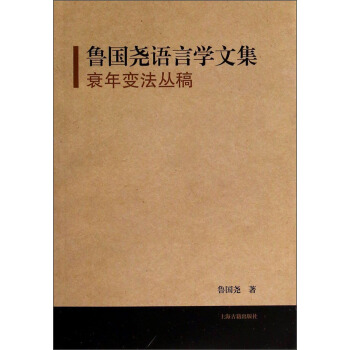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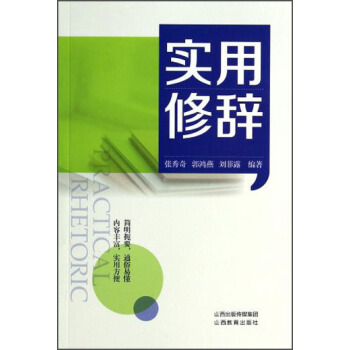
![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语言教育政策:关键问题(第二版) [Language Policies in Education:Critical Issues (Second Edi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54260/5438c1acN98340559.jpg)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学术英语的多维研究视角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65251/544da0c2N1d09b4ea.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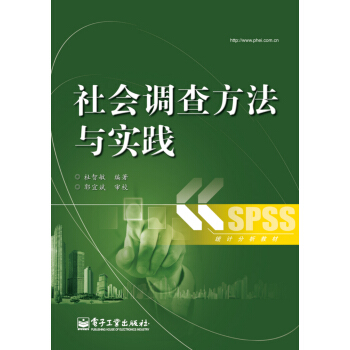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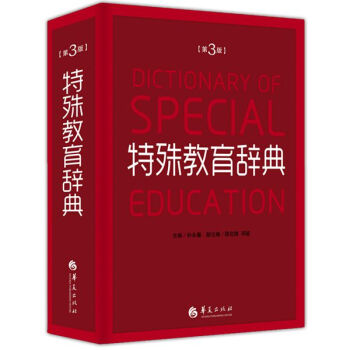

![中国消费文化研究丛书:家庭消费行为的制度嵌入性 [The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of Consumer Behaviors in Urban Chin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85258/5478585bN6ea4a23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