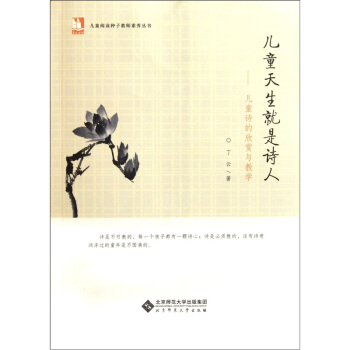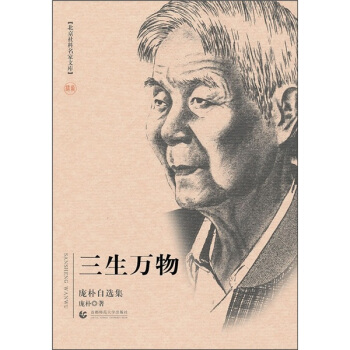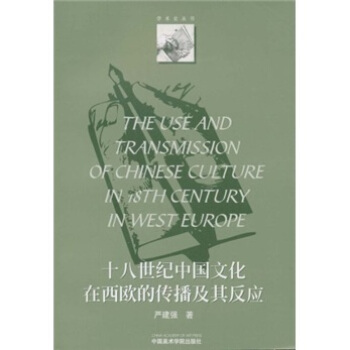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出版专著的数量为此后三十年间著述总数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低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整个20世纪50年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直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才出现复苏的迹象,著述数量逐渐增加。从1974年开始,在法国尚蒂伊多学科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interdisciplinaire de chantilly]每三年召开一次有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中国问题专家参加的国际汉学讨论会,“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是会议的基本议题之一,例如前几次会议的主题都涉及到“17—18世纪中国同欧洲(主要是同法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的交往关系,尤其是中国对它们的影响”,包括“哲学影响”、 “来自中国的艺术和科学”和“礼仪之争”等方面。1其他类似的国际会议也时有举行。目录
绪论上编: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18世纪西欧“中国热”
第一章 中国图像的变迁:从古典时代到新航路开辟1
一、丝绸之路与古典欧洲的中国图像
二、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图像
第二章 大航海以来欧洲对华贸易与中国报道
一、欧洲对华贸易与中国物质文化西传
二、17世纪前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中国报道
三、17、18世纪来自商人和使节的中国报道
第三章 传教士入华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一、适应政策与“中国礼仪之争”
二、法国传教士入华前的汉学研究
三、法国传教士入华后的汉学研究与翻译
第四章 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物热”
一、“中国风”与“罗可可”
二、中国物品与欧洲的装饰艺术
三、绘画与园林
四、“中国戏”与“中国小说”
第五章 中国文化与欧洲启蒙运动
一、作为启蒙运动思想材料的中国文化
二、宗教与哲学
三、政治与法律
四、经济政策与制度
下编:英、法、德三国的中国文化利用——一个以法国为中心的比较研究
第六章 英、法、德“中国热”的不同特征
一、西欧诸国宫廷与中国文化
1.法国宫廷与决策层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2.德国和英国宫廷与“中国热”
二、知识界对中国文化反应的差异性
1.人数与著述
2.范围与特征
三、“中国热”的进程与退潮
1.“早恋的”英国
2.德国的“中国热”及其变化
3.法国:由仰慕到排斥
第七章 西欧诸国“中国热”差异的社会原因分析
一、18世纪西欧诸国的社会性质与特征
1.从封建制度到中央集权国家
2.英国:议会制度与工厂制度的形成
3.法国:农本的专制主义国家
4.德国:四分五裂的封建国家与邦君制度
法、英、德社会状况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利用
1.法国对中国文化利用的取向
2.英国对中国文化利用的取向
3.德国对中国文化利用的取向
4.民族文化品格与文化利用的取向
第八章 法国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及变化319
一、启蒙学者关于中国文化之争的目的与性质
二、法国知识界对中国农业的评价及其与英国的区别
三、法国知识界“由仰慕到排斥”的社会原因分析
结语文化传播与文化利用367
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和上述国家相比,德意志可以说是一个内陆国家,直到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1620—1688]时才获得了临海的巴鲁伽。查理六世[Charles VI,1685—1740]虽热衷海外事业,但因西班牙和荷兰的阻挠难以遂愿。直到1714年,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上才出现了对东方贸易的奥斯廷汀公司。两年后,当飘扬着双头鹫旗的德国船出现在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各国商人大为吃惊,随即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干扰,这些障碍都被奥斯廷汀公司坚持向欧陆供应廉价商品的现实主义政策所克服。然而好景不长,查理六世为修改传统的“帝室继承法”,只得将蒸蒸日上的奥斯廷汀公司作为牺牲品。英、法、荷诸国不仅对该公司附属的特权作了7年限制,而且又于1731年把公司6艘从事东方贸易的船削减到2艘。此后的lO余年间,德国商船绝迹于中国海岸,一直到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II the Great of Prussia,1712~l786]时代“普鲁士国王号”的单头黑鹫旗再度出现在中国海岸。不幸的是腓特烈大帝卷人“七年战争”,无暇顾及远东的贸易,18世纪后半叶德国对华海上贸易再度中断。对华贸易为欧洲带去了品种繁多的中国商品。马尼拉总督的摩加[Antonio de Morga]所列的清单包括:
成捆的生丝、两股的精丝和其他粗丝;绕成一束的优质白丝和各种色丝:大量的天鹅绒,有素色的、有绣着各种人物的、有带颜色的和时髦的,还有用金线刺绣的;织上各种颜色、各种式样的金、银丝的呢绒和花缎;大量绕成束的金银线;锦缎、缎子、塔夫绸和其他各种颜色的布;亚麻布以及不同种类、不同数量的白棉布。他们也带来了麝香、安息香和象牙。许多床上的装饰物、悬挂物、床罩和刺绣的天鹅绒花毯:锦缎和深浅不同的红色花毯;桌布、垫子和地毯;用玻璃珠和小粒珍珠绣成的马饰,珍珠和红宝石,蓝宝石和水晶。金属盆、铜水壶和其他铜锅、铸铁锅。大量各种型号的钉子、铁皮、锡和铅;硝石和黑色火药。他们供给西班牙人小麦粉、橘子酱、桃子、梨子、肉豆蔻、生姜和其他中国水果;腌猪肉和其他腌肉;饲养得很好的活鸭和阉鸡;大量的新鲜水果和各种橘子、栗子、胡桃。大量的各种好的线、针和小摆设、小箱子和写字盒;床、桌、靠背椅和画有许多人物、图案的镀金长凳。他们带来了家用水牛、呆头鹅、马和一些骡和驴:甚至会说话、会唱歌、能变无数戏法的笼鸟。中国人提供了无数不值钱,但很受西班于人珍重的其他小玩意儿和装饰品;各种好的陶器、制服、珠子、宝石、胡椒和其他香料,以及我谈不完也写不完的各种稀罕东西。
在这些销往欧洲的中国商品中,茶、纺织品、瓷器、漆器等,无疑是最受欢迎的。新航路开辟伊始,丝绸就成为各国商人竟相收购的对象。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土利玛窦写道: “葡萄
牙人最乐于装船的大宗商品莫过于中国丝绸了……住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也把中国丝绸装,他们的商船,出口到西班牙和世界的其他地方。”160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指示在印度的商站要特别努力展开对华贸易,以取得大量的生丝和丝织品。首航的考克斯合恩号船就载了570件丝织品返回泰瑟尔。在法国,中国丝绸“像洪水一样涌进巴黎和各省,”以致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丝绸工业。荷兰、法国、瑞典、丹麦等国每年进口的丝绸一般多为数千匹,高的时候可超过2万匹。英国作为一个本土丝绸业发展较晚的国家,对丝绸的需求量很大。1704年“肯特号”所载丝织品占回程货物总值的63%。 1760年前,英国进口的甲国丝绸一般每年l一2万匹,多时可达3万匹。乔杜里[K.N.Chaudhuri]提供的1677年至1760年间的统计数据表明,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丝绸总量近60万匹,年平均进口接近1.5万匹;2中国海关材料显示,l750年经粤海关输往欧洲各国的丝织物,英国为5640件,法国为2530件,荷兰为7460件,瑞典为1790件,丹麦为809件,合计为18329件。3总之,18世纪中叶西方各东印度公司的丝绸年进门总量最多可达75000余匹。这些外销的丝绸有面料也有成品,包括窗帘、床罩和服装等。其样式有国内市场通行的,有适合欧洲市场专门设计而具欧洲风味的,有在装饰风格上体现中西合壁特色的,也有典型的清代装饰图案。
欧洲人真正便用中国瓷器是从达·伽马的航船返回里斯本开始的(图6)。最早从事华瓷贸易的葡萄牙人非常重视这种商品.从1552年的记录来看,瓷器占贸易总额的1/3。他们除了进口一般的中国瓷器外,还定制欧洲样式的瓷器。1602年和1604年荷兰人两度劫掠葡萄牙大帆船,将船上瓷器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此次拍卖使瓷器在欧洲的声望骤升,需求量急速增大,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欧洲的华瓷贸易。我们很难对18世纪中国瓷器销往欧洲的总量给出精确的统计,但可以从某些国家在一段时间内进口的中国瓷器看出贸易规模。据戴维斯[D.w.Davies.]估计,在1604年到1657年的半个世纪间,荷兰销住欧洲的中国瓷器不少于300万件。到18世纪,随着瓷器使用在欧洲的普及,瓷器贸易有进一步发展。1720年之后的半个世纪,销往英国的华瓷达到2500—3000万件。在荷兰对华间接贸易时期,英国华瓷贸易不仅供应本国市场,而
且大量从事转口贸易,甚至连荷兰都可以看到英国商人的瓷器销售广告:1722年之后的25年间,法国进El的华瓷约为300万件,在1761年至1775年问又进口200万件。据凯尼斯[J.P.Kemeis]与布朗恩[Y.Brunean]称,丹麦东印度公司仅1730年华瓷销售订单即达1000万件。瑞典是华瓷最重要的客户,瑞典第三东印度公司在1766年至1786年间进口华瓷达1100万件。在其存在的84年间,总共进口约5000万件,居各国华瓷贸易之首。
欧洲的远东贸易对欧洲历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将中国商品大量运往欧洲的同时,也将中国文化带到了欧洲各国。瓷器、丝绸、漆器、壁纸等丰富多姿的中国物品,成为中国文化
西传的载体,向欧洲展示了神奇迷人的中国文明。
二、1 7世纪前葡萄牙文和
西班牙文中国报道
欧洲远东贸易的兴起和商人、旅行家及从事殖民外交的官员的到来,关于中国的消息,经由大海而不是原先的陆路,以远超过马可·波罗时代的规模,通过信件、报告、传闻和行记被带往欧洲。
1515年柯尔萨利斯[Andrew Corsalis]首先打破了自曼德维尔之后长达两个世纪的沉寂。他在致洛伦佐·美第奇公爵[Lorenzo Medici]的信中送去了中国消息:中国人生产“丝绸和各种精致的面料,如锦缎、缎子和极其富贵的织锦。虽然他们由于眼睛小,在外表上比我们难看,但事实上他们技艺非凡,和我们具有同样的品质。”
前言/序言
全球一体化进程为我们审视17、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往提供了新的视角。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深切感受到多元文化碰撞和互渗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意识,使得该研究领域备受关注,它所包含的两个方向“‘中国热’中的欧洲”和“欧洲在中国”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本书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出版专著的数量为此后三十年间著述总数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低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整个20世纪50年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直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才出现复苏的迹象,著述数量逐渐增加。从1974年开始,在法国尚蒂伊多学科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interdisciplinaire de chantilly]每三年召开一次有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中国问题专家参加的国际汉学讨论会,“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是会议的基本议题之一,例如前几次会议的主题都涉及到“17—18世纪中国同欧洲(主要是同法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的交往关系,尤其是中国对它们的影响”,包括“哲学影响”、 “来自中国的艺术和科学”和“礼仪之争”等方面。1其他类似的国际会议也时有举行。
进入90年代,该领域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在欧洲和美国有一批重要的著作问世,所涉及的内容无论在专题分析方面,还是在综合性的研究方面,都有重要的突破。2更具有意义的是,研究中西关系史的中国学者开始改变原先主要局限于“西学东渐”研究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涉足“中学西被”的领域。我们知道,在中国,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或“中学西被”这一方向的课题很少有人问津,与“西学东渐”的研究相比,无论参加的人数,还是研究的成果都要少得多。例如,在关于欧洲社会的“中国热”以及18世纪欧洲盛行的“中国风”,西方已经出版了四五种名为《中国风》[Chinoiserie]的著作,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讨中国艺术风格对18世纪欧洲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而在中国,一直到现在都不曾有过一部这方面的专著。这种状况不仅与西方汉学界在该领域取得的成就不成比例,而且也与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欧洲乃至世界的贡献不相称。造成这种现象也有资料方面的原因,因为该方向的研究,无论文献资料还是实物资料,都主要集中在西方的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文献资料所涉及的语言包括拉丁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等,而且非常分散。这给中国学者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早期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多为在欧洲的留学人员,如范存忠、陈受颐、李肇义、陈铨、钱钟书等,文章大多用外文写成。随着70年代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中国学者开始有机会到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到博物馆观看实物,部分重要的西文原始材料和近人的研究成果也陆续翻译出版。同时,随着开放意识的加强和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对多元文化格局的重视,社会公众和学者对文化间交流的重要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这些都给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机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学西渐”或“中国文化对欧洲之影响”的研究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这十年间所出版的著作比此前所有著述的总和还要多1,同时有关论文的数量锰增,并出现了多种专门性的刊物。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处理得非常高明,不像很多学术著作那样枯燥乏涩,它读起来竟然有一种流畅的、近乎于小说般的魅力。作者仿佛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园丁,他引导我们穿梭于凡尔赛宫的中国亭台楼阁之间,又一同潜入到德累斯顿书房里哲人们关于《论语》的争论现场。我特别喜欢他擅用人物侧写的手法,比如对某些热衷于东方学的小贵族,或是某些来华传教士的内心挣扎的描绘,这些细节使得宏大的历史叙事鲜活了起来。例如,某位传教士的通信中流露出的文化冲击与身份认同的矛盾,被作者捕捉得丝丝入扣。这让我深思,在文化交流的浪潮中,个体是如何被裹挟,又是如何努力保持自身独特性的。阅读的过程,与其说是在学习历史知识,不如说是在体验一场穿越时空的“沉浸式剧场”,每一个场景都充满了那个时代独有的张力和矛盾美感。
评分这本书的贡献价值在于,它成功地将“中国形象”的研究从简单的文化符号学范畴,提升到了社会心态史的高度。它没有仅仅满足于“欧洲人看到了什么”,而是深入追问了“欧洲人为什么要这样看”。在启蒙运动的背景下,这种对异域文化的借用,本质上是一种“内部批评”的工具。当伏尔泰赞美东方的开明君主时,他其实在暗讽法国波旁王朝的专制;当欧洲人惊叹于中国科举制度的公平性时,他们正在对本国贵族世袭的腐朽发起挑战。作者将这些深层的政治意图和文化焦虑,梳理得条理清晰,如同外科手术般精准。读到后来,我甚至有些替当时的欧洲人感到悲哀,他们对一个远在天边的、可能并不完全真实的“中国”产生了如此强烈的精神依赖,这反映了他们自身文明在面对现代化转型时的那种迷茫和自我怀疑。这本书,与其说是写中国的历史,不如说是写欧洲在自我构建过程中的“他者依赖”。
评分这本关于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传播的书籍,简直是一面映照着启蒙时代欧洲精神世界的哈哈镜。我花了整整一个周末才将它细细读完,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就好像亲眼目睹了当时巴黎的沙龙里,那些身着丝绸长袍的贵妇们,如何为了一件来自东方的瓷器或是关于孔子的哲学思辨而兴奋不已。作者的笔触极其细腻,他没有停留在罗列事件的层面,而是深入挖掘了“中国热”背后那些复杂的文化动机。比如,书中对耶稣会士的报告文学如何被“去本土化”和“再包装”的分析,就非常到位。他们将儒家的伦理观巧妙地嵌入到欧洲自然神论的讨论框架中,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移植,更像是一场高明的哲学“借壳上市”。我尤其欣赏作者对“Chinoiserie”现象的解读,它不仅仅是建筑和园林上的装饰风尚,更是一种对自身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焦虑与反思的投射。每一次欧洲人在想象东方时,他们投射的其实是自己对某种“理想国”的渴望,或者说是对当时自身社会弊病的无声控诉。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文化传播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它更像是一场跨越大陆的复杂对话,充满了误解、挪用和最终的融合。
评分坦白说,这本书的结构和论证逻辑非常严谨,但也因此,它对读者的知识储备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如果不是对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脉络有所了解,初次接触可能会觉得某些地方略显跳跃。不过,对于真正有心探究这段历史的读者来说,这种深度的探讨绝对物超所值。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部分在于作者对于“汉学研究”从宗教(耶稣会士)向世俗(大学学者)转化的过程的细致描摹。这种学派的更迭,标志着欧洲对中国的看法从一种带有救赎意味的理想化,转向了一种更具科学性和政治性的审视。书中通过对一些早期汉学家书信往来的分析,展现了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观点交锋与知识的缓慢积累过程。每一次对新文本的翻译和解读,都像是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凿开了一个新的入口,虽然这个入口充满了光影斑驳的误读,但它确确实实地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全书读毕,我只剩下一个想法:我们今天看待“他者”的方式,是否依然被古老的思维定势所困扰?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反思参照点。
评分读完此书,我最大的感受是知识的密度和研究的深度。作者显然下了多年的功夫,他引用的史料之丰富,令人惊叹,仿佛能闻到十八世纪图书馆里羊皮纸和油墨的味道。尤其是对不同国家地区反应差异的对比分析,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展示。比如,英国的实用主义者如何热衷于中国的农业技术和科学管理,而德国的哲学家们又如何将老子的“无为”哲学视为对莱布尼茨式理性至上论的温和反叛。这种细致入微的比较,揭示了文化接受的“土壤性”——即便是相同的文化符号,一旦落地到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背景中,其意义也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书中对“理性的东方”与“感性的东方”这两种对立形象的考察,尤为精妙。欧洲人似乎总需要一个“他者”来定义自身,中国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可供投射的空白画布,承载了他们对“纯粹理性”和“和谐社会”的全部想象。这种多维度的解读,让整个叙事立体而丰满,远超一般的文化史著作的肤浅描述。
评分因为要急用,就买了凑着用了
评分下次还来买这本书现在我已经买下了,现在我来给它写段评论吧! 先从哪里说起呢?还是先从它的品相说起吧!也就是先从它的外表说起吧!这本书的品相还是很好的,绝对的是全品书。也就是说封面很平很新,没有折角,印刷精致美丽大方,当然就很漂亮啦。要说到品相好,还得说说它的正文啊!每一页上都有字呢!每个字都能看清楚呢!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每页都很规整,没有脱页、漏页的现象出现呢!每个字印刷的都很精细呢。好的,现在品相已经评论完了,至此品相这一个环节还是可以打个很高的分呢。 说完了品相,接下来我们该评论些什么内容呢?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包装?还是书的运输?还是书的价格呢? 我觉得还是先从书的内容说起吧!其实,说实话,这本书我也是刚买回来,也就是说我买的是本新书,或者说得更直白些,这本书事实上我还没有认真读,也只是粗略的翻了一下。从目录来看,这本书的选题还是很好的,还是很成功的,换句话说这本书的选题质量不是很坏,不是很失败。一个好的选题就保证了书的大半质量。这本书资料详实,论证扎实,考据精密,且符合学术史的主流趋势,是一本相当不错的书,读来可以让人受教很多。最难能可贵的是,它的选题非常地吸引我,因为我最近确实也在关注类似的选题,希望能在这本书中获得启发,并找到有用的东西,也就是说要自动屏蔽额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现在书的品相和内容我都已经评论完了,接下来我们评价什么呢?评论一下它的包装好吗?好的。这本书的包装还是很好的,它是用那一种很好的膜给包起来了,这个做法宝真的是非常的好和明智。它有效地组织了书不受尘土、细菌特别是水的侵扰,特别是水,被谁淋湿了,即使弄干也会发皱,这多不好啊!现在好了,自从有了这层膜啊,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剧的情况了。所以说包装还是很多的。 至此,品相、内容、包装这三项我都已经评论好了,接下来我们评论什么呢?要不评论一下运输?算了还是评论一下价格吧!这本书的价格还是很便宜的,如果要是在一般的实体书店里买,可定不会打折,也就是全价卖出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享受不到优惠的意思,多不值啊。但是在京东就不同了,什么不同呢?就是可以打折了,也就是说不必花高价以全价购买了。这还是非常优惠的,这本书在京东买要比在其它实体店买便宜十多块呢。 好的,现在价格也说完了,我们还是再来聊聊它的运输吧,我大概是昨天晚上订的,刚一下订单,我就发现它顺利地在5号库,给出库了,然后是拣货,拣货之后打包啊,分拣啊,今天早上就送到学校的营业厅,中午就到学校了,就收到书了,真心很快。 基于以上几点我给这本书一个好评。
评分《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
评分《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
评分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出版专著的数量为此后三十年间著述总数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低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整个20世纪50年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出版专著的数量为此后三十年间著述总数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低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整个20世纪50年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出版专著的数量为此后三十年间著述总数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低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整个20世纪50年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出版专著的数量为此后三十年间著述总数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低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整个20世纪50年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出版专著的数量为此后三十年间著述总数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低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整个20世纪50年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出版专著的数量为此后三十年间著述总数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低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整个20世纪50年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出版专著的数量为此后三十年间著述总数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低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整个20世纪50年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出版专著的数量为此后三十年间著述总数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低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整个20世纪50年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出版专著的数量为此后三十年间著述总数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低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整个20世纪50年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出版专著的数量为此后三十年间著述总数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低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整个20世纪50年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出版专著的数量为此后三十年间著述总数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低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整个20世纪50年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
评分《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
评分《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
评分学术性较强,资料丰富。
评分很喜欢这本书,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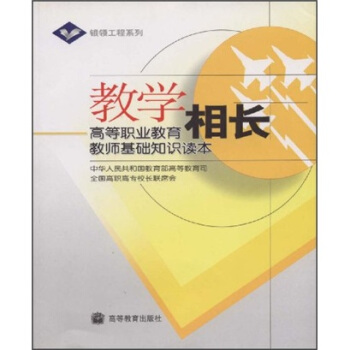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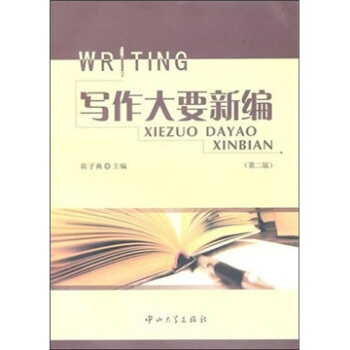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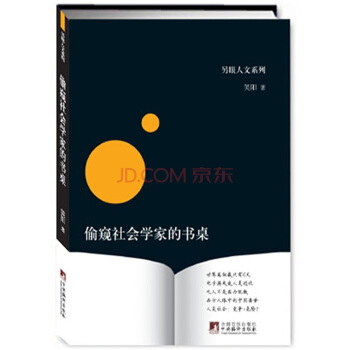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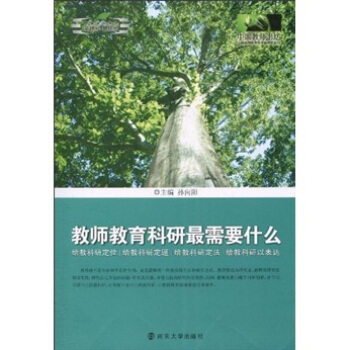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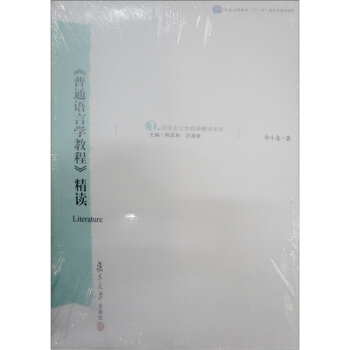
![翻译文体学研究 [Styl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775920/c2145f6c-ad59-4022-afbe-72398d2555a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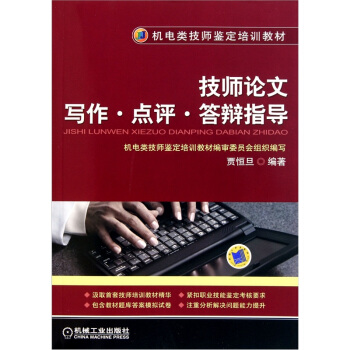
![消费社会学(第2版) [The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Second Edi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20083/ced5ef3f-e85f-4ce2-90fb-74c28f528ea1.jpg)
![职业教育教与学过程 [Teaching-Learning Processe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20840/9c2a8963-ba91-411e-8e57-117eb1d39b9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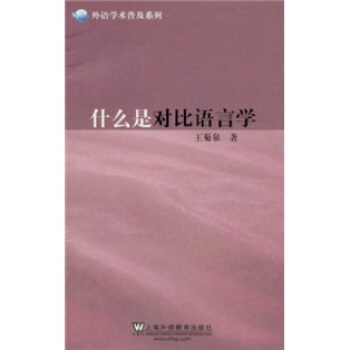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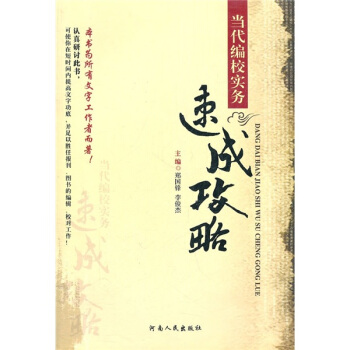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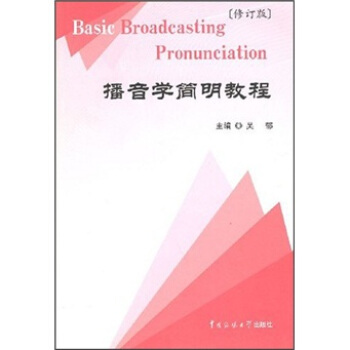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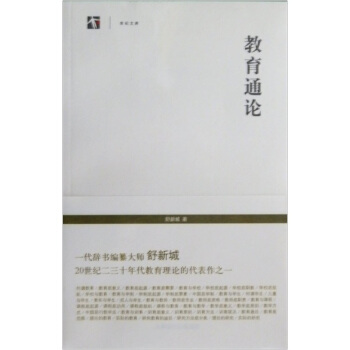
![教育大百科全书:教育哲学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2nd Edi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57385/087df600-7053-4995-aa57-c79a56bb72b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