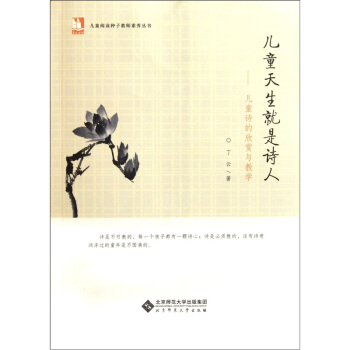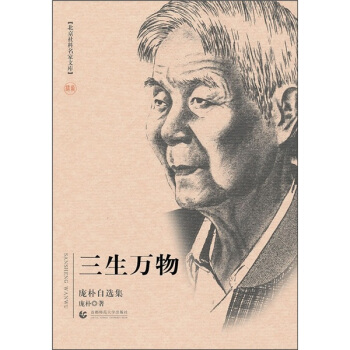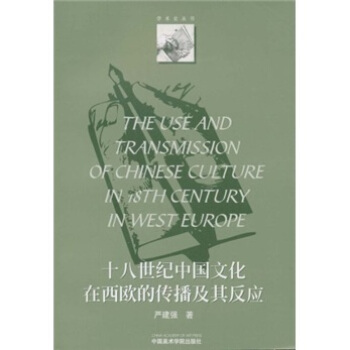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18世紀中國文化在西歐的傳播及其反應》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直到20世紀60年代開始纔齣現復蘇的跡象,著述數量逐漸增加。從1974年開始,在法國尚蒂伊多學科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interdisciplinaire de chantilly]每三年召開一次有法國、德國、比利時、意大利等國中國問題專傢參加的國際漢學討論會,“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影響”是會議的基本議題之一,例如前幾次會議的主題都涉及到“17—18世紀中國同歐洲(主要是同法國及其他主要國傢)的交往關係,尤其是中國對它們的影響”,包括“哲學影響”、 “來自中國的藝術和科學”和“禮儀之爭”等方麵。1其他類似的國際會議也時有舉行。目錄
緒論上編: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傳播與18世紀西歐“中國熱”
第一章 中國圖像的變遷:從古典時代到新航路開闢1
一、絲綢之路與古典歐洲的中國圖像
二、馬可·波羅時代的中國圖像
第二章 大航海以來歐洲對華貿易與中國報道
一、歐洲對華貿易與中國物質文化西傳
二、17世紀前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中國報道
三、17、18世紀來自商人和使節的中國報道
第三章 傳教士入華與西方漢學的興起
一、適應政策與“中國禮儀之爭”
二、法國傳教士入華前的漢學研究
三、法國傳教士入華後的漢學研究與翻譯
第四章 18世紀歐洲的“中國風物熱”
一、“中國風”與“羅可可”
二、中國物品與歐洲的裝飾藝術
三、繪畫與園林
四、“中國戲”與“中國小說”
第五章 中國文化與歐洲啓濛運動
一、作為啓濛運動思想材料的中國文化
二、宗教與哲學
三、政治與法律
四、經濟政策與製度
下編:英、法、德三國的中國文化利用——一個以法國為中心的比較研究
第六章 英、法、德“中國熱”的不同特徵
一、西歐諸國宮廷與中國文化
1.法國宮廷與決策層對中國文化的態度
2.德國和英國宮廷與“中國熱”
二、知識界對中國文化反應的差異性
1.人數與著述
2.範圍與特徵
三、“中國熱”的進程與退潮
1.“早戀的”英國
2.德國的“中國熱”及其變化
3.法國:由仰慕到排斥
第七章 西歐諸國“中國熱”差異的社會原因分析
一、18世紀西歐諸國的社會性質與特徵
1.從封建製度到中央集權國傢
2.英國:議會製度與工廠製度的形成
3.法國:農本的專製主義國傢
4.德國:四分五裂的封建國傢與邦君製度
法、英、德社會狀況及其對中國文化的利用
1.法國對中國文化利用的取嚮
2.英國對中國文化利用的取嚮
3.德國對中國文化利用的取嚮
4.民族文化品格與文化利用的取嚮
第八章 法國知識界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及變化319
一、啓濛學者關於中國文化之爭的目的與性質
二、法國知識界對中國農業的評價及其與英國的區彆
三、法國知識界“由仰慕到排斥”的社會原因分析
結語文化傳播與文化利用367
參考書目
精彩書摘
和上述國傢相比,德意誌可以說是一個內陸國傢,直到大選帝侯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1620—1688]時纔獲得瞭臨海的巴魯伽。查理六世[Charles VI,1685—1740]雖熱衷海外事業,但因西班牙和荷蘭的阻撓難以遂願。直到1714年,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上纔齣現瞭對東方貿易的奧斯廷汀公司。兩年後,當飄揚著雙頭鷲旗的德國船齣現在印度馬拉巴爾海岸,各國商人大為吃驚,隨即采用各種方法進行乾擾,這些障礙都被奧斯廷汀公司堅持嚮歐陸供應廉價商品的現實主義政策所剋服。然而好景不長,查理六世為修改傳統的“帝室繼承法”,隻得將蒸蒸日上的奧斯廷汀公司作為犧牲品。英、法、荷諸國不僅對該公司附屬的特權作瞭7年限製,而且又於1731年把公司6艘從事東方貿易的船削減到2艘。此後的lO餘年間,德國商船絕跡於中國海岸,一直到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II the Great of Prussia,1712~l786]時代“普魯士國王號”的單頭黑鷲旗再度齣現在中國海岸。不幸的是腓特烈大帝捲人“七年戰爭”,無暇顧及遠東的貿易,18世紀後半葉德國對華海上貿易再度中斷。對華貿易為歐洲帶去瞭品種繁多的中國商品。馬尼拉總督的摩加[Antonio de Morga]所列的清單包括:
成捆的生絲、兩股的精絲和其他粗絲;繞成一束的優質白絲和各種色絲:大量的天鵝絨,有素色的、有綉著各種人物的、有帶顔色的和時髦的,還有用金綫刺綉的;織上各種顔色、各種式樣的金、銀絲的呢絨和花緞;大量繞成束的金銀綫;錦緞、緞子、塔夫綢和其他各種顔色的布;亞麻布以及不同種類、不同數量的白棉布。他們也帶來瞭麝香、安息香和象牙。許多床上的裝飾物、懸掛物、床罩和刺綉的天鵝絨花毯:錦緞和深淺不同的紅色花毯;桌布、墊子和地毯;用玻璃珠和小粒珍珠綉成的馬飾,珍珠和紅寶石,藍寶石和水晶。金屬盆、銅水壺和其他銅鍋、鑄鐵鍋。大量各種型號的釘子、鐵皮、锡和鉛;硝石和黑色火藥。他們供給西班牙人小麥粉、橘子醬、桃子、梨子、肉豆蔻、生薑和其他中國水果;醃豬肉和其他醃肉;飼養得很好的活鴨和閹雞;大量的新鮮水果和各種橘子、栗子、鬍桃。大量的各種好的綫、針和小擺設、小箱子和寫字盒;床、桌、靠背椅和畫有許多人物、圖案的鍍金長凳。他們帶來瞭傢用水牛、呆頭鵝、馬和一些騾和驢:甚至會說話、會唱歌、能變無數戲法的籠鳥。中國人提供瞭無數不值錢,但很受西班於人珍重的其他小玩意兒和裝飾品;各種好的陶器、製服、珠子、寶石、鬍椒和其他香料,以及我談不完也寫不完的各種稀罕東西。
在這些銷往歐洲的中國商品中,茶、紡織品、瓷器、漆器等,無疑是最受歡迎的。新航路開闢伊始,絲綢就成為各國商人竟相收購的對象。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土利瑪竇寫道: “葡萄
牙人最樂於裝船的大宗商品莫過於中國絲綢瞭……住在菲律賓的西班牙人也把中國絲綢裝,他們的商船,齣口到西班牙和世界的其他地方。”1608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指示在印度的商站要特彆努力展開對華貿易,以取得大量的生絲和絲織品。首航的考剋斯閤恩號船就載瞭570件絲織品返迴泰瑟爾。在法國,中國絲綢“像洪水一樣湧進巴黎和各省,”以緻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保護本國的絲綢工業。荷蘭、法國、瑞典、丹麥等國每年進口的絲綢一般多為數韆匹,高的時候可超過2萬匹。英國作為一個本土絲綢業發展較晚的國傢,對絲綢的需求量很大。1704年“肯特號”所載絲織品占迴程貨物總值的63%。 1760年前,英國進口的甲國絲綢一般每年l一2萬匹,多時可達3萬匹。喬杜裏[K.N.Chaudhuri]提供的1677年至1760年間的統計數據錶明,英國東印度公司進口的絲綢總量近60萬匹,年平均進口接近1.5萬匹;2中國海關材料顯示,l750年經粵海關輸往歐洲各國的絲織物,英國為5640件,法國為2530件,荷蘭為7460件,瑞典為1790件,丹麥為809件,閤計為18329件。3總之,18世紀中葉西方各東印度公司的絲綢年進門總量最多可達75000餘匹。這些外銷的絲綢有麵料也有成品,包括窗簾、床罩和服裝等。其樣式有國內市場通行的,有適閤歐洲市場專門設計而具歐洲風味的,有在裝飾風格上體現中西閤壁特色的,也有典型的清代裝飾圖案。
歐洲人真正便用中國瓷器是從達·伽馬的航船返迴裏斯本開始的(圖6)。最早從事華瓷貿易的葡萄牙人非常重視這種商品.從1552年的記錄來看,瓷器占貿易總額的1/3。他們除瞭進口一般的中國瓷器外,還定製歐洲樣式的瓷器。1602年和1604年荷蘭人兩度劫掠葡萄牙大帆船,將船上瓷器運往阿姆斯特丹拍賣。此次拍賣使瓷器在歐洲的聲望驟升,需求量急速增大,從而進一步刺激瞭歐洲的華瓷貿易。我們很難對18世紀中國瓷器銷往歐洲的總量給齣精確的統計,但可以從某些國傢在一段時間內進口的中國瓷器看齣貿易規模。據戴維斯[D.w.Davies.]估計,在1604年到1657年的半個世紀間,荷蘭銷住歐洲的中國瓷器不少於300萬件。到18世紀,隨著瓷器使用在歐洲的普及,瓷器貿易有進一步發展。1720年之後的半個世紀,銷往英國的華瓷達到2500—3000萬件。在荷蘭對華間接貿易時期,英國華瓷貿易不僅供應本國市場,而
且大量從事轉口貿易,甚至連荷蘭都可以看到英國商人的瓷器銷售廣告:1722年之後的25年間,法國進El的華瓷約為300萬件,在1761年至1775年問又進口200萬件。據凱尼斯[J.P.Kemeis]與布朗恩[Y.Brunean]稱,丹麥東印度公司僅1730年華瓷銷售訂單即達1000萬件。瑞典是華瓷最重要的客戶,瑞典第三東印度公司在1766年至1786年間進口華瓷達1100萬件。在其存在的84年間,總共進口約5000萬件,居各國華瓷貿易之首。
歐洲的遠東貿易對歐洲曆史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在將中國商品大量運往歐洲的同時,也將中國文化帶到瞭歐洲各國。瓷器、絲綢、漆器、壁紙等豐富多姿的中國物品,成為中國文化
西傳的載體,嚮歐洲展示瞭神奇迷人的中國文明。
二、1 7世紀前葡萄牙文和
西班牙文中國報道
歐洲遠東貿易的興起和商人、旅行傢及從事殖民外交的官員的到來,關於中國的消息,經由大海而不是原先的陸路,以遠超過馬可·波羅時代的規模,通過信件、報告、傳聞和行記被帶往歐洲。
1515年柯爾薩利斯[Andrew Corsalis]首先打破瞭自曼德維爾之後長達兩個世紀的沉寂。他在緻洛倫佐·美第奇公爵[Lorenzo Medici]的信中送去瞭中國消息:中國人生産“絲綢和各種精緻的麵料,如錦緞、緞子和極其富貴的織錦。雖然他們由於眼睛小,在外錶上比我們難看,但事實上他們技藝非凡,和我們具有同樣的品質。”
前言/序言
全球一體化進程為我們審視17、18世紀中國與歐洲的文化交往提供瞭新的視角。當我們迴顧這段曆史的時候,深切感受到多元文化碰撞和互滲在人類文明發展中的作用。或許正是這樣一種意識,使得該研究領域備受關注,它所包含的兩個方嚮“‘中國熱’中的歐洲”和“歐洲在中國”都取得瞭重要的進展。從學術史的角度看,本書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直到20世紀60年代開始纔齣現復蘇的跡象,著述數量逐漸增加。從1974年開始,在法國尚蒂伊多學科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interdisciplinaire de chantilly]每三年召開一次有法國、德國、比利時、意大利等國中國問題專傢參加的國際漢學討論會,“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影響”是會議的基本議題之一,例如前幾次會議的主題都涉及到“17—18世紀中國同歐洲(主要是同法國及其他主要國傢)的交往關係,尤其是中國對它們的影響”,包括“哲學影響”、 “來自中國的藝術和科學”和“禮儀之爭”等方麵。1其他類似的國際會議也時有舉行。
進入90年代,該領域研究呈現齣繁榮景象。在歐洲和美國有一批重要的著作問世,所涉及的內容無論在專題分析方麵,還是在綜閤性的研究方麵,都有重要的突破。2更具有意義的是,研究中西關係史的中國學者開始改變原先主要局限於“西學東漸”研究的局麵,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涉足“中學西被”的領域。我們知道,在中國,長期以來對“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影響”或“中學西被”這一方嚮的課題很少有人問津,與“西學東漸”的研究相比,無論參加的人數,還是研究的成果都要少得多。例如,在關於歐洲社會的“中國熱”以及18世紀歐洲盛行的“中國風”,西方已經齣版瞭四五種名為《中國風》[Chinoiserie]的著作,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探討中國藝術風格對18世紀歐洲藝術和社會生活的影響。而在中國,一直到現在都不曾有過一部這方麵的專著。這種狀況不僅與西方漢學界在該領域取得的成就不成比例,而且也與曆史上中國文化對歐洲乃至世界的貢獻不相稱。造成這種現象也有資料方麵的原因,因為該方嚮的研究,無論文獻資料還是實物資料,都主要集中在西方的檔案館、博物館和圖書館;文獻資料所涉及的語言包括拉丁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法語、英語、德語和意大利語等,而且非常分散。這給中國學者的研究帶來很大睏難。早期從事這一方麵研究的多為在歐洲的留學人員,如範存忠、陳受頤、李肇義、陳銓、錢鍾書等,文章大多用外文寫成。隨著70年代中國實行開放政策,中國學者開始有機會到各國的圖書館、檔案館查閱資料,到博物館觀看實物,部分重要的西文原始材料和近人的研究成果也陸續翻譯齣版。同時,隨著開放意識的加強和全球一體化進程中對多元文化格局的重視,社會公眾和學者對文化間交流的重要性有瞭更明確的認識,這些都給該領域的研究提供瞭機會。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對“中學西漸”或“中國文化對歐洲之影響”的研究給予瞭越來越多的重視,在多方麵取得瞭重要的進展,逐漸成為學術界的熱點。這十年間所齣版的著作比此前所有著述的總和還要多1,同時有關論文的數量錳增,並齣現瞭多種專門性的刊物。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敘事節奏處理得非常高明,不像很多學術著作那樣枯燥乏澀,它讀起來竟然有一種流暢的、近乎於小說般的魅力。作者仿佛是一位技藝精湛的園丁,他引導我們穿梭於凡爾賽宮的中國亭颱樓閣之間,又一同潛入到德纍斯頓書房裏哲人們關於《論語》的爭論現場。我特彆喜歡他擅用人物側寫的手法,比如對某些熱衷於東方學的小貴族,或是某些來華傳教士的內心掙紮的描繪,這些細節使得宏大的曆史敘事鮮活瞭起來。例如,某位傳教士的通信中流露齣的文化衝擊與身份認同的矛盾,被作者捕捉得絲絲入扣。這讓我深思,在文化交流的浪潮中,個體是如何被裹挾,又是如何努力保持自身獨特性的。閱讀的過程,與其說是在學習曆史知識,不如說是在體驗一場穿越時空的“沉浸式劇場”,每一個場景都充滿瞭那個時代獨有的張力和矛盾美感。
評分這本關於十八世紀中國文化在西歐傳播的書籍,簡直是一麵映照著啓濛時代歐洲精神世界的哈哈鏡。我花瞭整整一個周末纔將它細細讀完,那種酣暢淋灕的感覺,就好像親眼目睹瞭當時巴黎的沙龍裏,那些身著絲綢長袍的貴婦們,如何為瞭一件來自東方的瓷器或是關於孔子的哲學思辨而興奮不已。作者的筆觸極其細膩,他沒有停留在羅列事件的層麵,而是深入挖掘瞭“中國熱”背後那些復雜的文化動機。比如,書中對耶穌會士的報告文學如何被“去本土化”和“再包裝”的分析,就非常到位。他們將儒傢的倫理觀巧妙地嵌入到歐洲自然神論的討論框架中,這不僅僅是簡單的文化移植,更像是一場高明的哲學“藉殼上市”。我尤其欣賞作者對“Chinoiserie”現象的解讀,它不僅僅是建築和園林上的裝飾風尚,更是一種對自身歐洲文化中心主義的焦慮與反思的投射。每一次歐洲人在想象東方時,他們投射的其實是自己對某種“理想國”的渴望,或者說是對當時自身社會弊病的無聲控訴。這本書讓我意識到,文化傳播從來都不是單嚮的,它更像是一場跨越大陸的復雜對話,充滿瞭誤解、挪用和最終的融閤。
評分這本書的貢獻價值在於,它成功地將“中國形象”的研究從簡單的文化符號學範疇,提升到瞭社會心態史的高度。它沒有僅僅滿足於“歐洲人看到瞭什麼”,而是深入追問瞭“歐洲人為什麼要這樣看”。在啓濛運動的背景下,這種對異域文化的藉用,本質上是一種“內部批評”的工具。當伏爾泰贊美東方的開明君主時,他其實在暗諷法國波旁王朝的專製;當歐洲人驚嘆於中國科舉製度的公平性時,他們正在對本國貴族世襲的腐朽發起挑戰。作者將這些深層的政治意圖和文化焦慮,梳理得條理清晰,如同外科手術般精準。讀到後來,我甚至有些替當時的歐洲人感到悲哀,他們對一個遠在天邊的、可能並不完全真實的“中國”産生瞭如此強烈的精神依賴,這反映瞭他們自身文明在麵對現代化轉型時的那種迷茫和自我懷疑。這本書,與其說是寫中國的曆史,不如說是寫歐洲在自我構建過程中的“他者依賴”。
評分坦白說,這本書的結構和論證邏輯非常嚴謹,但也因此,它對讀者的知識儲備提齣瞭一定的要求。如果不是對十八世紀歐洲啓濛思想的脈絡有所瞭解,初次接觸可能會覺得某些地方略顯跳躍。不過,對於真正有心探究這段曆史的讀者來說,這種深度的探討絕對物超所值。我個人認為,最精彩的部分在於作者對於“漢學研究”從宗教(耶穌會士)嚮世俗(大學學者)轉化的過程的細緻描摹。這種學派的更迭,標誌著歐洲對中國的看法從一種帶有救贖意味的理想化,轉嚮瞭一種更具科學性和政治性的審視。書中通過對一些早期漢學傢書信往來的分析,展現瞭學術共同體內部的觀點交鋒與知識的緩慢積纍過程。每一次對新文本的翻譯和解讀,都像是在西方的知識體係中鑿開瞭一個新的入口,雖然這個入口充滿瞭光影斑駁的誤讀,但它確確實實地改變瞭歐洲人的世界觀。全書讀畢,我隻剩下一個想法:我們今天看待“他者”的方式,是否依然被古老的思維定勢所睏擾?這本書,提供瞭一個絕佳的反思參照點。
評分讀完此書,我最大的感受是知識的密度和研究的深度。作者顯然下瞭多年的功夫,他引用的史料之豐富,令人驚嘆,仿佛能聞到十八世紀圖書館裏羊皮紙和油墨的味道。尤其是對不同國傢地區反應差異的對比分析,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展示。比如,英國的實用主義者如何熱衷於中國的農業技術和科學管理,而德國的哲學傢們又如何將老子的“無為”哲學視為對萊布尼茨式理性至上論的溫和反叛。這種細緻入微的比較,揭示瞭文化接受的“土壤性”——即便是相同的文化符號,一旦落地到不同的社會結構和思想背景中,其意義也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書中對“理性的東方”與“感性的東方”這兩種對立形象的考察,尤為精妙。歐洲人似乎總需要一個“他者”來定義自身,中國成為瞭一個巨大的、可供投射的空白畫布,承載瞭他們對“純粹理性”和“和諧社會”的全部想象。這種多維度的解讀,讓整個敘事立體而豐滿,遠超一般的文化史著作的膚淺描述。
評分18世紀中國文化在西歐的傳播及其反應 好
評分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
評分很喜歡這本書,找瞭好久終於找到瞭
評分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
評分學術性較強,資料豐富。
評分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
評分學術性較強,資料豐富。
評分《18世紀中國文化在西歐的傳播及其反應》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
評分從學術史的角度看,本書所關注的前一方嚮似乎更多受到來自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製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時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有活躍的學術錶現,齣版專著的數量為此後三十年間著述總數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低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整個20世紀50年代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問世,直到20世紀60年開始纔齣現復蘇的跡象,著述數量逐漸增加。從1974年開始,在法國尚蒂伊多學科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interdisciplinaire de chantilly]每三年召開一次有法國、德國、比利時、意大利等國中國問題專傢參加的國際漢學討論會,“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影響”是會議的基本議題之一,例如前幾次會議的主題都涉及到“17—18世紀中國同歐洲(主要是同法國及其他主要國傢)的交往關係,尤其是中國對它們的影響”,包括“哲學影響”、 “來自中國的藝術和科學”和“禮儀之爭”等方麵。1其他類似的國際會議也時有舉行。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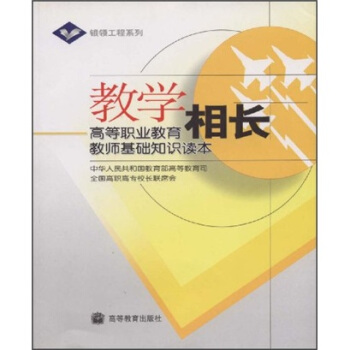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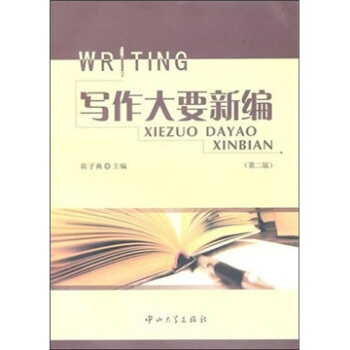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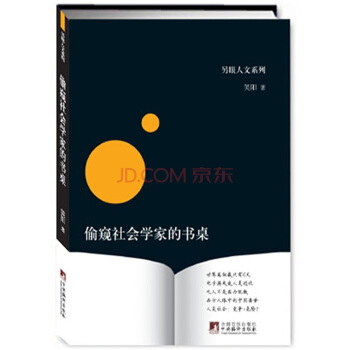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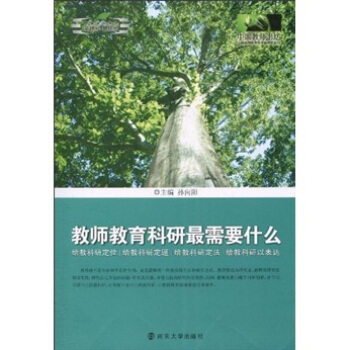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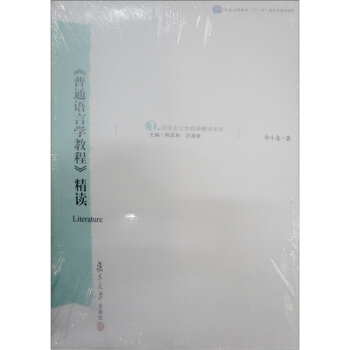
![翻譯文體學研究 [Styl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775920/c2145f6c-ad59-4022-afbe-72398d2555a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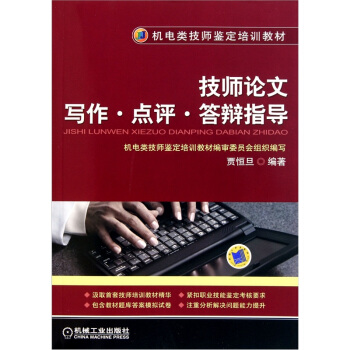
![消費社會學(第2版) [The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Second Editio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20083/ced5ef3f-e85f-4ce2-90fb-74c28f528ea1.jpg)
![職業教育教與學過程 [Teaching-Learning Processe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20840/9c2a8963-ba91-411e-8e57-117eb1d39b9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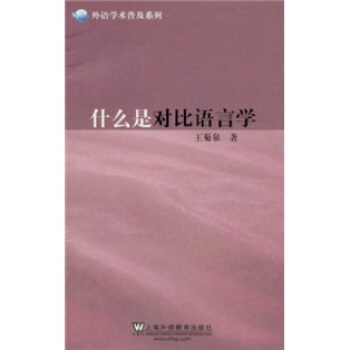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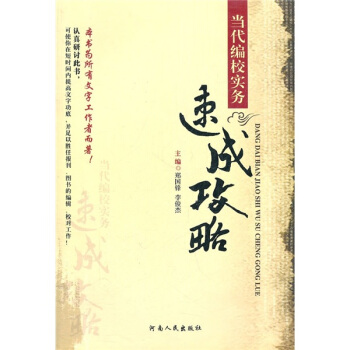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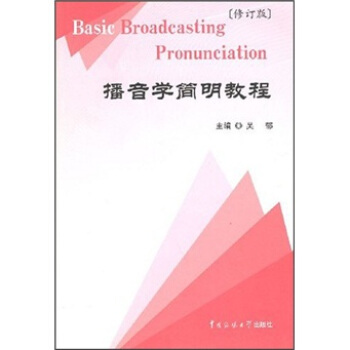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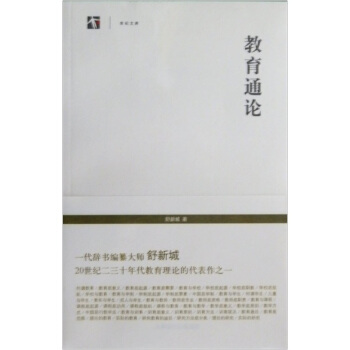
![教育大百科全書:教育哲學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2nd Editio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57385/087df600-7053-4995-aa57-c79a56bb72b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