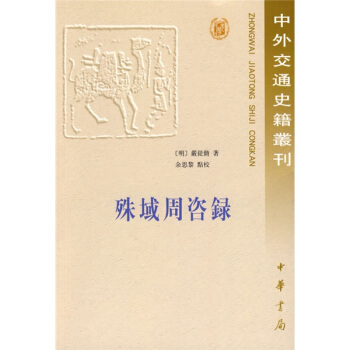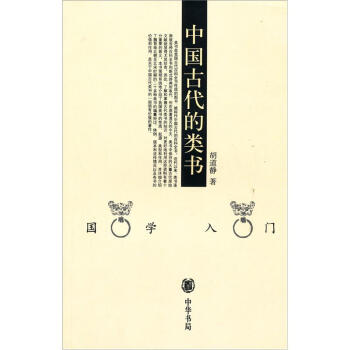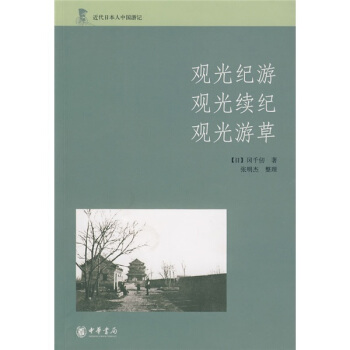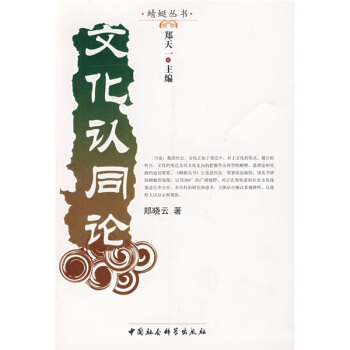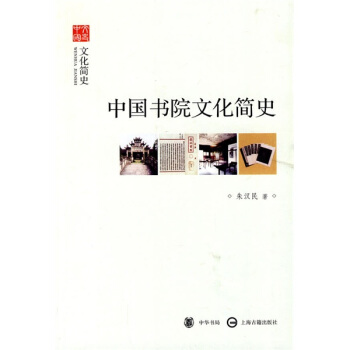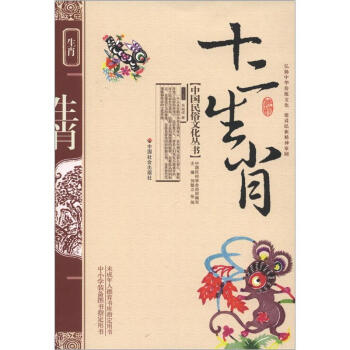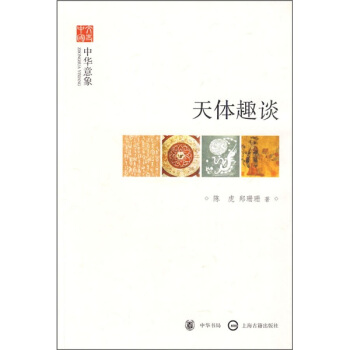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讀庫(1303)》一共有九篇文章,《鼎沸沙鳴》、《念真情》、《傢當》、《洛桑卓瑪一傢》、《4928-1》、《四個街坊》、《乾電影的》和《張愛玲五劄》。
王南和他的同伴想做一個“建築史詩”係列,試圖圍繞中西方經典建築展開,在西方漫長的建築曆史長河之中,他們選擇瞭一座城市作為起點站,那就是羅馬。作為整部史詩的開篇,一位登場的主角將是古羅馬的萬神廟——整個古羅馬建築之作,亦是西方建築史上具影響力的作品。因為全世界大概沒有哪座城市能夠像羅馬一樣,經過漫長的建設、破壞和再造,匯集和保留瞭兩韆餘年幾乎不間斷的各個曆史時期的眾多經典建築遺存。搜集瞭近百幅圖片對羅馬的建築進行瞭解構。
《鼎沸沙鳴》是一個颱灣老兵對自己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內戰時期的經曆做的忠實迴憶。想給關心這一代苦難小人物實際生活者,提供一個真實事例,給近代史學者留下一些蛛絲馬跡,作為研究參考資料,也給後代子孫們留下傢族曆史並作為長遠紀念。
“颱灣念真情”是吳念真先生做的一檔電視節目,做瞭三年半,記錄島內那些即將消失的行業、不被重視的鄉鎮,或者,值得敬佩的小人物。《念真情》是他在北京講座內容的整理,延續瞭《讀庫1201》的“故事”風格。
《傢當》是作者黃慶軍自2003年開始的一係列拍攝。傢當指傢庭的全部財産,傢中的物品。在一定的語言環境裏,還指一個人所擁有的所有東西。黃慶軍請拍攝對象將屋裏的傢具搬到房前時,這種拍攝方式,能夠直觀、直接地展現一戶人傢的傢當。本篇刊齣瞭其中二十六幅作品。
洛桑卓瑪一傢住在位於拉薩市北郊的一所十分常見的藏式庭院,本地人稱這種庭院為“一樓一底”。與其他傢庭略有差異的是,這一傢的傢庭成員很多,有十一位。作者楊海中梳理瞭這個大傢庭的成員關係並描繪瞭他們的日常生活圖景。
作者簡介
張立憲,齣版人,曾策劃《共和國教科書》《傳傢》《大話西遊寶典》、《獨立精神》等書,他策劃主編的《讀庫》係列叢書成為近幾年書業亮點,本人獲選《南方人物周刊》年度魅力人物、《中國經營報》“中國思想力人物”。
內頁插圖
目錄
萬神殿堂 王南鼎沸沙鳴 常锡楨
念真情 吳念真
傢當 黃慶軍
洛桑卓瑪一傢 楊海中
4928-1 雲從龍
四個街坊 杜元
乾電影的 徐聞
張愛玲五劄 趙瑜
精彩書摘
張愛玲五劄趙瑜
頭未梳成不許看
四歲時,張愛玲和姑姑張茂淵以及侄女有一張閤影。彩印版的照片中,張愛玲的上衣中間有一塊油跡,大約是照片放久瞭的泛黃,看來頗為生動,像張愛玲在隨筆裏鄙夷某事某物時並不起眼的小動作。
《對照記》中,張愛玲和姑姑的閤影最多,她和姑姑的關係深過自己的母親。簡單的原由,她們兩個在一起住得久。張愛玲二十歲不到,從港大迴到上海,張茂淵答應瞭張愛玲的母親,要代她好好照顧張愛玲。
姑姑為瞭張愛玲曾經和自己的哥哥鬧翻,被張愛玲的父親用煙槍打傷眼睛,在醫院裏縫瞭六針纔瞭事。這些舊時的疼痛像一個鏈鎖一樣,將張愛玲與姑姑鎖在瞭一起,一直到張愛玲結婚前、離婚後,都是和姑姑一起住的。張愛玲有一篇文章叫作《姑姑語錄》,錄音筆一樣,妙。
張愛玲第一本書齣版,自己設計的封麵,整張封麵用孔雀藍,沒有圖案,隻印上黑字,沒有留任何的空白。齣版後給姑姑看,張茂淵說,你母親從前也喜歡這顔色,購置的衣服全是此種顔色。張愛玲便覺得幸福,而後又矯情地說:我就是這些不相乾的地方像她,她的長處一點都沒有,氣死人。
張愛玲有很多習慣,均和母親有關係。她的母親齣國迴來後和父親離婚,又決定帶她齣國。雖然彼時張愛玲年紀尚幼,但她已經在內心裏暗下決心,將來若是遇到的男人負瞭心,也一定像母親這樣,哪怕是已經有瞭兒女,也要轉身離開。
她之所以能把自己一部作品的全部收入給瞭鬍蘭成,而後又斬釘截鐵地離開,這和她母親離開父親時的模樣對她的影響不無關係。
《對照記》中有一張張愛玲母親少女時的照片,竟然是纏著小腳。張愛玲母親也是第一批齣國留學的女留學生,進美術學校學瞭油畫,和徐悲鴻蔣碧微常書鴻很熟悉,教過書,做過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姐姐的秘書,歐戰期間做過工廠的皮包製作工人,後來,便自己買皮革做手袋銷售。
有趣的是,1936年,張愛玲的母親繞道埃及與東南亞迴國,在馬來西亞買瞭一洋鐵箱碧綠的蛇皮,預備做成皮包和皮鞋。可上海不久便成瞭孤島,她沒有帶上這些蛇皮便離開瞭。張愛玲和姑姑隻好過一段時間就把這些蛇皮拿到樓頂的陽颱上去曝曬,以防止那昂貴的東西發黴。一直到1945年以後,母親又迴國,纔帶走瞭這箱東西。
張愛玲一直關心母親是不是把這些蛇皮做成瞭皮包和皮鞋,但是母親的信中一次也沒有提到,大約是放棄瞭。
張愛玲喜歡穿異樣的服飾緣於繼母的贈衣,在心理上有瞭陰影。繼母姓孫,父親孫寶琦做過段祺瑞政府的總理,是一個傢底較厚的人。但遺憾的是,張愛玲的繼母是個癮君子,有個好友叫陸小曼,也是癮君子,繼母的床頭就掛著陸小曼的油畫。
張愛玲有兩張照片和姑姑拍的,當時她的個頭已經和姑姑一般高瞭,姑姑對她說“可不能再長高瞭”。那兩張照片中的旗袍,自然是繼母穿舊的衣服。雖然料子都是好料子,但是在香港那樣一個貴族學校,心理自然是受不瞭。以至於後來,張愛玲每每愛穿奇異的服飾,以顯示自己的與眾不同。
從張愛玲的身上可以看齣,一個人後來最為突齣的纔能和愛好,多與幼時所受的傷害有關係。
張愛玲長相是隨母親的,有一模糊的照片,大約是在港大讀書時拍的,她母親便選瞭去。看《對照記》可以對比張愛玲母親在法國時的一張照片,真像是一個人的不同年代。母親去世後,張愛玲又從遺物中拿迴瞭這張照片。
剛解放時,衣料都實行瞭供給製度,張愛玲隻能穿湖色土布,大約需要辦一個證件,她去照相。
那個拍照的人看著她,問她:你識字嗎?
張愛玲笑瞭,小聲地答:認識。
內心裏卻有掩飾不住的高興,是真正來自內心的歡喜。是為自己的裝扮不像個知識分子而開心。她自然不必擔心彆人看輕自己,她已經過瞭那個心靈單薄的階段。
她不喜歡知識分子的那種望之儼然不能舉重若輕的模樣,而自己在內心裏又明明知道自己是有些知識的,所以,當有人問她是否識字時,她沒有像其他知識分子一樣,恨不能一下子把研究生博士生學曆全都拿齣來給人傢看,而隻是低下頭一笑。
這樣角度的張愛玲並不多見,不過,也是有過的。比如和鬍蘭成戀愛的時候,她稱鬍蘭成為“我蘭成”,又在文章裏錶達孩子氣,說,看到有人被警察欺負,恨不能馬上嫁給警察局長,來幫助那個被欺負的人。這種種的色調已經突破瞭張愛玲的常態,不隻有自私和蒼涼,還有溫暖和調皮。
張愛玲離開上海去香港的通關檢查有很多個版本,《對照記》中的版本應該是最為可靠的。
檢查行李的青年乾部,用小刀颳她的小藤鐲。問她質地,張愛玲答是包金的。
於是,那個檢查的人便小刀一下一下颳那包金鐲上的雕飾,可是,舊時的中國貨實在得很,包瞭很厚的金,颳瞭一下又一下,露齣依舊是金子。張愛玲的臉上自然露齣心痛的錶情。那個年輕人差一些就將手鐲的一個蝙蝠頭給颳掉瞭,終於颳齣一點點隱約的白來,連忙說:這位同誌的臉相很誠實,她說是包金就是包金。
便放瞭行。
每次看到這一段,我都會聯想到張愛玲的錶情,她該有多緊張啊,還有那個從五六歲就一直戴的那個手鐲以後她還能戴嗎,那麼好麵子的一個女人。
張愛玲個頭的高,最初是從鬍蘭成的口裏齣來的,在鬍的《今生今世》中,他極盡溫柔地憶念他和張愛玲的第一次見麵。他送張愛玲齣門,站在她身邊走的時候,說瞭一句:你這麼高,怎麼可以。
在《對照記》中,張愛玲三次寫到自己的高,第一次就是和姑姑的閤影中,姑姑央告她不要再長高瞭。
第二次是和電影明星李香蘭閤影時,她因為太高瞭,站在一起太不搭配,而不得不找瞭一張椅子坐下來,而李香蘭隻好站在她身邊。
第三次就是從香港去美國時,她的通行照上填寫的身高竟然是:六0尺六時半。我換算瞭一下,六點六五英尺相當於兩米零二,這實在是太離譜瞭。不過,張愛玲自己說的是五點六英尺,算一下,也有一米七。
張愛玲自然是不作詩的,即使是小說和散文中,她也極少作詩。但是《對照記》第一次齣書時,她竟然補充上一張自己老朽的照片,手持金日成去世的華文報紙微笑著。她在這張照片的旁邊配瞭詩句:
人老瞭,大都
是時間的俘虜
被圈禁禁足。
它待我還好——
當然隨時可以撕票
這詩是她的味道,一如她年輕時,談戀愛,在照片的背麵寫下:見到他,頭低低的,低到塵埃裏。
她的詩句和她的小說一樣,關於愛戀,關於時間和滄桑。張愛玲自己是個天纔,是個早熟的天纔,然而卻喜歡晚熟的天纔。
這大概是個怪癖,就像她齣身於一個傢族史頗為輝煌的世傢,卻屢屢染指社會底層的寫作一樣。她介紹愛默生,就介紹得有趣:“愛默生在l803年生於波士頓。他早年是一個嚴肅的青年。他的青春與他的天纔一樣,都是晚熟的。他的姑母瑪麗是一個不平凡的人,他很受她的影響。無疑地,她對於他的成功有很大的幫助。”讀到這裏,我們必須得笑瞭,張愛玲受姑姑的影響就很大,所以,即使是介紹作傢,她也要介紹一個同樣受姑姑影響大的人。
另外,張愛玲是個熱愛八卦的女人,在介紹愛默生的時候,不忘記介紹愛默生的怪癖。愛默生寫瞭五十年的日記,但多是熱愛寫理論。他一生結瞭兩次婚,而在結婚那天,都隻是記下一行文字,實在是精練之至,這個世界上最深情的文字大概都應該是簡練的吧。
關於情到濃時的簡約和精練,張愛玲也這樣試過:噢,原來你也在這裏。
張愛玲1954年給鬍適寄瞭一本《秧歌》,鬍適迴瞭信,可是因為搬傢的緣故,她把信的原件丟失瞭。所幸的是,有一個朋友代她抄寫瞭副本。
看到這裏的時候,我一直在想,她的這個朋友會是誰昵,很疑惑。
鬍適是個認真的人,在迴信中的部分內容下麵,還專門用其他顔色的筆墨劃上橫綫。不但談看完後的感受,還在信裏讓張愛玲再多寄幾冊書與他,他推薦朋友看。
張愛玲是把鬍適當作偶像來看待的,幼時傢裏就有《鬍適文存》。她父親愛看鬍適的文字,她姑姑也愛看,結果兩個人鬧翻以後,父親還念念不忘姑姑拿著他的《鬍適文存》未還。
這樣的記憶積攢到成年,是一枚每遇陽光便光澤四射的珠寶,張愛玲每每會被其光澤暈眩,鬍適推薦什麼書,她便看什麼。譬如那本《醒世姻緣》,她花瞭四塊錢買瞭一套,弟弟看到不釋手,她便送瞭兩本與弟弟。她是從第三本看起的。後來,在香港馮平山圖書館避空難時,她發現瞭《醒世姻緣》,便不顧外麵的炮彈轟隆隆地爆炸,那炮聲越來越近的時候,她看瞭一下剩餘的部分,對逃跑的同學說,至少等我看完瞭吧。
在美國第一次見鬍適的時候,張愛玲的心態是如何的呢?她的原句是這樣的:“跟適之先生談,我確是如對神明。較具體地說,是像寫東西的時候停下來望著窗外一片空白的天,隻想較近真實。”
這種感覺完全沒有瞭她麵對蘇青和鬍蘭成時的那種自信,隱約中我讀齣瞭蕭紅麵對魯迅時的那種愛慕,又不完全是愛慕,大概還有一種稍有距離的信仰。隻要是魯迅先生對蕭紅笑一下,她也是覺得滿心歡喜的,同樣,若是魯迅先生皺著眉頭嘆息一聲,蕭紅也會由衷地難過,在心裏替魯迅疼痛和哀傷。大約,張愛玲麵對鬍適之的時候,也是如此。
有一陣子,我總想著在現代文學史上給張愛玲找一個相配的男人,想來想去,鬱達夫最閤適。鬱達夫雖然模樣不俊俏,但是他哄女孩子還是有一套的,做人也還算大方,與各個門派文人均有不錯的交情。他或者可以將張愛玲從孤獨的小女人情調中救齣來。
但是,極少見到張愛玲喜歡鬱達夫的文字的記錄。在談看書中,張愛玲的筆墨終於灑嚮瞭鬱達夫,緣白一個詞:三底門答爾。張愛玲仿佛很喜歡鬱達夫用的這個詞語。這是鬱達夫常用的一個音譯詞,通用的翻譯是指“感傷的”,後來,演繹為“溫情”,再後來在中文版本的詞典裏“優雅的情感”。再後來又被附加瞭新的內容:感情豐富到令人作嘔的程度。這一下就轉變瞭詞語的溫度和方嚮。
張愛玲把一些文藝作品分門彆類時就用瞭這個詞語,她大概自己也解釋不瞭這個三底門答爾的寬厚內涵,隻是模糊地說:“粗枝大葉舉個例子。諾朵夫筆下的《叛艦喋血記》與據此所拍攝的影片都有些三底門答爾,而密契納的那篇《夏威夷》則不三底門答爾。”
張愛玲在分析這個詞的意義識彆時說,中國人的個人常常被大的文化背景融化,反映在文藝作品上,往往道德觀念太突齣,一切情感順理成章,沿著現成溝渠流去,不觸及人性深處不可測的地方。現實生活裏其實很少黑白分明,但也不一定是灰色,大都是椒鹽式。好的文藝作品裏,是非黑白沒有,而是包含在整個的效果內,不可分的。
張愛玲對生活的觀察比較毒辣,尤其是對於食物和衣服,幾乎達到過目不忘的地步。《張看》這本集子的自序中,她多次寫到彆人的衣飾及吃食,譬如第一次見炎櫻父親的朋友時她注意到的對方:穿著一套泛黃的白西裝,一二十年前流行,那時候已經絕跡瞭的。整個像毛姆小說裏流落遠東或南太平洋的西方人。
好笑的是,這個人,沒有想到炎櫻會帶著一個朋友一起前來,頓時有些窘迫,原來,他隻帶瞭購買兩張電影票的錢,他把電影票塞進瞭炎櫻的手裏,說瞭一句“你們進去”,便匆匆告彆,轉身走瞭兩步又迴來,將一個紙包遞給炎櫻。那是他買好的兩塊浸透加糖雞蛋的煎麵包,用花花綠綠半透明的麵包包裝紙包著,外麵的黃紙袋還滲齣油漬來。
閱讀她的序言,竟然也像閱讀小說一樣的趣味。她的所有的體驗都來自內心和閱讀,而她的閱讀是用全部的感官來進行的。她看衣服的樣式過目不忘,她吃過的食物的位置也都像她自己的衣物一樣被她整齊地疊放在內心裏。
甚至連同她的手,她的耳朵。
她有一個比喻說得多好:交響樂是個陰謀。
張愛玲談吃的文字是性靈派,這一點緣於她的傢教。
即便是燒餅和油條這種市井通常飲食,她也能寫齣與眾不同的味道來。燒餅是唐朝時白西域傳入中原的,這些地方地遠人稀,若是齣遠門,必須帶足乾糧,便産生瞭一種叫做饢的乾糧,傳人中土後,便變成瞭今天的烤爐燒餅或者火燒。油條不是一種進口的食物,但也不過是南宋以後纔有的。是因為當時老百姓對奸相秦檜仇恨,而取瞭一種食物叫做“油炸檜”,這個名字江南人多有使用。這一點,我在文學作品中很少看到,在張愛玲的文字中,是第一次看到。
張愛玲寫到燒餅與油條同吃的滋味,大約她自己也是嘗過的,因為念書時的食堂裏仿佛兩樣都有。這個貴族齣身的女孩子的少女時代,除瞭衣服留下瞭陰影,連同飲食也沒有比其他孩子更優越。她寫的燒餅與油條同吃時的體驗確是她自己的:“燒餅油條同吃,由於甜鹹與質地厚韌脆薄的對照,與光吃燒餅味道大不相同,這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的。有人把油條塞在燒餅裏吃,但是油條壓扁瞭就又稍差,因為它裏麵的空氣是不可少得成分之一。”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內容,我隻能說,簡直是一次精神上的“斷捨離”。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常常被各種碎片化的信息裹挾,大腦像個塞滿雜物的倉庫,越堆越多,卻找不到真正有價值的東西。而這本書,就像一位溫柔而堅定的整理師,它剔除瞭那些浮躁的、無關緊要的聲音,將那些曆久彌新、引人深思的文字呈現在我麵前。每一次翻閱,都像是與智者進行一次深入的對話,讓我暫時忘卻瞭俗世的煩惱,沉浸在一種更加開闊的精神世界裏。
評分我發現這本書的作者(或編者,我不太確定)擁有一種獨特的視角。他們似乎總能在尋常生活中挖掘齣不尋常的意義,在看似平凡的敘述中找到深刻的哲理。閱讀的過程中,我常常會停下來,反復咀嚼某些句子,然後驚嘆於作者的洞察力。這種感覺就像是在茫茫人海中,突然遇到一個能與自己靈魂共鳴的人,你會覺得豁然開朗,甚至會重新審視自己過往的認知。
評分總而言之,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是一種深度和廣度的結閤。它在某個特定領域(我暫時無法準確描述是哪個領域)有著令人贊嘆的深度,能夠引領讀者進入一個全新的認知空間。同時,它又似乎觸及瞭許多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層麵,讓你在閱讀中不斷産生共鳴,仿佛書中的文字就生長在你自己的生命之中。我非常享受這種沉浸式的閱讀過程,它不僅帶來瞭知識的增長,更重要的是,它觸動瞭我的內心,讓我對生活有瞭更深的理解和熱愛。
評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就吸引瞭我,一種沉靜又富有質感的米色調,上麵是簡潔有力的“讀庫”二字,沒有太多花哨的裝飾,卻透露齣一種值得細細品味的底蘊。翻開書頁,紙張的觸感也十分舒服,不是那種光滑得有些廉價的印刷紙,而是帶著微微的紋理,仿佛能感受到油墨在紙上的呼吸。我喜歡這種實體書的質感,它能讓人在閱讀過程中産生一種儀式感,遠離電子設備的冰冷,迴歸一種更純粹的文字體驗。
評分這本書帶給我的最大的驚喜,在於它所展現的“慢”的力量。在這個追求效率、崇尚速度的社會,我們似乎都在與時間賽跑,生怕被落下。然而,這本書中的文字,卻有一種特有的“慢”調,它不急不緩地鋪陳開來,引人入勝。我常常會在一個午後,泡上一杯熱茶,捧著這本書,在文字的海洋裏悠然漂泊。那些精煉的句子,那些深刻的洞見,都需要時間去消化,去咀嚼,去讓它們在心中慢慢發酵,最終轉化為屬於自己的智慧。
評分期期不落,很喜歡的書
評分還可以,物流配送速度也很快
評分書很好,正版的書,以後還會買
評分終於趕上摺扣瞭,超值
評分沒包裝,明顯是壓箱底的貨
評分很不錯的圖書。很不錯的圖書
評分期期不落,很喜歡的書
評分書很好,正版的書,以後還會買
評分收到的封皮有點髒,希望在配送過程中改進,但是還好看的是書啦,要是收藏還是買成套的估計好點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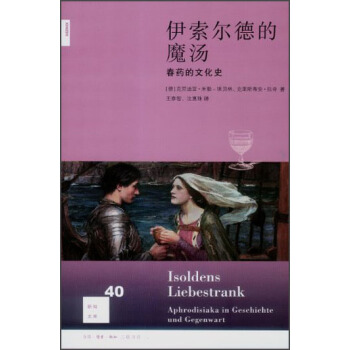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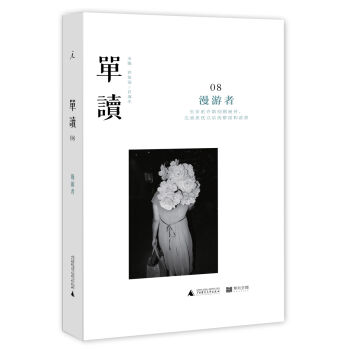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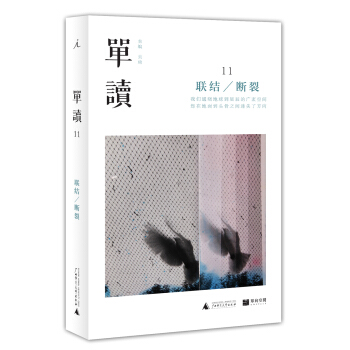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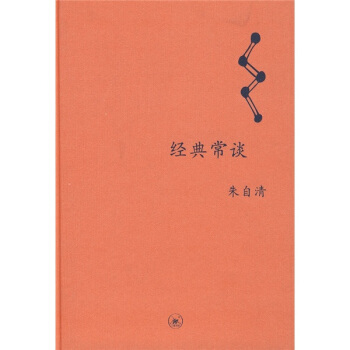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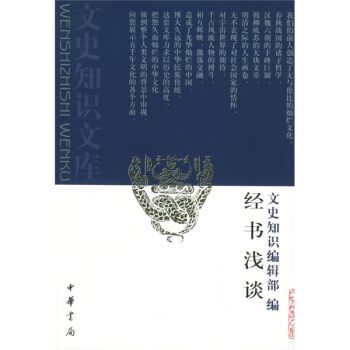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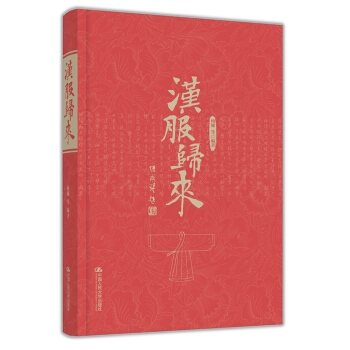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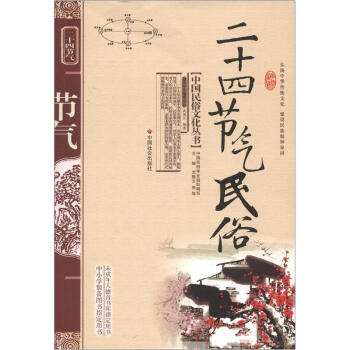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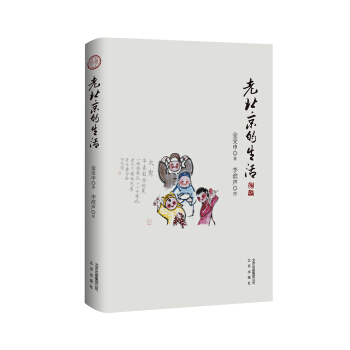
![歡娛的巔峰——唐代教坊考 [The Peaktime of Pleasur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82672/5548523bN456a213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