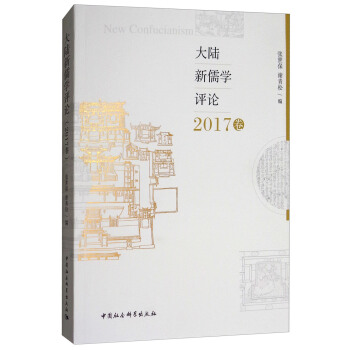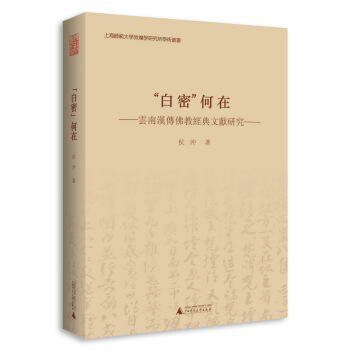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大理密教(即所谓阿吒力教)是云南佛教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对于大理密教此前有不同的释读,本书汇集了作者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期刊上发表的十四篇学术论文,在回顾大理密教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根据对大理佛教经典、图像、金石和传世资料的综合研究,在跨地域研究视野下,对大理佛教史料的种类、属性及其所反映的汉地佛教因素进行了全新的、全面的探讨。
作者简介
侯冲,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佛教,长于汉传佛教仪式及其经典文献研究。主要著作有《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云南与巴蜀佛教研究论稿》《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研究》《汉传佛教、宗教仪式与经典文献之研究——侯冲自选集》等,整理发表大理国写经《护国司南抄》、佛教仪式文本《楞严解冤释结道场仪》和《受生宝卷》、敦煌遗书《坛法仪则》(《金刚峻经》)等十余种。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目录
序言 方廣錩(1)如何理解大理地區的阿吒力教(代引言)(1)
學術史
雲南阿吒力教研究學術史
——以民國時期研究文章中心(3)
經卷文獻研究
滇雲法寶:大理鳳儀北湯天經卷(101)
大理國寫經研究(111)
從鳳儀北湯天大理寫經看旋風裝的形制(197)
“滇藏”考(211)
“白密”何在
——以大理鳳儀北湯天“秘教經儀”中心(236)
誰的密教
——以雲南《天宫科》和甘肅《天功科》的比較例(271)
圖像、金石和傳世文本
論阿嵯耶觀音出現的時間和原因(297)
論大理密教屬於漢傳密教(314)
唐宋至元的雲南華嚴禪(332)
元代滇僧圓護與普瑞(350)
楊黼家世及生平新證(371)
後記(385)
前言/序言
方广锠本书是侯冲继《云南与巴蜀佛教研究论稿》之后的第二本论文集,论述重点依然是云南地区的汉传佛教。其实,侯冲已经出版的两本专著《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与《云南阿咤力教经典研究》,论述的重点也是云南地区汉传佛教。但比较之下,可以看出侯冲的研究从云南地区汉传佛教的表现形态、所依经典,逐渐走向综合性研究,在研究中把云南地区与其他地区大体相同的佛教形态放在中国佛教发展史的大背景下进行整体的考察,并尝试进行理论的阐述。这说明,二十多年来,侯冲研究视野越来越广,在这块土地上的耕耘也越来越深。
本书的主要内容、所收诸论文的内在联系及学术创新之处,侯冲本人在本书后记中已经交代,毋庸我再置喙。我想谈谈由此延伸出来的若干感想。
学术研究靠学术资料,这一点,凡是搞学术研究的,人人都懂;但什么是本学科的学术资料,这一点,就未必人人都明白。学术资料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一点,凡是搞学术研究的,人人都懂;但如陷入盲目性,研究所用的资料有时反而会框限自己的视野,这一点,就未必人人都有清醒的认识。
就佛教研究而言,很多研究者至今把收集资料的眼光局限在传统大藏经中。无疑,传统大藏经至今依然是我们研究佛教最基础的资料。但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传统大藏经所收的典籍实际是被当年编纂大藏经的人们过滤以后留存的,还有大量的数据被他们排除在传统大藏经之外。所以,不把那些藏外的数据一并纳入视野,我们的佛教研究就是不完整的。当年陈寅恪先生评论敦煌遗书被发现的意义,称: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陈寅恪在上面提出“新材料”“新问题”“新潮流”,在他看来,利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便可以形成学术的“新潮流”。所以,虽然从“老材料”中也可以发现“新问题”,利用“新材料”也可以论证“老问题”提供新依据,但确如陈寅恪所说,“新材料”本身,必然会促使我们考虑许多“新问题”。所以,不管最终是否能够形成“新潮流”,新材料都能促进学术的发展。正因如此,百年来以敦煌遗书基础,出现了所谓“敦煌学”。
在敦煌遗书中,各类佛经及与佛教有关的文献约占总数的90%左右,其中不少都属于当年被编藏僧人过滤掉的东西。百年来,人们利用敦煌遗书在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但遗憾的是,至今止,这些成果大部分出现在国外。我国佛教研究界利用敦煌遗书虽然也取得不少成果,但与国外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不少研究者似乎依然习惯于用老资料来研究老问题。自然,研究中有些老资料得到新的解释,有些老问题有了新的开拓,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但也有不少论著,看来似乎花样百出,认真细读了无新意。这种现象未免令人惋惜。
百年来出现的佛教新数据,已经非常多。除了敦煌遗书、金石数据、方志数据、日本古写经之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大批至今依然在民间流传,并还在实际发挥著作用的法事文本。这些法事文本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它们至今影响着广大信众的宗教生活、思想信仰、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它们所反映的佛教形态曾经是宋元明清中国佛教的主流之一,属于信仰层面的佛教,但这些典籍基本被排除在作义理层面佛教的典籍总汇——传统大藏经之外,因而长期没有被纳入佛教研究者的视野,使佛教研究者对宋元明清以下中国佛教的认识产生偏差。可以这样说:不把握这批数据,无以了解唐五代佛教如何演变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佛教,也无以把握当今佛教在民间的实际地位及当今中国的宗教生态。在此,我们还应该注意这样一个现象:近代以来,佛教在文化层面的振兴与在学术层面的成果,往往遮蔽乃至转移了研究者对信仰层面佛教的关注。实际上,从古到今,信仰层面佛教与义理层面佛教始终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无论偏废哪一面,都难以使我们全面、正确地把握、评价佛教。
佛教向来被称“难治”。以前所谓的佛教难治,主要还是指一般读者认佛经难读、难懂。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怎样读佛经》,刊登在2001年第2期《世界宗教文化》上。我以,只要解决那篇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佛经其实不难读、不难懂。但对佛教研究者来说,《怎样读佛经》中提到的问题自然都不是问题,佛教“难治”的主要原因还在资料。亦即需要重视与发掘新数据,需要鉴别与重新审视老数据。只有这样,才能开拓佛教研究的新局面。这个问题很大,在此难以全面论述,仅是点题。
这些年来,侯冲通过各种渠道,从全国各地收集的各类民间法事文本已经有一千多种。他的研究,不仅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在传统佛教文献的基础上,更建立在这一千多种法事文本的基础上。当然,这一千多种法事文本,他目前已经研究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仅这一小部分,已经使他取得与众不同的创新性成果。这再次说明掌握学术资料,特别是掌握学术新资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收集到资料以后,用什么样的观念、视角、方法去考察、整理这些资料,发掘其中的内涵,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举例而言,正因有从全国各地收集到的这一千多种法事文本,使侯冲在处理云南地区的佛教形态时可以游刃有余。亦即他可以从整个中国佛教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云南地区的这些佛教形态,并与其他地区大体相同的佛教形态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更好地解释云南这些佛教形态的性质与把握它们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他的这条研究路径进一步证明了学术研究需要有大局观。没有中国佛教历史发展这一大局观,难以真正处理好云南汉传佛教这一局部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主张云南“阿吒力教”“白密”“滇密”的观点,其底藴或被云南“阿吒力教”法事文本所框限;或因未能建立起中国佛教发展的大局观,以致未能全面、正确地认识“阿吒力教”法事文本的真正性质;或两者均有。
所以,大局观的建立,固然应该归结研究者本人的思想方法,但在科研实践中,它又往往转化研究者占有数据的多少,以及研究者处理这些数据时的观念、视角、方法等问题。可以说,研究者的大局观是随着他所占有数据的增加与研究而逐渐建立起来,而研究者大局观的完善程度与他的资料占有量与研究程度成正比。由此,学术研究本身就变成资料的收集、分析、消化与观点的提炼、扩展、升华这两项科研活动的不断转换与轮回。在这一方面,我想侯冲二十多年研究的经历,本身就可以成一个典型的个案。如果侯冲能够抽时间把自己的科研历程总结出来,对年轻学者的成长一定会有所启迪。
本书所收诸多论文,当然并非篇篇珠玑,论及的诸多问题,当然并非均定论。正因是拓荒,缺点与不足便在所难免。在学术史上,一个新观点提出以后,学术界翕然而从,这种现象也是有的,但很少见。更多见的是新观点受到质疑,受到批评。但只要新观点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它会在质疑与批评中不断完善,成长起来,经过时间的检验,最终被学术界认同,成大家的共识。这种被质疑、被批评的过程,实际也是新观点成长的过程。或者说,在这一过程中,新观点本身就成学术的新的增长点。当然,如果大方向是错误的,这种所谓的“新观点”不可能经得起学术界的质疑与批评,不可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最终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本书提出的有些问题,目前在相关的研究者中仍存在不同的看法乃至较大的争议。我以,这是好事,符合上述新观点产生以后的学术发展的规律。有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才能得到发展与提高。我期待今后这一讨论能够更加深入地进行。
认识侯冲已有近三十年。看到他一步一步成长,在新开拓的学术领域中辛勤耕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他高兴,并预祝他今后取得更大的成绩。
2015年7月17日于古运河北端
用户评价
阅读过程中,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作者在史料运用上的广度和精准度。这本书所引用的原始文献数量之庞大,以及对这些文献的细致比对和考证,简直令人咋舌。作者似乎拥有一种将散落的碎片重新拼凑成宏大图景的能力。引文的规范性和注释的详尽程度,都体现了极高的学术规范性。每当读到一个关键论点时,我都能清晰地追溯到其在原始文献中的出处,这极大地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对于希望深入进行二次研究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的这些详实的一手资料和考证线索,无疑是一座宝库。它不仅提供了结论,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如何通过扎实的基础工作去构建一个可靠的学术大厦。
评分《白密何在:云南汉传佛教经典文献研究》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封面那种深邃的藏青色调,配上烫金的标题字体,显得既庄重又不失典雅,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其学术的厚重感。纸张的选择也十分考究,内页的米黄色调对长时间阅读非常友好,减少了视觉疲劳。装帧的工艺可见用心,书脊的装订非常牢固,即便是频繁翻阅,也无需担心松散。整体来说,这本书的外观品质完全符合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应有的水准,让人在捧读之前就对接下来的阅读内容充满了期待,也体会到了出版方对学术成果的尊重。这种对细节的打磨,无疑是提升阅读体验的重要一环,使得这本书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工艺品。
评分在内容深度上,这本书无疑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坚实的理论基础。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那些边缘化或被忽视的文献资料时所展现出的敏锐洞察力。许多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定论,在作者的细致考证下,开始显露出新的可能性和更丰富的内涵。这种对既有学术范式的挑战和拓展,正是优秀研究成果的价值体现。我感觉作者并非满足于文献的表面解读,而是深入挖掘了其背后的文化土壤和地域特性,使得原本看似冰冷的文献资料重新获得了鲜活的历史生命力。这种深度挖掘和创新解读,无疑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中国佛教地方化进程的认知,让我看到了云南这片土地上独特的信仰实践是如何被文献所记录和塑造的。
评分这本书的行文逻辑和结构布局,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研究态度。初读便能察觉到,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史料,而是构建了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引导读者层层深入地理解云南汉传佛教文献的复杂性。尤其是在梳理不同历史时期文献的演变脉络时,那种抽丝剥茧般的论述方式,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对史料的驾驭能力。每一章节的过渡都显得自然而然,逻辑链条紧密相连,没有丝毫的跳跃或含糊不清之处。对于一个非专业研究者而言,虽然某些专业术语需要多花心思去理解,但作者在关键概念的阐释上总是给予了充分的铺垫,使得整体阅读体验流畅且富有启发性。这种结构上的精妙设计,无疑是这本书能够吸引并留住读者的关键所在。
评分总的来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既挑战智力又收获颇丰的。它要求读者投入专注和耐心,因为它绝非一本可以走马观花的读物。然而,一旦你沉下心来,跟随作者的思绪一同跋涉在这片文献的海洋中,你会发现那些晦涩的章节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你会开始理解那些看似孤立的文献是如何交织成云南汉传佛教复杂而迷人的历史图景的。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把钥匙,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去探究特定地域信仰体系的形成奥秘。对于任何对中国宗教史、文献学,或者云南地方文化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提供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高水准的参考点,值得反复研读和细细品味其深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汉传因明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etuvidya in Chinese Language-Are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75423/591eeedeNa76973b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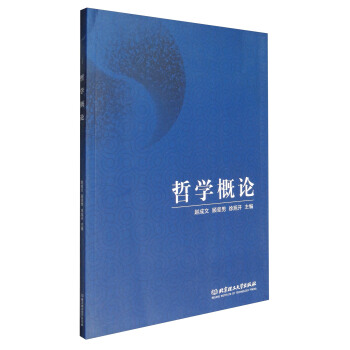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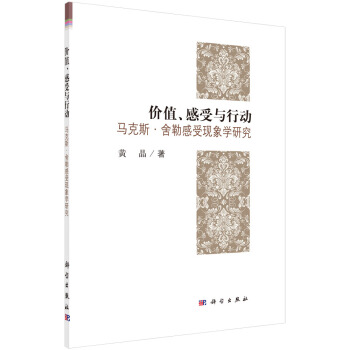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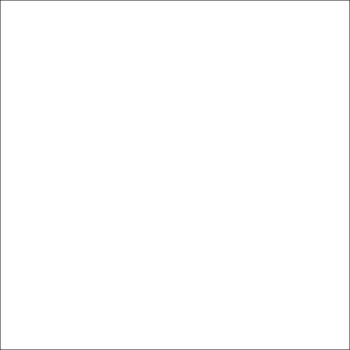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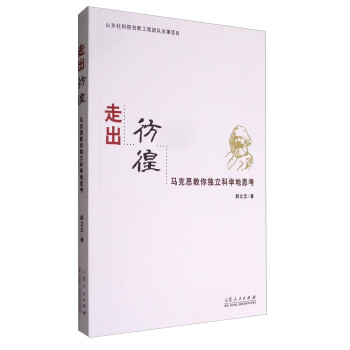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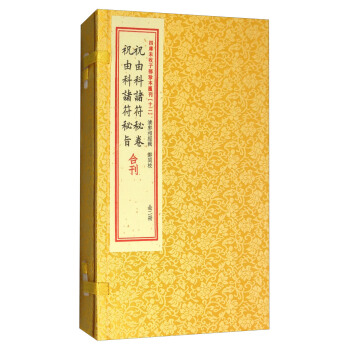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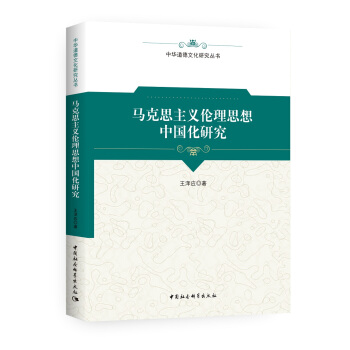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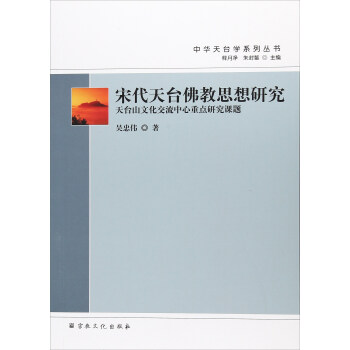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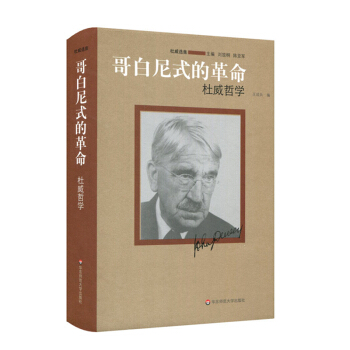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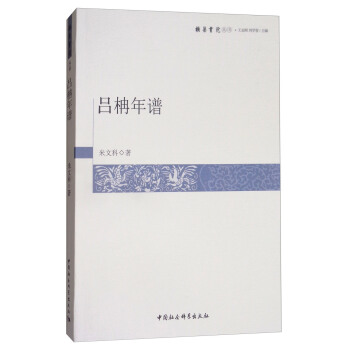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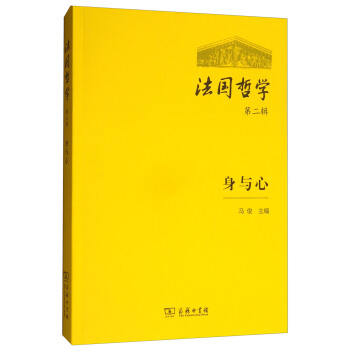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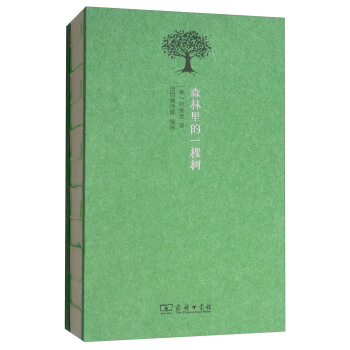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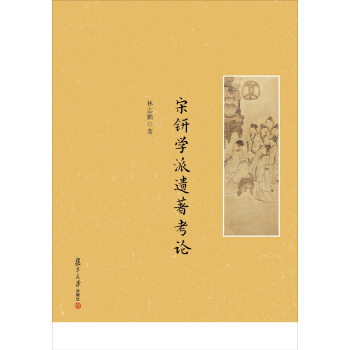
![人的哲学与现代性批判:波兰新马克思主义文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A Philosophy of Man and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Writings of Polish Neo-marxism]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28860/5ac9cc81N19fcfe5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