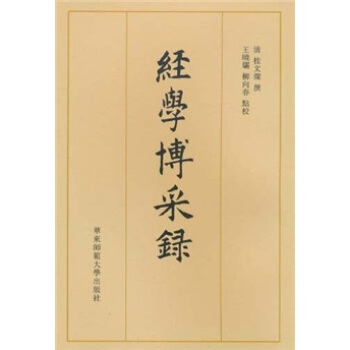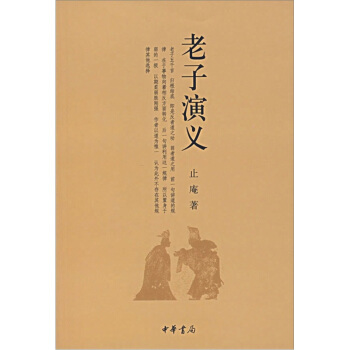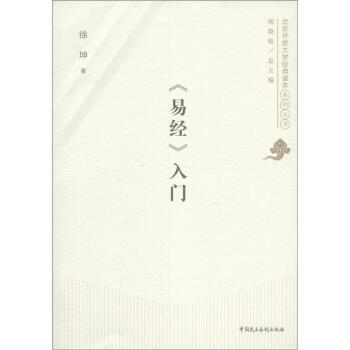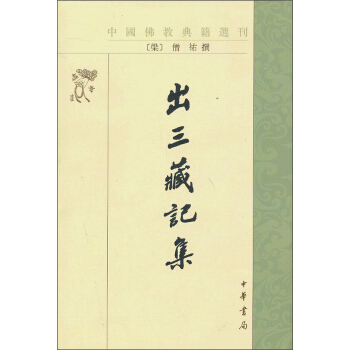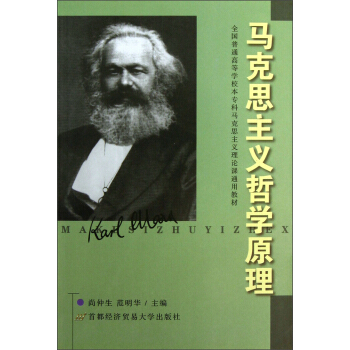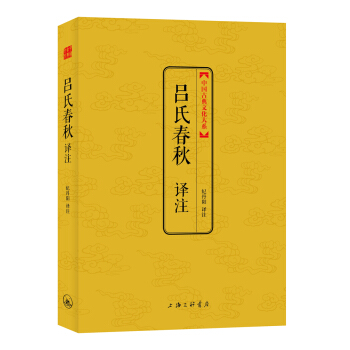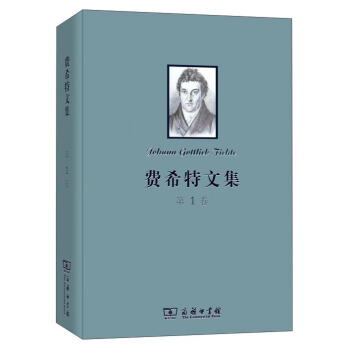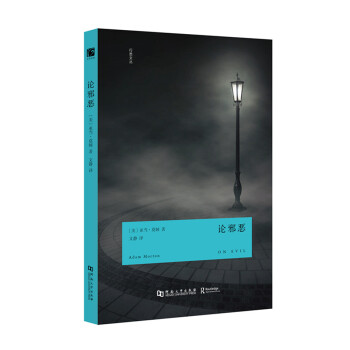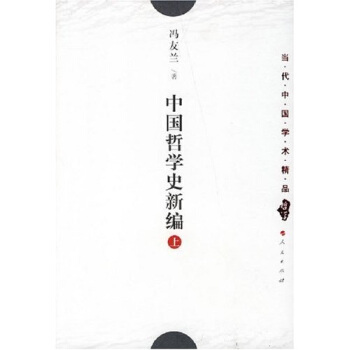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哲学史有各种的写法。有的专讲狭义的哲学,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身世及其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性格。“各有千秋”,不必尽求一致。我生在旧邦新命之际,体会到一个哲学家的政治社会环境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影响。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在《中国哲学史新编》里边,除了说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讲了一些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样作可能失于芜杂。但如果做得比较好,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以哲学史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有所阐述的历史。如果真是那样,那倒是我求之不得的。无论什
内容简介
在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它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种企图,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就困难多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期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专靠读几本书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说掌握和应用了。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专家”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
到了70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
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些知识, 也可以说是在生活、工作、斗争中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在一个考试中间,一个学生可以照抄另外一个学生的卷子。从表面上看,两本卷子完全一样。可是稍有经验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一本卷子是自己写的,哪一本是抄别人的。
现在,我重理旧业,还想实现我原来的计划。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我还自以为有点理解,有点体会。值此旧邦新命之际,我应该把我的一点理解和体会写出来,以加入新长征的行列,跟上新长征的进程。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这也算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吧。
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当然也有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据我自己所见到的,不是依傍,更不是抄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我的业务水平还不高、理论水平更低。我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可能是很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如果要做一点事,他只能在他现有的水平上做起。
作者简介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一九一二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一九一五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一九一九年赴美留学,一九二四年获歌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一九四六年赴美任客座教授。一九四七年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一九五二年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简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肯定了传统儒学的价值。四十年代写《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以程朱理学结合新实在论,构建其“新理学”体系。一九四九年后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等 。目录
自序全书绪论
第一册
绪论
第一章 商、周奴隶兴盛与衰微——商代和西周时期(公元前16世纪至前8世纪)宗教天道观的变化和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转变——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第三章 齐、晋两国的改革及齐桓、晋文的霸业
第四章 前期儒家思想的形成——孔丘对于古代精神生活的反思
第五章 邓析与子产的斗争,名家的起源
第六章 春秋末期军事思想和经济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第七章 墨翟和前期墨家的哲学思想
第八章 晋法家思想的发展
第九章 道家的发生与发展和前期道家
第二册
绪论
第十章 秦国进一步的改革——商鞅变法
第十一章 道家哲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第十二章 孟轲——儒家思想向唯心发展
第十三章 墨家的支与流裔宋钘、尹文;农民的思想家许行
第十四章 庄周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道家哲学向唯心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
第十五章 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后期名家的发展
第十六章 慎到和稷下黄老之学
第十七章 稷下黄老之学的精气说——道家向唯物主义的发展
第十八章 楚国的改革与屈原,稷下精气说的传播
第十九章 墨辩——后期墨家向唯物主义的发展
第二十章 阴阳五行家的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世界图式
第二十一章 易传的具有辩证法因素的世界图式
第二十二章 荀况——儒家思想向唯物主义的发展
第二十三章 战国时期最后的理论家韩非的哲学思想
第二十四章 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终结
精彩书摘
君的变动不就是国的灭亡,国与君也不是一体,国应高于君,这一点也为当时进步的人所认识。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君,晏婴不肯从齐君死。他说:“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为己亡,非其私�颍�谁敢任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是说,一个国的君与臣都是为国家办事的,一国的公事应该与君的私事分开。只有君的私人,才为他办私事。这种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当时社会思想的一个进步。天上的上帝和神灵本来是人间的统治者的反映。奴隶主统治者的威权既已削弱和没落,上帝和神灵的威权也必然随之降低。在春秋时期,神权政治的观念有进一步的动摇。
统治阶级中的人也看出来,要维持他们的“国家”,“民”比神还重要。随国的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虢国的史嚣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庄公三十二年)宋国的司马子鱼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僖公十九年)“民”是“神之主”,主是宾主之主,就是说,神还倚赖于人。神“依人而行”,而不是人依神而行。这些材料表明,民和人被提到首要的地位,而鬼神降到了次要的地位,鬼神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意志,一切要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实质上是一种无神论的观点。这是当时关于宗教的思想的一个大转变。
在孔丘以前的鲁国的展禽(柳下惠)给祭祀一个新的解释。他认为,祭祀的对象都是有利于民的自然界的东西,或者是有功于民的历史人物。前者如“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后者包括“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的历史人物(《国语·鲁语上》)。祭祀这些对象,为的是“崇德报功”。古时的宗教迷信认为鬼神能赏善罚恶,支配人的命运,祭祀的目的在于祈求鬼神保佑自己。照展禽的解释,祭祀的迷信成分就很少了。
由于宗教迷信的动摇,人们也逐渐了解到,人的吉凶祸福是人自己的事,与“天”没有关系。公元前645年,宋国有陨石,又有“六鸛退飞”。这些不常见的现象,当时迷信的人认为与人事的吉凶有关。他们认为自然界的非常变化是由人事的好坏引起的,同时这些非常的变化又意味着人将要得到幸福或灾难。这是一种“天人感应”的思想。周内史叔兴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这是说,自然界的非常现象,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是由自然界的阴阳之气的失调造成的,与人事的好坏没有关系,人事的祸福是人自己造成的。这是一种无神论的观点。鲁国的闵子马也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左传》又记载说,宋国和薛国关于营建周城的问题引起了争论。宋国引证鬼神以辩护自己的观点;薛国引证人事以辩护自己的观点。弥牟评论说:“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定公元年)他认为依赖鬼神是十分错误的。
郑国的占星术者裨灶,因天象而预言郑国将要大火。郑国的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左传》昭公十八年)这里所谓裨灶的“预言”的根据是依据星辰的出没而推测人事祸福的占星术。子产对这种占星术表示怀疑。从子产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宗教的天道观开始动摇和没落。吉凶祸福在于人事的好坏,不在于鬼神的赏罚,也与自然界的某些非常现象无关。这也表明当时人的思想从宗教中得到一定的解放。
……
用户评价
这部著作的篇幅之宏大,内容之详实,着实令人惊叹。作者在梳理中国哲学流派的发展脉络时,展现出了极高的学术功底和驾驭复杂史料的能力。我尤其欣赏它对于早期思想家,如先秦诸子百家的论述,不是简单地罗列观点,而是深入挖掘了他们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关怀,使得那些古老的思想如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阅读过程中,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那个思想激荡的年代,亲耳聆听智者们的辩驳与思辨。那些关于“道”、“仁”、“礼”等核心范畴的阐释,逻辑清晰,层层递进,极大地拓宽了我对中国传统智慧的理解深度。它并非那种枯燥的教科书式叙述,而是充满了对历史的关怀和对哲理的深邃洞察,读起来酣畅淋漓,令人受益匪浅。对于任何想要系统了解中国哲学源流的读者来说,这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宝典,其严谨的考据和精妙的分析,足以让老饕也感到满足。
评分这部作品在学术规范和前沿视野的结合上做得非常出色。一方面,它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扎实可靠,引用的注释详尽而精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献学基础。另一方面,作者并未固步自封于传统史学的框架,而是勇于引入近现代哲学思潮的视角,对传统哲学进行再诠释和再定位。尤其是在涉及对“现代性危机”的探讨时,作者能够清晰地指出传统智慧如何能为当代人提供超越性的思考资源,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感令人耳目一新。它不是简单地复述旧闻,而是带着现代人的问题意识,去激活古老的思想遗产。这使得全书的论述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不失与当下的强劲连接力,读起来有一种“古为今用”的振奋感,仿佛是作者在用一种全新的语言,重新向世界介绍中国思想的博大精深。
评分坦白说,我起初对阅读厚重的哲学史有些畏惧,担心会陷入无休止的术语辨析和文本引证之中。然而,这本书的魅力恰恰在于它对“人”的关注。作者似乎总能从那些高悬的理论背后,捕捉到提出这些思想的先贤们的“人味儿”——他们的困惑、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无奈。例如,对某一时期士大夫群体如何在政治高压下保持精神独立性的描摹,非常细腻动人。这种将思想史与人物命运紧密结合的写法,赋予了哲学探讨以温度和厚度。它不是冰冷的知识灌输,而是一次对历史灵魂的深切探访。读罢此书,我不仅明白了“他们说了什么”,更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这么说”,这种对思想动机的挖掘,远比单纯的知识记忆来得深刻和持久,真正做到了“观其妙,而知其所以妙”。
评分我对这部书的结构安排印象极为深刻,它没有采用绝对线性的时间轴推进,而是巧妙地在不同思想阶段之间设置了富有洞察力的“回响”与“张力”。这种处理方式,使得中国哲学的演变不再是孤立事件的堆砌,而是一场绵延不绝的对话。可以看到,后世的思潮如何回应前代的挑战,又如何为未来的发展埋下伏笔。特别是在处理佛道思想与儒家思想的互动时,作者的处理显得尤为老辣和平衡,既肯定了外来思想的冲击力,也揭示了本土哲学的强大韧性和融合能力。这种多维度的审视,使得对“中国哲学”这个整体概念的理解不再是单一面向的,而是充满了动态的辩证张力。每次阅读到不同章节的衔接处,我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历史河流的转向和暗流涌动,这对于构建一个立体、丰满的哲学史图景至关重要。
评分这本书的行文风格非常新颖,它不像传统史著那样板着面孔,而是采用了非常现代的叙事手法来解构古老的思想体系。作者似乎非常擅长将那些抽象的概念具象化,让那些晦涩难懂的命题变得触手可及。比如,在讨论宋明理学中“理”与“气”的关系时,他引入了大量的类比和生活化的场景,使得原本需要反复研读才能领悟的道理,在初读时便能抓住其精髓。这种“化繁为简”的叙事技巧,极大地降低了阅读的门槛,对于初学者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同时,它也保持了足够的学术锐度,并未因为追求流畅性而牺牲内容的准确性。每次合上书本,我都能感觉到自己的思维被一种清晰、有力的逻辑链条所牵引,这种阅读体验是极其愉悦和充实的。它成功地架起了一座沟通古今思想的桥梁,让人在轻松的阅读中,完成了对宏大哲思的探索。
评分这部上册和中册送来时封面上有黑色的指印,非常可惜!
评分喜欢冯友兰的著作!购买收藏!
评分纸张很好,,,还没看。
评分也是最好的哲学史。经典之作。值得阅读
评分物流快,包装好书是正品,推荐的好书
评分冯友兰的哲学史新编,绝对经典,物美价廉。
评分第六十四章 农民大起义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
评分很有用的书,绝对正版!
评分第六十七章 戊戌维新运动的激进理论家和哲学家——谭嗣同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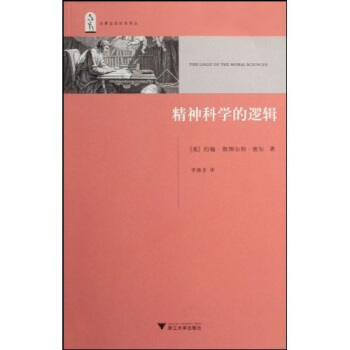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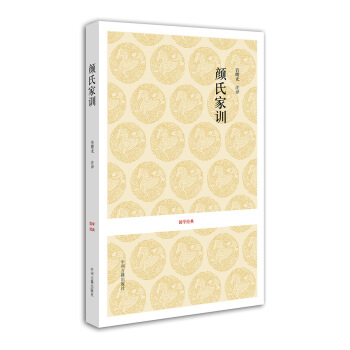
![《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 [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500293/4d17155a-c66d-43cc-85b7-1cd93bb7804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