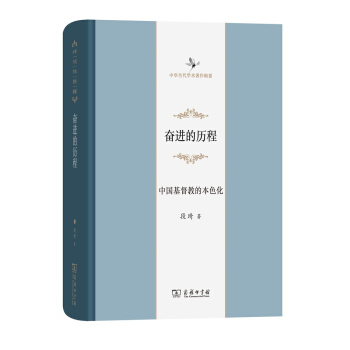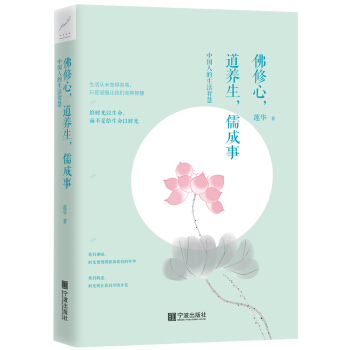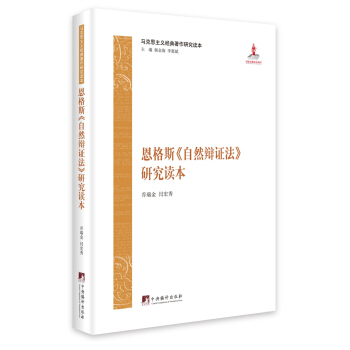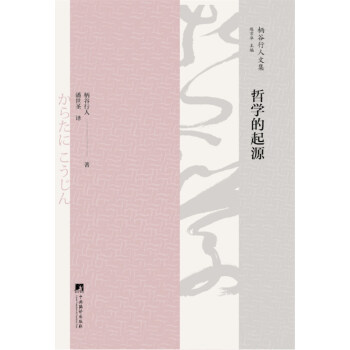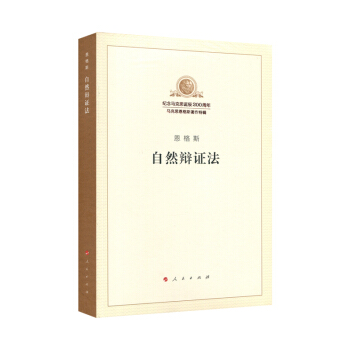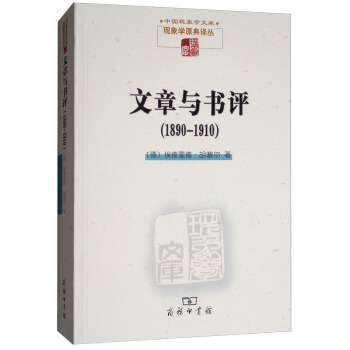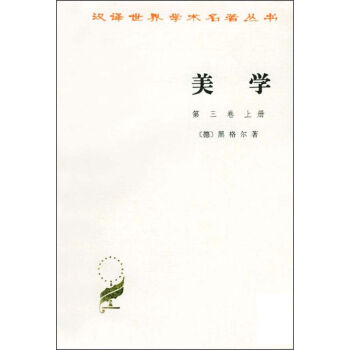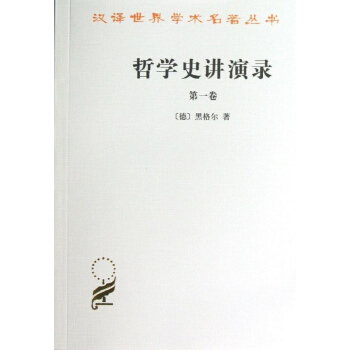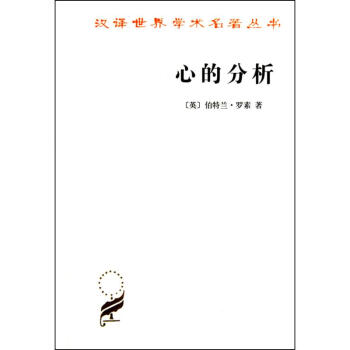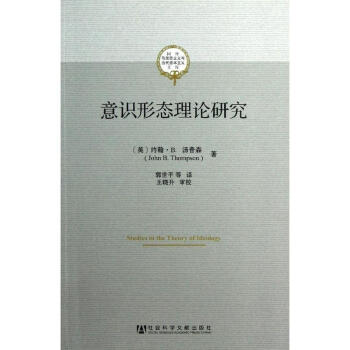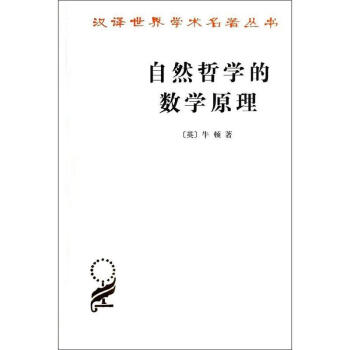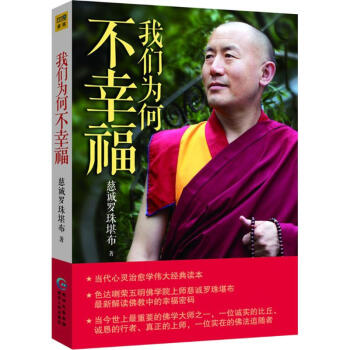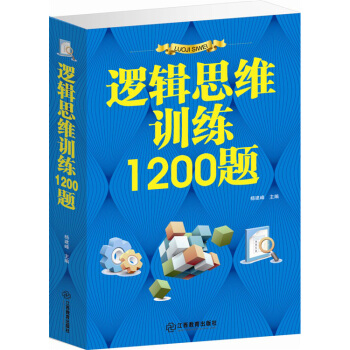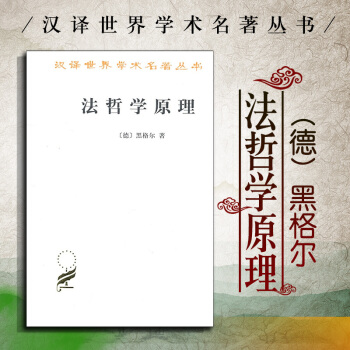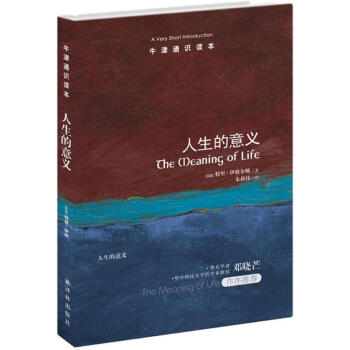![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哲学概念系统引校 [Das Philosophische Begriffeslexikon zur Kntik der reinen Vernunft]](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09531/5a129c08N24154cc5.jpg)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哲学概念系统引校》聚焦于第1批判,对其中的哲学概念、术语进行辑录、比类、翻译和集校。注重从德文原著出发,致力于把一手的康德、原汁原味的康德交给读者,为研究康德者提供一本相对完备的专业辞书,简洁明了地呈现出先验哲学的精髓。《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哲学概念系统引校》紧扣文献,凸显康德的写作特点,还原语境,钩沉互证,在概念使用中理解概念,挖掘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章节、不同段落中的特殊规定,并且,抓住概念的相关性,着眼于概念与命题之间、概念与问题本身之间、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联分析和脉络清洗,沉入到实实在在的概念使用氛围中,通过交代概念出现的具体语境而向读者呈现概念本身的界定。删繁就简,去除芜杂,遴选重点,而不求而面俱到。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哲学概念系统引校》以词条分疏归类,所有概念按照出现顺序逐一排列,清晰有序,方便征引。读者只要打开书,先验哲学体系的许多概念就可以信手拈来,迅速查对,可以帮助人们阅读康德经典文本,进而在义理上消化和吸收批判哲学。
作者简介
余治平,祖籍江苏洪泽,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湖南科技学院、河北衡水学院特聘教授。河jE省董仲舒研究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中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中华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理事,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特约研究员。《中西哲学论衡》(年刊)主编,上海市江苏淮安商会副秘书长。已出版《唯天为大》、《哲学的锁钥》、《中国的气质》、《忠恕而仁》、《哲学慧眼识究竟》、《董子春秋义法辞考论》、《春秋公羊夷夏论》、《万集乡下这些年》、《做人起步<弟子规>》等专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康德哲学概念谱糸”(Das Begriffe slexikon der Kant Philosophie)主持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忠恕而仁”负责人。香港中文大学(CLTHK)、德国柏林一勃兰登堡科学院(BBAW)、柏林自由大学(FUB)访问学者。内页插图
目录
精彩书摘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哲学概念系统引校》:46.理性的思辨在先验运用中最后所导致的终极意图,涉及到三个对象: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此在。(KrV,A798;B826)
47.意志可以是自由的,但这只与我们意愿的理知原因相关。(KrV,A798;B826)
48.一切通过自由才是可能的东西,都是实践的。(KrV,A800;B828)
49.而且在此首先说明,我目前只在实践的理解中使用自由概念,并且这里则完结了先验意义上的自由概念,这种先验意义上的自由概念不能被经验地预设为现象的解释根据,而本身对于理性却是一个问题,就如上面所标的那样。(KrV,A801;B829)
50.但那种,不依赖于感性冲动、因而只能够被理性所介绍的动因所规定的任意,就叫作自由的任意(arb1,numhbe — rum, 自由的任意)。(KrV,A802;B830)
51.实践的自由能够被经验所证明。(KrV,A802;B830)因此理性也给出了规律,它们是命令、即客观的自由规律,它们说明,什么应该发生,即使它同样也许决不会发生,并且它们在这点上与只处理那些发生了的东西的自然律相区别,因此也被称为实践律。(KrV,A802;B830)
52.所以我们通过经验而认识到,实践的自由作为自然原因之一,即在意志的规定中的理性的原因性,然而先验的自由却要求这个理性本身(鉴于它的开始了一个现象序列的原因性)独立于感官世界的一切规定的原因,并且只要先验的自由看起来是与自然律、因而与一切可能的经验,显得是相违背的,所以就仍还是一个问题。(KrV,A803;B831)
53.后者抽掉了爱好和满足这些爱好盼自然手段,而只一般地考察一个理性存在者的自由,以及那个:在其之下自由唯有按照原则而与幸福的分配相协调的——必要条件,所以至少能够以纯粹理性的单纯理念为基础并被先天地认识。
……
前言/序言
康德哲学是西方现代哲学发展过程中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一大里程碑。在欧美世界,自康德第一批判诞生以来,研究康德哲学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大约在20世纪初,康德哲学被零零碎碎、断断续续地介绍到中国以后,几乎在不同时代都能涌现出一批专门的研究论作。仅关于三大批判,每年所产生的最新研究成果就相当可观。纵览一百多年的学习和研究历史,康德哲学似乎颇受中国学人的青睐,好之者不绝,所论所作的内容广泛涉及哲学、伦理学、美学、文学、政治学、历史学、自然科学等领域。单在康德著作的翻译方面,自1933年胡仁源首译《纯粹理性批判》(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张铭鼎译出《实践理性批判》(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唐钺翻译《道德形而上学探本》(上海:商务印书馆)之后,1957年蓝公武又译出《纯粹理性批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这四个译本,筚路蓝缕,功劳卓著,完成了康德哲学中文翻译的开创性工作,但由于其文白相间的限制,而难以完全融入现代中国的学术话语系统。北京商务印书馆于1964年出版了分别由宗白华、韦卓民翻译的《判断力批判》的上、下册。1968年牟宗三在台湾翻译出《认识心之批判》(上、下册),(台北:学生书局)。
1980年代以来的主要翻译成果,先后有庞景仁发表了多年精心翻译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韩水法译出了《实践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台北的学生书局出版发行了牟宗三所译的《纯粹理性批判》。1991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了韦卓民所译的《纯粹理性批判》。1997年何兆武编译了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武汉大学邓晓芒与杨祖陶两位教授通力协作,伏案七年,译出“三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李秋零教授历时十年终于翻译出整套普鲁士科学院版的《康德著作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些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全新译本,现实地构成了康德哲学的中文语境,不仅突破了“让汉语说哲学”的瓶颈,有效激活了汉语的哲学张力,同时,也为当代学人进一步解读康德哲学创造了良好的文本条件。
但是,中国人要真正读懂康德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主要是因为:康德之难,首先难在概念术语上。1790年9月2日,康德在写给约翰·亨利希·兰贝特教授的一封信中说:“形而上学的关键,却仅仅在于纯粹理性的概念和基本原理。”康德本人无疑是一位制造概念的哲学高手,批判时期的经典著作里,不仅常会出奇制胜、波谲云诡地冒出一些崭新而生硬的名词、术语,而且许多概念的使用也显得非常独特,一些概念自身甚至还会不断嬗变,前后的含义经常不相一致。同一个概念在康德那里如果自身歧义就比较大,到后人的理解中则更加混乱不堪了,这就为澄清概念之所是增加了一定的困难。
康德很少对一个概念做清楚、明确的一次性交代和全面而完整的阐释,许多概念必须通过具体使用和前后语境才能够凸显出其内在规定与基本含义。因此,哪怕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都会牵扯进许多章节里的文字,其关联幅度甚至可以从著作的一开始到最后结束。只有把这些文字和盘托出,读者才能够对这个概念大致有数。
仅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里,几乎每一页都会冒出新的概念。康德哲学的大厦几乎完全建立在自己独特的概念体系的基础之上。许多一直被先前哲学家所使用过的概念,到了康德这里却发生微妙、甚至重大的意义转变。因为语言的障碍和翻译的困难,许多前辈学者大多只能够在自己当下的写作语境中理解与使用康德的概念,而难以针对康德原著的文本本身。这样,势必又很容易导致康德的概念本义与后人的理解之间的紧张和矛盾。
而概念的含混不清,在客观上又必然导致义理的分歧,于是,康德哲学的许多内容及其价值、意义经常处于一种模糊不堪、似是而非的状态。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在解读康德的黑暗中徘徊,而找不着北,因为没有方便的捷径。
不把康德文本——尤其是第一批判——中的基本概念的基本含义弄清楚,就不可能进入先验哲学体系。1920年代末以来,德语的、法语的、俄语的、英语的、日语的类似于《康德词典》或《康德手册》的辞书早已相继问世。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汉语世界里,尽管每年都有大量研究康德哲学的论作面世,但至今却还没有一本针对康德德文原著自身、专门整理、汇校和辑录康德哲学概念的研究辞书或专业工具书,这无论如何都适应不了中国康德学的发展需要。
用户评价
从一个“学习者”的角度来看,我更看重这种辅助材料提供的“校正”功能。在阅读各种二手研究资料时,常常会发现对康德某些核心概念的阐释存在着微妙的偏差或过于现代化的解读,这对于初学者来说极具误导性。因此,我期望这本以“引校”(Lexicon/Glossary)命名的书籍,能够提供一种高度忠实于文本的权威性解释。它应该是一个锚点,一个让我们随时可以返回去核对和确认的“标准参照系”。这意味着,它不仅要解释“是什么”,更要谨慎地说明康德在特定的语境中是如何使用这个词的,避免用后世的哲学概念去简单套用。如果这本书能够提供严谨的引文出处,甚至标明该概念在原著中首次出现或得到关键阐释的页码,那无疑会大大增强其作为研究辅助工具的可靠性,让读者在面对复杂的论证时,能够拥有足够的信心去坚持康德原著的语境。
评分更深层次的期待在于它对概念之间内在联系的揭示。康德的哲学体系之所以宏大,正在于其概念之间精密的相互依存关系,比如“知性”、“感性”、“判断力”是如何层层递进,最终构建起整个知识论大厦的。我非常好奇这本书是如何处理这种“系统性”的。仅仅列出名词的定义是不够的,真正的困难在于阐释这些名词在康德的论证结构中扮演的角色——它们是如何被“推导”出来,又是如何相互支撑的。如果这本书能清晰地勾勒出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路径和张力所在,那么它就超越了一般的词典范畴,真正成为了一个“系统引校”。我希望它能帮我理解,当康德谈论“三大先验理念”时,这些理念在整个批判的布局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起到了何种关键性的功能。这种对结构深度的挖掘,才是哲学辅助读物的核心价值所在。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读起来就有一种厚重感,光是“康德”和“纯粹理性批判”这两个词汇,就足以让人望而生畏了。我一直想深入了解康德这位哲学巨匠的思想精髓,但面对原著那种艰涩的语言和复杂的逻辑结构,总是难以真正入门。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座桥梁,帮助我跨越理解上的鸿沟。它似乎不仅仅是简单的术语解释,更像是一份导览图,旨在梳理康德思想的脉络和核心概念。想象一下,如果能清晰地掌握“先验”、“范畴”、“物自体”这些关键概念的精确含义,那么阅读原著时,那些曾经晦涩难懂的段落或许就能豁然开朗。我期待它能以一种系统化、结构化的方式呈现知识,而不是零散的碎片信息。如果它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它对于任何想要认真对待康德哲学的读者来说,都将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书,甚至可以被视为是通往康德思想殿堂的一张详细地图,能有效避免在浩瀚的哲学迷宫中迷失方向。
评分最后,我希望这本书的呈现方式能够体现出对读者学习进度的体贴。哲学学习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一次性完全掌握所有内容。好的工具书应该能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对于刚接触《纯粹理性批判》的读者,它提供清晰的基础释义;对于已经有一定基础,希望进行深入研究的读者,它则应该提供更细致的辨析,也许是不同版本间的差异处理,或是与莱布尼茨等前辈哲学的对比。一个优秀的“概念系统”不应是僵硬的,而应该像一个智能向导,能够根据读者的提问深度,提供相应层级的反馈。这种弹性和适应性,使得这本书能够伴随读者从最初的阅读障碍,直至最终的学术探索,成为一本能经受住时间考验、不断被翻阅和引用的常备工具。
评分拿到手的时候,我首先关注的是它的装帧和排版。哲学著作的阅读体验往往与书籍本身的物理形态息息相关,毕竟我们要与这些沉思了几百年的智慧进行一场持久的对话。我希望看到的是一种清晰、克制的设计美学,既要体现出主题的严肃性,又不能牺牲阅读的舒适度。那种需要反复翻阅和对照的工具书,如果字体过小或者索引设计不合理,会极大地消耗读者的耐心。我设想中的“概念系统引校”应当具备极高的可操作性——当你被一个陌生的哲学名词卡住时,能迅速定位到准确的解释,并且这个解释本身是经过精心提炼和整合的,而不是简单地复制粘贴原著的定义。这种工具书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否在不喧宾夺主的前提下,高效地支撑起读者的独立思考过程,让阅读《纯粹理性批判》成为一种流畅而非痛苦的体验。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往往决定了一本工具书的生命力。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